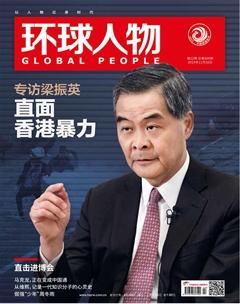“想让年轻人明白我70岁才懂的道理”
杨学义

2019年11月,梁晓声在北京接受本刊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就我的眼光看,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正从当代人的生活之中逸去。有人看到了这一点,于是掉头而去,想要到别处寻找。我看到了这一点,于是将脸更凑近生活,看一看同时还消失了些什么,又嬗变出了些什么,滋生出了些什么。”在一封给作家同行周梅森的信中,梁晓声谈着他对“写平凡的能力”的理解,“这也许是时代对我们这一批人的新的苛刻的要求。”
几十年来,梁晓声正是这种平凡的书写者。2019年,他的《人世间》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这部115万字的长篇小说依然延续着这种书写。和书写传奇相比,书写平凡挑战更大——不光耗费心血,还可能在市场上受冷遇。同梁晓声对话伊始,《环球人物》记者想知道他
书写平凡的勇气来自何方,但随着对话的深入,才明白他向来如此,这是本心而非“勇气”。

2019年10月14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北京举办,图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右),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左)为梁晓声颁奖。
翻开各种版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梁晓声往往会出现在有关“知青文学”的章节中。可实际上,这位与共和国同龄的当代作家和他的身边人,以及他笔下众多虚构与非虚构的人物,涵盖范围已远超“知识青年”这个群体。在梁晓声的客厅里,他让记者坐到沙发上,自己
却拿了一个小马扎迎面而坐,解释说由于常年坚持手写,颈椎和腰部都有严重的职业病,只能坐硬板凳。落座后,这个看似再平凡不过的老头缓缓点了一支烟,说起了他与他所经历的时代。
那一口袋榆钱儿
《人世间》以周氏一家为主角,刻画了与之相关的十几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他们都生活在北方某省会城市的一个平民区。其中,周家父亲周志刚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在国家困难时期到四川支援三线建设。
用小说人物对标现实人物,是不严谨的。但梁晓声的父亲确实也是“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在梁晓声上小学一年级时,跟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将妻子和五个孩子留在哈尔滨。直到1978年退休,梁晓声的父亲在将近20年的岁月中,绝大多数的时间没有和家人生活在一起。
梁晓声回忆过很多父亲在参与大三线建设期间的往事。在梁晓声很幼小时,父亲的工友到家里看望母亲,说:“梁师傅太仔细了,舍不得买食堂的菜吃,自己买点儿酱买几块豆腐乳下饭,两分钱一块豆腐乳,他往往就能吃三天!”省下来的大部分钱都给了家里,“父亲的工资当年只有六十四元,他每月寄回家四十元,自己花用十余元,每月再攒十余元。如果不攒,他探家时就得借路费了,而且也不能多少带些钱回到家里了。”即便如此,父親也只得隔两三年才能回家一次。
梁晓声的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到一个铁路工厂去做翻砂临时工。翻砂是将融化的金属浇灌到铸型空腔的重体力活儿,即便男人干,都很危险。梁晓声记得,母亲每天回家时,他和兄弟姐妹都已睡下。为了省电,晚上9点半,母亲还会坐在床角,借着极其微弱的灯光为孩子们补缀衣裤。多年后,梁晓声将67岁的母亲接到北京住,发现她已患严重眼疾,医生责备他:“你是她什么人?为什么到这种地步才来看?”梁晓声竟无言以对。
像这样新中国第一代工人的往事,梁晓声在文章中记述了不计其数。梁晓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那时对整个国家来说,和贫穷始终处在一种胶着状态,有时候甩也甩不掉,按倒葫芦起了瓢。”这是新中国在积贫积弱的历史基础上发展的必经阶段。所以,梁晓声将
那一代人的贡献理解成一种宿命。“在这种宿命的过程中,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能承受范围内的坚忍,还有一种是在坚忍之外,将自己奉献的能量发挥到最大。”

梁晓声和父亲的合影。
父母正是在那样的宿命中,教会了他美与善。有一次,梁晓声非要跟随母亲到厂里,为的是爬上厂里的榆树撸榆钱儿吃。他在母亲的协助下偷偷进去,终于撸满了一口袋,从工厂墙洞爬出,满载而归。回家的路上,遇到一群孩子,央求他:“给点儿吧!”“不给,告诉我们在哪儿的树上撸的也行!”梁晓声见势不妙,想跑回家,终于被孩子们追上,榆钱儿被一抢而空。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梁晓声在母亲下班后委屈地哭诉,母亲却对他说:“怨你。你该分给他们些啊,你撸了一口袋呀!都是孩子,都挨饿……往后记住,再碰到这种事儿,惹人家动手抢之前,先就主动给,主动分。别人对你满意,你自己也不吃亏。”
“那个时期的中国人,有一种‘有一分热,发十分光的精神,我想这种精神不只是在焦裕禄这种党员干部身上,而是在很普通的农民、工人、科技知识分子,甚至相当多的父亲、母亲身上全部体现了。”梁晓声说。
“文学对我意味着改变命运”
1968年,高中毕业的梁晓声赶上了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启知青生涯。那时的他,只是中国千千万万平民子弟的一员,让他真正脱颖而出的,是文学。
此前,文学带给梁晓声的,是一种虚荣感。在小学五、六年级,梁晓声读了第一部国内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和第一部国外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阅读范围超出别的小学生,那么作文的内容就更多一点,受到表扬”。年幼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到了中学,身边的男女同学大多开始喜欢读长篇小说了,梁晓声也进入了读小说最多的阶段,被大量小说熏陶。
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后,梁晓声与文学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他频繁参加连队文字任务。团里的宣传股也知道了,梁晓声有了进一步的施展空间,他越来越多地在《兵团战士报》上崭露头角。不久,他参加了全兵团第二届文学创作培训班,真正向文学迈出了第一步。次年,第三届培训班上依然有他的身影。
参加培训班期间,兵团最多给学员两个月的脱产创作假期。特殊时期,他们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写稿的热情和认真程度超出了今天人们的想象。梁晓声经常创作到深夜,写了撕,撕了写,寒冷的冬季,写一阵,哈一阵手。那时,拥有共同爱好的人相聚在一起的时光,是非常宝贵的。当他将作品拿给同学们看时,所有人都会停下手头创作,为他“会诊”,并且提出的意见都极为认真。
文字水平的精进,让梁晓声调入一团宣传股当报道员,他的主要精力都投入到小说、散文和诗歌上。但仅过了一年,他就被“精简”了。在《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故事的主人公“我”因连里不批假,擅自回城市探望生病的母亲,被连里领导扣上帽子,副指导员李晓燕替“我”向领导辩护。这一情节的原型就是梁晓声在现实中被“精简”的过程,梁晓声是“李晓燕”,团里一名木材加工厂的鹤岗知青是“我”——鹤岗知青在回到连队之前,处分已经确定了,开除团籍。梁晓声以团政治部工作组成员的身份参加了会议。会议上,鹤岗知青痛哭流涕反复承认错误,当主要领导表决通过处分决定后,其他工作组成员保持沉默,梁晓声却按捺不住情绪,开始“慷慨激昂”起来。“我当时说了些什么,连我自己如今也记不清了。但有一点却记得很清楚,连长没坐多一会儿,就一言未发,面色青白地怫然而去。”在梁晓声的争取下,鹤岗知青最终保留了团籍,得到了警告处分。不久,团里就“精简机构”了。团部只有两名知青被“精简”,梁晓声就是其中之一。
出于一种较劲的心态,梁晓声主动申请到干活最累的木材加工厂。那时的他身体瘦弱,又生了肝病,工厂连长问他想干什么活,梁晓声反问“什么活儿最重?”工厂连长回答“抬大木”。“那我就抬大木!”梁晓声就这样成为一名苦力。
好在,在培训班期间抓全团文学创作的崔干事得知了他的情况,千里迢迢来找他。看到梁晓声身体被累垮,严肃地对他说,一定要挺过这段时期,“我将把你调离一团!”梁晓声坚决反对崔干事和领导交涉,但崔干事坚持认为,培训班的知青必须要有几个成为作家,“我对你不只有友情,还有责任!”半个月后,梁晓声就被借调到黑龙江出版社,为期一年。
文学让梁晓声在知青岁月中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那个时期,文学对我意味着改变命运。”梁晓声说,1974年,复旦大学来到黑龙江招生,招生老师看了兵团总部编写的集子后,对他写的小说《向导》印象深刻。当时,梁晓声经过一系列辗转,又回到了团里继续抬大木。招生老师下决心见一见梁晓声。“他先从佳木斯乘车12小时到哈尔滨,再从哈尔滨坐车到黑河,而铁路到中途的北安就没有了,所以要下车,再坐8个小时的公共汽车,最后到我所在的团,路上就有三天时间。”经过一个半小时交谈后,招生老师决定招收他,还特意向团里领导打招呼:如果复旦大学决定招收该名知青,那么名额不可以被替换。
在梁晓声的作品中,散发光芒的人物往往牺牲了小我,成就了大我,也成就了时代。梁晓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这是一个美学范畴,更多时候,还是一种本能。在特殊年代,他出于本能,坚持了人性;而他身边的“贵人”们,出于本能,帮助他抓住了文学这个唯一的希望。1974年9月,梁晓声从北大荒来到上海滩,进入复旦大学。

梁晓声作品:《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人世间》。

電视剧《今夜有暴风雪》剧照。
60岁之后,猛醒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创作《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并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开始,梁晓声蜚声文坛。随后的《今夜有暴风雪》《雪城》,以及据此改编的电视剧,更是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作品。在那个文学热情高涨的年代,梁晓声绽放出耀眼光芒。
梁晓声开始寻求一种自我证明。“我得奖了,但我还要继续证明,还能得奖。”梁晓声后来发现,自我证明对相当一部分作家来说,是最长的一个过程,甚至有人最终也没有完成。
相较而言,梁晓声是幸运的,很早就完成了自我证明。2002年,他到北京语言大学任中文系教授,迎来了又一次转变。“到了大学做老师,开始给学生讲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这时候就真的应该去想这个问题了,这时你才会猛醒!”这种“猛醒”在他60岁之后尤其强烈,“我都当了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了;都评上二级教授了,而一级教授又很少;60岁以后该退休了,但学校说你不必退休。所以,你还要证明什么?得到什么?”梁晓声对这个问题进行深思,最终明白了:“回想我做的文学这件事,它的意义在中国究竟是什么。”带着这个他长时间没有认真思考过的命题,他开始再一次回归文学,并认为应该为了这个意义写一些东西了。
梁晓声对《环球人物》记者说,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的不同点在于,西方文化由文学艺术和宗教组成,对于西方来说,宗教是文化的长子。“这意味着什么呢?全人类都是通过文化来影响世道人心,而宗教做起来有深入人心的地方,因为它历史悠久,有固定的组织,更有力度。但是中国所说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更多集中在文人阶层,在民间缺乏广泛性。即便对民间影响最大的儒家文化,老百姓又对孔子及其弟子,以及后世的朱熹、王阳明这些人,了解多少?”梁晓声意识到,“这个国家经历那么多历史的沧桑和变动,社会的进化说到底就是人性的进化。尤其是商业时代怎样对待财富,怎么对待和他人的关系,等等,这些都要通过文化来给予诠释。”
在中国,文学是文化的长子。梁晓声将文学比喻为文化的“二传手”,是在替文化分担一些重量。“我从小生活在城市,更了解城市底层百姓的生活。我有一个心愿:写一部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有年代感的作品。我一直感到准备不足。到了六十七八岁,我觉得可以动笔,也必须动笔了。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对他们将来的人生有所帮助。”这是《人世间》中,梁晓声写在附赠书签上的一段话,恰能让人理解他为影响青年、影响世道人心做出的努力。
“70岁的人,看到一部票房很高的电影,但文化含量、认识价值有限,那这个电影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梁晓声说,年轻人写出销量很高的书,拍出票房很高的电影,是值得另眼相看的,但这依然是年轻人在自我证明,甚至是在求慕虚荣。在一个70岁的人看来,“那样也没多大意思了”。
“活到70岁左右时会发现,做文学做了一辈子,你总得有件像样的手艺活儿放在那里。”梁晓声说,《人世间》就是他做的像样的手艺活儿,对得起文化,对得起文学。因此,“我想让年轻人明白我70岁才懂的这些道理”。
立足当下的人,应该得到更多敬意
《环球人物》:《人世间》被誉为“50年中国百姓生活史”,您最想向读者传递什么?
梁晓声:把50年历史讲全面,是不可能的。表面上是客观,实际上你是选择了角度。文学同样如此,所以我只选择了我观察的一些事,尽量选择以点带面的素材。
我们经常习惯横向比较,中国和美国、欧洲相比,比来比去,总觉得我们的遗憾太多。但作为一个理性的人,也应该学会纵向比较。所以我想向读者传递,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们的国家变化了没有?哪些方面变化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没有?是只有一部分人提高了,还是绝大部分人不同程度上得到了国家发展的益处?这不光是经济上的,还有思想方法上的,人作为个体,毕竟是有观念的。
还有就是阶层,不同社会阶层在这50年来要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一个国家的进步,不能仅仅以满足民间诉求为标准,还要兼顾到数量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物质诉求和精神自由度的诉求,表面上看起来像两条各自运行的车道,但总有一天会交叉起来,变成绝大多数人想要的。《人世间》就是通过叙述,缓慢地表现这些道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环球人物》:您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怎样看待新中国70年的成长,以及成长中的曲折艰辛?
梁晓声:写《人世间》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大小,都曾犯过同样的错误。后人能做的,就是包容这些历史,当然包容的前提是反思。因此我非常尊重研究历史的人,他们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给出公平的评价,做了难能可贵的事。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做的不是这样的事,而是全身心地致力于当下。当下需要建设什么就建设什么,当下需要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站在当下看明天。
这两种人之间,我以前可能是对前者敬意更大,现在突然悟到了,我可能对后者敬意更大。我们的一切成果都不能仅仅通过回顾历史、反思历史自然而然地生成,无论你反思得多么深刻,都是要靠后者,就是那些当代人,来做具体的事。
《环球人物》:在您的作品中,经常有一些人物在特定时代中牺牲了生命、爱情、机会,您怎样看待时代与人性的冲突?
梁晓声:全世界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种冲突之中,一个幸福的人,大抵也只是这种冲突在身上体现得平和了一些。事实上,一个人是有分层的,除了有自我,还有他我,自我与他我是伴随一个人终生的。文明也包含着人如何看待自己身上这种自我和他我的关系。人往往觉得自己越长大,摆平这种矛盾的能力越高明,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发现,这种冲突会越来越强烈。你会发现,整个社会在他我方面对你要求更多了。
有些东西,是时代怎样发展都无法解決的。你爱一个人,她不爱你,你再怎么爱,都是活该,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不要把问题完全归结于时代的过错,大多数情况下时代并没有将刀放在你的颈上、把枪顶在你的胸膛,还是你自己选择的,只是你舍不得付出代价。当然,这种冲突随着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发展有所改善,比如现在两个人恋爱,不存在阶级成分的问题了。除了人性的自我觉醒,还有时代和社会本身对自我的尊重,比如我们现在评价任何工作、任何政策,都用了人性化三个字,这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梁晓声
当代著名作家。原名梁绍生,1949年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代表作品有《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等。2019年8月,凭借长篇小说《人世间》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