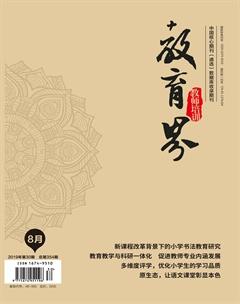桐边时光:我的家及其世情的敞开与澄明
陆嘉明
(续前)
10
要说喜鹊的成人之美,最可称道者当数“鹊桥相会”也即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
这一神话传说千古流传,可谓家喻户晓、婦孺皆知,堪为爱情经典。天上织女私自下凡,与人间牛郎缔结姻缘,终被王母娘娘用金簪划出一道天河,从此夫妻二人分隔于波涛汹涌的银河两岸。幸得情动喜鹊仙,每到七月初七,千万只喜鹊飞来搭成横跨天河的鹊桥,牛郎织女便可于鹊桥相会了。
天宇茫茫,银河滔滔,一夕相见,可慰一年相思之苦。秦观有《鹊桥仙》一词道尽个中情味——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一段情,刹那即成永恒。
一夕相逢,胜却情话无数。
天上。地上。人间。纵然天河相隔,怎能隔断双星相照,心心相印?纵然有愁有悲伤,怎能截断有情有爱水长流?纵然一年一夕鹊桥相会,又怎能胜过凡情俗意的朝朝暮暮?
凄美的爱情绝唱,固而弥坚,阻而不断,成就了天地间绝美的风景。星空无涯,天长地久,年年岁岁的七月初七,演绎成一个人间节日:七夕节,中国的情人节。柔美的小夜曲缓缓响起,在优雅轻快的旋律中,仰起头来,遥望星海,黑色的眼睛,寻寻觅觅,寻觅黑夜的光明。呵,两颗星,今夜最亮也最动人心弦的两颗星:牛郎星,织女星。还在银河的两岸吗?是此岸还是彼岸?刹那间,两岸连成一体了,此岸即彼岸,彼岸即此岸。真真梦梦真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原来落在两个情人心上的,是梦;落在两个情人牵手上的,是真。
天上的星星交映为一道道璀璨的光晕了,地上的两情相悦叠印为一声声缠绵的情话了……
于是,鹊桥,一个美丽的传奇故事,既浪漫又现实,化为我们民族的一个爱情符号、一个圣洁的符号、一个堪与日月星辰同辉的文化符号啊。
11
无怪乎我们中国人如此钟情喜鹊了。它是瑞鸟、报喜鸟、吉祥鸟。宋·赵琥有《题喜鹊栖树》一诗云:
梳翎刷羽立高柯,不落人间小风罗。
一点通灵良不谬,檐头报我喜还多。
然而也有人说,喜鹊报喜不报忧,而乌鸦既报忧也报喜,它才是忠鸟、吉鸟。三国时,孙权见赤鸟集于殿前,大喜,视之为大吉兆,遂改年号为赤乌。果然,吴在三国中立基最固,吴王在三帝中寿数也最长。其实,报喜报忧云云,皆不足为凭,只不过都是人的文化心理或地域习俗所致。
历来确有称乌鸦是吉鸟祥禽的。比如唐·元稹作诗道:“巫言此鸟至,财产曰丰宜。”白居易为之应和说得更透彻:“此鸟所止家,家产日夜丰。上以致寿者,下可宜田家。”简直比财神和寿星还要灵验了。怪不得有名士薛季宣者作《信鸟赋》云:“南人喜鹊而恶乌,北人喜乌而恶鹊。”
据说英国的伟大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最“喜鸦”了,他养了一只乌鸦,取名格里普。格里普会学说人话,时不时大喊:“哈喽,老姑娘”,或者“我是个魔鬼”!狄更斯对其宠爱有加,竟以其为原型,写进了小说《巴纳比·拉奇》中,那只乌鸦,简直神了。
然而,我不管你白居易、狄更斯,不管人信什么,我还是“喜鹊”派,只要听它叫,就激起我童稚的回想。至于其喜报应验与否,倒也未必当真,任其逗我玩就是了。
民间文化到底是以“喜鹊”为瑞鸟为主,在各类传统艺术中,诸如剪纸、年画、刺绣、木雕、砖刻、面塑、糖艺……工笔写意也常见喜鹊或翔或栖的潇洒身姿。赫赫如徐悲鸿不仅爱画马,也爱画喜鹊。香港著名作家董桥喜收藏古物和书画,他在《徐悲鸿画喜鹊》一文中写道:
我向来偏爱小品,尺幅越小越惬意,老朋友黄伟明割爱匀给我的这幅《喜上眉梢》也别致,只有三十八乘二十一厘米,题“辛巳中秋悲鸿写”,钤“徐”姓朱文圆印。喜鹊神采动人,带点西画规矩的气韵,虬枝铁干干净利落,随兴点了几点水红梅影倒是国画至深的意境了:西画根基坚固,国画攀越传统樊篱是应分的。(《故事》)
又说:
《徐悲鸿年谱》的插图有一幅一九三二年徐悲鸿画给舒新城的梅花喜鹊,题识说“喜上眉梢,俗题也,但写与雅人新城吾兄为莼羹饷我,以此为报。壬申中秋悲鸿”。老派的人过年过节都爱图个吉利,一九三二年中秋舒先生那幅画于上海,一九四一年中秋我这幅画于新加坡,我沾得了一点俗气一点喜气之余,庶几给我走过的南洋青葱岁月留个念想。(《故事》)
是的,如“喜上眉梢”这样的俗题俗画,也许称不上大雅,然大俗的极致,恰是大雅。徐悲鸿藉此题此画写与“雅人”朋友,以报“纯羹”之饷,俗耶?雅耶?
董桥硬是让朋友“割爱”“匀”到徐氏同题小品,果然觉得在“沾得了一点俗气一点喜气之余”,激起了“走过南洋青葱岁月”的悠悠“念想”,俗耶?雅耶?
大俗的极致,不也是大雅吗?
我时见新婚人家,门上多贴大红剪纸的“囍”字,窗花也有各式剪纸图案,“喜上眉梢”当为传统题材,贴在明晃晃的玻璃窗上。梅间鸣鹊,跃然枝头,昂首报喜,此时无声胜有声,果然喜气盈盈……有邻家过春节也贴上类似题材的窗花,正如董桥所说:“老派的人过年过节都爱图个吉利。”是的,守望这一民俗惯例的,多是“老派”也即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和浸染过的人,其中有雅士,也有凡俗者。尤其在农村乡下,过年喜贴门神年画对联窗花。窗花皆为红色剪纸,红红火火,吉吉利利,“喜上眉梢”一类的窗花一贴,牖外窗内,自然而然地透出一种欢快喜庆的氛围。
我家庭院探不到梅花消息,就那一株古意梧桐春萌嫩叶,夏生绿凉,秋叶飘拂金色的恬静,冬岁枝桠勾勒出雪色的纯美……那天喜鹊倏然飞来,叫声悦耳,所报何“喜”?所报何“吉”?不知道,不说“喜上眉梢”,但可以说是“鹊鸣桐枝”,倒也别有一番境界意思。
悲鸿画鹊赠友,董桥喜得名画,我则树下闻鹊,日常情景中的数声天籁,叩开了少年心扉,俗中见雅的一抹喜色,恐也染上天真未凿的眉梢。今届暮年,蓦然忆起,情思翩跹,不由得也和董桥一样,“沾得了一点俗气一点喜气之余”,庶几给我走过古市幽巷的青葱岁月,留下了几许喜悦几许念想……
12
梧桐树下,曾筑一鸡舍。
在困难年代,母亲养过一只鸡——一只母鸡,一只会生蛋的鸡,一只喜欢照镜子的鸡。
那是一只多么漂亮的鸡啊。白羽如雪,冠头胭染,眼睛圆而亮,双爪粗壮蜡黄……一旦发现蠕动的小虫之类,迅即张翅扑将过去,啄起活物时神气活现的样子,惹人忍俊不禁。
母鸡丰腴如“贵妇”,闲庭信步悠闲自在,喜欢跟人走动,好像与人特别亲近,有时跟来跟去讨吃食,却又毫无“贵妇”的矜持派头了。但静静地孵在鸡舍生蛋时,最不愿有人打扰了。有次我出于好玩,伸手摸了摸正在生蛋的它,它竟然狠狠地啄了我一口,好痛好痛啊。
三天生两蛋,从不脱板。待蛋生出,就咯咯咯地报喜讯。母亲听到随即将蛋取出,并犒劳母鸡一把碎米。有时正忙,未能及时喂食,它竟不依不饶,出窝就是一摊屎,盯着人叫个不停,真拿它没办法。
我們有蛋吃了。蛋有好营养,在困难时期,倒也补养了我们全家人。吃的多为炖蛋。一碗橙黄,鲜嫩水滑,葱花飘绿,香油数滴,袅袅蛋香味飘散出来,煞是吊人胃口。有时积攒了三四只蛋,就可以吃到炒鸡蛋了。不过,母亲总要羼些儿“和头”进去(按:“和头”,吴方言,意即于主料中加入辅料以“和”而成复味),诸如韭菜炒蛋、笋丝炒蛋、雪里蕻炒蛋、茭白炒蛋等,都很好吃。只是太少了,吃不过瘾。全家人动嘴,三筷两筷就一扫而光了。不知是不是“少吃多滋味”的缘故,现在好像再也吃不到那时的味道了。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说过:
记得当时我在乡下时,把新采的茭白切成丝炒鸡蛋,端盘上桌,白是象牙白,黄是柠檬黄,二色相谐,真趣盎然。蛋中茭白,熟中带生,鲜洁中不脱清味,确是“渐近自然”的至美之肴。(《苏州美学映像·茭白:葑水清味》)
现在回想起来,那盘茭白炒蛋,依然齿颊留香,余味犹在。那时的鸡蛋,于我等常人,确是极为奢侈的美味了。
著名作家韩少功曾在《山南水北·养鸡》篇中说:
放在以前,鸡是一般农家的油盐罐子,家里的一点油盐钱,全是从鸡屁股头挤出来的。现在经济有所改善,但鸡还是一般农家的礼品袋子,要送个情或还个礼,大多冲着鸡下手。
何止是油烟钱,瘾君子的香烟钱,也要“从鸡屁股头挤出来的”。这种情景,我也曾在苏州车坊乡下目睹过:
有位作家说:春天最美是黎明。有一天我起了个大早,再想领略一下薄明中的油菜地。当我出门时,只见住在隔壁的全福老人在场上兜圈子,手里紧紧地捏着一只鸡蛋,并不时地探头探脑,眼睛瞟着场边的一只鸡窝。我哑然失笑,想起他的女儿曾向我说起她爹的“鸡屁股烟行”的事。老人是个本分的庄稼人,就爱吸烟。他吸的“大铁桥”香烟,当时一角四分一包。因为穷,手中无钱,照牌头两只鸡蛋换一包烟。那时一家只准养两只鸡,多养了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那天老人烟瘾上来了,偏偏另一只老母鸡“难产”,可把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我因急于观赏油菜花,不及细想,和老人打了个招呼,就向村边的田野走去。 (《苏州美学映像·哦,油菜花》)
当然,在国家经济好转且人民生活提高之后,再也不会如此困窘了。但韩少功说的不错,不仅是“农家”,即便是城里人,“要送个情或还个礼”,有时也会送一两只鸡以表人情。记得多年前,我的一位朋友,是苏州知名医学专家,竟也不避俗情,曾拎了一只活鸡趋访寒舍。斯时所感,不惟在鸡,而更在朋友的诚心,在人情。这种人情交往,恰恰体现了一种亲切而淳朴的传统礼节。
中国向有“礼尚往来”的传统,“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待人以礼,则表示敬意和尊敬的意思。孔子说,为人应“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依民族传统,人“不学礼,无以立”啊。且不往大里说,仅就人的日常交往而言,他送个人情,你领个情,或也还个“礼”,只要情感合拍,且无染功利俗尘,无论是物的形态还是精神的交流,皆能以其定义“礼”的文化真谛,回归“礼”的本源意义。
近年我数度回故乡南通,儿时伙伴热诚款待交流欢洽不说,临别也是送鸡送鸡蛋,还送了不少蔬菜,带到苏州吃了好多天。天天吃,还是吃不厌。蔬菜很新鲜,鸡和鸡蛋特别鲜美,好像又吃到过去的味道了。
清代李渔说过,吾为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哦,我懂了,原来好东西好味道,要“渐近自然”;同理,好的为人之道,也要“渐近自然”,不是吗?因其“自然”,饮食可得“本味”“真味”;因其“自然”,为人之道,则可得“本心”“真心”。
是的,大道至简,大味至简,大美亦至简啊。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