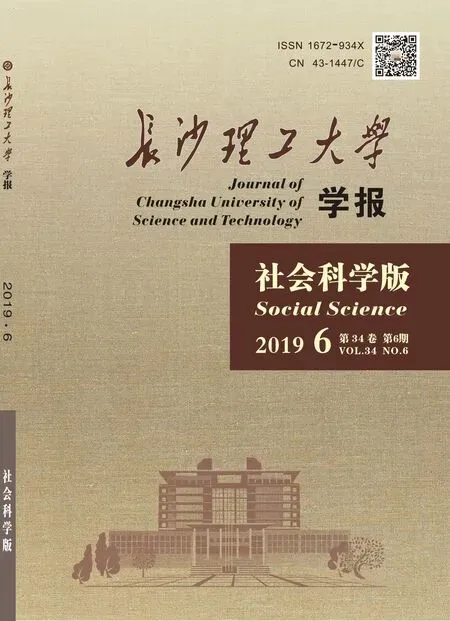《亨利五世》中的民族性建构
邢莉君
(福建江夏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期,人们对某一民族状况(nationhood)有着不同的观念。民族(nation)是指一个文化政治共同体,或者是一个较为稳定的民众社区,它的语言、领土、经济生活、种族或表现,是在共同的文化/传统的心理构成基础上得以形成。厄内斯特·勒南认为,一个国家不是建立在语言、宗教、王国、地理或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的。他在以《什么是民族?》为题的学术演讲中指出,“一个民族是一个灵魂,一个精神原则。两件事,实际上只是一件,构成了这个灵魂或精神原则。一个在过去,一个在现在。一个是丰富的记忆遗产的共同拥有;另一种是现今一致的同意,共同生活的愿望,以及使人们以不可分割的形式获得的遗产价值永久存在的意愿。”“遗忘(forgetfulness),我甚至会说历史错误,是创建一个国家的关键因素。……一个国家是一个大规模的团结,由过去人们作出的牺牲的感觉以及人们准备在未来作出的牺牲所构成。”[1]民族身份/国家归属(nationality)是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法律关系:国家为个人提供国家保护,并拥有对个人的管辖权;同时,个人对国家也具有按照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本尼迪克·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他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指出,“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民族意识的起源与印刷技术、方言(取代拉丁语的地区俗语)和16世纪宗教改革密切相关,“在积极的意义上,促使新的共同体成为可想象的,是生产体系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传播科技(印刷品)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然的,但又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2]民族性(nationness)是个人的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能够分享过去光荣的遗产和遗憾,以及将来实施的共同计划或事实,可以一起受苦、享受和希望,这是长期以来的努力、牺牲和奉献的结晶。一个英勇的过去、伟大的人物、共同的荣耀是一个基于民族观念的社会资本。在过去有共同的荣耀,现在有共同的意志,一起表现出色,希望取得更多的成就——这些是成为一个民族的必要条件。共同的苦难不仅仅是喜悦。在涉及国家记忆的地方,悲伤比胜利更有价值,因为他们担负责任,需要共同的努力。它标志着一个过去,然而,现在通过一个实际的事实,即同意,明确表达继续共同生活的愿望,对它进行了总结。
一、民族性或者“英国性”
不列颠群岛的各民族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统一的、一致的国家认同。1487年,亨利七世建立了都铎王朝,最终结束了英国玫瑰战争。以英格兰为主导的、统一的国家意识、民族认同感(English identity)逐渐增强。1532-1534年期间,亨利八世(Henry VIII,1509-1547)的英国改革极大地重塑了英国的民族性,这不仅仅是脱离罗马天主教的英国国教改革,这场改革运动深入到社会文化更广泛的领域。斯蒂芬·格林的《莎士比亚的民族身份协商》(Stephen Greenblatt,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1988)、约翰·克里冈的《英伦群岛》(John Kerrigan,Archipelagic English,2007),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都铎王朝时期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而戏剧则成为某种政治功能实体的表达,从现代民族意识的凝聚来看,历史剧在根本上即是政治戏剧。

D.J.贝克在《各民族之间》之“想象的不列颠: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Imagining Britain:William Shakespeare's Henry V)中写道:“在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的第一场/幕中,坎特伯雷大主教将英格兰王国与蜂巢作了一个比较。他告诉亨利王,蜜蜂是‘靠了自然规律为人类国家之有秩序的活动而示范的小生物’(1.2.188-189),因此,他总结说,就像这些昆虫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采取‘持续的行动’(1.2.185),‘一千种的工作,一经发动,会达成同一目标,而且可以全部顺利完成,不有挫败。’(1.2.205-206)像许多后来的评论者一样,在这部戏剧中,坎特伯雷坚持认为,英国国家权力具有崇高/高尚的完整性(integrity),诸多矛盾即是[对完整性的]明显违背。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光耀的‘英格兰’的整体性(wholeness),恰恰取决于它对别的威胁性他者的定义,威胁性他者几乎存在着,且未完全消除。”[6]霍利迪的《简明英国史》认为,爱德华一世制止贵族和教会对王权的侵犯,缩小贵族的特权,禁止向教会赠送土地,采取一些措施以赢得全国下层阶级的支持,尤其是提倡东部的伦敦方言(英语),在不列颠首次出现了英吉利民族的概念[7](P25)。基于共同的语言、宗教、传统、法律和道德制约下的行动准则,民族意识的建构首先是一个群体达成一致的观念或行动,聚合各自分散的、随意的成员去实现特定的目的/任务。《亨利五世》在第一场第2幕预备作战之前说道:“现在每个人都要竭尽忠诚,推动这正义的大业向前进行。”[8](P45)而且,在第二场第2幕中,亨利王严厉惩罚了与法国阴谋杀死他、背叛英格兰国王的贵族康桥伯爵理查、斯克庐帕主教亨利、格雷爵士,他们被亨利指责为“英格兰的怪物”(English monsters)、“狡狯的恶魔”“诱人叛变的恶魔”,亨利王还指责这些背叛者“会回到广大无垠的地狱里去对他的属下宣称:我永远不能赢得一个人的灵魂,就像赢得那个英国人的灵魂那般容易”[8](P65)。亨利王宣称将维护国家的安全,制裁国家颠覆者:“你们阴谋对我叛变,串通敌国,接受他们的贿金,受雇置我于死;你们是企图将你们的国王出卖加以杀死,将他的王公贵族出卖为奴,将他的臣民出卖遭受凌辱,将他的国家出卖给破亡毁灭。”[8](P69)莎士比亚却意外地让这3个阴谋叛变者一致认罪,并表达对恶毒的背叛的悔意/后悔,突出了更高的英吉利民族意识。其次,民族意识的建构,按照勒南、安德森、霍布斯鲍姆的观点看来,是人们有意识地对过去历史的选择性记忆和遗忘。《亨利五世》第一场第2幕,坎特伯雷大主教对法国《萨利克法》的解释,以及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1327-1377)和黑王子爱德华对法战争的回忆,可以看作是无意中建构想象的、强大的英吉利民族观念。第四场第7幕,弗鲁哀伦说:“你的名垂不朽的曾祖父,请陛下原谅,还有你的叔祖威尔士的黑王子爱德华,我在历史上读到过,在法兰西这里打过一场顶漂亮的仗。”[8](P185)对英国历史上荣耀的回忆和对未来荣誉的追求都是英吉利民族观念建构的重要方式。伊雷主教说:“唤起对于这些英勇死者的回忆,用你的强壮的胳膊重演他们的伟绩吧。”坎特伯雷大主教说:“英格兰的国王从来不曾有过更富足的贵族,更忠实的臣民,身在英格兰而心早已卧在法兰西战场上的营帐里面了。”[8](P33)亨利王说:“这件大事[对法作战]对于你们会是像对于我一般的光荣,我毫不怀疑这将是一场圆满成功的战争。”[8](P69)
中世纪后期,法兰西与英格兰的竞争性敌对关系,有利于加强英吉利民族意识。爱德华三世较早发起了入侵法国战争,而后,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及其政治盟友坎特伯雷大主教继续对法作战,亨利四世即使在镇压众多叛乱之中也没有放弃对法作战的思想。亨利五世的对法战争暂时缓和了英格兰、威尔士等内部矛盾,并达成临时的一致的国家认同感。《亨利五世》第三场第1幕,亨利王在哈夫勒攻城时喊道:“把每一种力量都尽量的使用出来!前进,前进,你们最高贵的英国人!你们的血是从身经百战的祖先们传下来的;你们的祖先,都像是亚历山大一般,……健壮的庄稼汉,你们的胳膊是英格兰培养出来的,在这里给我们表现一下你们的地道的本领吧。”[8](P87,P89)第五场第2幕,法国国王说:“这互争雄长的英法二国,因嫉妒对方的幸福连海岸都露出了苍白的脸,现在可以停止他们的恨意了。”[8](P231)弗鲁哀伦对英格兰低级军官威廉斯愤怒地吼道:“这简直是全世界,全法兰西,全英格兰,最可恶的一个叛徒。”[8](P191)
二、威尔士、爱尔兰、苏格兰与英吉利民族的认同
与波利多罗·维吉利的《英国史》(Polidoro Virgili,Anglica Historia,1534)、拉斐尔·霍林谢德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历史》(Raphael Holinshed,Chronicles of England,Scotland and Ireland,1577)、爱德华·哈勒的《兰开斯特和约克两大家族的和解》(Edward Hall,The Union of the Two Noble and Illustre Families of Lancastre and Yorke,1543)、威廉·坎登的《不列颠史》(William Camden,Britannia,1586)叙述的不列颠整体历史相近似,《亨利五世》想象性地表达了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苏格兰一致认同的英吉利民族意识。在1623年的第一对开本中,莎士比亚写到了三个分别来自威尔士、爱尔兰、苏格兰的营长(上尉)弗鲁哀伦、马克毛利斯、霍米(the Scots Captaine,Captaine Iamy),但在剧中人物直接标识为Welch、Irish、Scot;来自英格兰的营长(上尉)写作Gower(高渥),这些勇敢而粗鲁的下级军官在剧中往往近似于喜剧形象。
莫尔顿在《人民的英国史》之“威尔士、爱尔兰、苏格兰”中写道:“诺曼底人所征服的疆域,起初仅约以英格兰为限,不列颠群岛的其余部分仍是独立的,组织成无数个小王国和小公国,大部是部落性质。诺曼底人致力于把这些地区荡平和封建化的过程,曾用去几百年的功夫。虽则苏格兰南部已实行封建制,苏格兰却从没有被征服,而在爱尔兰,则到了都铎王朝,诺曼底人才在都柏林周围取得较稳固的立足地。这种征服事业在威尔士最先开始,也在威尔士做得最彻底。”[9]《亨利五世》第五场第2幕,亨利王向卡萨琳公主求婚时说:“拉着我的手说:‘英格兰的哈利,我是属于你了’。我一听到你说出这句话,我就大声的告诉你:‘英格兰属于你,爱尔兰属于你,法兰西属于你,金雀花家族的亨利(Henry Plantagenet)属于你。’”[8](P223)这表明此剧中的英吉利民族观念主要包含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却摒除了敌对的、独立的苏格兰,而且爱尔兰的融入尚待加强。莎士比亚在这个历史剧中的想象性叙述,并不是亨利五世时期的真实历史,而是亨利八世、伊丽莎白以来普遍的英吉利民族观念。
L.菲德勒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陌生人》(Leslie Fiedler,The Stranger in Shakespeare,1972)较早评论莎士比亚作品中的“陌生人”“外邦人”是在各自不同的社会情景下被表现出来的,这些表现方式不仅反映了莎士比亚自己的价值观,也反映了同时期观众的价值观。例如,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等,再现了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共同所处的特殊历史困境,以及他自己的潜意识神话。G.K.汉特的《戏剧中的身份认同与文化传统》(George Kirkpatrick Hunter,Dramatic Identitie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tudies in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1978)集中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陌生人”“外邦人”所代表的政治意义和情景意涵,他们与别的形象共同建构了莎士比亚戏剧的形态。R.赫尔格松的《民族意识的诸多形态》(Richard Helgerson,Forms of nationhood:The Elizabethan Writing of England,1992)认为,16-17世纪编年史(Chorography)、诗歌、戏剧、骑士小说(Chivalric Romance)、地图(cartography)、法律书籍、宫廷游戏、教会的辩论、国际商务和海外探险的叙事等都致力于建构英吉利民族,身份认同和差异性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文化问题。这一时期,英吉利民族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整个社会普遍推进了一致认同的民族意识。安妮娅·鲁姆巴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英格兰与外邦人》(Ania Loomba,Outsiders in Shakespeare’s England)认为,英吉利民族意识(Englishness)是相对于一切非英吉利的事物而言的,“种族的、民族的、宗教和文化差异的形象常常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戏剧中。印第安人和摩尔人、吉普赛人和犹太人、埃塞俄比亚人和摩洛哥人、土耳其人、摩尔人、犹太人、‘野蛮人’、‘狂野的爱尔兰人’、‘未开化的鞑靼人’以及别的‘外邦人’在现代早期的英国公共或私人舞台上被反复表现。”“我要表达的是,差异性(difference)的观念对于加深理解英吉利民族意识的出现是极其重要的,而且对于理解持续的殖民活动、边缘化和使得居住或者并不居住在英国的不同人民群体凝聚为一体等现象也是重要的。相对而言,英吉利民族的观念本身在莎士比亚时代还是新的观念。直到1534年亨利八世与罗马天主教决裂,英国的宗教领袖(教皇)还不是英国人。欧洲封建君主彼此之间不断的战争与联姻,他们之间的角力与联盟,重铸了民族/国家的种种形态。”[10]
(一)中世纪的威尔士是以凯尔特人为主体的、分裂的封建王国
大卫·休谟的《英国史》之“亨利三世”写到,威尔士短暂地臣服于亨利三世,后者也把对威尔士的宗主权看作是既有权利,“虽然威尔士和诺曼诸王对威尔士享有很大的君权,但土著王子仍然统治自己的国家。他们虽然被迫向英格兰王室称臣纳贡,事实上却很少臣服,甚至很少保持边境和平。征服以来,几乎每个朝代,威尔士人必定犯边。小规模的入侵连绵不绝,一般历史著作很少记录。英国人仍然满足于击退入侵,将他们逐回山区,不指望从他们身上获得什么利益。即使最伟大最能干的君主也不能彻底征服他们,哪怕是将他们降为封臣也做不到。最软弱最懒惰的现任君王却完成了这个任务。”[11]威尔士与英格兰的民族认同最初源自爱德华一世的军事征服,威尔士成为英国王室“兼并与联合”的领土。威廉·坎登在《不列颠史》之“格拉莫干郡-威尔士亲王”中指出,出生于卡那凡城堡的爱德华王子(Edward of Carnarvon)曾受封为威尔士亲王(1301年),1343-1376年,黑王子爱德华(Edward of Woodstock)受封为威尔士亲王[12]。而后,亨利四世(Henry IV,1399-1413)成功镇压了威尔士的反叛/叛乱,威尔士人最终放弃了独立国家的意识。亨利八世废除了作为凯尔特传统的威尔士法律的最后残余,并以英国法律取代之。屈勒味林的《英国史》(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A History of England,1945)写道:“历中古之世常足以困英人的威尔士问题,都铎王室亦能完全解决,一劳永逸。亨利七世处理威尔士时占了两种便宜。……他自己是威尔士人,受过威尔士的教育,且终生笃爱威尔士的诗歌风范而不衰。威尔士人常把他之能于波斯卫司战场上获得英国王位为民族已经取到独立的一证,故他们竞趋于他的朝廷而无所嫌忌。……[亨利八世]虽于苏格兰及爱尔兰两国的处理极不得法,而于威尔士问题的解决则颇有得心应手之妙。他采用恩威兼施的政策,一方以武力取缔纷扰,一方又秉公待遇凯尔特人民。……亨利八世之把威尔士划入英吉利,且一视同仁,无有歧视,实鲜有违他的谏言。此勇敢的处置实为不列颠史中的第一次的《合并法》(Act of Union),而把全境分成十二郡,各有治安法官以料理一切,并须服从国会的法律及枢密院的命令,自此而后威尔士的各邑各城亦得送代表于英吉利的众议院。”[13]
在《亨利五世》一剧中,亨利王对威尔士表现出极高的民族认同,蒙茅兹的亨利曾受封为威尔士亲王(1399-1413),在剧中第四、五场中,亨利王反复宣称:“我是威尔士人”,“还是他的亲族”,“因为我是一个威尔士人,你知道吧,老乡”。事实上,作为勇敢的骑士和威严的君王,亨利王也暗示某种英格兰式的偏见:“这个威尔士人,虽然有点古怪,却很有心机,很有勇气。”[8](P141)同时,威尔士上尉(营长)弗鲁哀伦对英吉利民族却表达了高度的一致性认同。第四场第7幕,弗鲁哀伦承认亨利五世与威尔士的密切关系,“他是生在蒙茅兹”[8](P179),“我告诉你,有好多好人都是生在蒙茅兹”[8](P183),“魏河所有的水也不能把陛下的威尔士的血液从你身上冲洗掉”[8](P187),“我是陛下的老乡,我不怕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我愿向全世界承认这件事:我无需为了陛下而感到惭愧”[8](P187)。后来,亨利还把一件有关于骑士荣誉的秘密任务交给弗鲁哀伦去执行,即接受威廉斯的挑战,“你替我佩戴这个纪念物,放在你的帽子上。”[8](P189)“因为我知道弗鲁哀伦是勇敢的,激怒起来,性烈如火药,会很快的回手伤人。”[8](P191)被激怒的弗鲁哀伦对英格兰低级军官威廉表达了对于背叛者的蔑视,“这是多么荒谬,下流,卑鄙,龌龊的一个奴才。”[8](P193)
剧中关于威尔士上尉(营长)弗鲁哀伦佩戴韭菜的传统是一个惹人注目的喜剧性场景,却暗示威尔士的文化及传统是根深蒂固的,并被人们自豪地保持并流传下来,“威尔士人在那生长韭菜的园子里确曾建过战功,在他们的蒙茅兹帽子上佩戴着韭菜;那韭菜,陛下知道的,一直传到今天仍是作战的光荣标帜。”[8](P185)亨利王表示愿意遵从这一传统,“我要佩戴它,作为荣誉的纪念。”[8](P185)第五场第1幕,英格兰上尉(营长)高渥指出,英格兰人对威尔士人表现出不恰当/不合理的歧视,尤其是对威尔士方言、传统习惯的歧视,“一项古老的传统,其起源是光荣的,其佩戴乃是纪念久已死去的勇者,你竟愿意加以嘲弄而又不敢以行为来保证你的语言么?我看见你接二连三的讥讽嘲骂这位先生。你以为他不会说流利的英语,便也挥不动一根英国的棍子:你发现不是这样的;此后让这一番威尔士的惩罚给你以教训,使你养成一种良好的英格兰的品格吧。”[8](P207)值得指出的是,弗鲁哀伦与高渥的友谊显然是基于骑士精神,而不是一致的英吉利民族。英格兰旗官皮斯多就轻视来自威尔士的骑士(上尉)弗鲁哀伦,甚至戏弄后者,第五场第1幕,弗鲁哀伦指责皮斯多对他的轻蔑与嘲弄,“你昨天喊我为山地老倌,我今天要你成为一个低级侍卫。”[8](P205)皮斯多故意嘲笑弗鲁哀伦佩戴韭菜,“到圣大卫节那一天,我要拔掉他头上戴的那根韭菜来打他的头。”[8](P139)结果,弗鲁哀伦找到一个机会报复了前者,强迫前者吃下那些让他恶心的韭菜,并说:“那个下流的,肮脏的,卑贱的,龌龊的,说大话的奴才,皮斯多。”[8](P203)
此外,在威尔士地区包括英格兰边境还有一种康沃尔方言,皮斯多误会了乔装后的亨利王,“一个康沃尔人的姓,你是属于康沃尔部队的么?”(a Cornish name:art thou of Cornish crew?)A.布尔德在《知识见闻录》(Andrew Boorde,Bok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Knowledge,1542)中写道:“在康沃尔郡有两种方言,一种是不规范的、低微的英语,另一种是康沃尔方言。许多男人和女人不会说一句英语,但所有人都会说康沃尔方言。”[14]
(二)整个中世纪,爱尔兰一直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即使英格兰国王对爱尔兰保持着宗主权,但大部分英格兰贵族不愿意到爱尔兰去
爱德华三世的对法战争时期,英格兰在爱尔兰和苏格兰边境上的小规模战争屡遭失败,使得英格兰感到不安。直到1485年,爱尔兰完全操纵在英裔爱尔兰人(约克家族一派)手里。都铎王朝初期,约克家族的反叛力量、神圣罗马帝国、法国先后支持爱尔兰反对英国。摩根主编的《牛津英国通史》写到了理查二世(Richard II,1377-1399)提出对爱尔兰的王权要求,并发动了两次对爱尔兰的战争,最终失败。直到1485年,英格兰君王再也没有重申这一要求,“1394年至1395年理查德对爱尔兰进行了耗资巨大的大规模征讨,这是自1210年以来英格兰国王的首次征伐,它成功地给那儿的英格兰统治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以巧妙的刚柔并济的方式使凯尔特的和盎格鲁-爱尔兰的贵族就范;他这次的冒险活动确实加强了他在又一王家领地的权力,并显示了他的王室组织和资财能做出怎样的成就,虽然只是短暂的。”[4](P206)“1399年他再次征讨爱尔兰,给予原德比伯爵,现为赫里福德和兰开斯特公爵的亨利·博林布鲁克以可乘之机,……博林布鲁克在得到为理查德疏远的珀西家族支持后便夺取了王冠。”[4](P207)“凯尔特人享受着独立和相对的繁荣,盎格鲁-爱尔兰人珍惜他们自己的权利,便与凯尔特对手达成协议。英格兰政府的主要考虑是安全(‘爱尔兰是英格兰的支撑和柱石’,一位当时的人在1430年代说),只有在威尔士叛乱(1400-1409年)期间和1450年代当安全受到威胁时,英格兰政府才对爱尔兰事务表现出较大的关注。”[4](P208)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写到,即使在理查二世征服时期,爱尔兰语依然顽强的坚持了下来,“爱尔兰的首领们在归降称臣和宣誓效忠于英王时,只用一种语言,就是爱尔兰语”。“理查二世发动的首次征服显然是一个失败。由于英格兰政府既无足够的财力又无足够的人力可以用来对付爱尔兰,结果本地民族光复了三分之二的爱尔兰土地,在征服时期也已退缩到穷乡僻壤的爱尔兰语言和文化也重新传播了开来。爱尔兰的民族精神再次抬头,并且战胜了外来的民族精神;只可惜政治的统一没有和种族的统一同时恢复,因为五、六十个凯尔特氏族的首脑只希望恢复旧时的贵族传统,并复兴环绕在他们身边的行吟诗人、布雷亨法和编年史家所代表的学究文化。”[15]1494年,亨利·都铎(Henry Tudor,1491-1547)受封为爱尔兰亲王(Lord Lieutenant of Ireland),并宣称自1327年以来,英国国王对爱尔兰拥有主权,尤其是“波伊宁兹法令”(1495)使得爱尔兰大领地降为完全的、绝对的屈从地位。
《亨利五世》第三场第2幕写到了爱尔兰人很勇敢的骑士马克毛利斯营长(上尉)。高渥营长(上尉)表示,马克毛利斯是一个懂得兵法的军官:“奉命围城的格劳斯特公爵完全是听从一位爱尔兰人,一位很勇敢的贵绅的指导。”[8](P93)弗鲁哀伦出于嫉妒对马克毛利斯较为不满,甚至抱怨后者,“他是蠢驴,世上最蠢的蠢驴:我可以当着他的面证明他是蠢驴:你要注意,他不比一条小狗懂得更多的兵法,罗马人的兵法。”[8](P93)然而,苏格兰人霍米营长(上尉)积极肯定了马克毛利斯的才能:“两位都是好营长。”[8](P95)马克毛利斯自责与愧疚地承认挖地道的工作做得不好,表明他具有理性的、自律的良好品格。在战事最紧张的时刻,马克毛利斯拒绝与弗鲁哀伦辩论兵法,“这不是高谈阔论的时候,……城是被包围起来了,号角在呼唤我们冲向豁口。……任事不做,这是我们大家的耻辱,上帝救我,站着不动是耻辱。”[8](P97)
第四场第1幕,亨利王提及志愿军,“我是营里的志愿军(As good a gentleman as the company)。”[8](P139)第四场第7幕提及法国雇佣兵(mercenary)[8](P185),爱尔兰马克毛利斯营长(上尉)可能即是雇佣兵/志愿军。第三场第2幕,威尔士人弗鲁哀伦无意间不自觉的表现出民族意识上的偏见与歧视,暗示爱尔兰对英吉利民族意识的疏离,马克毛利斯却很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马克毛利斯营长,我想,你要注意,如果我错了,你可以纠正,没有很多的你们贵国人——”[8](P95)。(Welch:Captaine Mackmorrice,I thinke,looke you,vnder your correction,there is not many of your Nation.)[16]而马克毛利斯的回答是过分敏感的、过激的,“我们贵国!我们贵国怎么样?他是个小人,杂种,奴才,流氓吗?我们贵国怎么样?他想议论我们贵国?”[8](P97)(Irish:Of my Nation? What ish my Nation? Ish a Villaine,and a Basterd,and a Knaue,and a Rascall.What ish my Nation? Who talkes of my Nation?)[16]剧中有意突出了马克毛利斯的混杂盖尔语、英语的语音,以增强舞台的表演效果,而不是民族身份的焦虑。第三场第2幕,威尔士人弗鲁哀伦似乎更愿意强调出身与才能,而不是英吉利民族意识,“也许我就要以为你欠思考,没有以你应该对待我的礼貌来对待我,你要注意;讲到兵法,出身,以及其他各方面,我都不比你差。”[8](P97)(Welch:…… peraduenture I shall thinke you doe not vse me with that affabilitie,as in discretion you ought to vse me,looke you,being as good a man as your selfe,both in the disciplines of Warre,and in the deriuation of my Birth,and in other particularities.)[16]换言之,在亨利五世时期,爱尔兰与英格兰的关系是极其敏感的,尤其是对于那些被英格兰称为“英裔爱尔兰人”或者“爱尔兰的英国人”。第五场合唱队证明,即使在伊丽莎白时期爱尔兰仍然有为独立而发动的反叛,“如果我们的仁慈女皇手下的那一员大将现在——很可能就在现在,——从爱尔兰回来,剑挑着叛逆者的头颅,平静的城里面要有多少人来欢迎他啊!”[8](P203)这是指伊丽莎白女王晚期由于宗教改革而引发的爱尔兰独立战争(1593-1603),爱尔兰得到了西班牙、苏格兰的支持,1599年,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Robert Devereux,2nd Earl of Essex)未能成功镇压这次叛乱,1600年,双方在谈判后宣布停战[17]。莎士比亚似乎满怀希望,以为罗伯特·德弗罗能获得对爱尔兰战争的完全胜利,暗示由此达成一致的英吉利民族意识。
另一方面,法国似乎对爱尔兰民族持有一定的好感。第三场第7幕,法国太子说到了爱尔兰的轻装步兵,显然他们是十分勇敢的,“你骑上去的时候,像是爱尔兰的轻装步兵一般,脱下你的法国裤子,穿着你的紧腿裤。”[8](P125)第四场第4幕,一个法国士兵被英格兰旗官皮斯托俘虏,皮斯托要求法国士兵提供庞大的赎金,“阶级?绥尔河边的姑娘!你是绅士么?你姓甚名谁?说吧。”[8](P169)(Pist:Qualtitie calmie custure me.Art thou a Gentleman? What is thy Name? discusse.)由于皮斯托听不懂法语,因而他胡诌乱扯一通,“Calmie custure me”是1582年刊印的爱尔兰歌谣——《噢 可爱的年轻姑娘》(Cailíng a Stór)中的一句戏拟拉丁语的最末合唱歌词,爱尔兰语原写作:“Cailín ó Chois tSiúre mé”(我是一个来自绥尔河边的姑娘),此句也见于17世纪爱尔兰语诗歌《用细绳扎辫子的姑娘很讨厌》(Mealltar bean le beagán téad)。歌谣《噢 可爱的年轻姑娘》现可见于1584年的英语抒情歌谣集(Broadside ballad)[18]。显然,李成坚《〈亨利五世〉中麦克默里斯的身份探源及文化解读》对此有过度解读(over interpretation)。
(三)公元843年以来,苏格兰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以它的抗拒、反叛和战争,拒绝认同统一的英吉利民族意识
霍利迪《简明英国史》写道:凯尔特部落居住在苏格兰高地,撒克逊人居住在苏格兰低地,后者实行采邑制。1295年,苏格兰与法国国王建立了长期的联盟(Auld Alliance),次年,爱德华一世以王位继承权为借口入侵苏格兰,激起了威廉·华莱士、罗伯特·布鲁斯的民族反抗斗争,苏格兰挫败了爱德华的四次入侵。1314年,苏格兰国王罗伯特·布鲁斯趁英格兰的内乱在班诺克伯恩打败英格兰军队。1388年,英格兰军队在奥特本战役中失败,此后的两个多世纪,苏格兰与法国联盟一直是英格兰持续的威胁,苏格兰与英格兰处于敌对状态[7](P30)。摩根主编的《英国通史》写到了苏格兰长期以来对英格兰带来的困扰,因此,一些英格兰国王已放弃了在苏格兰和大部分爱尔兰的宗主权要求,“在15世纪,部分地因为在法国的战争又起,部分地由于亨利四世统治时期和1450年以后英格兰内部的纷乱,他们对苏格兰处于防御地位;苏格兰甚至在1419年派出大量增援部队援助法国人。英格兰俘虏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短时间内(1406-1424年)阻止了边界上大规模的军事对抗,但此后苏格兰人变得更为大胆,他们希望收复罗克斯伯勒城堡和贝里克,并于1460-1461年达到了目的。袭击,小规模的海战,海上掠夺,还有时效的休战协定,加在一起构成了没完没了的冷战状况。……1475年签订了盎格鲁-苏格兰条约,1502年签订了‘永久和约’。这些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两国关系的重大转变。”[4](P207)
《亨利五世》的叙述显然基于英格兰与苏格兰敌对、冲突的历史。在《亨利五世》一剧中,“邻国”(neighbour)先后出现过7次,其中3次指苏格兰,亨利五世和别的英格兰贵族称之为“冲动的邻国”(giddy neighbour)、“坏邻国”(bad Neighbour)、“恶劣的邻国”(ill neighbourhood)。第一场第2幕写到了苏格兰与法国联盟,“我们不可以仅仅挥兵侵入法国,我们还要酌量分兵防备苏格兰人,他们有机可乘便要向我们进犯的。”[8](P33)“我怕的是苏格兰人大举进犯,它一向是我们的一个不稳定的邻邦;……苏格兰人不对他的无防御的国土倾巢来犯,像海潮一般以全部的力量乘隙而入,以快速的攻击骚扰这空虚的国土,围困堡垒城池;于是英格兰因国防空虚在这恶邻之下战栗了。”[8](P35)韦斯摩兰德公爵也承认苏格兰与法国联盟,“如果你想赢得法兰西,要先从苏格兰做起:因为英格兰一出去捕食,苏格兰那只黄鼠狼就偷偷地来到它的没有防御的巢里吮吸它的蛋,扮演猫不在家时的老鼠,扯烂糟蹋的东西比它所能吃的还要多。”[8](P35-36)坎特伯雷大主教也说到爱德华三世打败苏格兰的事件:“它不仅把它自己保卫得好,而且把苏格兰国王(James I of Scotland,1406-1437)像流窜的野狗一般捉到关了起来;随后把他送往法国,作为被俘的国王之一,以增长爱德华国王的威名,并且彪炳英格兰的史册,使得它充满了光荣事迹。”[8](P35)“如果我们有四分之三的兵力留在国内,而不能抵抗那狗侵入家门,那么就让我们被撕成碎片,让我们的国家失去坚强多谋的美名吧。”[8](P39)他轻蔑地称呼苏格兰为老鼠、黄鼠狼、狗(野狗),意味着苏格兰与英格兰的敌对/对立是显著的,二者远未达到一致的民族认同,效忠亨利王的韦斯摩兰德公爵、坎特伯雷大主教等英格兰贵族敌视并畏惧苏格兰的独立存在。
苏格兰人霍米上尉(营长)首次出现在第三场第2幕,霍米在剧中出现的次数极少,这位英裔苏格兰人可能是雇佣兵。弗鲁哀伦称霍米“是个非常勇敢的人,那是一定的,他富有经验,而且精通古代兵法,这是我从他指挥战事中所亲自领教过的:指耶稣为誓,讲到古罗马战争中的兵法,他逞起雄辩能不下于世上任何军人”。而且霍米在战场上表现得很勇敢,“我要好好的效力一番,否则我就要倒在地上;对了,倒地而死;我要尽可能的勇敢的效力。”[8](P97)
三、余论
M.多勃松的《民族诗人的形成:莎士比亚,改写,权威化》(Michael Dobson,The Making of the National Poet:Shakespeare,Adaptation and Authorship,1660-1769,1992)认为,自18世纪以来,莎士比亚被认为是可敬的启蒙作家和英国民族诗人,他的创作被认为与英吉利民族性紧密关联在一起,是英吉利民族的象征。《亨利五世》想象性地表达了一致的英吉利民族意识,该剧的主题是亨利七世以来的“都铎王朝的神话”,或者建构英国的民族性(make nationness)。拉尔菲·何特勒《英国(戏剧)舞台上的伊丽莎白时期的历史剧》认为,伊丽莎白时期的戏剧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ining community),戏剧通过故事的叙述在舞台上重新阐释了民族的历史(Making History:Staging the National Past),这些历史剧向戏剧观众传达了英吉利民族性,而观众亲眼目睹了戏剧舞台上表现出来的英国历史和民族性,并对英国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加以认同[19]。布朗·沃尔西《莎士比亚,女王剧团,伊丽莎白时期的历史剧演出》认为,伊丽莎白时期的历史剧发挥作用的重心是政治领域。历史剧紧密地关联着伊丽莎白时代的民族认同、王权、臣民的质询和国内外的国家权力扩张等问题[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