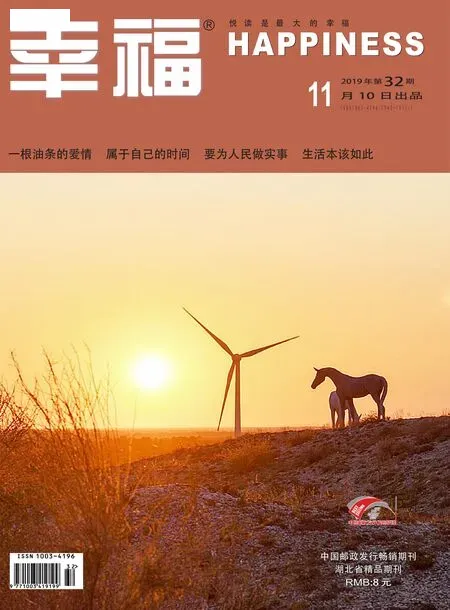睡在炊烟里的等待
文/金凯歌
我那个活到九十二岁的老姥娘——我奶奶的母亲,是个很厉害的老太太。
奶奶六十多岁的时候突然撒手人寰,老姥娘白发人送黑发人。但整场葬礼,她没落下一滴眼泪。那年,我刚上一年级,很不理解老姥娘的冰冷无情。好几次,我都想走过去问她:“老姥娘,你怎么不难过?”她那布满老年斑的脸,竟然渐渐舒展开来,那是笑——“因为我很舍得。”她是个懂得放手的人。
客人浪潮般退去,悲伤的晌午最终化作平淡的午后,露出本该淡然的模样。她坐在门槛前锃亮锃亮的石板上,撑手遥望远处的乡村。我在她的身旁坐下来,看见飘起来的炊烟,潮湿湿的,在她的眼睛里缭绕。彼时,正是放学的时候。夕阳很美,炊烟背靠背,亲亲密密地升上天空。她伸手,捋顺鬓边的白发,喃喃道:“这个时候,妞妞该放学了。”老姥娘叫奶奶妞妞。
我担心她悲伤起来,哄着让她给我扎漂亮的羊角辫,还叽叽喳喳说了一堆学校里的事情,顺道在她的怀里钻来钻去。她禁不住笑了,粗糙的手在我乌黑的小辫子上摩挲:“格子啊,女人,就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落落大方。”
我瞄上她的眉,柳叶形,像炊烟底下的柳树,娉娉婷婷。老姥娘爱美,现在的眉毛是八十五岁时,她要求奶奶带她去文的。
我本以为,这样每日在夕阳中踏着炊烟归来的日子,可以永远流转下去。可有一天,突然来了一群人。他们神采奕奕地来,走家串户。很快,就到了我们家。我躲在老姥娘和父母的身后,看到面前中年人脸上的疲色。他们的额上挂着汗珠,开始向父母解释此行的目的:要买下我家的田,在上面建工厂,带动县里经济发展。
解释完此行目的,他们就立在那儿不敢动了,像等候发落的孩子。父母望向老姥娘,希望她能拒绝——这是她老人家最心爱的田啊。出乎意料地,她点了头。男人们走过来,深深地鞠躬,说拟好合同再来商议。折腾完时,炊烟已经飘起来了。老姥娘平静地坐下来,像炊烟走过的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般,剥收来的棉花——这大概是她最后一次剥棉花。
“后悔吗?”“不后悔。”
“卖了地不吃亏吗?”“吃亏是福。”
“那就等着让他们买走咱们的地?”“人家不是说了,让咱等好日子哩。”
和老姥娘待在一起的日子,总是那样平淡,却又意义非凡,就连她走的那天,亦如此。
母亲打电话通知我。我静默,隔着听筒聆听母亲的声音从千里之外——那个让我魂牵梦萦的小村庄里,飘荡过来。人常说,夕阳下了,我在山边等你;叶儿落了,我在树下等你;细雨来了,我在伞下等你。可为了寻找那把遮风挡雨的大伞,我们竟在时光里,跋涉了很多年……于是我的眼眶开始潮热,渐渐雾气萌生,眼前的景象变得模糊起来。
母亲顿了很久,接着说,老姥娘留了话给我:“二格子不准哭,死不就是两腿一蹬的事嘛!若是诚心想念我,我自会来看你!”热滚滚的泪,最终在这一番话里,化作平静的雾气,消失无踪。
记得很多年前,一次学校里布置作业,让写以“家乡”为题的作文。我去找她,絮絮叨叨地跟在她身后抱怨,嫌主题太大众。她却颤巍巍地,一边拢拢耳旁垂下来的白发,一边往装了麦糠的盆里撒盐:“写炊烟吧。”
“什么是炊烟?”
“放学路上,各家各户都有,还带着香气,勾着你回家的那东西呗。”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认识炊烟。而等待睡在炊烟里,我花了很多年,才懂得。也许有时候,往事不堪回首,并不完全因为过去埋藏了多少无奈、多少辛酸,而是那一句“炊烟起了,我在门口等你。”这句话落在心里很重、很重,刻到骨子里很深、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