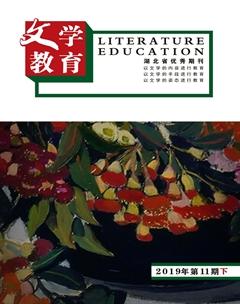语言系统与变化的自组织理据
内容摘要:语言变化的自组织首先表现在耗散结构论层面,是非线性和非平衡的过程,是开放流动的“活结构”。其次是协同学层面,协同效应是推动语言从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转化的关键。再次是超循环论层面,即语言与社会关系是适应--不适应--再适应无限循环过程。最后是分形学层面。语言系统的自组织演化过程亦即混沌(平衡态)→有序→混沌(非平衡),是语言的混沌与有序辩证转化、循环发展的图景。因此,语言自组织系统有序变化机制是语言系统内部相互作用形成的动态平衡态势。
关键词:语言变化 耗散结构 协同论 突变论 超循环论
自组织理论是研究系统自组织过程的机制、规律和形式的科学,是系统科学研究的基石。[1]耗散結构论、协同学、突变论、分形学等分学科构成了自组织理论的总称。系统的运动、发展和演化是自组织理论的核心问题,它很好地揭示了作为系统演化内部动力的相互作用、竞争和协同与系统循环演化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事物的循环发展。
20世纪70年代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比利时物理化学家L·普律高津(L·Prigogine)在总结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耗散结构(Dissipatire Structure)这一自组织理论核心概念。随后,赫尔曼·哈肯(H,Haken)将自组织理论研究更加深入,第一次从科学意义上提出了自组织概念,将自组织和被组织两个概念清晰界定。[2]他认为,自组织是:“在获得空间、时间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受到外界的特定干扰的系统。这里的‘特定一词是指那种结构和功能并非外界强加给系统的,而且外界是以非特定的方式作用于系统的”。[3]
一.语言系统与变化的耗散结构论
耗散结构理论认为,一个系统如果形成耗散结构需要具备四个必要条件:一是系统必须是一个开放系统;二是系统必须处于远离平衡态;三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四是涨落导致有序。
(一)语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语言是一个复杂而缜密的系统,其系统的复杂性就像复杂分子、电磁场和人类视觉系统一样。语言本体和生物有机体之间有许多共性。归纳起来大致如下:两者具有相同的层次性。生物有机体的层次性从低到高顺序是:细胞→组织→器官→系统。[4]语言的层级系统如同生物层级系统一样。[5]信息和意义是生物有机体的性状,它是通过信号和符号来实现和表达出来的。无论是生物信息还是语言信息他们都承载着相类似的编码方式:“形式”和“意义”分别按照层次顺序进行着不同的排列组合,其规模和程度是从小到大、从有限到无限。[6]
(二)语言系统处于远离平衡状态
雅各布森指出,语言系统从来都不是完全平衡的。语言的交际功能产生了语言系统的不平衡性,而且处于语言交际的客观世界不断变化、错综复杂。因此,语言在实现其功能的同时,不断地打破平衡以适应纷繁复杂、不断变化环境下语言交际功能的需要。在词汇层面上,这种语言系统处于远离平衡状态的情况尤为明显(封宗信,2006:22)。如同自组织系统,语言其实就是一个复杂、开放和互相作用的过程载体,其变化就是贯穿远离非平衡,由混沌转向有序的非线性和非平衡的自组织过程。语言内部结构体系随着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等因素不断丰富新内容,处于非平衡的开放状态。语言持续而又重复地引入”负熵流”,消除自身熵的增长,始终保持“活结构”态势。
(三)语言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相互关系
系统中必须存在非线性相互作用,只有这样系统方能自组织,从无序到有序,形成耗散结构。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个倾向性的研究趋势是从非线性的角度来对物质世界的自组织行为进行研究,而根据自组织理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的有关论述,可以认为非线性正是组织系统产生非平衡态和耗散结构的内部动力机制,也是自组织的动力源泉。近些年来,人们开始用这一研究视角来观察社会现象,并且业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徐通锵(1997)、王艾录和司富珍(2002)、司富珍(2008)等曾讨论认为语言系统是一种开放的自组织系统,非线性构成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特性,因此非线性的研究方法同样适用于语言自组织的研究。[7]
(四)语言系统涨落导致有序
随机涨落是耗散结构形成的孵化器,依靠个体变量涨落的诱导和启发,通过随机涨落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化,在非线性相互作用下,构成体系的各部分间相互制约、相互耦合、相互作用,形成时空有序的耗散结构。在常规情况下,知识系统保持它持续的稳定态。然而,在有些情况下必然要求语言发生相应的结构变换,即消除过时的术语、语义和句法,引入新的术语、语义和句法中合理的规定性,从而保持域语言与操作语言的一致性或协调性。任何有意义的科学知识系统源自于自身的语言结构辨证运动,形成动态的、开放的“语言耗散结构”,并通过有效合理的“涨落”显示出科学知识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语言系统的协同论
协同学是理解语言变化的新思想和新方法的又一理论基础,也是改变人们思维方式和科学的世界图景。语言系统是由语音、词汇、句法、语篇等要素组成的,各要素彼此不是孤立和毫不相干,协同学就印证了语言系统内部各层次要素结构和功能的对立统一关系,也是证明语言由无序转向有序的重要理据。而且,在语言系统中,序参量是积极的可变因素,作为语言使用者的序参量强与弱直接影响着语言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协同效应,也就是说,序参量越强,语言系统的有序状态就越能建立,协同效应的作用就越能显现。[8]在语言的变化过程中,对语言进行抽象、概括、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是语言使用者常用的逻辑方法,同时还要对语言系统结构进行归类、提取、整合和补充等。另外,语言使用者除了对语言系统内部进行探究以外还要探究系统内部结构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认知科学证明,大脑这一不同质的器官掌管视觉、数字、语言等能力的模块组合体,而组合体模块之一即是语言能力。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88)指出,“语言能力是人脑的一部分,这个部分专用于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他将语言器官视同为“智力器官”,其意义如同心脏、视觉和听觉等其它物质器官。语言系统的句法、词法、音系、语义、词汇等是“语言器官”的子系统或子模块,一旦大脑受损或遭遇其它影响,“语言器官”就停止工作。即使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会出现语言理解上的偏误,但是,他们的语言生成能力却完好无损,反之亦然。由此可见,语言的协同性表现在语言的器官性、语言的模块性以及语言的基因遗传性三个层面之中。[9]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78:312)又认为,人们终究会发现语言能力的基因突变,人们以生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来研究语言能力的内在属性指日可待。由此可见,语言的变化就是协同的过程,协同学揭示了大脑结构与语言的关系,并试图通过语言的建构、习得、使用、机制和进化等实现语言的有序性,实现语言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协同效应。[10]
三.语言进化的突变论
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都认为语言是一种自然发生体系的进化。艾伦(Aaron)等(2006)提出了目前4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框架:(1)突变论(Macro-mutation)。该理论认为人类语言与动物交流之间有着无法跨越的鸿沟,语言的产生是由神经结构突然变化形成的;(2)渐变论(Microevolutionary)。该理论认为语言的产生是由无数微小的基因变异渐渐地形成的,其过程包括随机突变、遗传传递、适应、和选择;(3)新表型发生学说(Neophenogenesis)。该理论认为语言的产生是由于基因和基因组以外的體系(包括社会文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社会需求和文化因素是推动语言进化到一个空前复杂体系水平的两个重要方面;(4)功能变异理论(Exaptation)。[11]该理论认为语言的产生是在基因组内存在着无数潜在的遗传基因中,那些具有环境适应的基因进行选择性表达做到的。
在语言进化的基因研究领域中,R.A.费希尔(R.A.Fisher)等人(2006)认为:鸟类的翅膀不同于其他脊椎动物的四肢。但是,两者都具有继承性和延续性等特点。FOXP2对于人类语言形成和功能体现是明显的,但是它也离不开动物进化与完善的过程。然而,科学研究证明,尽管当下关于进化分子遗传学研究大多集中于FOXP2基因,然而语言的进化并不是由单个FOXP2基因演变而成的。实际上,人们已经发现更多基因,如与语言遗传相关的认知和运动技能基因。如Spiteri等在胎儿脑组织基底神经节和额皮质下层发现285个FOXP2的靶基因,并在体外证实FOXP2基因的调控作用(赵云静,2009)。其中很多靶基因对于中枢神经系统发育起到关键作用。同时,这些靶基因的进化研究为人类研究语言的起源和进化提供了更加详实而又科学的理论依据。[12]
四.语言系统与变化的超循环论
从历时语言学层面来看,语言的演变从来不能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相脱节,相反,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催生或加速语言的演变。语言的变化遵照超循环模式:即适应--不适应--再适应。[13]超循环模式告诉我们,作为动态性的语言系统在特定的条件下会呈现平衡,但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语言暂时的平衡状态在另一特定条件下会进行更高层次的复制与再生。语言的使用者要把握语言的超循环特征,同时又在不断地将循环的一个环节推向另一个环节。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在万事万物中,物质的静止是相对的,物质的运动是绝对的,物质的运动存在于物质的静止之中。罗曼·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2012)曾提出,变化了的过去的残片蕴含着共时的状态,人类语言具备这种可提供变化的潜能,而且将自己和其它语体区别开来。符号学给了我们提供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自然语言具备人为控制的超越性,人们使用语言,将自己与跨越了时空的其它人群联系起来,形成了独特的交际方法以适应特定的语言环境,语言的使用者就是遵循着这样一种动态性的规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社会交往的日臻频繁以及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也越来越加深,因而,在语言新词不断涌现的同时,词义的变化也随之不断出现新的情状。[14]无论语言怎么演变,但也不能偏离其内部和外部原因的藩篱。外部原因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分不开,社会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以及作为语言使用者的人是推动语言变化的外部原因。语言演变的内部原因是系统内要素的调整、取舍、更迭以及相互作用、相互影响。[15]正是语言演变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推动语言沿着适应--不适应--再适应这一超循环模式。
五.语言系统变化的分形论
1967年本华·曼德博(Benoit B. Mandelbrot)发表的《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统计自相似性与分数维数》是分形学的诞生标志。他认为海岸线错综复杂,海岸线长度的测量方法莫衷一是,不同的测量尺度会有不同的测量结果。 [16]应该根据自然多数是不规则这一特征,充分考虑到无限嵌套层次的逻辑结构,而且在特定条件下,充分认识到自相似特征。
语言的变化确实具有普遍性。语言离不开社会,社会发展不能离开语言,更离不开语言使用者。只要语言被使用,就会在历史的时空中逐渐地演变和发展,任何语言的变化都是首先发生在某些“言语社团”,然后逐步推广。[17]从历史语言学层面来看,语言是复杂的,语言的历时变化也是复杂的。从语源层面看,在漫漫的历史时空中,语言使用社团或民族因生产力发展,社团或民族人员增加而不得不扩张到更大空间的不同地点,从而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各自的社会。与此相应,社团或民族成员之间语言出现了阻隔,长期以往,信息不能交流,语言差异越来越大,最终,这样就分化为不同的语言或方言。再者,在历史的时空中,社团成员或社会也可能因扩张或经济文化的往来而彼此发生密切程度不同的接触,甚至融合为一个社会,他们的语言也会彼此影响而不同程度地趋同。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源关系引发的语言变化,即同一语言的演变分化与不同语言或方言的接触趋同,在历史的时空中并行不悖、又相互交织。[18]比如,人类历史上出现一个社团或民族强盛后扩张到另一个语言社团或民族领地,于是,从强盛扩张到别人领地的人群与被扩张领地的人群语言因空间距离的阻隔而分化。与此同时,从强盛扩张到别人领地的人群与被扩张领地的人群语言因同居一地的接触而趋同。但是同一语言的演变分化与不同语言的接触趋同所引发的语言变化规律却各不相同。因而,历史语言学既要分别研究语言演变与语言接触各自的规律,又要综合研究语言演变与语言接触交织作用的结果。
六.结论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曾指出,语言离不开语言的使用人,与使用人的活动相交织,而且语言还是人们彼此交流和传递信息的动态化载体。语言是动态的、是系统内部复杂的、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动态平衡系统。语言的自组织本是系统出现的一种稳定有序结构,这种结构是系统在不断地耗散语言外界供应的语源、功能和大量信息的条件下得以维持,因而是一种非平衡有序结构。语言系统的非平衡是语言自组织系统有序演化的前提和条件。
通过以上自组织理论要素分析得出:第一,是语言的发展和变化具有开放性,语言的使用者要保持开放的态势,使之处于远离平衡态的涨落过程,同时充分注意其传播通道的耗散性。只有在语言的使用中保持开放的“活结构”才能使语言从混沌无序走向有序。第二,语言使用者要对语言系统内部机构进行探索和研究,又要注重系统内部结构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功能。第三,语言的使用者要把握语言的超循环特征,同时又要不断地将语言推向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脉搏,使之达到新的适应。第四,考察语言的变化不可以定型思维模式,而应该认识到语言演变和发展的不规则性和复杂性,在把握语言结构“自相似”基础上,认识语言具有无限嵌套层次的逻辑结构,从而从整体上把握语言的变化历程和变化细节。
参考文献
[1]尹付.语言动态性的哲学思想表征[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2]沈小峰.混沌初开:自组织理论的哲学探索[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Haken H. Synergetics: Introduction and Advanced Topic [M]. Berlin: Springer, 2004.
[4]Haken H. Synergetics: Introduction and Advanced Topic [M]. Berlin: Springer, 2004.
[5]李慧.生物学范式下的语言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4.
[6]Prigogine N G. Self-Organization in Non-Equilibrium System from Dissipative Structures to Order through Fluctuation [M]. New York: Wiley,1977.
[7]王路江主编;司富珍执行主编,数理逻辑之美 方立教授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2.08,第190页
[8](德)哈肯著,徐锡申等译,协同学[M].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84.
[9]史忠植.认知科学[M].合肥: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10]周统权.语言的生物机制(2) [J].外语学刊,2010,(3).
[11](德)哈肯著,郭治安等译.信息与自组织[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1988.
[12]Teramitsu I, Kudo LC, London SE, et al. Parallel Foxpl and Foxp2 Expression in Songbird and Human Brain Predicts Functional Interaction [J].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004, (24).
[13]Haken H. Fluctuations and Stability of Stationary Non-equilibrium Systems in Detailed Balance [J]. Zeitschrift furPhysik, 1971, 245( 2).
[14]Mummery,C.J.,Patterson,K., Hodges,J.R.,&Price,C.J.Functional neuroanatomy of the semantic system: Divisible by what? [J].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1998,(10).
[15]Prigogine N G. Babloyantz A. Thermodynamics of Evolution [J]. Physics Today, 2008,(11).
[16]譚长贵.动态平衡态势论研究 [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
[17]谢奇勇.语言学概论精要与练习[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3.
[18]Haken H, Kelso J A S, Bunz H. A Theoretical Model of Phase Transitions in Human Hand Movements [J]. Biological Cybernetics, 1985, (5) .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认知视域下的英汉动态性语义对比研究”(16YYD001)。
(作者介绍:尹付,常州工学院副教授,从事认知语言学和英语教学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