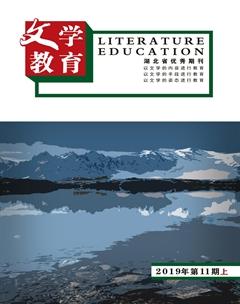从双性同体视角解读《所罗门之歌》中派拉特的形象
内容摘要:女性主题是托妮·莫里森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在她的第三部作品《所罗门之歌》中同样透射出双性同体女性主义思想。小说中的派拉特是一个具有双性气质的女性人物。在她身上既有女性自然、母性、感性的特质,又兼具男性理性、独立、刚强、果敢的特质,实现了男性意识与女性意识的交流融合,美好的女性特质和理想的男性特质的和谐共生。通过塑造这样一个理想的女性,莫里森表达了她的性别文化理想。
关键词:莫里森 双性同体 和谐人格
女性主义是托妮·莫里森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莫里森开始创作的时期,双性同体女性主义思潮正在美国盛行。贝蒂·弗里丹在其1963年的《女性的奥秘》一书中挑战了美国传统的性别文化,为其后来提倡的双性同体观埋下了伏笔。凯特·米利特也在其1970年出版的《性的政治》一书中渴盼一个双性同体的未来。莫里森的创作始于20世纪70年代,难免会受到这种当时盛行的女性观的影响。此外,双性同体观作为文学批评的一般标准最早是由英国女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弗吉尼亚·伍尔夫引入文学领域的。莫里森曾在其硕士论文中研究伍尔夫的作品。熟读伍尔夫作品的莫里森自然而然受到该思想的影响。双性同体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古老话题,它的着重点在于解放真正的人性,尊重男女的个体性,追求自身人格的完善。与“双性同体”对应的英文是“androgyny”。“androgyny”这个词对于希腊人来说指的是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在一个雌雄同体个体身上的共同作用与表现。”[1]古希腊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曾提出最初的三个性别,分别是与太阳、大地、月亮相对应的。男人本是太阳的后裔,女人本是大地的后裔,双性化的人则本是月亮的后裔,而月亮是太阳和大地的结合体。因此这种结合体的人有着极其强大的力量和极高的思想。[2](23)而莫里森《所罗门之歌》中所体现出来的双性同体思想主要通过这部作品中派拉特形象的塑造得以诠释。派拉特身上既有女性自然、母性、感性的特质,又有男性理性、独立、刚强、果敢的特质。她是莫里森塑造出来的理想的女性形象。
一.派拉特的女性特质
作为女人,派拉特身上有着很多美好纯粹的女性特质,她担当着慈爱的母亲、宽厚的妹妹,可亲的小姑等不同的女性角色。
派拉特的女性特质首先源于她身上洋溢的自然气息。在小说中,派拉特是自然的化身。女性是自然的象征物,女性本质上与自然是密切联系的,这是多种文化之中都存在的一种观念。派拉特的身上体现了自然与女性的完美融合。完全在自然的抚育中长大的派拉特纯朴自然,与树木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兄长麦肯的回忆中,她从小就喜欢嚼松针,嘴里有一股森林的味道。在故乡老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整天在农庄“林肯天堂”的林子里疯跑的小丫头。在一百五十亩的“林肯天堂”中有八十亩是一片树林,长着橡树、松树和各种果树,那是派拉特儿时的王国。而在奶娃和吉他看来,她本身就是一棵黑树。值得一提的是,她的名字拼写起来就像一棵大树庇护着一行小树。后来她在都市定居的住所背后则是四棵高大的松树,她用树上的松针作褥垫,住所内到处弥漫着松树的味道。派拉特与树的密切关系寓意出她就是大自然的女儿。她与大自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谐共处。小时候,她会自己从树上摘果吃,会把嘴凑到乳牛的奶头上直接吮吸奶汁,或者从蔓上摘下一颗西红柿,当场站在那里吃掉。后来,年迈的派拉特虽然住在都市,却选择住在远离都市喧嚣的一座背靠着四棵松树的平房里,房子简陋却通透,洒满阳光;门窗从不上锁,门口也没有门牌号码;房子内找不到任何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浸染的东西,室内弥漫的松枝、发酵的水果与醇酒的香味让人感到愉悦。她带着女儿和外孙女用劈柴和煤来取暖做饭,吃简单自然的食物,“她们有什么,碰上什么或者馋什么,就吃什么。”[3](33)随性的生活快乐而充实。她古朴、纯真的原生态生活方式和良好的自然本性使她与自然融为一体,从而拥有了一种独特的女性魅力。
派拉特与生俱来的神秘感更增添了她的女性特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派拉特,作为生命养护的大母神,为多年不育的露丝送来了奶娃,从而拯救了处于极度压抑状态的露丝,使她有了生活的希望。派拉特不仅设法使露丝孕育了奶娃,而且让她自己成功孕育了女儿丽巴。母性是她的又一个重要的女性特质。她是女儿丽巴和外孫女哈格尔的老妈妈,是家中慈爱的女家长,给予了女儿和外孙女无限的母爱。同时在某种意义上她还是奶娃精神上的母亲,辅助他的成长,引领他走出了个人的狭隘世界,学会了爱,进而走向真正的心灵的成熟。
除此之外,派拉特的女性特质还体现在她对黑人传统文化的传承。“承载文化的母爱使黑人民族的文化传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延伸的母爱或‘泛母爱具有愈合伤痛。救赎一切的力量。”[4](viii)黑人的传统文化主要由母辈代代相传。在《所罗门之歌》中,派拉特承担起这样一种黑人文化传承的使命。
二.派拉特的男性特质
传统文学作品里性别二元对立下的女性通常是柔弱、被动、消极的形象。但派拉特不同于男权文化规定的传统女性形象。她身上既有很多人们期望的女性特质又兼具部分人们崇尚的男性特质。莫里森通过塑造派拉特这个具有男性一样的主体性和主动性的形象解构了二元对立的父权意识体系。
派拉特宗教色彩浓郁的名字暗示了她具备男人的气魄。在《圣经》里,派拉特是钉死救世主耶稣的古代罗马犹太总督的名字,是一个男人的名字。第一代麦肯为女儿挑选名字时看中了“派拉特”英文字母的挺拔神气,“觉得像是一排小树中高贵、挺拔、有压倒一切气势的一株大树。”[3](22)莫里森为派拉特取这样一个名字实质上象征了女性主义者对传统的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挑战,她塑造的是一个和男人一样,有能力、有魄力改变自己世界的女性人物。
派拉特不拘小节,狂放不羁,洒脱爽朗。这是她很明显的一个男性特质。她天生狂野,成长中几乎没有受到传统女性角色的种种限制。在故乡老人的记忆中她是一个爱在林子里疯跑的漂亮的小丫头。可见小时候的派拉特就像个男孩般淘气,同时可知派拉特容貌出众。但是她并不像其他女人那样注重打扮修饰,在意自己的外貌。她不穿艳丽的服装,不带任何饰品,头发总是剪得短短的,像个男人一样。而且她不像露丝那样穿紧身胸衣,她在衣裙里一丝不挂。脚上爱穿双没系带的的男鞋。奶娃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劈开腿坐在门前台阶上,身穿长袖长裙的黑色衣裙。她的头发也用黑色的东西包着。”[3](39)她的坐姿和着装都表现出她不拘小节、随性的男性气质。
不仅如此,派拉特的行事作风也和男人一样。她从不淑女般微笑,总是爽朗地哈哈大笑。她也不像一般的女性那样爱落泪,反而像男人有泪不轻弹。小说中的派拉特只哭过一次。父亲遇害后,瑟丝给她端来樱桃酱当早点时因为无法无拘无束地生活,她曾放声大哭,自那以后到她六十八岁,她再也没哭过。她有着男人般的刚强。莫里森在强调派拉特与树的紧密联系时,特别选择了伟岸挺拔的松树来映衬她,而不是婀娜多姿的柳树或绚烂多彩的桃树。她完全不同于一般女性的软弱形象,她高大、强壮、坚强不屈。她和哥哥麦肯一样健壮有力,和他打架时并不示弱。在奶娃看来“她居然和他父亲一样高,头和肩都超过了他”。[3](41)而她保护女儿丽巴时的表现则凸显了她的男性特质。丽巴在被一个男人殴打时哭哭啼啼,不知所措,哈格尔看到后只知道无助地尖叫。通常,女性在这种情况下只会这样无助地哭喊或双腿瘫软。正在屋内看书的派拉特听闻这一消息时,却沉着冷静、泰然处之。从派拉特面对险境勇敢沉着的理性表現中可见其无所畏惧、坚决果敢的男性特质。此外,在小说结尾处,奶娃从南方回来去见派拉特时,失去哈格尔的派拉特一瓶子将他砸晕扔进地窖里。其表达内心情感的方式是典型的男人的做法,并不像一个年近七十的老妇人所能做出来的。
同时派拉特还具有男性独立、自信、叛逆的性格。她从不按照所谓的淑女的标准和愿望界定自我,不对任何男人惟命是从。当哥哥麦肯要将杀死的白人的金子据为己有时,她不仅反对,还与他大打出手,并用刀子对准他的头逼退他,并从此与他分道而行。她恪守自己的道德准则,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不为任何人的见解所左右,并且藐视所谓的餐桌礼仪和卫生习惯,蔑视世俗礼法。在她那个年代,女性应专注于家务,而她却跳脱出家庭生活的禁锢,不仅有自己独立的工作而且曾游历全国。她不是纯粹的家庭主妇,也不是卖笑为生的女人,她像男人一样有自己的职业,酿造和出售酒水,经济上独立。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莫里森塑造的众多女性人物中,派拉特是最具理想色彩的一个人物形象。该人物身上女性特质的博爱、包容、感性和男性特质的勇敢、独立、理性的共同作用使她成为一个具有和谐人格的人。通过派拉特,莫里森传达了她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深切关怀,现代人只有在自身特质上以开放的心态取长补短,追求和谐人格,才能更好地在这个多元文化背景的世界里生存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王伟.完美和谐人格的追求—对莫里森三部小说“双性同体”式的解读[D]. 兰州大学,2008.
[2]Plato.The Symposium [M]Trans.Benjamin Jowett.Forgotten Books, 2008.
[3]莫里森,托妮.所罗门之歌.胡允桓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4]Zhu,Rongjie. Pain and Healing: A Study of Maternal Love in Toni Morrisons Fiction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M].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04.
(作者介绍:吴金莲,内蒙古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