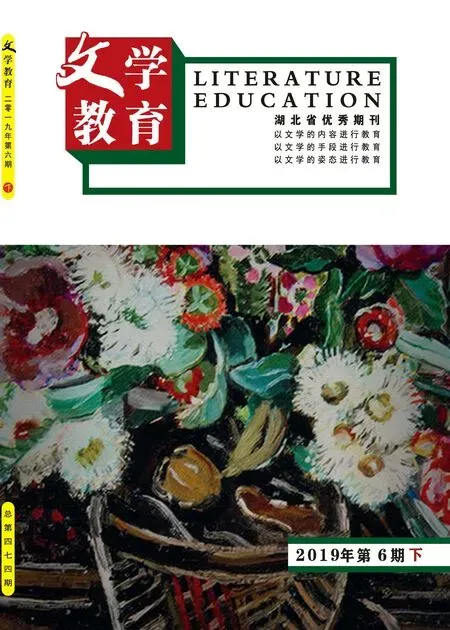《五卷书》框架结构在东西方民间文学中的发展
段孟洁
框架式结构,是一种文学叙事架构,多见于民间文学当中。其形成与口头文学息息相关,拥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框架式结构起源于印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古典梵语时期的《五卷书》,但这种结构并不是以《五卷书》为代表的印度民间文学所独创的,追根溯源还是要回到印度文学当中,从吠陀文学时期的四大吠陀以及其相关的吠陀文献,到史诗时期的印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诸多的文献中都包含有许多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童话和寓言。《五卷书》正是对这一讲故事的悠久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薛克翘,76)随着《五卷书》的对外译介传播,这种框架式结构对东西方民间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五卷书》的框架式结构及特点
《五卷书》的具体成书时间难考,按照金克木先生的说法,“现在印度有几种传本,最早的可能上溯到公元二、三世纪,最晚的梵语本是十二世纪编订的。”初始也是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在民间传播,后期逐渐形成了一些本子,西方学者根据文本的繁简不同,划分出“简明本”、“修饰本”和“扩大本”等。(季羡林,2)目前国内现有的《五卷书》译本是由季羡林先生根据“修饰本”从梵文译出的,下文皆依据这一版本展开论述。
《五卷书》共分五卷,因此称为《五卷书》。开头有一个序言部分,讲述了《五卷书》的缘起,也就是串起整本书的主干故事:印度的一个国王请婆罗门毗湿奴舍哩曼以故事的形式教导自己的三个儿子。所讲的这些故事构成了《五卷书》,在主干故事下,书中的每一卷都另有一个核心故事,比如说第一卷《朋友的决裂》的核心故事讲的就是豺狼离间了狮子和牛的友谊,导致了两个朋友的决裂。除这一核心故事外,第一卷书还通过核心故事中不同角色之口讲述了30个小故事,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五卷书》的这一结构特点可大致分为以下三层:
主干故事→核心故事→小故事
整体结构如同树状图,主干故事与核心故事相连,但发散出来的小故事与小故事之间未必有必然关联,因此季羡林先生以“大树干”、“粗枝”和“细枝条”的关系来形象地描绘这种框架式结构的特点。这种框架式叙事结构的特点在于其包容性强,可能性多,内容丰富。
二.《五卷书》的框架式结构对东方民间文学的影响
刘守华先生曾提到过,《五卷书》“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童话和寓言的发展,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这里的影响指的是故事内容情节相似,关于印度故事母题这一方面,国内外学者多有考证。在《五卷书》的世界流传方面,德国印度学家,流传学派的建立者本菲有着深入的研究。故事内容的借鉴与传承方面已有定论,那么在作品叙事结构方面《五卷书》又有怎样的影响,这是以下两节准备讨论的核心。《五卷书》在东方的影响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印度本土,二是西亚和中亚,三是中国。
首先说印度本土,与《五卷书》相关的故事文集有《佛本生经》、《益世嘉言集》、《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宝座故事三十二则》和《鹦鹉故事七十则》等,这些故事文集在故事内容和结构上都明显受到了《五卷书》的影响。其中《佛本生经》通过佛教的传播对中国文学也产生了极大影响,目前《佛本生经》和《五卷书》的成书先后仍没有定论,薛克翘先生认为“从时间的先后和故事的数量看,《五卷书》显然要比《本生经》晚出和逊色。”而赵国华先生则指出,《佛本生经》“是在佛灭后的华氏城(今巴特拿)结集时代,约公元前三世纪中叶,用接近梵文的巴利文编订成集的。”而正如前文提到的,《五卷书》的几个传本“最早的可能上溯到公元二、三世纪”(金克木,215)无论时间先后如何,两者在故事组织结构上有相通之处,即都有一个主线故事贯穿全文,将类型丰富的故事串联在一起。
次说西亚和中亚,在这一地区地区产生影响最大的故事文本是《卡里来和笛木乃》,这一文本的形成经历了由梵语到巴列维语,再从巴列维语转译至古叙利亚文,再到“公元七五○年,伊本·穆格法的《卡里来和笛木乃》阿拉伯语译本问世,后者主要依从巴列维文和古叙利亚文本《五卷书》。”(宗笑飞,76)但相较于《五卷书》的主干故事:婆罗门讲故事教育三个王子。《卡里来和笛木乃》的主干故事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扩充,但主干故事的核心仍是“某人讲故事”,即印度哲学家白德巴讲故事规劝专横跋扈的国王德卜舍利姆。受这些译自《五卷书》的故事集的影响,在西亚和中亚地区产生了《一千个故事》、《一百零一夜》和《一千零一夜》等。以《一千零一夜》的叙事模式为例,首先都有一个“某人讲故事”的主干故事,《一千零一夜》的主干故事是:萨桑王国暴虐成性,日杀一女,宰相女儿莎赫扎德为拯救无辜少女,主动入宫为国王讲故事。其次,故事内容十分丰富,包容万象,故事数量逐步增大,嵌套技术越发成熟。最后,故事集中都含有大量的“隐含作者”(徐娴,97),即叙事视角丰富多样。
最后是中国,印度故事传入中国,主要是经由佛教东传,但经刘守华先生的搜集与比较,发现《五卷经》中“情节结构相类似,可以初步断定源于印度的中国民间故事有二十三例”(刘守华,63)由此可见《五卷书》对中国民间文学的影响深远,但在叙事架构上是否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一点仍需要考证,季羡林先生在《五卷经》序言中提出,“《五卷书》的结构也与中国一些故事有关联,如隋唐间王度的《古镜记》就是采取了‘连串插入式’的写法。”所谓的“连串插入式”就是框架式结构的一种形象的说法。《古镜记》的叙事特点在于,文本从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王度如何获赠古镜之后,开始讲述古镜的流传和奇闻异事,在这一过程中,“王度的讲述是主线,主线中穿插其他人的讲述,其他人讲述中又穿插进一些人的讲述。”(刘俐俐,112)可见《古镜记》包含了众多联系不紧密的故事,但采用了以古镜为叙事核心,多视角叙述的方法组织作品叙事结构,与《五卷书》的结构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五卷书》的框架式结构对西方民间文学的影响
印度学者D.P.辛加尔曾在《印度与世界文明》一书中指出,印度的《五卷书》对西方寓言故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它无疑是以《卡里来和笛木乃》为媒介的。(转引自宗笑飞,77)另一种说法认为,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传入欧洲的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才是对西方民间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源头。无论是哪种说法,都可佐证《五卷书》外传对西方民间文学的影响。
首先,在内容上直接或间接受到《五卷书》影响的作品有伊索的《伊索寓言》、胡安·马努埃尔的《卢卡诺尔伯爵》、薄伽丘的《十日谈》、斯特拉帕罗拉的《滑稽之夜》、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和拉·封丹的《寓言》等等。其中,据学者考证,写于1335年的卡斯蒂利亚语小说《卢卡诺尔伯爵》“对《卡里来和笛木乃》的借鉴与模仿是十分明显的”(宗笑飞,81),当时《卡里来和笛木乃》的卡斯蒂利亚语译本(1251)已经问世了半个世纪,影响十分广泛。“《卢卡诺尔伯爵》是由谋士帕特罗尼奥讲述的五十一个故事。”可以看出,其主干故事也有“某人讲故事”这一核心,符合框架式结构特点,并且“至少有四个故事”移植自《卡里来和笛木乃》。(宗笑飞,77)
其后,将框架式结构进一步发展的是意大利文学巨匠薄伽丘的《十日谈》,这部作品比堂胡安·马努埃尔的《卢卡诺尔伯爵》晚十多年,包含一百个故事,这些故事串联在一个大的主干故事下,即十位青年男女在别墅躲避瘟疫时分别讲述的故事。但薄伽丘对框架式结构的开拓性发展是在故事叙述外又加上了一层结构,即薄伽丘自诩作为观察记录者对《十日谈》创作动机和经历的一些叙述,学者称之为“附表层结构”。(刘清玲,112)《十日谈》的叙事模式对十四世纪英国诗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产生了直接影响,这一部诗体短篇小说集讲的是来自不同阶级的朝圣者们在往返圣地途中应店主提议开始的讲故事比赛。
总之,框架式结构经历了一个东学西渐,逐步发展的过程,从吠陀时期到史诗时期的发展与积淀,到以《五卷书》为代表的印度民间文学采用框架式结构将形形色色的故事串联在一起,外传后经过改编和扩充,《卡里来和笛木乃》、《一千零一夜》等作品“整个主线故事由古朴简单变得丰腴饱满、扣人心弦”(穆宏燕,142),流传到西方后这种开放式的结构与西方“整饬分明”(林文琛,43)的文学特点相结合,叙事结构变得规整的同时仍然具有很大的开放性,框架式结构由东方发源,在西方得到了发展,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