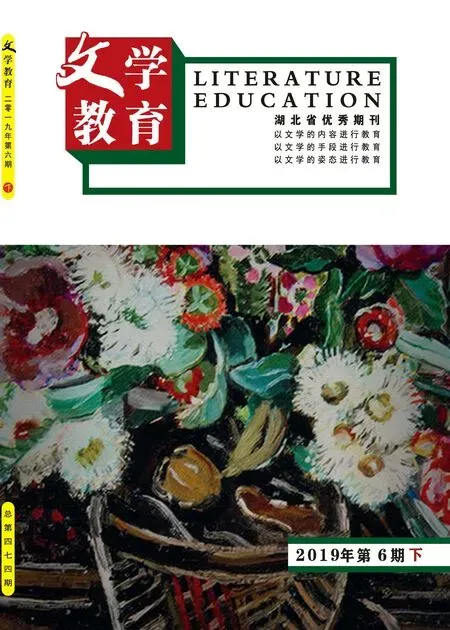关于《管锥编》论“绩师空织”的思考
黄婷婷
一.导论
《管锥编》[1]是钱锺书先生生前的一部古文笔记体的巨著。本书堪称“国学大典”,是钱锺书先生灌注大量心血而成的学术著作,书中对《周易》、《毛诗》、《太平广记》、《老子》等古代典籍进行了详尽而缜密的考证和诠释。《管锥编》最过人之处在于钱先生凭借自己学贯古今中外的丰富文化涵养,在书中旁征博引,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其中关于《太平广记》的论述二百一十三则,充分体现了《管锥编》的之一特点。
《管锥编》考证《天平广记》的第三十八则,是借由《太平广记》卷八十九中记载的《鸠摩罗什》篇发端,具体论述了“绩师空织”故事的演变流传以及“二西”的真正含义及误解情况,论述过程充分展现了钱先生对材料驾轻就熟的运用和善于举一反三的思维特点,值得学习和借鉴。
二.“绩师空织”故事的源头及演变
《太平广记》卷八十九《鸠摩罗什》一节记载了东晋高僧鸠摩罗什的生平事迹,主要的资料来源是梁代慧皎编写的《高僧传》一书,但是《太平广记》的编者只截取了鸠摩罗什来中国后的事迹,删去了来中国之前事。钱先生博览群书,《高僧传》自然也多有涉猎,他注意到《高僧传·鸠摩罗什》中被《广记》删去的部分记载了有关“绩师空织”的有趣故事,这是大师盘头达多与鸠摩罗什讨论大乘佛法与小乘佛法时讲述的故事,《高僧传》记载如下:
师谓什曰:“汝于大乘,见何异相,而欲尚之。”什曰:“大乘深净,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诸漏失。”师曰:“汝说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舍有法,而爱空乎?如昔狂人令绩师绩绵,极令细好。绩师加意,细若微尘。狂人犹恨其粗,绩师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细缕。’狂人曰:‘何以不见?’师曰:‘此缕极细,我工之良匠,犹且不见,况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绩师。师亦效焉,皆蒙上赏,而实无物。妆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连类而陈之,往复苦至。终一月余日,方乃信服。[2]
作为鸠摩罗什老师的盘头达多,对跟随自己学习毗昙学多年的学生如此热衷于宣弘大乘佛教之般若“空观”,颇多不解,于是讲了一个“绩师空织”的故事来告诫弟子也表达了对大乘佛法中“空观”的疑惑。钱先生不愧为学贯古今中外的大学者,他在看到这个小故事时自然联想到闻名世界的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篇,与“绩师空织”机杼酷肖。盘头达多讲述的“空织”故事,只是对民间故事转述,相比较而言安徒生童话是作家的文学创作,情节更加生动曲折,并且精心构思的结局耐人寻味,这一点是僧传描写所不具备的,钱先生在文中说道:“惟末谓皇帝脱故着新,招摇过市,一小儿呼曰:‘何一丝不挂!’转笔冷隽,释书所不办也。”可见给予了童话高度的评价。
关于《皇帝的新装》这篇童话的取材,一般都认为14世纪西班牙作家胡安·曼纽埃尔所搜集的民间童话故事《织布骗子和国王的故事》是其母本,慧皎《高僧传》是6世纪的作品,“绩师空织”也可视为这篇童话的古版源头。骗子和国王骗与被骗的寓言故事在世界上不同民族中都有流传,钱先生还在文中提到了“母猴之削”的故事,记载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燕王好微巧。卫人曰:“能以棘刺之端为母猴”。燕王说之,养之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试观客为棘刺之母猴。”客曰:“人主欲观之,必半岁不入宫,不饮酒食肉,雨霁日出,视之晏阴之间,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也。”燕王因养卫人,不能观其母猴。郑有台下之冶者谓燕王曰:“臣为削者也。诸微物必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于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锋,难以治棘刺之端。王试观客之削,能与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谓卫人曰:“客为棘刺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观见之。”客曰:“臣请之舍取之。”因逃。[3]
这个小故事虽然没有“空织”情节,但骗子编造维护骗局的手段与《皇帝的新衣》有异曲同工之妙,《韩非子》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因此这可以看做“空织”故事最古老的原型了。到了明代末期“临川四才子之一”的陈际泰在《已吾集》卷一《王子凉诗集序》中也讲述了黠者空织欺骗国王的故事:
余读西氏记,言遮须国王之织,类于母猴之削之见欺也。欲其布织轻细。等于朝之薄烟,乃悬上赏以走异国之工曰:“成即封以十五城市,不则齿剑,余无堕言。”盖杀人而积之阙下者累累矣。有黠者闭户经年,曰:“布以成。”捧于手以进。视之,等于空虚也。王大悦,辄赏之。因自逃也。[4]
从文中可见陈氏所言的故事是他从“西氏记”中读到然后转述的,故事中的的黠者,并不是骗子,而是一个智者,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借空织巧妙地欺骗了残暴的国王,这里的“黠者”与《高僧传》中的“绩师”一样,是出于自保才指空为实。但是相对于僧传故事的简洁,陈氏在文中加以渲染,表现了国王的凶残和黠者的智慧,因此更具有可读性。
由于人类历史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发展阶段,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会产生许多内容大同小异的文学作品。与《皇帝的新装》故事类型相似的民间故事在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也是普遍存在的,如美国的《两个老妇打赌》,印度的《上帝的织工》中也都写到了骗子用空织的布来欺骗别人的情节,钱先生在读《太平广记·鸠摩罗什》时想到被《广记》删去的《高僧传》中的有趣故事,然后将思绪打通古今中外,进而联想到安徒生童话与《韩非子》以及明代学者对这一类型故事的转述,充分体现了钱先生不仅博闻强识还能够在治学中举一反三,这种态度和能力让人钦佩。
三.“二西”的真正含义和误解情况
陈际泰《已吾集》卷一的《王子凉诗集序》中提到“西氏记”,但是作者并没有说明具体是哪本书,因此留下了疑问,钱先生推测“西氏记”可能就是指《鸠摩罗什传》,钱先生的推测的依据从何而来,这就涉及对“西氏”的理解问题。
钱先生在《谈艺录·序言》中说道:“凡所考论,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5]若不加思考可能会将“二西”理解为欧西新学,其实并非如此,“二西”指的是佛教和耶稣教,“二西”之书也即两教的教义经书。钱先生也担心读者理解错误,因此在序言中自注曰:“‘二西’名本《昭代丛书》甲集《西方要纪·小引》、《鲒埼亭诗集》卷八《二西诗》”。“二西”这一名称的由此而来。对这段注解笔者略作疏证,《西方要纪·小引》云:
西洋总名为欧罗巴,在中国最西,故谓之大西。以海而名,则又谓之大西洋……从极西到中国多浮海,二三年始至。过小西天竺国登岸。小西离大西六万余里……小西又须半载余,换舟行二三月,方抵中国。[6]明确提到大西指欧罗巴,小西是天竺国。清代大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二西诗》云[7]:
《乌斯藏》
三危旧是中原地,分比苗民尚有存。
其在五灯亦无赖,偏于诸部称独尊。
诲淫定足招天谴,阐化空教种祸根。
安得扫除群孽净,不教西士惑游魂。
《欧罗巴》
亚洲海外无稽语.奇技今为上国收。
别抱心情图狡逞,妄将教术酿横流。
天官浪诩庞熊历,地险深贻闽粤忧。
夙有哲人陈曲突,诸公幸早杜阴谋。
很显然,前一首诗所针对者主要乃佛教教义,后一首则是针对西方传教士传播的教义,认为传教士以舆图、历算为诱饵,实则隐藏了图谋不轨的别种“心情”,故其遗患更大,更应及早防备。这两书中“二西”的意思非常明确。钱先生在《管锥编》中继续考证,说道:“明季天主教人中国,诗文遂道‘二西’;如虞淳熙所著之《虞德园先生集》卷二四《答利西泰书》曰:‘幸毋以西人攻西人’,正谓耶稣之‘西’说与释迦之‘西’说相争也。”耶稣之“西”是欧洲,释迦之“西”是印度。印度文化通过佛教传人中国,欧洲文化则通过基督教传人中国。因此“二西之学”并非仅指欧西新学。
近世的学者对“二西”的含义多有不察,导致许多张冠李戴的错误理解,如魏源曾评价龚自珍云:“晚犹好西方之书,自谓选深微云。”[8]现代学者侯外庐在《中国思想通史》卷五评价龚自珍思想时根据魏源的说法,竟说:“可惜他研究‘西方之书’太晚,不见于言论,只有用‘公羊春秋’之家法了。”[9]显然这是把“西方之书”理解为欧美的哲学和社科。其实“西方之书”是指佛书。黄庭坚《山谷全集》卷十九《与潘邠老》曰:“西方之书论圣人之学,以为由初发心以至成道,唯一直心,无委曲相。”[10]其中“西方之书”是指佛经而言,即为明证。对此错误理解钱先生不无挪揄的说道:“直可追配王馀佑之言杜甫通拉丁文、廖平之言孔子通英文、法文也!”明末随着东西文明信息交流的增多,士大夫们在治学时多不免有穿凿想像之言论。如钱先生所说,清代学者王余祐在《五公山人集》卷七杂著《老瓦盆》一则说道:“西洋之俗,呼月为老瓦,杜诗:‘莫笑田家老瓦盆’然则此盆即月盆耶?如月琴、月台之类,取其形之似月耳。”[11]以西洋之俗揣摩杜诗,不免荒唐。
江庸《趋庭随笔》廖平言孔子通英文法文之说,见于是书卷一。原文作:“郭允叔云:‘闻蜀人董清峻曰:季平解《论语》‘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谓法兰西文比英文难学云云,真是儿戏矣。”[12]可见这样穿凿附会的荒唐之言不止一例。钱先生对近代学者误解“二西”之意以及迎合西方新学牵强附会的做法表达了不满,可见治学态度严谨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证明“二西”的真正含义,钱先生用最擅长的层层推进的论证方式,例举数例:
如钱谦益《有学集》卷八《金陵杂题绝句》之一五、卷一九《陆敕先诗稿序》又《题交芦言怨集》、卷二二《送方尔止序》皆用卖针儿至针师家故实,卷三八《复徐巨源书》标明来历曰:“西国有诮人说法者,曰:‘贩针儿过针师门卖针耶?’”此典出《杂阿含经》卷四一(一一四三)、《佛本行集经》卷一三《角术争婚品》下等,则所谓“西国”腾“诮”,正指佛书。陈际泰“读西氏纪”,亦类斯欤。
这段话涉及材料颇多,为更好理解,我们须做一些疏解。钱先生提及钱谦益《牧斋有学集》中有四处提到“卖针儿至针师家”的故实,足见读书治学钱先生始终能做到举一反三。古籍资料浩瀚庞杂,记忆难免出现疏漏,这四处材料中钱先生记错一例,《金陵杂题绝句》中涉及这一掌故的是第十四首,而非第十五首。
《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13]其十四
杜陵矜重数篇诗,《吾炙》新编不汝欺。
但恐旁人轻着眼,针师门有卖针儿。
诗的最后一句巧用“卖针儿过针师门卖针”这一典故。钱谦益在《陆敕先诗稿序》和《送方尔止序》中也涉及此典。在《复徐巨源书》中标明了典故来历,原文如下:
养由基之射穿杨叶,百步而射之,发无不中,楚人观之曰:“可教射也。”西国有诮人说法者曰:“贩针儿过针师门卖针耶?”以仆之固陋,苟不见弃于世之君子,见誉则为楚人之教射,见笑则为西人之贩针,亦安有以自效而已。[14]此典故其实来源于佛经,《杂阿含经》第一一四三经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尊者摩诃迦叶为诸比丘尼种种说法,示教、照喜。示教、照喜已,时偷罗难陀比丘尼不喜悦,说如是恶言:“云何阿梨摩诃迦叶,于阿梨阿难稗提诃牟尼前,为比丘尼说法?譬如贩针儿于针师家卖,阿梨摩诃迦叶亦复如是,于阿梨阿难稗提诃牟尼前,为诸比丘尼说法。”[15]
故事中用卖针儿在针师门前卖针作喻暗讽班门弄斧的行为,此外《佛本行集经》卷十三中记载了佛主释迦牟尼在未得道成佛前娶亲的故事。释迦牟尼为了娶“工巧铁师”之女,苦练作针技艺。后把制作的许多铁针,放在竹筒里,来到铁师门前叫卖。凭借出色的制针技艺打动铁师,迎娶到了心爱女子。佛经中的故事是此典的源出处,钱谦益在文集中多处使用此典故,也是深谙典故来源及含义,因此他说此典出自“西国诮人说法者”,即是指来源于佛书,由此可见陈际泰《已吾集》中所说“西氏记”也定当是指佛书无疑。钱先生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例举了大量事实证据,并且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论说,在论证过程中常常能够举一反三,勾连古今中外,对佛典经书烂熟于心,展现了涵养深厚、学识过人的大师风范,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因此研究与总结《管锥编》中文学陈案的梳理与思考,对于如今的文学研究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能够帮助我们养成一种严谨的、广博与精深相结合的学风。
——谈谈徐兆寿长篇小说《鸠摩罗什》
——戴维·戴姆罗什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