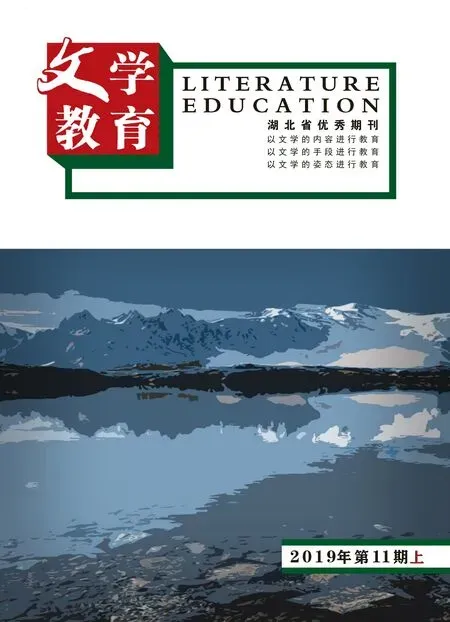《平原》中的“疼痛”写作
梁 恋
毕飞宇自称其创作是以“疼痛”为主题展开的,围绕伤害与疼痛展开的写作在他的小说中占据重要地位。他在《平原》中以王家庄之名,重建逝去的乡村社会图景,并深切地注视着身处其中痛苦挣扎的年轻人及其失落的人性,在对疼痛的写作中回顾与思考着一个时代的爱与怕、哀与乐。
一.几类疼痛的书写
毕飞宇在《平原》里书写了各式各样的疼痛,成长中的“犟”与忧,家庭成员间的隔阂,群体性的失落——各个环节难以纾解的疼痛汇聚在一起,最终形成了王家庄人的集体之痛。
首先是个人的成长之痛,《平原》中的众多青少年在无形的伤害与痛苦中成长。主人公端方幼时丧父,在舅舅家寄居,直到十四岁作为“油瓶”被母亲“拖”到王家庄,“端方”二字前面从未冠以任何姓氏,父母之爱的缺失是端方疼痛的根源。他经常在巷子来回狂奔,成长的焦虑、青春的孤独和莫名的恐慌时时围绕着端方,而他无法排解这些压抑的情绪。红旗的成长伴随着迷茫而不自知的痛苦在母亲孔素珍的眼里他“奴才相”十足,身上没有一根硬骨头,作为年龄最大的“小跟班”,红旗是一个盲从者,既没有自我意识,也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端方和红旗有着共通的成长状态,即对痛苦生活体验却无能为力。
其次是家庭的疏离之痛。端方的家“有相当复杂的错综”,“外面看,这个家是一个家,暗地里其实还是两个家”。他对家庭的渴望与可有可无的地位形成反差,而重组家庭又充满了“复杂的歧义”,端方是“两个家”中间的隔阂,他与继父王存粮的割麦心理战更集中地展现了家庭的疏离之痛。父子两人沟通不顺畅导致内心的防备与疏离,内心世界的封闭使得一家人不得不忍受彼此疏离的关系,端方感到“疼痛就是这个太阳的光芒,光芒四射,光芒万丈。”
最后是群体的失落之痛。王家庄的第一大群体由本地的闲散青年构成,他们大多失学在家,无所事事的围绕在佩全周围,在大街小巷漫无目的的四处游荡,凭个人好恶与人打架斗殴。这些本地青年欺软怕硬,没有立场。在王家庄,知青团体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大部分知青已经返城,留下来的只有吴蔓玲和混世魔王。与内化为本地人的吴蔓玲不同,混世魔王懒而蔫,无法回城的现实消解了他所有的青春与活力,知青团体的失落情绪由他一人品尝,其中的疼痛滋味可想而知。
毕飞宇在《平原》中从个人之痛出发,引出家庭之痛,继而延伸到群体之痛,随着情节的深入,情绪的转换以及节奏的加快,叙述的力量不断加强,从而使作品成为一部疼痛运作下的“不安之书”。
二.人物形象的动物化
毕飞宇曾说,小说要写的有生命力就需要表现世态人情,世态人情是小说的基础,更是技术,它是文学的拐杖。在《平原》中,毕飞宇借用各类家禽的内在特征,把人物的性格及其行为举止与动物对照起来,将人物形象动物化,展示王家庄日常生活中的世态人情。书中常用动物的特征、习性来描述几个主要人物的动作、神态或心理活动,其中最常出现的就是驴、狗、牛以及蛇、喜鹊、狐狸、乌龟等,下面以几个主要人物为例展开论述。
首先是端方,他的出场始终与牛联系在一起。开篇部分,端方利用忙假回乡割麦,这个“初生的牛犊”嘴泼牙壮、敦实稳健,仗着“一身的好肉和一身的好力气”,顶着毒辣的太阳在地里挥洒“豪情”,绝不惜力,他强烈的自尊心与好胜心在劳作中表露无疑。端方遇事沉默不语却固执己见,犟得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寡言少语、卖命劳作,端方的行为举止在众多与牛相关的描述中进一步凸显出来,他像牛一样任劳任怨、付出血汗,却一无所获,这样残酷的现实描写极具痛感体验。
其次是孔素贞和三丫,这对母女间的矛盾更多的集中在以狗自喻的观点上。孔素珍规劝女儿与端方断绝来往,三丫“心比天高”,却用狗作践自己以便迁怒母亲,两人以狗自比,互相败兴。如果此时的三丫表面上说着反话,内心对狗是极其排斥的,那么后来她绝食未果,被徐半仙说服吃下山芋饭时“酷似一条正在吃屎的狗”的比喻则与她的处境与情绪十分贴切了。三丫对以狗自喻这个看法从反抗到认同的态度即是她追爱不成、幻想破灭的受伤与疼痛心理的隐射。
再有就是混世魔王,这个南京青年在王家庄经历了小马驹、懒驴和缩头乌龟三个阶段的个性转变。混世魔王刚到王家庄的时候 活泼开朗,打篮球身手敏捷,他积极“表现”,“不怕牺牲”的卖命劳动。吴蔓玲看出他假借劳作换取返城机会的投机心态批评了他,同伴们陆续回城,“这匹活蹦乱跳的小马驹终于变成了一头最懒的驴”。在被嫉妒与懒惰打垮后,他连一头驴都比不上,“简直就是一只乌龟……缩头乌龟,说的就是他。”混世魔王心态转变的根源是他对回城的期盼与失望,这种疼痛书写展现了知青对愿望难以实现、自暴自弃的苦楚之态。这些动物化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疼痛的内涵及其深广度。
三.叙述中的宿命论意味
“**就是**”,这是《平原》中最常见的叙述方式。毕飞宇运用下定义的方法去展现王家庄约定俗成的“规则”,这些反复言说的话语带有极大的宿命论色彩。
首先是庄稼人的众多传统。庄稼人不断重复关于人、人的日子以及人的一辈子“就是这样”的论调,这主要体现在以“人哪”为主的王家庄老话里。“庄稼人就是这样”“劳作简直就是受刑”,庄稼人坦露出又喜又怕的复杂心态,这种怕深入骨髓,同时又无处躲藏,因为“路还远着呢,日子还长着呢”,并且“人哪,就是这样”,只能迎头而上。
其次是天时与人生的关系。庄稼人不误农时才会过日子,“庄稼人的日子都被‘天时’掐好了生辰八字,天时就是你的命,天时就是你的运。”“农时就是太阳和土地的关系”,“银河是庄稼人的时钟”报告一年的四季,“是一对巨大的指针”指出季节的转变。这些都是祖辈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是庄稼人自觉遵守的推不倒的真理,每个人都是“一口井,每一口都有自己的吊桶,上,或者下,深不见底。”
返乡的端方不理解王家庄约定俗成的老话,他对土地有一丝恐惧,还有恨。“泥土,说到底它就是泥土,没心没肺,把你的一生一世都摁在上头,直到你最后也变成了泥土”,“一辈子就这样了”的想法令他沮丧又绝望,心里一阵酸楚,“用不了几天,也这样了”的结论打击了他的干劲。端方的一生注定与土地难解难分,他被“**就是**”的论断牢牢压制,徒劳地挣扎,祖辈的老话在他身上显示出宿命论的意味,毕飞宇道出了书中人物残缺的人生及其悲剧性的命运走向。
毕飞宇的疼痛写作经由人的动物化,在推不倒的王家庄传统这里达到高潮。动物化的人物形象描述,运用“**就是**”的陈述句式说出王家庄的陈年旧习与农民的老传统,此类话语具有情感的认同及加固作用。庄稼人多次重复的老话像一把锤头,一下下打碎了端方微弱的幻想,把他牢牢地钉在地上,日复一日的劳作流汗,做无谓的挣扎;王家庄奉行多年的陈年旧习在“**就是**”的演绎中具有推不倒的顽固力量。理想与现实背道而驰,行动离预期相距甚远,年轻人无法冲破陈规、走向“美丽新世界”,于是三丫为爱而死,端方的军人梦破灭,吴蔓玲追爱不成,被狗咬疯,混世魔王靠卑劣的手段走出王家庄。《平原》的文学价值是在毕飞宇对人生的幻灭和生命的悲悯的建构中体现出来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年轻人连最基本、最日常的梦都做不了,这样的结局令人心力交瘁。
四.结语
《平原》中的疼痛来自于每一个受到伤害后被环境扭曲、异化的灵魂。端方、红旗、吴蔓玲和混世魔王,每个人都过得不如意,悲剧性的人生与逃不开的宿命感把大家牢牢地捆住,没有一个人能逃开,这是一个人、一群人、一代人的疼痛体验。毕飞宇认为这部作品“谦虚都很困难,我只能说无可挑剔。”[4]他自称“《平原》的写作是一个完美的旅行”,“我和《平原》一直手拉着手,我们来到了海边,她上船了,我却留在了岸上。”他关注“人为什么不如意”,王家庄是他拷问人性的场所,疼痛是他的叙述手段,在探索时代与人性的相互摧残与折磨的过程中,一个时代的爱与诚,怕与惧浮现出来,讲述着年轻人疼痛的灵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