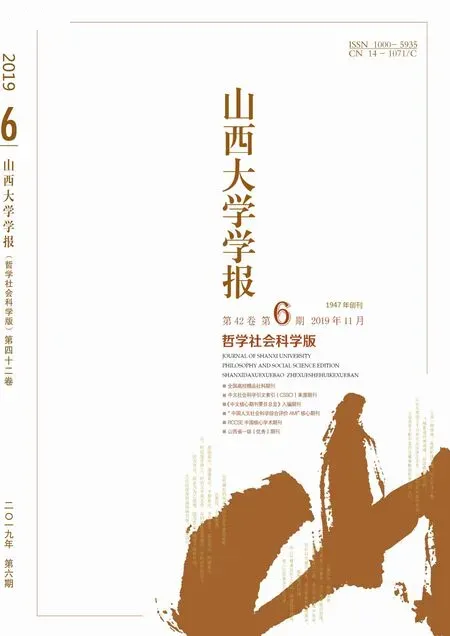中德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研究
杨有振,崔泽园,2
(1.山西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2.中共山西省委党校 山西行政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一 引言
2014年10月,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德国,双方在两国友好交流合作方面达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发表《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指出中德两国将执行尽责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加强国际金融的协调,为保持和促进全球经济和金融关系的稳定做出贡献,中德两国间的这次合作吸引了世界的目光。然而,中德两国在经济和金融发展方面展开合作的过程中,收入不平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一方面,根据北京大学2015年公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1)《中国民生发展报告》是基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撰写的系列报告,以全国25个省市160个区县的14960个家庭为基础样本,主要探讨民生问题的现状、差异以及形成原因和机制。来看,中国目前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日趋严重,中国财富排名在前1%的家庭所持有的财产规模占全国财产总量的三分之一,而财富排名在后25%的家庭所持有的财产规模仅占全国财产总量的1%,呈现出明显的分配不平等现象。另一方面,德国的大多数人认为他们的收入差距太大。德国经济研究所(DIW)公布的研究表明,德国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在1991至2014年间增加了12%,而收入的趋势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有所不同。中等收入家庭增加了8%以上,高收入家庭增加了26%,而低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减少(2)数据来源于http://intl.ce.cn/sjjj/qy/201702/14/t20170214_20181435.shtml。
对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探讨源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议(Bagehot,1873;Schumpeter,1911;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Shaw,1973),Kuznets率先提出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Kuznets效应”,国内外学者在此基础上开始逐渐关注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1-6]。20世纪90年代,随着对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关系探讨的逐渐深入,逐渐形成了三大理论观点:其一,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Rajand & Zigales,1998;Maurer N & Haber S,2007;Gimet & Lagoarde-Segot,2011;胡宗义等,2013;Dabla-Norris et al.,2015;Jakob de Haan & Jan-Egbert Sturm,2017)[7-12]。其二,金融发展可以减小收入不平等(Galore & Zeira,1993;Banerjee & Newman,1993;Beck et al.,2007;Kappel,2010;Hamori & Hashiguchi, 2012;Sehrawat & Giri,2016)[13-18]。其三,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非线性关系,具体包含“倒U型”关系(Greenwood & Jovanovic,1990;Aghion P & Bolton P,1997;胡宗义和刘亦文,2010;李志军和奚君羊,2012;Zhang Q & Chen R.,2015;Younsi M & Bechtini M,2018),以及门槛关系(Kim & Lin,2011;王书华和苏剑,2012;Law et al.2014)[19-27]。
可以看出既有文献并不否认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间的关系,并进行了相应的实证研究,那么中国和德国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间的关系如何?并且基于前文分析,为何具有相似金融发展分布的两个国家却在收入不平等方面呈现出迥异的特征?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结合1992-2015年的相关数据,对中德两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效应进行比较研究。本文可能的主要贡献有:第一,从比较的视角,对不同国家间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差距的效应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第二,在金融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比较分析中,通过对初始条件、传导中介的比较分析,探索影响中德金融发展收入效应差异的因素;第三,利用PLS-SEM(偏最小二乘法下的结构方程模型)对两个国家金融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路径进行分析。
二 理论假设
既有关于金融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研究为本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若要对中德两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则须进一步对二者影响机制的比较因素进行深入探索。
20世纪70年代中期,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全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存在着显著的差距。文献从多个方面对各国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进行探索。
一些文献认为,发展中国家初始条件的差异—工业基础的差异、技术引进的差异、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以及不同的初始资源禀赋、人力资源等等,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后续的经济增长会出现较大差异的重要原因。缅甸发展经济学家明特(Myint,H.)以及印度发展经济学家拉尔(Lal,D.K.)选取了全世界21个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对其经济发展过程进行了比较分析之后发现,选取的21个发展中国家制度组织与经济政策等初始条件的差异,是最后导致经济发展不同的原因,并提出了由初始条件、国民经济和发展成果为主体的模型,即明特-拉尔经济发展理论。

图1 明特—拉尔经济发展理论的逻辑框架
图1反映了明特—拉尔经济发展理论的传导机制,其中初始条件、制度组织和经济政策为该理论的解释变量,发展成果为被解释变量,国民经济为传导中介变量。在选取的21个发展中国家当中,经济发展成果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在三个解释变量当中,却出现了两项相似一项不同的情况。因此,明特和拉尔得出结论:一个解释变量的差异就会导致被解释变量出现变化,并通过大量的对比性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进一步说明了各个解释变量在传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明特—拉尔经济发展理论的“配对比较”思想为经济体之间的比较提供了新的思路,但依然存在着些许不足:首先,三个解释变量之间没有联系,仅仅是简单的并列关系,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其次,该理论没有说明初始条件对发展成果所起的作用是否是决定性的;最后,缺乏对中间过程的解释,即国民经济在整个传导过程中形成的特定经济机制。因此,如何处理初始条件在解释经济增长差异过程中效应的差异,以及对初始条件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解释是丰富明特—拉尔理论的重要方向。
为了弥补明特—拉尔经济发展理论的缺陷,日本经济学家石川滋(Ishikawa Shigeru,1963)[28]提出了更加详细具体的分析框架,即石川滋经济发展理论,与明特—拉尔理论框架不同,石川滋分析框架的侧重点在经济发展的中间传导机制上。石川滋假定各个国家的初始条件没有较大差别,主要的不同在于发展机制的不同,同样会造成发展过程和发展成果的不同。

图2 石川滋经济发展分析框架
图2反映了石川滋经济发展框架的传导机制,与明特—拉尔理论相类似,初始条件和发展成果分别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且试图利用发展中国家之间初始条件等差异来说明其经济发展成果间的差异。与此同时,两种理论之间也存在着一些不同:
首先,明特—拉尔经济发展理论将初始条件等解释变量直接与发展成果相联系,利用配对的方法来比较发展中国家的初始条件和经济发展成果。石川滋框架通过中间发展环节机制将初始条件和发展成果联系起来,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中间环节上。石川滋框架中的发展机制包含了制度组织以及生产力变化机制等丰富的内容,二者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制度组织还包含经济体制、市场组织、企业组织、政治组织以及行政组织等因素,生产力变化机制包含对外经济活动、生产力水平和结构、货币流量以及收入等因素。除此之外,发展机制还收到一国的政策策略以及内外政治势力的影响。
其次,相较于明特—拉尔理论,石川滋框架的初始条件所包含的内容要更加丰富,既包括一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经济和政治环境、制度组织及生产力的状态,又包含自然要素和生产要素禀赋间的差别。
最后,石川滋框架中的发展成果不仅局限于经济增速的提高,还包含了经济结构的进一步优化以及市场经济效率的提高,以及社会中存在的收入不平等现象等。
综上,既有文献在经济增长、收入分配成因及作用机制的比较证实了初始条件差异是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形成的重要原因,同时推理了初始条件相近的条件下,作用机制的差异如何导致经济增长、收入差距的形成。但文献研究与实证经验的不足主要体现在:
一是关于初始条件本身的刻画,文献在初始条件的界定上多从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本的角度探索初始禀赋差异对经济成长、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少将金融发展要素纳入初始条件进行分析。
二是关于初始条件作用经济增长、收入差距的机制文献仍存在较大争议,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差距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在引致长期差异中作用仍需进一步的实践证据。
因此,本文在明特—拉尔分析、石川滋分析的基础上,借鉴Levine(2005),在初始条件中引入金融发展要素,在控制其他初始禀赋的基础上,探索金融发展初始条件差异对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传导变量以及效应比较,并尝试从金融发展初始条件、作用机制和影响效应三个方面对中德两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进行比较分析。
结合明特—拉尔分析、石川滋分析,本文从两个角度构建理论分析框架:
一是对初始条件的修正及其比较分析,首先,在控制其他初始禀赋的基础上,本文将金融发展因素纳入初始条件的比较分析,因此,相较于之前的分析逻辑,本文将重点关注金融发展因素其中,Z为除金融发展因素之外的其他初始条件,X:为金融发展因素。

综合前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中德两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差异;
假设H2:造成差异的原因有两个。
H2-1:中德两国初始条件的差异;
H2-2:中德两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

图3 理论假设框架
图3为比较中德两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效应的理论框架图。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初始条件、作用机制和发展成果。初始条件包括金融发展、职业选择、人力资本投资和宏观经济绩效,即前文理论中出现的金融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作用机制描述了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其中金融发展是解释变量,收入不平等是被解释变量,职业选择、人力资本投资和宏观经济绩效为中介变量;在发展成果中,石川滋经济发展分析框架中的发展成果为单一变量,如经济增速的提高、经济结构的优化以及收入分配等,本文在石川滋模型的基础之上对发展结果予以改进,将单一变量变为多个变量间的关系。假设收入不平等为Y,金融发展为X,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其余解释变量为Z,则中国和德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影响可以分别表示为:
(式1)
其中,F表示中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G表示德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此,基于上述假设,发展成果可以表示为,即两个国家之间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同。在(式1)中,F、G实际上是对两国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差距作用机制的刻画,前文假设H2视之为引起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在后文中进行检验。相较于明特—拉尔、石川兹的分析,本文在作用机制的分析时强调人力资本以及宏观经济绩效对金融发展收入分配效应的影响分析,在初始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作用机制中介效应的差异更可能是引起金融发展收入分配效应差异的重要原因。变量X、Z则从初始条件的视角,考察初始条件差异对金融发展收入效应的影响。
箭头① 和② 分别表示造成中德两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影响存在差异的两个原因,即初始条件的差异和初始条件间作用机制的差异。接下来,利用不同的方法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
三 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变量定义
本文以1992—2015年中德两国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其中金融发展数据来源于金融结构与发展数据库(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Database,FSDD),收入不平等数据来源于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SWIID),其余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以及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PWT)。
(二)变量定义
1.收入不平等。收入不平等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借鉴陈华等(2017)的研究以及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用基尼系数(gini)作为收入不平等的替代变量。由于中国有关基尼系数的数据存在部分缺失,因此本文采用三项移动平均法对缺失值进行处理。
2.金融发展。金融发展是本文的解释变量,一般地,金融发展包含了一国金融要素的进展与改进,对金融发展的考核涉及机构、市场、工具、制度等各层面的分析,当前,关于金融发展的度量指标存在多个层面,一些指标(如金融机构的规模、数量)侧重于从机构视角进行衡量,一些指标侧重于从工具视角考察(如资本市场交易额等)。为充分反映金融发展的程度,借鉴Levine(2002)的研究,本文从银行、证券和保险市场三个方面定义金融发展。其中,选用存款货币银行资产占GDP的比重(bank)作为银行市场的替代变量,股票市场资本占GDP的比重(stock)作为证券市场的替代变量,寿险和非寿险保费占GDP的比重(insurance)作为保险市场的替代变量。三个变量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金融发展的程度进行衡量,同时,为避免可能出现的相关性问题,后文分别构建三个变量形成的分位数回归。
3.控制变量。为了更全面地考察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本文借鉴Ünal Seven & HakanYetkiner(2016)、Beck et al.(2000)、Barro(1991)、Dollar & Kraay(2004)以及Jeong & Townsend(2008)等学者的研究,对教育投资回报率(edu)、人均实际GDP(pergdp)、政府购买支出(gov)、通货膨胀率(inf)、贸易占GDP的比重(trade)以及失业率(unemployment)等变量加以控制。其中,教育投资回报率(edu)用于定义人力资本投资,人均实际GDP(pergdp)、政府购买支出(gov)和通货膨胀率(inf)用于解释宏观经济绩效,其中人均实际GDP(pergdp)表示经济增长,政府购买支出(gov)和通货膨胀率(inf)表示宏观经济稳定性,贸易占GDP的比重(trade)以及失业率(unemployment)分别用于解释开放程度及职业选择。

表1 变量定义表
注:估计中使用的所有变量均以省略百分号的百分数形式呈现
(三)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分位数回归模型以及偏最小二乘法下的结构方程模型对假设H1和假设H2进行检验。
为验证假设H1和假设H2中导致中德两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影响存在差异的第一个原因,即两国初始条件的差异,建立第一组模型:
yt=c+α1×xt+α2×zt+εt
yt=c+β1×xt+β2×et+θt
其中,yt表示中国和德国的基尼系数,c为常数项;xt表示金融发展,α1和β1分别为两国金融发展的系数,若系数为正,则说明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zt和et表示控制变量,α2和β2分别为两国控制变量的系数;εt和θt为随机扰动项。
为验证假设H1和假设H2中导致中德两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影响存在差异的第二个原因,即作用机制的差异,建立第二组模型。
四 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中国和德国的金融发展以及收入不平等变量存在一定差异。例如,中国存款货币银行资产占GDP的比重(bank)分布在76.8%至153.4%的区间范围内,而德国在96.6%至147.4%的区间内分布;中国的基尼系数(gini)的最小值为38.4%,最大值为51.6%,而德国的最小值为26.2%,最大值为29.1%。可以看出,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的增长速度要高于德国,但收入不平等程度较德国而言更加严重。
(二)相关性分析
为了检验控制变量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本文进一步分别对中德两国六个控制变量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中国和德国的部分控制变量之间相关系数较高,会导致模型在估计过程中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Ang & McKibbin,2007)[29]。为解决这一问题,尝试对中德两国的控制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
五 实证结果分析
如前文所述,本文选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和偏最小二乘法下的结构方程模型来对假设H1和假设H2进行检验。因此,后文将对这两种方法的结果进行分析。
(一)分位数回归模型
表3和表4表示中国和德国在五个分位数水平(10%、25%、50%、75%、90%)银行市场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结果。总体而言,中德两国银行市场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这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设H1。一方面,中国银行市场的系数值在所有分位数水平上均为正,即中国银行市场的发展会加剧收入不平等;中国银行市场的系数值在10%到50%的分位数水平上逐渐上升,在50%到90%的分位数水平上逐渐下降,这表明中国银行市场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促进作用会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然而,德国银行市场的系数在10%、25%、50%以及75%的分位数水平上为负,即总体而言,德国银行市场的发展可以减缓收入不平等。另一方面,中国银行市场系数在五个分位数水平上均显著,而德国银行市场系数的显著性在10%、25%和50%上较高,说明中国银行银行市场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加剧作用更为明显。
表5和表6表示中国和德国在五个分位数水平(10%、25%、50%、75%、90%)股票市场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结果。总体而言,中德两国股票市场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这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设H1。一方面,中国股票市场的系数

表3 中国银行市场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在各个分位数水平上均为正,即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另一方面,中国股票市场的系数在10%到75%的分位数水平上升,在75%到90%的分位数水平下降,表明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促进作用会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但是,德国股票市场的系数值在10%、50%和75%的分位数水平上为负,其余为正,呈现出波动的特征。

表5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6 德国股票市场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7和表8表示中国和德国在五个分位数水平(10%、25%、50%、75%、90%)保险市场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结果。总体而言,中德两国保险市场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这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设H1。首先,中国和德国保险市场的系数在个分位数水平上均为正,说明中国和德国保险市场的发展均会加剧收入不平等,但中国和德国各分位数水平上的系数值存在差异。一方面,中国保险市场在各分位数水平上系数值均大于德国,表明中国保险市场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作用要强于德国。另一方面,中国保险市场的系数值在10%到90%的分位数水平上逐级下降,表明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作用会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呈下降趋势;但德国保险市场的系数值在10%到50%的分位数水上升,50%到75%的分位数水平下降,75%到90%的分位数水平上升,表明德国保险市场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促进作用先增加,后减小,再增加。其次,总体而言,中国保险市场系数的显著性要高于德国,说明中国保险市场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促进作用较德国更为明显。

表7 中国保险市场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8 德国保险市场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二)偏最小二乘法下的结构方程模型回归(PLS-SEM)
前文利用分位数模型验证了假设H1,即中国和德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差异。然而,由于是将解释变量和主要控制变量直接与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且对控制变量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因此对于回归结果所呈现的差异性可以由初始条件的差异进行解释,即对假设H2中的第一个原因进行了验证,但由于未对中德两国主要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分别回归,故无法看出中德两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影响机制的差异性,想要进一步验证假设H2中的第二个原因,需要考察中德两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
表9和表10表示中国和德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作用机制的回归结果。总体而言,中国和德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结果再次验证了假设H1,并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2中的第二个原因,即中德两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作用机制的不同导致了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差异。
表9为中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作用机制的回归结果,为简化分析,仅列出估计结果中显著性最高路径结果。从表中结果可以看出,有两条路径显著性较高,即“bank->edu-> gini”和“insurance-> edu-> gini”。首先,对于方向而言,中国银行市场和保险市场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中介变量为“edu”,说明中国银行市场和保险市场会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其次,各路径系数符号相同,说明中国银行市场和保险市场会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不平等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该结果与之前分位数回归结果以及Galore & Zeira(1993)提出的结论一致,即金融发展对人力资本投资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收入不平等产生。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表10为德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作用机制的回归结果,为简化分析,仅列出估计结果中显著性最高路径结果。从表中结果可以看出,有三条路径显著性较高,即“bank-> inf-> gini”“stock-> inf-> gini”“insurance-> inf-> gini”。首先,对于方向而言,德国银行、股票和保险市场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中介变量为“inf”,说明德国金融发展会通过宏观经济稳定性影响收入不平等;其次,各路径系数值符号不同,说明德国银行、股票和保险市场通过宏观经济稳定性对收入不平等产生负向的减小作用,最终表明德国金融发展会通过宏观经济绩效对收入不平等产生作用。此外,德国保险市场的结果与之前分位数回归结果存在一定偏差。从表中结果来看,路径“insurance-> gini”的系数为正(0.458)并且在1%的水平显著,因此这种差异可以解释为保险市场通过宏观经济稳定性以外的其他因素对收入不平等产生正向影响。

表10 德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机制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六 主要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首先通过分析中德两国1992-2015年金融发展与收入不平等变动趋势后提出问题,即什么原因导致了拥有相似金融发展模式的两个国家在收入不平等方面会存在较大差异;其次,根据这一问题提出两个假设,即假设H1:中德两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差异,假设H2: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有两个,两国初始条件的差异以及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作用机制的差异;再次,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和偏最小二乘法下的结构方程模型对两个假设予以验证;最后,得出如下结论。
中德两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差异,即对假设H1进行了验证。具体而言,首先,关于银行市场,中国银行市场的发展会加剧收入不平等,并且这一作用会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相比之下,德国银行市场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具有减小作用。其次,关于股票市场,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先上升后下降;然而,德国股票市场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关于保险市场,一方面,中国和德国保险市场的发展均会对收入不平等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但中国的这一作用较德国而言更加显著和强烈;另一方面,随着收入不平等现象的不断加剧,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促进作用呈下降趋势,但德国保险市场的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促进作用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
上述结论在验证了假设H1的同时,对假设H2中第一个原因也进行了验证,即中德两国初始条件的差异导致了其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存在差异。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H2中的第二个原因,本文利用偏最小二乘法下的结构方程模型对初始条件间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即中德两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作用机制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导致中德两国金融发展对收入不平等影响存在差异的第二个原因,即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1的同时也验证了假设H2中的第二个原因。具体而言,中国银行、股票和保险市场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中介变量是教育投资回报,即中国的内在影响机制为金融发展通过影响教育投资回报进而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相比之下,德国银行、股票和保险市场发展影响收入不平等的中介变量是通货膨胀,即德国的内在影响机制为金融发展通过影响宏观经济稳定性进而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影响。
(二)政策建议
首先,中国的银行业应将发展重点从数量转向质量。德国分工明确、体系完善的全能型银行制度使得德意志、德累斯顿等银行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较德国而言,中国的工、农、中、建四家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虽然在国际排名较为靠前,但评级与国际化程度较低。因此,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方向不能局限于规模和数量,要将战略重点转向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能型商业银行。
其次,中国应进一步完善证券市场监管体系。德国以联邦金融管理局(BAFIN)、联邦州财政部门监管机构(BAB)以及法兰克福交易所(FFM)为主体的三级监管机构对德国证券业进行保驾护航。中国证券业的监管体系以中国证监会统一监管为主,证券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为辅,相比于德国而言,中国还需进一步健全并完善证券行业监管体系,尽可能避免由证券市场引起的金融风险,从而进一步增加直接融资的占比。
再次,进一步发挥保险业的“保险”功能,增加保险的普及率。德国的保险市场凭借其丰富的险种以及雄厚的再保险实力在整个欧洲保险市场中占据这重要地位。相比与德国,中国的保险业起步较晚,在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方面均与德国有着较大差距,人们对于保险的观念也较为落后,限制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因此,中国保险业应充分发挥保险业的“保险”功能,丰富险种,培育适合每一类人的保险产品,逐步扭转保险业在人们心目中的观念,增加保险的普及率。
最后,注重教育的公平性。中国从基础教育阶段便已显露出一定的欠公平性,居高不下的学区房价、私立学校学费和补课费,无疑催生了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出现。因此,中国应进一步注重教育的公平性,对教育资源进行合理配置,逐渐缩小城乡家庭间教育资源的差距,最终达到减小收入不平等的目的。
——写在中德建交45 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