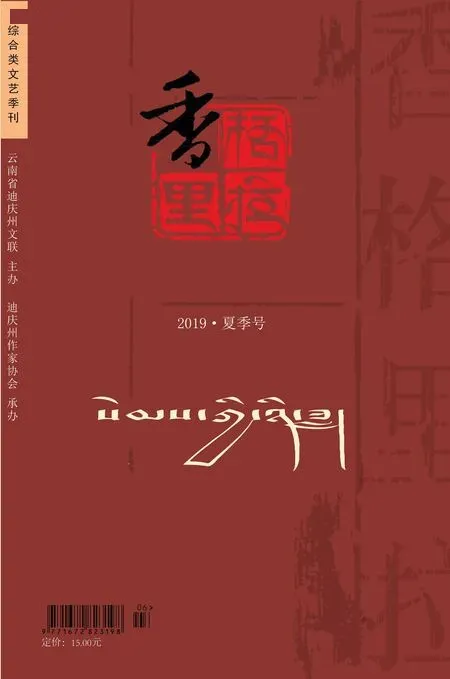薄雾沉沉迷梦中
——此称作品集《没时间谈论太阳》中小说的特质
◇隋军 魏春春
薄雾沉沉迷梦中,藏族作家此称的作品集《没时间谈论太阳》中的小说特点或许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描述。“薄雾沉沉”是指此称这部作品集中的小说似乎都笼罩在一片淡淡的雾霭中——朦胧之中充满着阴郁。“迷”指的是此称小说中由阴郁朦胧特质、神秘气息以及叙事障碍与圈套等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扑朔迷离的效果。“梦”则是指该作品集的部分小说会出现梦境或者类似于梦境的情景,在这类作品中扑朔迷离的效果表现得最为突出——不仅读者,甚至连小说中的人物也陷入迷离之中,颇有“庄周晓梦迷蝴蝶”的韵味。
一、此称小说阴郁朦胧基调的产生
阴郁、朦胧是《没时间谈论太阳》收录的小说最为突出的特点。全部十四篇小说,或多或少都带有这一特征。造成这一特点的原因有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则是每篇小说在开篇便奠定了作品整体氛围——即阴郁朦胧的基调。但是开篇奠定基调(而且是相似的基调)这一方式的反复使用并没有使得这些作品显得单调乏味,因为在每一篇小说中,此称奠定作品基调的具体手段都是不同的,总体而言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通过对环境或者物品的刻画来奠定作品阴郁、朦胧的基调,这其中又有三种不同的情况。有的是通过单纯对物的刻画来塑造小说的这种氛围,《薄暮之雪》便是采取的这种手段。该小说开篇刻画的对象是一张残破的黑白照片,这使得小说染上了一种历史的沧桑感。照片中奶奶遗容的模糊和“我”对奶奶记忆的模糊是小说描写内容的模糊,但这一细节却好似给小说画面撒上了一层薄雾,使小说一开始便陷入略显阴暗的朦胧中。除了单纯刻画物品,单纯描写环境也是这类方式中比较单一的方法,《我们夜晚站到楼顶眺望》采用的便是这种方法。这篇小说开篇描写的是一场骤然遮蔽了晴空的急雨,这场雨湮灭了蝉鸣,浇湿了A大妈。画面由明到暗、由极其嘈杂到极静的突转,A大妈的浑身不适与自责,使得此处氛围也变得阴沉。以上两篇小说属于这类开篇方式中运用单一方法的类型,而这类方式的最后一种开篇手段则是兼用这两种手法。《老牧人曲甲》开篇既描写了梨树笼罩房子、炊烟被穿过梨树枝叶缝隙的夕阳粉碎的景象,又刻画了白色梨花被熏黑的状貌、炊烟虚幻的状貌和花、光、炊烟难分彼此的状貌,朦胧的景色和物品交织一处,共同使得小说此处情景变得虚幻。《剃度》则首先刻画了医院的宏伟,接着便用周围民房“低矮又拥挤,像是被成片砍伐的林地”的状貌进行对比,从而使画面显得压抑、灰暗;进而再用烟霾笼罩医院的方式对医院大楼进行虚化处理,让医院的宏伟变得不真实,让画面整体也变得朦胧。小说的氛围由此立马坠入阴郁、朦胧之中。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发现,运用第一类方式的小说几乎都对所描写的景与物进行了朦胧化或者幽暗化的处理,但其中使用的具体策略又各不相同。即便是同样运用烟尘对景物进行虚化的《老牧人曲甲》和《剃度》,表现出的具体操作手段依旧大相径庭——前者是将烟尘与其他景物揉捏在一起使景象变得朦胧,后者则是单纯用烟尘笼罩医院大楼来取得虚幻的效果。这种同而不同的写作,一方面使得作者的不同作品因为在景物色调上的联系而变得整体化一,另一方面也使得此称的小说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不至于陷入单调乏味的囹圄。
第二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行为来奠定作品阴郁、朦胧的基调,《奔跑的羊群》、《流亡者》、《没时间谈论太阳》和《拯救》这四篇小说便是采用了这种方式。《奔跑的羊群》开篇描写的是次仁扛着死羊走山路回家这一事件,以及该事件中次仁放下羊,扛起羊,梦呓般哼唱山歌,“对着空旷的山野喊叫几声”等行为。放下羊、哼唱山歌如梦呓或许是为了说明次仁极度疲劳的状态,但这却在客观上表现出次仁身体状态的糟糕与精神状态的恍惚与混沌。而次仁扛起羊后喊叫的行为,则是次仁克服对豺狼恐惧的方式。遇上豺狼对次仁来说意味着死亡,他扛着的这只羊又是被狼杀害的,于是笼罩次仁的巨大的死亡阴影便由此在开篇铺展开来,并与次仁的恍惚一起形成一种阴郁迷蒙的氛围。虽然同样与死亡有关,但《流亡者》的叙述者却在一开始就主动直言“桑珠死了!”然后直接展开对桑珠葬礼的描写。葬礼本身便已使小说变得有些压抑,而葬礼上桑珠弟弟女儿的忍俊不禁、“平日里人模狗样的大人们”的痛哭和上师对桑珠尸体的温和叮嘱的对比更使得这份压抑变得阴冷、尖锐、纠结起来,并进一步成为了筑成整篇小说的基调。除了死亡,身体残缺同样能带来强烈的恐惧,《没时间谈论太阳》的阴郁基调的奠定便是由罗布被“少了一条腿”的发现惊醒这一事件完成的。而罗布半睡半醒的迷糊与被鸡叫醒的烦躁则给这份阴郁撒上了一丝迷蒙的烟尘。在这种情景与氛围中展开的小说便也难免受其影响染上了阴郁迷蒙的色彩。《拯救》中阴郁色彩的来源更多的则是旺杰的一系列动作——捡地上的烟头吸,翻看仍在地上的报纸,丢下报纸,继续喝酒。这些行为都是在忧愁、伤痛与迷茫中做出的,阴郁的氛围便在这串动作中得以产生。总体而言,这类方式奠定作品阴郁朦胧基调的途径:一是事件和人物行为本身带有的灰暗色彩,二是冲突。但是前三篇作品中的冲突类型又是不同的。《奔跑的羊群》依靠的是人物内心恐惧与压制恐惧的冲突。《流亡者》依靠的是不同人物行为对比的冲突。《没时间谈论太阳》依靠的则是外部环境的召唤与罗布不想起床的心理之间的冲突。这同样是一种同而不同的写作,同样对淡化小说的单调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
第三类方式是通过人物简要的自白来渲染出阴郁、朦胧的氛围。其中比较特别的是《寂静的仓子桥》,因为这篇小说开篇的人物自白是一首诗。诗中“终于”表现出让手机欠费的艰难与如释重负,“挖掘机的掌心”则是现代机械生活的阴影,其中充满着深深的痛苦、恐惧与忧虑。“割舍了自己”是“恋人”的自我抛弃,表现出了真爱中人的决绝和当下恋爱的残酷。“竟”则渗透着一种震惊、悲戚与绝望,从侧面表现出“我”人性的丧失。“行将就木的尸体”便是“我”直言自己已经全无人性,麻木、空虚、迷茫。这段诗的自白在对现代社会和生活在其中的“我”进行强烈控诉的同时,也以表现出的各种现象、情绪和状态给小说蒙上了阴郁、迷蒙的色彩。像这样用诗来进行氛围的塑造是比较华丽的写法,而更多的时候,此称笔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在篇首只用一两句简单朴素的话便将阴郁朦胧的氛围渲染开来。其中表现得最直白的是《闯进来的究竟是谁》。该小说在开头对“激动又紧张”“忐忑不已”的自我状态进行直接表述,个人情绪先入为主,小说以迷乱为主的基调由此直接奠定。而《黑池》凭借的却是语言背后隐藏的景象——即“即使天黑了,我也能看见一切”背后还隐藏的黑夜中的视觉景象——惨淡的色彩和朦胧的画面。《牧羊人季志》的氛围的营造在更大程度上则是依靠开头两句话中的“也许”一词。因为“也许”当中充满着不确定性,其背后潜藏着“我”对可能无法继续放羊的恐惧。不过由于这份阴影潜藏得比较深,所以这句话奠定的基调相对而言可能比较隐晦。以上就是对第三类小说开头方式的分析,显而易见,他们最终都是通过在自白中使用能够传达某些情绪或者蕴含些感觉的词汇来实现对基调的奠定的。但是,这些词语能够完成使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些小说全都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因为这种叙事能够给接受者带来强烈的代入感,从而能够使接受者在最大程度上体验词语中蕴含的情绪和情景。
最后一类方式则是同时运用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来制造隐喻朦胧的氛围。《糖果盒子》的开头刻画的是“我们”筛细粒土的场景。筛土的行为通常伴随着飞扬的尘土,这便使得小说展现的景象蒙上了一层尘埃。筛土造房的行为背后展现的是布满土坯房的村落,略显荒凉。曲品的闲散与对“我们”的怒斥则让小说的氛围显得有些压抑。其中展现的曲品苦寒、脏乱的形象——手背布满冻伤的裂痕,鼻梁下挂着清涕——使得小说的阴郁色彩愈发浓重。之后紧跟的一片破败脏乱的景象——枯黄的叶子,逼仄的沟口,深不见底的沟渠,湍急的水流,水中的苹果和枯叶,碎了一地的苹果,满地的苹果汁,黏糊糊的脚底,腻人的果香——则进一步加重了小说的阴郁色彩。相较于《糖果盒子》开篇的大篇幅的描写,《走在黎明和雪夜里的人》的开头要简短许多。冻结的水,破棚中悲戚吠叫的狗,木棚中叫声古怪的公鸡——寒冬的凌晨死气沉沉,故事的环境充满阴冷。拉初行走在这样的黑暗中,她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这无疑显露出深深的无助和迷茫。这种寂静阴冷和迷茫正是这篇小说的基调所在。
二、此称小说阴郁、朦胧基调的贯彻与确认
基调是能够影响整篇小说的东西,而这些小说的开头所营造的氛围之所以都能笼罩整篇小说,跟读者阅读时的心理体验以及小说内容对这种氛围的贯彻是密不可分的。
小说开头对于读者心理体验的影响首先依赖于读者已有的审美经验(既包括对文字的理解能力和对文字所表现的情景的感知)。前文分析的小说开头营造氛围的方式,在根本上便是通过读者对语言的认知和想象来使读者直接唤醒阴郁、朦胧等感知觉和心理体验,或者通过读者在脑海中构建出小说语言描述的情景来间接引起读者相关感知觉和心理体验。这些由读者在接触作品的第一时间便产生的感觉和心理体验并不会马上消失,它们反而往往会转化到读者的期待视野中,伴随读者完成整个阅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期待视野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读者的阅读。这便是使小说开头营造的氛围成为小说基调的心理原因。
相对于读者心理体验对小说基调奠定起的作用,小说文本自身对基调的贯彻似乎更加重要。在阅读伊始产生的心理体验在阅读的过程中可能会消失或淡化,这时候便需要不断有色调相同的刺激来保证这种心理体验的延续,这便有赖于小说文本对基调的贯彻与确认。在贯彻小说基调的过程中,此称同样运用了很多方式。其中连续性最强的是环境的延续。这种方式使得整篇小说笼罩在统一的色调、氛围中,从而使得小说开头营造的氛围成为整篇小说的基调。如《我们夜晚站到楼顶眺望》的环境,在开端转入暴雨中后便始终笼罩在这团阴雨之中,整篇小说也被暴雨带来的阴沉氛围淹没。《走在黎明和雪夜里的人》的故事环境则几乎一直都置于寒冬凌晨的黑暗中,但与《我们夜晚站到楼顶眺望》相比,这份黑暗并非是连续的,而是断裂的——因为时间和空间的跳跃——拉初从梦中世界到醒后世界。虽然从动作上来看从睡梦到惊醒是连续的,但梦中的世界和醒来的世界是两个,两个世界的时间也不同步——梦境已经从凌晨五点过了一段时间,但醒后世界却刚到凌晨五点。这份从黑暗到黑暗的跳跃虽然使得黑暗产生断层,但却并没有影响黑暗对几乎整篇小说的覆盖,所以也就没有影响到小说基调的确认。
相对于延续外部环境,在贯彻小说基调时,连续性稍弱一些的是色调相同或相似的词汇的使用,但却也基本是贯穿全文的。如在《寂静的仓子桥》中,失神、脏乱、猥琐、枯瘦、烦躁、痉挛、麻木、昏暗、虚无、零碎、渗得发白等同样带有阴郁朦胧(甚至狞恶)色彩的字眼贯穿始终。这些灰暗的词汇所带来的心理体验使得小说从头到尾笼罩在了开篇造就的阴霾之下,开篇的氛围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整篇小说的基调。再如《我们夜晚站到楼顶眺望》,贯穿小说始终的也是挣扎、不适、刺鼻、阴冷、不耐烦、哀伤、窒息、揪心这类色调灰暗、压抑的词汇。这种延续小说氛围的方式与部分小说开头营造氛围的方式是一致的,所以也可以将其看成是对小说氛围的不断塑造。小说开头营造的氛围便在这种反复的塑造中得以延续甚至强化,进而成为全文基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营造氛围的这些词语以动词和形容词为主,它们修饰的大多是人、物、情、景,所以这种手段的使用跟人物形象和情景事物的经营通常是形影相随的。《寂静的仓子桥》中的“失神”是用来形容哈巴狗的眼神,“脏乱”是用来形容哈巴狗的外貌,“猥琐”则用于评价哈巴狗的行为,“枯瘦”是用来形容商店主阿婆的外貌,“烦躁”是对“我”的心理状态的直接表达,“昏暗”则是对环境的刻画……伴随带有特定色调和情绪的词汇的修饰下,小说中的人、物、情、景很明显因此具备了相同的色彩,小说开头营造的氛围由此同样得到延续,所以小说主体部分对人、物、情、景的刻画也就成为了确认小说基调的重要因素。而且上述词语营造氛围的方式本来就是靠修饰、表现人物情景来完成的。以这种方式来贯彻基调的小说,少了同色调词汇和人物情景的任何一种,其小说基调都是很难得到确认的。
经营的人物情景是有意刻画的,但还有一些事物场景本身便带有强烈的阴郁色彩,并没有经过刻画,而是直接作为意象来对小说基调进行贯彻的。《黑池》中的“黑池”是贯穿该小说的一个意象,它是“我”的恐惧之源,象征着“我”内心深处的大恐怖,也是一直笼罩“我”的巨大阴影。该意象的反复出现,时刻渲染着幽暗恐怖的氛围,于是小说开端的阴郁朦胧基调便由此得以贯穿整篇小说。无独有偶,《剃度》中的“烟(香烟)”也是贯穿小说全文的一个意象。烟是一种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品,也是一种能够让人上瘾的物品。而抽烟的原因大抵不外乎为了缓解忧愁和疲劳、帮助思考等。由烟燃烧制造出的烟雾又会带来呛人的异味和烟雾缭绕的朦胧景象。由于烟的这些特征,“烟”这个意象便暗示了病躯、难以遏制的欲望、忧愁矛盾、疲乏、身体不适、朦胧等一系列阴郁或者朦胧的生理和心理体验。于是这一意象的反复出现则不断刺激着读者的感觉和心理,使得读者不断地感受到小说中阴郁和朦胧的气息,从而实现对开头基调的贯彻。除了“烟”,《剃度》中还有“监狱”这一意象。“监狱”给人的印象同样是昏暗的,而且其中还昭示着犯罪、凶恶、绝望等阴暗的事物与情绪。伴随着“烟”和“医生”在监狱中的出现,小说阴郁、朦胧的氛围在此处被集合的意象渲染得极为强烈。由此可见,意象对于小说基调的贯彻甚至加深具有非常突出的作用。
与意象的使用相类似的手法还具有神秘性质事件的使用。《老牧人曲甲》中分担曲甲劫难的放生羊——“曲甲次里”死亡这一事件,暗示着曲甲将来的死亡。笼罩在曲甲头上的死亡阴影延续着小说开端制造的阴暗色彩,成为确认该小说基调的一个要素。《我们夜晚站到楼顶眺望》中的“蛇吞兔”事件也是这样一种具有神秘性质的事件。在小说中人物的认知中,路上碰见“蛇吞兔”是一种不祥的预兆。而在小说结束前,人物儿媳也始终都被这团阴影笼罩,以至于整个人陷入焦虑之中,坐立不安。这种紧张的情绪在儿媳妇反复念叨“蛇吞兔”之中蔓延开来且愈发强烈,由此也使得小说的阴郁氛围愈加浓厚,从而也实现了对小说阴郁、朦胧基调的落实。
除了具有神秘意味的事件,一般的事件和故事对于小说氛围的延续有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同样是在《我们夜晚站到楼顶眺望》中,点缀在小说中的儿媳妇与A大妈争吵这类事件的发生构成了小说中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对于加剧小说氛围的阴郁与压抑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薄暮之雪》中,爷爷回光返照这一事件则始终笼罩着整篇小说,它时不时地通过爷爷、父母等人的行为表现出来——爷爷的咳嗽、易困乏等身体状态,父母对爷爷的特别关照,医生的叮嘱等——皆使得小说处在死亡的阴影和紧张之中。此外,与之并行的还有买电视时间,“我和哥哥”对电视的期待,这一事件与爷爷讲故事在爷爷时日无多的情况中构成一对激烈的矛盾,小说中的阴影和紧张氛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由此也进一步增强了小说基调的存在感。在此称笔下,像这样借由事件烘托氛围的作品还有很多,但《流亡者》这篇小说却在其中显示出不同的特质——小说主体只有“桑珠娶亲”这一事件。事件当中人物关系异常紧张,矛盾冲突十分激烈。整篇小说的阴郁氛围便总体上由这一事件中紧张关系和矛盾冲突进行建造和延续。此外,《没时间谈论太阳》对小说阴郁基调的接续则是通过罗布讲的一则砍柴伤腿的故事。因为这则故事讲于他们即将砍柴的时候,情景的相似性便使得这则故事具备了一定的暗示作用,暗示之中也使得小说开头的阴冷、惊惧与迷糊得以唤醒和接续。与《没时间谈论太阳》不同,《薄暮之雪》在涉及到故事时更大程度上的是通过讲故事的行为而不是故事本身来营造阴郁、朦胧的氛围。除了上文所述的讲故事与看电视的冲突,在讲故事过程中爷爷和“我们”的困乏、爷爷的停顿和父母打断爷爷的讲述带来的叙事中断,都有唤起读者心理不适的可能,从而造成小说阴郁朦胧氛围的加重。
讲故事是人物的行为,而人物的言行正是这些小说实现基调确认的又一重要方式。在此称的作品中,这种方式表现的最突出的是《剃度》,“他”抽烟、犹豫、寻找借口以及自责等行为的反复,表现出了人物内心的挣扎、煎熬、无奈等情绪。作为小说叙述的核心,他的这种纠结、复杂的行为难免会对给小说本身侵染上阴郁、迷乱的色彩。这与小说开篇营造的氛围无疑也是一脉相承的。
以上阐述的各种方法基本都是从细部上确认小说基调的,还有一类从宏观上贯彻小说基调的方式在此称的小说中多有运用——即小说的结构布局。这类方式共包括以下三种具体方法。第一种是比较简单的双线索交织对比的手法,《薄暮之雪》便是使用的这种方法,具体分析参见上文,不再赘述。第二种是反差的方法,《牧羊人季志》便是用的这种方法。在小说正文中,作者所写的内容几乎没有忧郁、朦胧的氛围。然而在小说结束处,作者突然点出这是一场梦,而梦的结尾是“羊都被狼吃了”和狼要同化季志们的宣告——这打破了季志要做一生牧羊人的梦想,原本已经淡化到几乎消失的阴郁氛围骤然被唤醒,并以呼应开头的方式笼罩了整篇小说。小说开头奠定的基调以跨度极大的方式得以落实,同时给读者造成极大的心理冲击,留下深刻的印象和思虑。《糖果盒子》也是用的这种方法,不过这其中却包含着两层反差。小说开端写的建村子一事,在完成筛土和规划之后,作者才讲明这只是过家家的游戏,而在小说结尾处事情再次发生突转——过家家背后的“现实”原来也只是一场梦。两层反差使得小说扑朔迷离,读者很难肯定最终梦醒后的“现实”是不是真实。读者由此陷入叙事迷宫中,小说由此变得愈发朦胧。而结尾处梦的惊醒和“我”的风烛残年也再次为小说覆盖上一层阴影,使得小说更显阴郁。第三种方式是对时空的破坏,运用这种方法的小说在这部作品集中共有五篇。其中《走在黎明和雪夜里的人》又同样结合了叙事迷宫的方式进行叙述。小说共有两重世界,一重是梦境,一重是“现实”。梦境开始的时间是凌晨五点,在梦境进行了很久,拉初却没有感觉到寒冷时,拉初才发现自己正在梦境中。之后拉初醒来,依旧是凌晨五点,故事时间发生了重置,小说的时空也由此发生断裂并进入平行状态。最终平行时空的终点依旧是如梦般的没有知觉,于是拉初再次准备用石头砸自己进行验证,小说在此处也戛然而止。这时小说又形成了一种叙事圈套,其结果是读者甚至拉初自己无法判定最终拉初是否仍在梦境中。这便使得小说带上了“庄周晓梦迷蝴蝶”的韵味,于是小说的画面因为结局的扑朔迷离变得更加朦胧起来。另外四篇小说同时具备的是意识流的特征。《老牧人曲甲》的时空在故事现实、回忆与梦境之间不断跳跃,造成了小说叙事时空的碎片化。这种大幅度跳跃的叙事方式使得小说内容显得不是那么明晰,而恐怖之梦的反复出现又使得小说始终笼罩在一团阴云中。朦胧与阴郁的氛围在这些方面便再度得到回应,小说的基调也进一步得到了确认。《黑池》依靠的则是一个鬼魂的回忆与飘忽。小说的时空在回忆之间以及回忆与现实之间不断跳跃,而现实中的鬼魂“我”又在不同空间中穿梭。小说的时空支离破碎,画面也变得模糊。而四十八天前、三年前时空的反复出现又表现出了“我”强烈的执念、遗憾与痛苦,这便又是阴郁的表现。在《拯救》中,小说时空如回忆一般在现在、六年前、十年前的时空里跳跃,这其中还伴随着在大军和旺杰二人所处的不同时空的跳跃。时空跳跃的最终指向便是小说开头的报纸内容。报纸内故事的原委得以明晰,但情节内容本身却因为人物的处境和遭遇始终处在一种压抑、幽暗的氛围中。《闯进来的究竟是谁》的时空跳跃则发生在狭小的空间范围内——“我”的家中。从“我”服侍亲朋到进入梦境再到回到现实,时间一直在流动,但是空间却是毫不相干的同一空间——现实空间的家和不同时间的梦境中的家。现实中对家中压抑的服从与梦境中对家的逃离在断裂的时空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现实更加阴郁。而“我”回到现实后的迷茫与思忖也使得小说尤其是梦中的身影变得更加朦胧起来。
以上就是对此称小说基调确认原因的分析。不难发现,在每一篇小说中,此称都使用了两种以上方法来保持小说开头营造的氛围。而且这些方法往往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共同使得小说几乎一直处于同一、甚至更加强烈的氛围之中。
三、此称小说特质的个人原因与作者的提升空间
此称的这十四篇小说全部笼罩在阴郁、朦胧的氛围中绝不是偶然的,这背后潜藏着一些深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或许可以从他的小说作品当中找到蛛丝马迹。
在其作品当中,表现的最直接的是对现代文明的忧虑、恐惧与抗拒以及对于未知未来的迷茫,这些作品占据了这十四篇小说的绝大部分。在《牧羊人季志》中,季志对“狼”有着深深的恐惧。这里的“狼”明显象征着现代社会中的人,因为他们只吃羊不放牧,而且势在同化季志这些人。这预示着现代文明终将进入季志他们的生活,喜欢放羊的季志难免对此有着恐惧。《寂静的仓子桥》中,挖掘机的“手”笼罩着城市,笼罩着生活。世界的一切都被破去“练习铁的语言”,变得机械化。“我”便是其中变得机械、空洞、无情的人——“我”写出的东西近乎是机械地复制别人讲的故事,“我”只把别人作为自己写作来料的来源而不是人。现代社会将人异化成了他物,这无疑也是非常恐怖的情景。《拯救》经由大军、旺杰困顿的生活,报纸讲述的大军获得三百万后的做派和贪官污吏的落网的消息,对金钱对人的戕害进行揭示。《老牧人曲甲》中的曲甲对拆迁的抵制,曲甲对手机的疏离,都是因为曲甲享受传统的农牧生活,对不能进行农牧作业的现代社会充满着抗拒。《奔跑的羊群》中的次仁同样是以对拆迁的抵制来抗拒现代文明的。然而不同的是,这篇小说还采用了“羊”的视角来表现现代社会对生命的驯服——“铁盒子”(车)便是现代社会的象征。被驯服的生命对自己的未来只有迷茫,只能等待驯化者的审判。这背后散发出一股深深的恐惧与忧虑。而《流亡者》中桑珠对于自由恋爱的争取和对媒妁婚姻的反抗也表达着他对于现代文明或者说金钱文明的反叛。因为其父母制定的媒妁婚姻是建立在追求物质和权力的基础上的,这并不符合桑珠对爱情的向往。但是抗争的结局却充满了悲惨,虽然这可能只是意外造成的结果,但这股冥冥中的命运,无疑与“现实”的社会一同成为了笼罩世人的恐怖暗影。《黑池》中现实压垮了爱情,压迫着“我”的身心,最终使“我”变成了鬼,这是一种莫大的恐怖。《剃度》中医院的富丽堂皇与民居的低矮破败形成的强烈对比,表现了居民生活的窘迫和居民总体身体健康状况的低下。“他”为了金钱抗拒放牧后的堕落与悲惨,“他”入狱和老板的逍遥,全都揭示着金钱社会戕害、蚕食底层人的恐怖之处。而“他”妈妈对卖羊的拒绝和“他”对剃度的渴望无疑又全部是对于现代社会的抗拒。《闯进来的究竟是谁》则凭借现实中“我”的劳累、虚与委蛇与身不由己来表现“我”的无奈和压抑,梦中“我”逃离家的景象则是“我”内心深处对当下生活的抗拒。逃亡的愿望和逃不离的现实构成一对张力,在二者的矛盾冲突中,现代社会对人规训的恐怖得以昭示。
事出必有因,此称恐惧和抗拒现代文明的原因在小说中也多有揭示。其中最表层的原因是对旧有生活的留恋。《糖果盒子》中的“糖果盒子”便是“我”的童年的美好回忆。当一双黑手将要夺走它时,“我”便从这梦境中惊醒。《老牧人曲甲》和《奔跑的羊群》中的牧人们抗拒搬迁也多是源自对农牧生活的依恋,但这其中还有对农牧的信任以及对金钱的怀疑。在他们眼中,金钱都是废纸,因为金钱并不能像农牧生活一般,给他们的生活提供稳定的物质保障,所以只有大山里的农牧生活才能让他们有安全感。用《老牧人曲甲》中的原话来讲便是“只有山才是可靠的……大山永远会给我们安全感……到了江边……那时如果手头突然没了钱……该有多么无奈啊。”然而,金钱带来的危机并不只有这些,更加严重的是对人的操控。《剃度》中的“他”便是被金钱操控的人偶——为了金钱卖了家里的羊,铤而走险贩弄一些违禁物品,在这过程中“他”对自己厌恶的烟产生了依赖。这都是在金钱的摆弄下,人丧失自我的结果。《寂静的仓子桥》中的“我”更是几近丧失了人性,被机械同化,冷酷无情。因为金钱,人与人之间矛盾激烈,就如《流亡者》中的人们,家人之间甚至都因此相对抗。更何况《牧羊人季志》中的“狼”对羊的无情吞没更揭示了“狼”出于利益对人死活的不顾。金钱造就的恐怖景象不得不让人对钱产生怀疑,也让人不得不对金钱操控下的社会产生怀疑。
然而,阴郁与朦胧并不仅仅是因为对现代社会的恐惧和对未来的迷茫,还有着对逝去事物的遗憾与哀伤。就像《薄暮之雪》中“爷爷”的回光返照似乎也是为了与电视的到来进行接力,但“爷爷”还没把故事讲完就突然去世了,故事的结局“我们”也永远无法再知道,“爷爷”所能讲的所有故事,也随着爷爷的逝去而消散于世。
此外,《没时间谈论太阳》表达的是对于现代社会精英人事的嘲讽,这突出地表现在罗布二人对新闻的态度上。他们回家喝酒时,开电视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有个响声,他们说的话也与电视新闻上播报的内容毫不相干。因为播报的那些经济数字和所谓的世界大事,并不能给他们提供生存基础——只有通过他们的劳动获得的实物才是他们生活依靠。每天忙于劳动的他们根本无心理会那些跟他们毫不相干的事情,更论谈论太阳了。除了暴露、抗拒、嘲讽这些尖锐的问题,还有作品表现了传统藏族农牧民家庭生活的温情。《我们夜晚站到楼顶眺望》便是唯一一篇表现这种温情的作品。虽然该小说依旧被阴影笼罩,但是这份阴影与家庭中的人物矛盾更多的是为了衬托人物间的相互关怀。比如“蛇吞兔”事件的阴影,便是为了表现儿媳妇对婆婆的担心。即便在日常生活中婆媳二人经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或者一些误会激烈争吵,但这却丝毫没有影响她们相互之间的关怀。这些情景不过是生活的常态。然而这种常态,某些时候也恰恰是值得书写的东西,因为这中本真的生活更容易打动人心。这种小说的创作,或许可以成为此称的创作方向之一,这对于丰富此称笔下的文学世界也无疑是有益的。在此基础上,此称或许还可以在小说中尝试发现现代社会中依旧存在的温情,或者进一步探索农牧民之间那种质朴的温情在现代社会中得以实现的可能。
还值得注意的是,金钱、机械等事物虽然是种种苦难的诱因,但说到底它们只是人类制造的工具。它们并没有价值判断,也并不能主动做什么事情。所有不良后果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所以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批判的同时,作者或许还可以继续往下追索,探讨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人的问题,或者更进一步地深度挖掘在人的背后可能潜藏的问题。
在创作技巧方面,此称在《牧羊人季志》中使用的反差方式或许还可以进一步深化,即尝试在小说基调建立之后突然打破基调,从而造成更加强烈的反差效果,甚至以此来突出更加尖锐的问题和某些情感。这种对于小说技法的探索是必要的,但在探索过程中也需要保持对技巧的警惕,以免像《寂静的仓子桥》中的“我”那样,被机械的东西同化而失去创作的活力。这其中的平衡则需要作者自己去谨慎把握。
总体而言,此称的小说还在起步阶段,虽然已经表现出了诸如思索的深刻、叙事技巧的丰富等许多难能可贵的品质,但是仍然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随着他创作的继续,其创作水平未尝不能提升到一个很高水准。在未来,他的小说未尝没有成为国内外优秀作品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