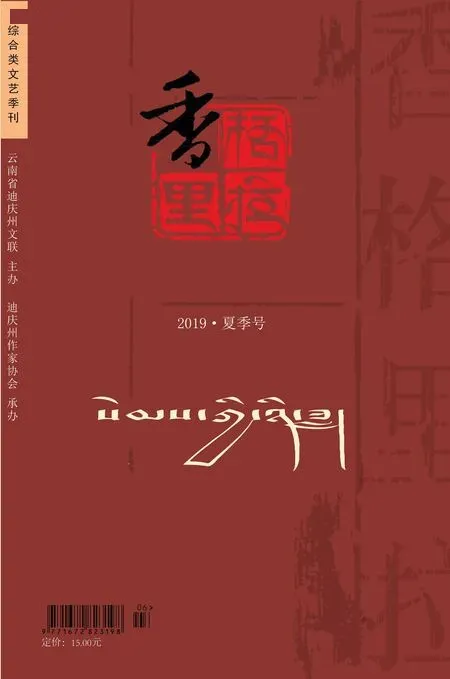高原神曲(组章)
◇李智红(彝族)
大高原的酒
大高原的酒有胆么?
大高原的酒有魂么?
有,那雄心勃发的大高原,就是酒的胆;那剽悍如山豹,桀骜如苍鹰的高原汉子,就是酒的魂……
大高原的酒,用苦荞煮,用苞谷烧,用青稞酿,用高粱熬……
大高原的酒,是用蛮荒的传说发酵过的野性狂飙;大高原的酒,是用刚烈的血气勾兑过的隐隐雷霆。
大高原的酒,是液体的火,是流质的钢,是十万大山反复提炼过的豪迈,是千岁峡谷经久陶冶过的粗犷。
大高原的酒,坚硬、放纵、炽烈得无所顾忌。
大高原的酒,敦厚、结实、清纯,挥洒着浩然之气,充盈着刚正不阿……
没有被这无声地沸腾着的高原酒灌溉过喉咙的男人,算不上是真正的好汉。
没有用高原酒浸泡过生命,浸泡过爱情,淬火过人生与灵魂的高原人,绝不是个纯粹的高原人。
没有让这剑刃般锋利的汁液,把岩石般强劲的身板,酥软成一滩烂泥的人,就算不上是真正喝过酒;没有在山寨那百年不熄的老火塘边,就着呼啸的山风,就着沉沉的夜色,就着原始的野性,端着粗陶海碗一醉方休的人,就不算是真正喝过酒;没有在冷冷的西北风中,哼着古老的民谣,怀抱着被旧时光摩挲得紫红铮亮的酒葫芦开怀畅饮的人,就不算是真正喝过酒……
大高原的人喝酒,或举杯豪饮,一如汹涌的江流鼓荡起湍急的漩涡;或浅斟细酌,一如清澈的山泉,一个优美的跌落;或觥觞壮举,且饮且歌,一任淋漓的肝胆,去激荡起酒碗中那一串串无声的惊雷。
大高原的人喝酒,讲究气度,不是粗暴的宣泄,不是虚伪的酬酢。
仿佛高亢的铜号震撼着,仿佛灼灼的爝火炽燃着。大高原酒所独具的那种惊心动魄的力量,被打高原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挥洒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
仗一身酒胆,高原人才敢把巍峨苍茫的群山峻岭踩踏在脚下。
凭一身酒力,高原人才能够坦然地面对陡峭的人生。
大高原的酒,是孤独的高原人永远值得信赖的朋友。
大高原的酒,是高原人的第二个太阳!
雪域的太阳
铜汁淋漓的光焰,在千年的坚冰上燃烧,在玉质的灰烬般的白雪上燃烧,在雄峻的山峰、在辽阔的草甸上燃烧……
在狂飙般的马群飞扬的鬃毛上燃烧。
在云朵般的羊群浑圆的脊背上燃烧。
在黑矿石般的牦牛群高挑的犄角上燃烧……
炽烈、瑰丽、坚韧、持久……
像一面黄金的旗帜,卡瓦博格是它高耸入云的旗杆。
像一支亘古不熄的,喷薄着圣火的火炬,唐古拉山脉是它坚不可摧的根基。
这,就是雪域的太阳。
在中国西部,在滇西这块圣洁的高原雪域,它像红宝石一样晶莹,像牛粪火般炽热的藏民心中那盏天国的酥油灯般灿烂。
这雪域高原的阳光,是纯粹的青稞酒熏陶过的,是圣洁的雪莲芬芳过的,是浑厚的法号嘹亮过的,是飘扬的经幡烘托过的……
这阳光,是浓得化不开的酥油,是老妇人的转经筒上那一道道闪烁的信仰。
雪域高原的太阳,宁静、吉祥。普照着一切平和且蓬勃自由的生命。
普照着生与死的轮回之路。普照着朝觐者遥遥的西征。普照着残桓断壁的遗址上那星散的野花,斑驳的苔痕。
雪域高原的太阳,中国西部一座长明的灯盏。
高原之鹰
寒铁样的大鸟,雷霆般的猛禽……
当一只鹰从彩云之南那一大片高插云天的山峰,抑或那一条条深不可测的峡谷,猎猎起飞,高原的天空,便显现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空旷和高远。
鹰凌空飞翔的时候,整个大高原那一大片黑压压的群山,便全都挺举起了冷峻的头颅。
鹰,这冷冽的黑色闪电,这飞翔这的血性寒铁……
当它矫健而刚毅的翅膀,奋力地拍打着西部的天空中那些白如静玉,轻若丝绸的云朵,所有高原人的胸膛里,也会随之呼呼生风。
在中国西部,只有鹰才能够最先窥视到我们的生命中,那些最软弱的部分。
在中国西部,鹰是一种境界,一种信念,一种灵魂的符号,一种生命的激昂……
因为鹰的飞腾,西部高原才始终保持了一种苍茫的辽阔。
因为鹰的俯冲,西部大峡谷才永远沉浸于一种深邃的神秘。
鹰,永远飞翔在我们高原人恒久而挚着的仰望里,甚至飞翔得比我们的仰望更远更高。
水深,再深也深不过鹰的胸襟。
山高,再高也高不过鹰的翅膀。
鹰的降落与飞翔,同样让我们心旷神怡,荡气回肠。
在中国西部,我永远也难以逼近一只真正的鹰。对于真正的鹰,我们只能够永远满怀着敬重的心情,远远地把它凝视。
在我们的想象疑惑比我们的想象更为广阔更为深远的地方,鹰飞翔着,像一只锋芒毕露的箭,像一把百折不挠的弓。
当然,高原的鹰也有静若止水的时候。当鹰把尖锐的铁爪,紧扣在一座冷硬的岩石疑惑一棵千年古树苍老的枝干上,进入一种平和的睡眠,大地充满了宁静,夜百合沐浴着澄明的露水,悄然盛开……
在鹰栖落的地方,每一块石头,都布满了杀气,每一株草木,都满怀着警觉……
在中国西部,关于鹰的传说,比满天的星汉还要灿烂。
在中国西部,关于鹰的神话,比浩荡的江河还要冗长。
鹰,以最敏捷的速度,撞击着西部的天空,从不优柔寡断。
鹰,以最锐利的风骨,切入我们的生命,不需要任何缘由。
鹰,使西部的峡谷,更坚定了它的深邃与沉默。
鹰,使西部的天空,时刻充盈着一种生命的勃起与亢奋。
鹰,是高原人世代传袭的生命图腾。鹰,是西部人血性的标记,操守的象征。
高原人都是鹰的传人!
民歌里的云南
在云南高原,一年四季,总有民歌如风中散落的草籽,自由自在地在阳光下,在雨水中,抽芽,开花,并随意地芬芳着每一个寻常的日子。
更多的时侯,民歌蓬勃如一棵枝繁叶茂的桂子树,浓浓的树荫下,纯朴的爱情,凡俗的乡村夜话,常常席地而坐,相得益彰。
彤红的篝火,总会在一些值得记忆的夜晚,愉快而热烈地燃烧,我那些朴实厚道的民族兄弟,一边喝着自酿的烈酒,一边跳着板扎的舞步,粗糙的面庞,被民歌优美的旋律,舔吻得表情丰富,仪态万方。
云南高原的女人,都善于用眼睛说话,用民歌表述喜怒哀乐。她们用民歌医治痛苦,她们用民歌寻找爱情。当浪漫的诗人,循着一个美丽的传说,自陌生的远方,蹒跚而来,她们便会用一束又一束情愫浓得化不开的民歌,充盈诗人干瘪的行囊。她们与生俱来的聪慧与贤淑,足够让诗人,感叹一生,回味一生。
在云南高原,民歌无处不在,并且生生不息。每一个寨子,每一条峡谷,每一道山梁,每一块坝子,都有民歌在飞红流翠,都有民歌在五彩缤纷。
只要山鹰能够歇脚的地方,只要白云能够驻足的谷地,都有民歌在滋长,平常如小麦或者包谷,又贵重似钻石或者黄金。多少浪迹天涯的旅人,总能凭着民歌的指引,轻松地找寻到回家的小路。
在云南高原,民歌,就像是一脉营养丰富的奶水,滋养着一方水土,一方文化,一方风俗,一方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