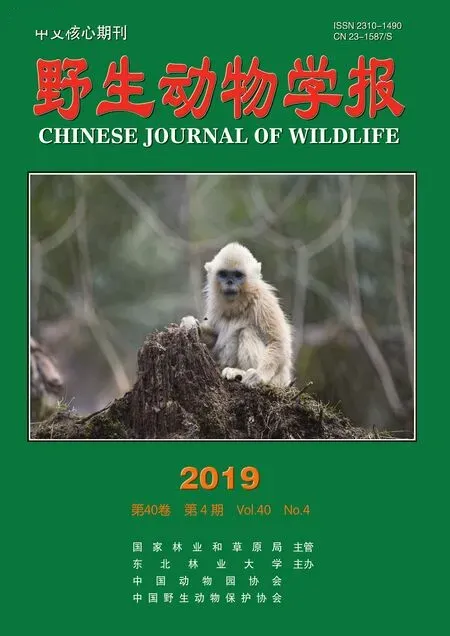广州地区蚁类对外来物种红耳龟人工巢的捕食作用
葛 研 魏玉峰 段好冉 龚世平
(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究所,广东省动物保护与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广东省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公共实验室,广州,510260)
巢捕食(nest predation)是指卵或未离巢的幼体被其他动物捕食的现象,是造成爬行类(Reptilia)、鸟类(Aves)等动物繁殖失败和早期死亡的重要因素之一[1-2]。龟类属于卵生爬行类动物,且无护巢行为,巢中的卵或幼体易被蚁类等其他动物捕食,影响繁殖成效[3-4]。对于外来入侵龟类而言,入侵地捕食者(天敌)对其繁殖巢的捕食作用有助于抵御和控制外来龟类入侵。红耳龟(Trachemysscriptaelegans)是全球100种最具威胁的入侵物种之一[5],该种原产美国和墨西哥,已被引入到欧洲、非洲、亚洲,以及美洲原产地以外的其他地区[6],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成功入侵[7-8]。目前,红耳龟已在中国野外环境普遍存在[9],并被发现可在华南地区野外环境中成功繁殖[10-12],该种不仅与中国本土物种争夺生存资源[13],而且还携带高致病性的沙门氏菌(Salmonella),威胁人类健康[14-15]。在红耳龟原产地,一些爬行类、兽类(Mammalia)、鸟类等动物为其天敌[16-17],其巢中的卵或幼体经常被臭鼬(Mephitismephitis)、浣熊(Procyonlotor)及蚁类等天敌捕食[18]。在中国广东和海南地区的研究发现,红耳龟巢经常被小型兽类、蛇类和蚁类等动物捕食,其中蚁类对红耳龟巢的捕食率达20%—66.7%[10-12,19],这表明蚁类在抵御红耳龟入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选择红耳龟潜在生态危害较严重的广州地区,开展了蚁类对红耳龟人工巢捕食作用研究,以期为红耳龟入侵风险评估以及有关生物防控技术研发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样区环境概况
基于前期对红耳龟在广州地区的分布调查,选择3个不同环境类型的野外研究样区(图1),包括黄婆洞水库(113°18′E,23°11′N)、小坑水库(113°28′E,23°36′N)和民政林场(113°28′E,23°40′N)。黄婆洞水库位于广州白云山风景区,水库周边的植被以次生植被为主,辅以人工植被,该区域游客活动较多,存在红耳龟放生活动。小坑水库位于广州从化区的农业区,周边为果园和人工经济林,水库中有渔业养殖生产活动,也存在红耳龟放生活动。民政林场属于天然林保护区,山溪周边的次生林植被较完整,人为干扰较小,该区域暂未发现红耳龟放生活动。选择以上3种不同的环境类型作为研究地点,有助于了解不同环境中蚁类种类的差异及其对红耳龟巢捕食的作用,探讨不同环境类型中蚁类抵御红耳龟入侵作用的大小。

图1 野外研究样区的地理位置示意图Fig.1 Distribution of the three field study sites(black dots)in Guangzhou,China
2 材料与方法
2.1 研究材料
于2017年7月从广东佛山市龟类养殖场购买红耳龟受精卵,卵均产自7 d之内。运输过程中将卵平放埋入铺有潮湿蛭石(蛭石与水的比例为1∶1)的塑料箱内,蛭石层厚度约8 cm,龟卵放置于蛭石层的中部,以减少运输过程对卵的不良影响。
2.2 研究方法
2.2.1 红耳龟人工巢的营造
龟类巢捕食研究通常分为对野外自然巢的研究和对人工巢的研究。由于许多龟类野外巢非常隐蔽,发现难度极大,而人工巢操作简便、可控性强,因而广泛用于龟类巢捕食研究[2,20-21]。本研究采用红耳龟人工巢来研究蚁类对巢捕食的作用。2017年7月中旬,在3个研究样区分别设置20个红耳龟人工巢,相邻巢的距离大于10 m。根据红耳龟巢址环境选择特点[11-12],在距水源5—10 m,植被盖度较大(70%—90%)的位置选择巢址。根据红耳龟巢的结构特点[10,12],挖15—20 cm深,直径10—15 cm的人工巢,每巢放置6枚受精卵,用挖出的松软土壤回填覆盖龟卵。为了防止孵出的幼龟逃逸到野外,同时也能方便观察蚁类对龟卵及新孵出幼龟的捕食情况,本研究采用了两种防逃措施。在黄婆洞水库采用细软塑料网袋防逃法,将龟卵装入细软的塑料网袋内,然后将网袋埋入巢内;在小坑水库和民政林场,采用硬质塑料网覆盖防逃法,将塑料网(规格:0.5 m × 0.5 m,网孔呈菱形,孔径0.8 cm)覆盖在巢上方,网的四周边缘10 cm宽范围用泥土覆盖。
2.2.2 龟巢观察与幼龟收集
红耳龟人工巢营造好以后,每隔5—7 d观察1次,避开阴雨天,直至红耳龟卵孵化结束或全部被捕食。每次观察时挖开龟巢上面覆盖的土壤,检查龟卵被捕食情况,检查完毕后将龟巢恢复原状。实验结束后收回所有成功孵化的红耳龟幼体,防止其逃逸到野外。
2.2.3 蚁类采样与鉴定
每次野外龟巢检查时,对捕食龟卵或幼龟的蚁类数量进行粗略估计,每种蚁采集标本10只以上,置于装有85%乙醇的1.5 mL采样管中保存,以备鉴定。本研究的蚁类标本由我国知名的蚁类分类专家广西师范大学周善义教授进行形态学分类鉴定。蚁种鉴定主要参照《广西蚂蚁》[22]和《中国蚂蚁》[23]。
2.2.4 数据处理
使用SPSS 21.0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卡方(χ2)检验比较3个样区之间巢捕食率的差异及不同蚁种对巢捕食率的差异,显著性水平设置为0.05,极显著性水平设置为0.01。
3 研究结果
3.1 红耳龟人工巢的被捕食情况
野外观察发现所有人工巢均遭到蚁类不同程度的捕食,其中黄婆洞水库样区有19个巢(占该样区巢数的95%)被完全捕食,民政林场样区有18个(占该样区巢数的90%)巢被完全捕食,小坑水库样区有17个巢(占该样区巢数的85%)被完全捕食。以完全被捕食的巢计算,3个研究样区的巢捕食率无显著差异(χ2=1.111,P>0.05)。在3个研究样区共有6个巢未被完全捕食,共孵化出9只幼龟,其中黄婆洞水库样区孵化出1只,民政林场和小坑水库样区各孵化出4只。
3.2 各样区捕食红耳龟人工巢的蚁种与数量
在3个研究样区共发现14种蚁类对红耳龟人工巢具有捕食作用(表1),其中黄婆洞水库样区6种,分别为全异巨首蚁(Pheidologetondiversus)、聚纹双刺猛蚁(Diacammarugosum)、费氏盘腹蚁(Aphaenogasterfeae)、中华短猛蚁(Brachyponerachinensis)、横纹齿猛蚁(Odontoponeratransversa)、爪哇中猛蚁(Mesoponerajavana);小坑水库样区5种,分别为全异巨首蚁、某种大头蚁(Pheidolesp.)、双齿多刺蚁(Polyrhachisdives)、知本火蚁(Solenopsistipuna)、平和弓背蚁(Camponotusmitis);民政林场样区10种,分别为全异巨首蚁、爪哇中猛蚁、中华短猛蚁、黑头酸臭蚁(Tapinomamelanocephalum)、蓬莱大齿猛蚁(Odontomachusformosae)、横纹齿猛蚁、费氏盘腹蚁、近缘巨首蚁(Pheidologetonaffinis)、聚纹双刺猛蚁、夏氏尼氏蚁(Nylanderiasharpii)。其中,全异巨首蚁在各样区均有发现,有5个蚁种在黄婆洞水库样区和民政林场样区均有发现,有8个蚁种只在小坑水库和民政林场样区发现(表1)。从个体数量看,全异巨首蚁、某种大头蚁、中华短猛蚁、黑头酸臭蚁、近缘巨首蚁、知本火蚁数量丰富,费氏盘腹蚁、双齿多刺蚁、夏氏尼氏蚁数量中等,其他蚁种个体数量较少(表1)。
表1 研究样区捕食红耳龟人工巢的蚁种、数量等级、分布及捕食龟巢的数量

Tab.1 Species,number of individuals,distribution of ants preyed upon artificial nests of Trachemys scripta elegans,and the number of artificial nests preyed upon by each ant species in the three field study sites in Guangzhou,China
注:数量等级:+.稀少(0—50只),++.中等(51—100只),+++.丰富(大于100只);分布样区:Ⅰ.黄婆洞水库,Ⅱ.小坑水库,Ⅲ.民政林场;a.蚁种编号按照各个种捕食红耳龟人工巢的数量从大到小顺序排列
Notes:No.of individuals:+.Rare(0-50 individuals),++.Common(51-100 individuals),+++.Rich(over 100 individuals).Distribution sites:Ⅰ.Huangpodong Reservoir,Ⅱ.Xiaokeng Reservoir,Ⅲ.Minzheng Forest Farm.a.Ant species codes: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the number of turtle nests preyed upon by each ant species from large to small
3.3 各蚁种对红耳龟人工巢的捕食作用
对红耳龟人工巢捕食数量的大小反映了各蚁种捕食作用的大小。按照14个蚁种对红耳龟人工巢的捕食数量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依次为全异巨首蚁、某种大头蚁、中华短猛蚁、爪哇中猛蚁、费氏盘腹蚁、横纹齿猛蚁、聚纹双刺猛蚁、黑头酸臭蚁、双齿多刺蚁、蓬莱大齿猛蚁、近缘巨首蚁、知本火蚁、平和弓背蚁和夏氏尼氏蚁(表1)。不同蚁种对红耳龟人工巢的捕食率存在极显著差异(χ2=216.544,P<0.01),其中全异巨首蚁对红耳龟人工巢的捕食作用最强,总体巢捕食率达66.7%;中华短猛蚁、某种大头蚁、爪哇中猛蚁、费氏盘腹蚁等对龟巢的捕食作用较强,总体巢捕食率分别达到或超过10%,其余蚁种对红耳龟人工巢的捕食作用相对较小(表1)。各蚁种在3个研究样区中对红耳龟人工巢的捕食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图2),例如全异巨首蚁在黄婆洞水库、小坑水库和民政林场3个样区的巢捕食率分别为95%、60%和45%。

图2 各蚁种在3个研究样区对红耳龟人工巢的捕食数量(横坐标的数字为蚁种编号,见表1)Fig.2 The number of turtle nests preyed upon by each ant species in the three field study sites in Guangzhou,China.(The numbers in abscissa represent the ant species codes,see Tab.1)
4 讨论
龟类巢的捕食者包括多种动物类群,如蚁类、爬行类、啮齿类及食肉类动物等[16-17,19,21,24]。蚁类因其种类繁多、数量大、分布广,对龟类巢的捕食危害较大,如红火蚁(Solenopsisinvicta)[3,25]、热带火蚁(Solenopsisgeminata)[4]等是龟类巢的常见捕食者。Allen 等[25]研究发现,红火蚁不能破坏纳氏伪龟(Pseudemysnelsoni)的卵,但可以捕食破壳后的幼体,导致70%的初生幼体被捕食。Dziadzio 等[3]对哥法地鼠龟(Gopheruspolyphemus)的研究中也发现红火蚁无法破坏卵壳,但可以捕食破壳后的幼体,导致50%的幼体被捕食。纳氏伪龟和哥法地鼠龟的卵属于硬壳卵,卵壳相对坚硬,而红耳龟的卵壳为较柔软的革质,相对容易被蚁类咬破。本研究发现,在实验开始初期(前15 d 内)当红耳龟卵尚处于孵化阶段时,全异巨首蚁、中华短猛蚁等多个蚁种已开始破坏卵壳捕食龟卵,说明红耳龟卵壳无法有效抵御研究地区蚁类捕食。周鹏[10]在广东古田省级自然保护区对红耳龟人工巢的野外研究发现,有大头蚁属、巨首蚁属等7种蚁类捕食红耳龟巢,完好无损的红耳龟卵和初破壳的幼体均可被蚁类捕食。
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环境中的红耳龟巢捕食者的种类存在差异,对龟巢的捕食率也有所不同。在广东古田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研究发现红耳龟人工巢的主要捕食者为蚁类,野外实验观察的84枚红耳龟卵中有56枚被蚁类捕食,巢捕食率为66.7%,另外啮齿类动物也捕食龟卵和幼体[10]。在海南万泉河流域对红耳龟自然巢被捕食情况观察发现,台湾小头蛇(Oligodonformosanus)、双齿多刺蚁和印大头蚁(Pheidoleindica)是主要巢捕食者,99枚卵中有33枚被捕食,捕食率为33.3%[11]。在海南南渡江流域对红耳龟自然繁殖巢研究发现,5个巢中有1个巢被印大头蚁部分破坏,破坏率为20%,其余巢未被破坏[12]。在海南吊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利用红耳龟卵替代黄额闭壳龟(Cuoragalbinifrons)卵进行的人工巢被捕食研究发现:66.7%的巢被捕食,其中51.30%的巢被小型兽类(针毛鼠Niviventerfulvescens和树鼩Tupaiabelangeri)捕食,28.8%的巢被蚁类捕食,但未对蚁种进行分类介绍;次生林和原生林的人工巢被捕食率均为62.5%,人工林中的被捕食率为72.5%,人工林的捕食率与次生林和原生林的差异不显著[19]。在本研究中,3个不同环境类型的研究样区中蚁类对红耳龟人工巢的捕食率均达80%以上,显著高于上述其他研究地区[10-12,19]。除了蚁类捕食者外,在小坑水库发现1例啮齿类动物(针毛鼠)捕食红耳龟人工巢,在黄婆洞水库样区发现2例台湾小头蛇捕食红耳龟人工巢。有趣的是,其中1条台湾小头蛇在捕食红耳龟卵时,被进入人工巢的全异巨首蚁捕杀。
龟类自然巢往往野外很难寻找,研究难度极大,人工巢相对容易操作,可以根据研究需要进行条件控制,因而被广泛用于龟类巢捕食研究[2,19-21]。但是人工巢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人工巢可能不能够真实地模拟自然巢的某些条件,另一方面人工巢可能会由于人为留下的气味线索而招引天敌,从而增加了巢的被捕食风险[26]。与自然巢被捕食率相比,红耳龟人工巢具有更高的被捕食率。例如,海南南渡江和万泉河地区红耳龟自然巢被捕食率分别为20%[12]和33.3%[11],而广东古田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红耳龟人工巢被捕食率为66.7%[10],本研究发现广州地区红耳龟人工巢被捕食率达85%以上。可见,红耳龟人工巢被捕食率通常高出自然巢被捕食率的1—3倍。不同地区的红耳龟人工巢与自然巢的被捕食率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不同地区天敌差异以及人工巢与自然巢之间存在的差异共同所导致,这一问题有待在同一区域做进一步深入的对比研究。
本研究发现,3个样区中捕食红耳龟巢的蚁种差异明显,其中黄婆洞水库样区6种,小坑水库样区5种,民政林场样区10种,各个样区的天敌蚁种存在重叠,但也有差异。从环境特点看,民政林场样区属于天然林保护区,自然环境受外界干扰相对较小,天敌蚁种最多;黄婆洞水库样区位于风景区,小坑水库样区位于农业区,这两个样区人为干扰大,天敌蚁种相对较少。但从蚁类对红耳龟人工巢的捕食率来看,3个研究样区并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蚁类数量众多,即使少数几个种类也可以达到相对高的捕食率。
从捕食红耳龟巢的蚁种来看,大头蚁属、巨首蚁属、短猛蚁属、盘腹蚁属、齿猛蚁属、双刺猛蚁属、酸臭蚁属、多刺蚁属、火蚁属、弓背蚁属、尼氏蚁属的有关种类均捕食红耳龟巢。从各蚁种对红耳龟人工巢的捕食数量来判断,不同蚁种的捕食作用大小差异显著,其中全异巨首蚁的捕食作用最强(捕食率66.7%),某种大头蚁、中华短猛蚁、爪哇中猛蚁、费氏盘腹蚁、捕食作用中等(捕食率均达到或超过10%),横纹齿猛蚁、聚纹双刺猛蚁、黑头酸臭蚁、双齿多刺蚁、蓬莱大齿猛蚁、近缘巨首蚁、知本火蚁、平和弓背蚁和夏氏尼氏蚁捕食作用较弱(捕食率小于10%)。野外观察发现大多数龟巢往往同时被2种以上的蚁类捕食,可能是由于其中一种蚁首先破坏龟卵后,龟卵的腥味进一步吸引了其他蚁种的捕食。周鹏[10]研究发现,完好无损的红耳龟卵也会遭到蚁类的破坏,而破损的红耳龟卵会更快地吸引更多的蚁类,导致其附近完好的红耳龟卵遭到捕食。蚁类除了捕食红耳龟卵外,还会捕食初破壳的幼龟,本研究的3个样区中共孵化出9只幼龟,但仅2只存活,其他7只幼体均被蚁类捕食,在广东古田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研究中也发现未能及时爬出巢进入水中的初生幼龟被蚁类捕食的现象[10]。
本研究表明,广州地区蚁类对红耳龟人工巢的捕食作用较其他动物类群更强,推测蚁类对红耳龟的入侵具有较好的抵御作用。巨首蚁属、大头蚁属的有关物种在红耳龟生物防治中具有潜在的利用价值,但其对红耳龟自然巢的捕食作用以及其他生物和自然环境的安全性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致谢:广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周善义教授帮助鉴定蚁类标本,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究所杨江波、蓬友红参加野外工作和样品采集,董以协助制作地图,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