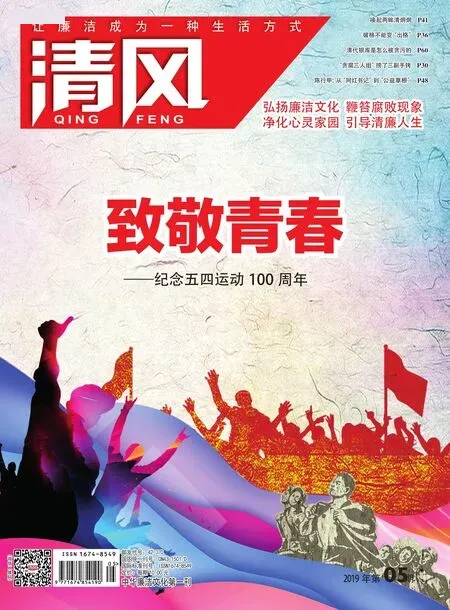清代银库是怎么被贪污的
文_张宏杰
清代一个著名的肥缺,叫作“户部银库郎中,佩带银库印钥”。户部银库是收贮各地送到京师的赋税饷银之所,关于这个职务,一直以来有一种误解,以为是户部的一个下属部门。其实户部虽有侍郎例兼三库,但由于三库地位之重要,朝廷历来另外捡派管理三库大臣,所以和三库中的另外两库一样,户部银库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户部之外的一个部门。
众所周知,银库一直是清代财政中水最深的部门,就像时人所评:“三库蠹弊,以银库为最甚。”对这点皇帝心知肚明。为了让这些“护肉”的“饿犬”不至于偷吃太多,所以对京官十分吝啬的清代皇帝对“三库”官吏不但给予养廉,且金额独丰。雍正十一年(1734 年)奏准支给户部有关官员养廉银,其标准为:“户部银库郎中、员外郎,每员岁给养廉银各五千两,司库三千五百两,大使二百两,库使三百二十两,笔帖式八百两;颜料库郎中、员外郎、司库,每员岁给养廉银各一千两,大使三百两,库使、笔帖式各一百八十两,掌稿笔帖式、库使二百七十六两六钱有奇;缎匹库郎中、员外郎、司库,每员岁给养廉银各四百五十两,大使、库使、笔帖式各一百五十两,掌稿库使、笔帖式二百一十两。三库总档房主事三百六十两,笔帖式一百二十两。”
当然,这笔养廉根本阻止不了银库官吏的贪婪。道光二十三年(1844 年),银库发生库吏盗银案,清查时发现银库短少或被盗的库平银竟至925 万两以上。显然这并非一时所为,而是历朝累积的结果。
除去“盗银案”这样赤裸裸的偷窃行为不说,银库之所以水深,还因为在银两出入库的过程当中,银库官员可以制造大量的受贿机会。按规定,外省解送到京的赋税饷银,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入库。一旦银库将验收日期拖后,则银两保管、委解人员食宿之类费用就要由解饷委员自掏腰包。所以贿赂银库官员以期尽先验收,成为委员们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清代各地银两的成色差别很大,形制亦别。故在验收银两的过程中,银库官员对银两成色及分量可以百般刁难,要想顺利入库,解饷委员还需另外花钱。至于银两发放之时,各衙门领到银两的成色及形制,库员亦可上下其手,“或给以元宝、银锭,或给以散银(滴珠),并有扣平及搭放成色银等例规”。因此“有无向银库行贿就成为他们是否能得到足色库平银的重要基础”。因为拥有如此巨大的营私空间,银库的官员和胥吏自然是京官中的“异数”。光绪末年,有御史在调查后认为,“(银库)郎中一缺任满,辄挟赀数十万,员外郎以下次之。此款率取之库书之手,库书之下有库丁,又有保护库丁者,无不以财自豪”。
骆秉章在其自叙年谱中则主要记述了库丁们收银时以少充多的舞弊手法。道光二十年,骆秉章奉旨稽查户部银库,当时的四位库官是荣庆、荣禄、公占、苏经额,皆满员。骆氏到库数次之后,库官就开始对他介绍银库“惯例”,说稽查官员每年照例会得到两万多两“辛苦钱”。骆氏问其来源,原来银库以前收各地捐项银两时,规定每百两要多收四两,归银库官吏私分。后来成亲王稽查时,奏请归入公款。不过就像中国历史上许多次兴利除弊的结果只是“弊外加弊”一样,此后不久,银库在此四两以外又开始加收四两,继续分肥。其中二两归库丁,二两归库官和查库御史。
弄清原委后,骆秉章对库官说,这笔钱如果曾经奏明我就收,否则我不收。“四库官皆语塞。皆云,阁下不收则弟等五人亦收。”
骆氏拒不受贿,让库官们很担心。过了几天,库官又向他提出建议:“四两平足下即不收,何不带银号捐,每年约得万余金。”同样被他拒绝。
又过几天,库官又托骆氏同乡李某来进言,说各银号准备了到任礼,共七千两。以后三节,每节也送七千两。
各银号送此重礼的目的“不过求都老爷勿挑斥”。原来,多年以来,各银号送到银库的银两照例都是非足平色,经常“以少作多,银色低潮”。银库官员收了重礼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遂致国家资产经年大量流失。
骆秉章的例子揭示,库官库丁们舞弊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在银两入库之时,私自以少充多,以低成色充高成色。“从前收捐多有六七百两或四五百两作一千者。库项之亏短多在捐也。”也就是说,各地捐项,流失率可达百分之三十到六十之多。由此推测,道光年间的库银短缺案,很有可能并非完全如人们传说的那样是因库丁以肛门夹银方式带出,一个可能的渠道是在入库时弄虚作假。因此骆秉章说,库丁作弊之法,“亦易查出”,一般来讲,就是在银两入库出库之时,认真审查过秤过程而已。在他的监督之下,库丁无法舞弊,库官库丁收入大减,十分着急,因此千方百计“总欲使御史受规”。最后他们想到的办法居然是托银号活动,把骆氏调走。道光二十一年(1842 年)“四月时有一京畿道缺出,银号等约五六人到帅副宪宅求见少爷。”要求少爷动员副宪,将此缺放予骆,“送一千银与二爷,送六千银与大人门上。”
晚清满族官员那桐的履历显示,他在担任银库郎中后的第二年,就收入暴增,在京城繁华地段开始经营当铺。《那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廿四日记载:
余托孟丽堂价买北新桥北大街路东增裕当铺作为己产。计占项一万二千余金,架本三万金,存项一万金,统计领去五万三千余金。
时隔一年多,那桐再次购买当铺。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那桐在日记中写道:
余托孟丽堂价买灯市口北,东厂胡同口外,路东元丰当作为己产,改字号曰“增长”。价本市平松江银三万两,占项市松一万七千两,存项京松二万五千两,统计市松七万二千余金(合京松七万二千九百六十两)。
这两笔高达十二万余两的巨额投资显然不是他的公开收入所能承担的。事实上,分析那桐的升迁之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银库郎中一职是他宦途升腾的关键点,在此之前,他一直是中低级京官,在此之后仅仅一两年间就跻身高级京官之列,后更飞黄腾达成了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