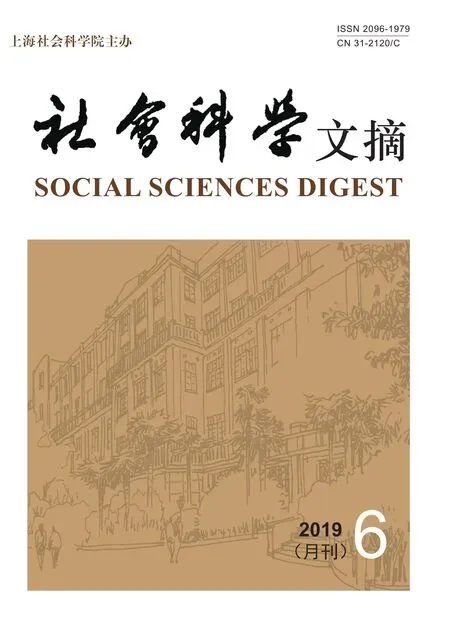美国崛起的社会心理演变
从大国崛起的战略、心理准备角度看,美国从物质性崛起到全面崛起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战略缓冲期,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战略试错与社会心理塑造时间——尽管这未必是有意识的前瞻性设计的后果。战略试错与社会心理塑造是大国崛起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尽管战略试错貌似寻找崛起的更佳战略抉择,但它同样是在寻找国内长期性战略动员或社会心理的坚实基础。因此,充分的战略试错与社会心理塑造时间,事实上也是大国崛起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内涵。事实证明,美国充分利用了从物质性崛起到全面崛起的战略机遇期,有意或无意地开展了至少三轮战略试错,推动美国社会心理从榜样论向救世主论转变,从而为崛起后的社会心理奠定了坚实基础。美国经验表明,充分的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时间,对大国崛起的长期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如何抓住演变中的可能正遭严重挤压的战略机遇期,逐渐提高崛起可持续性,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崛起大国的当务之急。
榜样需要尊重:现实主义权势政治的成与败
随着美国持续崛起并在20世纪末期成为世界性的物质强国,美国人自移民之初便不断自我强化的榜样心理进一步固化,对榜样应得的国际尊重也日益渴望。但事与愿违的是,国际社会直到此时仍严重忽视美国的物质性崛起。美国对尊重的强烈渴望,促使以武力确保榜样得以尊重的偏执心理逐渐占据上风,并在美西战争中得以释放。而正是由于美西战争很大程度上释放了以武力保障尊重的偏执心理,美国社会对以老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权势政治信奉者大加挞伐。美国向帝国主义的转型在实践中是成功的,但却遭到美国社会的排斥。
南北内战后的国家重建迅速使美国崛起为世界性强国。一方面,在内战之后的数十年里,美国的经济增长才真正达到令人晕眩的速度。据计算,1873年至1913年之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年均增长率为5%。这个超常的增长速度几乎体现在任何经济部门。另一方面,内战结束也加速了美国的内部扩张,从仅有13个州发展成为一个两洋国家,美国所塑造的新权势格局很大程度上为其对外扩张奠定了思想基础。
美国的物质性崛起极大地强化了其对自身充当世界“榜样”的自信心。但美国的榜样作用或地位并未被国际社会所重视,从美国人的视角看,自身作为世界榜样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例如,直到1892年,驻华盛顿的外交官仍没有一位是大使级的,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认为美国足够重要。可以认为,在物质性崛起与全面崛起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且需要充分的战略机遇期以实现从能力到权力的转换。
对物质性崛起与全面崛起之间的时间滞后缺乏理解,加上国际社会对美国崛起的客观事实和心理变化不够重视,极大地伤害了美国社会的自尊,推动先前只是相对中性的“榜样需要尊重”心理需求,向颇为偏执的以武力确保榜样得到尊重的方向发展。首先,美国人更加强调自身的榜样作用;其次,随着自身崛起,美国对自身利益的想象逐渐从相对保守向强势肯定的方向发展;最后,美国社会日益欢迎以武力手段解决问题或确保自身得到尊重。
以武力确保榜样得到尊重,最为明显地体现在美国迈向帝国主义的首次重大努力即美西战争中。美西战争的直接诱因是古巴危机,但在美西战争前事实上已有过多次古巴危机,尤其是1869—1870年和1873年危机。比较这两次危机,榜样自身的危机对于公众期待通过武力确保榜样得到尊重的意愿有着明显的影响。
到1897年再次爆发古巴危机时,美国的实力相比上述两次危机时已大为进步,公众对榜样未得到相应尊重的认知更加极端,刺激美国政府和社会对于通过武力确保榜样得到尊重更加狂热。由此而来,在1898年4月做出的对古巴进行干涉的决定和随后向西班牙的宣战所产生的分歧要小得多。首先,绝大多数持有榜样论的人都认为应当在古巴采取行动;其次,以武力确保榜样得到尊重,也有利于强化榜样自身;最后,通过战争强化爱国主义,既有助于进一步消弥内战前的南北裂痕,也有助于促进种族团结,尽管这一效应很快被证明并不持久。
一场以维护榜样尊严为名且仅持续3个月的战争,使美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美国在亚洲得到了一个能够发号施令的阵地,并正式赢得在西半球的统治者地位。尽管如此,以老罗斯福总统为代表的权势政治信奉者们却抱怨“能让我们大显身手的战争机会还不够多”。
尽管美西战争的胜利使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社会心理危机”得到有效释放,美国似乎摆脱了“中年危机”重返“青年时代”,但通过武力确保榜样得到尊重的偏执狂并不符合美国的建国传统。因此,尽管战争获胜被大加宣扬,但反对呼声也同步上涨,其代表是1898年6月成立的“反帝国主义联盟”。尽管各种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理由不尽相同,但根本上由于权势政治与美国建国传统在根本哲学取向上的不同,美国社会对榜样需要尊重的偏执狂热在经历美西战争和“门户开放”等对外扩张行动的有效释放后逐渐趋于冷静,美国紧随物质性崛起后的第一次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以失败告终。
榜样必须纯洁:全面胜利与重返孤立
美国在物质性崛起后的第一次战略试错及相应的社会心理塑造的失败,与其说是目标的错误,不如说是手段与目标的结合存在问题,并诱发了严重的公众反感。对自认为是世界榜样的美国人民来说,第一次战略试错及社会心理塑造的根本问题在于,以美西战争为代表的战略手段事实上玷污了榜样本身。这一心理推动美国在一战中的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转向另一极端,无论是保持中立还是追求全面胜利的目的都是维护榜样的纯洁性,但由此导致的“非黑即白”的战略方法同样不是美国社会所渴望的。
一战的爆发为美国实现从物质性崛起到全面崛起转换提供了另一重要战略机遇。它一方面使美国得以尝试与前一阶段完全不同的战略,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的物质性崛起。但由于前一轮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的遭遇,这一战略机遇本身并未被及时发现和捕捉。
对美国社会而言,美西战争后至一战后期,其核心关切是美国作为榜样的纯洁性。鉴于美西战争后的美国社会心理,威尔逊总统尝试延续自华盛顿总统以来的孤立主义,以孤立维护榜样的纯洁。
尽管如此,威尔逊总统内心却有着远为宏大的目标。在他看来,美国物质性崛起的天然后果是向外扩张。他在1912年总统竞选中强调,美国工业已经膨胀到如此程度,国际市场必须成为美国制度的新边疆,否则意味着灾难。因此,尽管坚持中立,但威尔逊本人及其主要顾问们都更同情协约国。
随着战争发展,美国社会心理逐渐变化,从一开始的绝对中立逐渐转向武装中立。在1917年3月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威尔逊总统强调,尽管美国并非参战国,但战争的确对其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尽管如此,美国仍应设法置身事外,追求超越与战争直接相关的利益。尽管有的伤害已无法容忍,但美国仍不应对公平交易、正义、生活自由及共同对抗有组织的错误等抱有奢望。美国要以武装中立来确保自身最低限度的权利和行动自由,既不是征服也不是想获得优势;美国不追求以他国为代价的利益,而应发挥巩固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榜样纯洁性的维护至少可以有两种手段:一是保守性的孤立或隔绝战略,通过孤立自身而避免被玷污;二是进取性的全面胜利战略,全面改造整个体系或将榜样的模式推广至整个世界,从而实现榜样的纯洁。随着战争发展,美国对协约国的同情心逐渐上涨,美国社会经历了从绝对中立到武装中立,从维护和平到赢得完全胜利的心理转变。
1917年4月2日,威尔逊总统请求国会对德国宣战,其理由是美国作为榜样的纯洁性正在被德国玷污。他说,德国政府是一个恶魔,危及“人类生活之根本”。威尔逊总统的核心逻辑在于,为持续维护榜样的纯洁性,美国参战必须拥有在道德上更加高尚的目标。一方面,美国是个民主国家进而是热爱和平的,它不喜欢打仗、不会轻易挑衅;但一旦它被挑衅而必须要动武,它不会轻易宽恕它的对手造成了这样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就美国参战是确保未来和平而言,战争结束的方式和条件有着重大区别。它将导致一个值得保卫的和平,得到整个人类同意的和平,而非一个仅服务于参战国利益的和平。
以维护榜样纯洁性为出发点,美国参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场战争的性质,使其不再是野心勃勃的列强相互争夺权势的传统争霸战,而成为一场十字军的东征、一场“确保民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的战争”。美国不应当对帮助欧洲恢复战前状态感兴趣,它不是为了这种昔日的过时目标而战,更迫切在于为重塑未来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并为之带来真正的变革。这正是威尔逊总统于1918年1月提出“十四点”原则作为建立世界和平纲领的深层逻辑。
需要指出的是,威尔逊在回避权势政治、追求榜样纯洁性的道路上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的目标如此崇高,因此也与老罗斯福总统一样不在乎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仅关注目的正当性,威尔逊总统及其政府对所有反对战争的舆论强加了严厉限制,当官方行动不能迅速使公众就范时,治安维持会就会自动过问。
威尔逊总统对榜样纯洁性的极端追求与不择手段,不仅引发了来自民间的强烈反对,更是遭到国内政治力量的强烈抵制。尽管与老罗斯福总统相比,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话语更能动员美国公众,但其倡导的理想方案在现实政治中难以推行,是美国人物质性崛起到全面崛起的第二次战略试错与社会心理塑造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榜样可以普及:救世主与霸权确立
威尔逊总统推进的战略试错与社会心理塑造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在于高度理想化的方案与政治的现实可行性之间的差距过大。美国社会拥抱因建国理想而来的天然理想主义,并不代表其对政治现实的全然无视。与其前辈们相比,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很好地利用了二战所带来的战略机遇,在推动美国逐渐卷入战争的过程中,有效地结合了理想主义与权势政治,既延续了威尔逊总统在一战中基本确立的美国作为“救世主”的地位,更变相复活了老罗斯福总统的权势政治,从而确保了第三次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的成功,为全面崛起后的美国外交战略奠定了持续稳定的社会心理基础。
美国实现从物质性崛起到全面崛起的战略试错有一个独特特征,即尽管战略试错很大程度上以失败告终,但并未对其物质性崛起产生负面影响,反而是持续推动美国朝全面崛起方向迈进,对美国崛起的社会心理塑造也渐趋成熟。正是持续的物质性崛起,为美国反复进行战略试错提供了经济和军事基础;而二战的爆发则提供了第三次战略试错的战略机遇。
随着二战阴影渐趋浓厚,源于确保榜样的纯洁和被尊重的中立论再次浮现。1937年10月,罗斯福总统发表著名的“隔离演说”。这一源于榜样纯洁性的中立战略认为,传递“美国价值观”肯定是积极的,但只能通过在国内设定美德榜样的手段予以实现。美国应安全地躲在两大洋背后,扮演其恰当角色。这一保守战略有着相当强的社会心理基础。盖洛普(Gallup)公司于1938年9月的民意测验表明,只有34%的美国人赞成一旦英法与轴心国交战就卖给他们武器。
可以认为,1937年的美国仍然遵循标准的榜样纯洁性和榜样需要尊重的逻辑。但随着战争的迫近和爆发,美国社会心理基础遭到严峻挑战。因为大萧条导致了世界经济的整体性转向,敌对的经济集团使得回归正常经济状态变得更加复杂,日本和德国政治生态的变化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危机已演变成为自由主义的危机”。这样,在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后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罗斯福从一开始不指名地公开谴责蓄意以侵略战争或战争威胁作为政策工具的国家,转变为公开点明这样的国家就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并进一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支持那些反法西斯国家。《慕尼黑协定》后,美国民众中赞成向英法出售武器的人数升至68%,但认为保持和平比打倒纳粹更重要的人却有64%。
更大范围的社会心理转变主要体现为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ustin Beard)和新教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一场持续约3年(1939 —1941年)的大规模辩论。比尔德视美国为全世界效仿的美德榜样。但作为神学家,尼布尔也强调应对权势不公需要强调社会正义;任何对权势的垄断都是“最大的不公”,因此需要民主制度。尼布尔所建构的基督教现实主义较好地结合了理想主义与权势政治,得以在学术界之外广泛流传。
随着美国思想界逐渐转向更加进取性的立场,加上二战全面爆发并持续,罗斯福在1941年1月6日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了后来成为美国宣战官方理由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予匮乏的自由和免予恐惧的自由。这不仅标志着美国正式参战,更标志着美国全面从对榜样的保守战略转向进取性的救世主战略。因为,美国参战不是仅为了美国自身,而是在一场“介于人类自由与人类奴役之间”的战争中保卫自由,反对专制主义的黑暗力量对自由的围剿和攻击,反对专制主义对世界的奴役。
这一进取性战略或救世主战略中有着同样明确的榜样纯洁性追求,甚至远超过一战时的威尔逊总统,因为正是基于这一纯洁性要求,推动了人类战争史上的一大发明即“无条件投降”。正是“四大自由”和“无条件投降”,使罗斯福得以在与“魔鬼”(苏联)结盟的过程中推广美国的价值观,从而真正将理想主义与权势政治相结合,使美国得以从“山巅之城”发展成为“城中山巅”。一种典型的救世主心理在美国社会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美国作为一个榜样国家,从此往后的任务不再是确保榜样得到尊重,而是如何得以普及,或者说如何使美国“从海洋到照亮海洋”。
罗斯福成功地结合了老罗斯福和威尔逊的优势,同时又成功地避免了后两者的悲剧,其所奠定的美国社会救世主心理,成为此后美国霸权的一个基本特征。
结束语
从物质性崛起到全面崛起,美国用了约50年时间。从个体角度看,利用近半个世纪进行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几乎让一整代人没法看到美国的全面崛起;但从整体角度看,这50年大大提升了美国崛起的可持续性。就此而言,美国崛起的社会心理塑造及其演变至少可提供四个方面的启示:第一,充分的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时间对大国崛起的长期可持续性至关重要;第二,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的底线是不破坏物质性崛起的可持续性;第三,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的渐进性对于维持甚至延长战略机遇期相当重要;第四,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合理平衡是战略试错和社会心理塑造得以成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