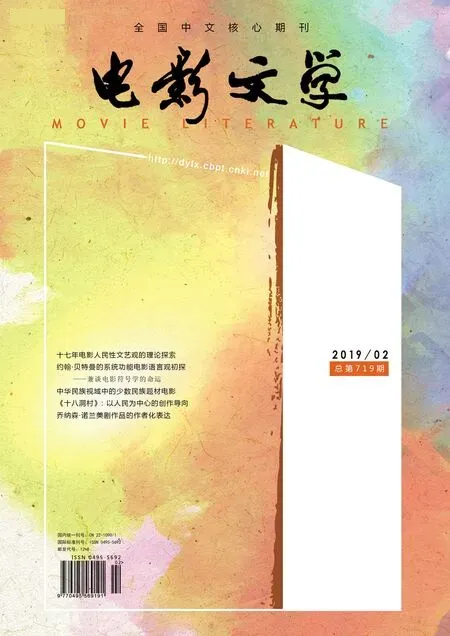《历劫佳人》:一个声音文本的范式
蒋星垚 (成都文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401)
奥逊·威尔斯执导并亲自出演的黑色电影《历劫佳人》是他仅次于《公民凯恩》的代表作。影片出色的声音设计具有反叛传统、拒绝确定意义的现代主义美学色彩,其不仅保障了本片的艺术效果,还彰显出超越时代的先锋性,非常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究。
一、《历劫佳人》的自然音响:混乱边境空间的构建
(一)边境小镇的音效奇观
《历劫佳人》的故事发生在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小镇弗龙特拉,这座肮脏分裂的小镇是滋生罪恶的温床。影片伊始,气势恢宏的管乐与鼓乐迅速将观众的情绪引入电影叙事氛围。紧接着,电影从一名手持炸药者的特写镜头开始,这人随即拧上了炸药的定时发条,然后我们便听见一对男女欢笑着从远处走近的声音。此时,手持炸药者匆忙地回头以确认这对男女行走的线路,然后将炸药放置在他们轿车的后备厢中便仓皇跑开,这对男女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坐上了轿车。随后,车上的两人与瓦格斯和苏珊交替在电影画面中前行并最终在边检处会合。接下来,视点再次切换到瓦格斯与苏珊,在两人正要接吻的刹那,之前驱车离开的那对男女的汽车发生了可怖的爆炸。
威尔斯这个著名的3分20秒长镜头因其巧妙的构思、灵动流畅的场面调度多年来一直为影迷及影评人所津津乐道。然而,这个镜头的声音设计也是非常精妙入微的。我们知道,自然音响指涉了环境声、自然声、机械声、动作声等,而“影视中的自然音响大都起着与动作和环境同步的自然作用”[1]138。在电影开始的长镜头中,一人以颇具仪式感的方式拧上炸弹发条,嗒嗒嗒嗒的发条声与此时加入的具有拉美风情鼓点节奏的配乐形成了有趣的对位,表征出放置炸弹者紧张焦灼的心态,渲染了一种危险、紧绷的情绪氛围,并预示着危险的降临。紧接着女人放荡的笑声由远而近,其混合着发条声与逐渐加快的鼓点节奏,像加速摆动的节拍器不断挑动着观众的神经。
(二)声音的“同步整合”与“增值”
威尔斯在关于《历劫佳人》的音效笔记中曾提到,“这个边境小镇的街道应该总是充斥着各种扩音器所发出的嘈杂而刺耳的声音,充满从夜总会入口处……小酒吧、小酒馆传出来的广播声……”[2]从这里,我们看到威尔斯能够游刃有余地安排这些复杂的自然音响去创造一个令人信服并极具感染力的混乱边境小镇的声音环境。法国著名电影声音理论家米歇尔·希翁从诗学和美学的维度来探究电影声音,并由此提出了“同步整合”的原理。它是指“在特定的听觉现象和视觉现象同时出现时,它们之间出现的一种自发的、不可抗拒的结合。这种结合导致的结果与任何理性逻辑无关”。[3]55同步整合实际上就是一种声音与画面的“巴甫洛夫效应”。由于同步整合的作用,特定的电影声音与电影画面组合在一起时会在我们的感觉中建立一种立即和必要的紧密联系。声音赋予了相应画面的现实意义,使其符合观众的直接或记忆经验,因而让这个场景变得真实可信。实际上,这也就是希翁所描述的“增值”现象,希翁指出“声音可以充实一个给定的影像,以产生确切的印象”[3]4。
稍加注意,我们便能发现在《历劫佳人》开头的长镜头中,当这对男女坐上轿车时,作为画外音的爵士配乐与鼓点的声音突然减弱。然而等他们发动汽车离开之际,一段新的爵士乐旋律出现并逐渐扩大音量。基于“同步整合”的原理,我们有理由认为此时出现的爵士乐就是从这部轿车中传出来的。接下来,在汽车驶向边检站的沿途及瓦格斯与苏珊走向边检站的过程中,我们能听到警察的哨声、路人的喧哗声、羊群的咩咩声、酒吧与脱衣舞厅扬声器所发出的嘈杂声等。这些纷繁芜杂的声音构建出一个混乱但可信的环境空间,因为这里的每一个有声源或无声源的环境声都符合我们的生活经验。
二、《历劫佳人》的电影人声:身份的混合与跨越
(一)声音的间离与身份的失焦
在影片中,墨西哥黑帮“乔大叔”的手下潘科将苏珊从迎面疾驰而来的汽车面前拽开救了她一命,这时潘科向苏珊说了几句西班牙语。随即周围有一些人用英语向苏珊解释潘科的意思,而苏珊此时却误将潘科的话语理解为“求欢”。“对于母语是英语的观众,场景中其他任何语言的使用都能够形成特殊的反应。其目的可能是对其他人物或观众消除或揭示信息,或者创造一种身处国外的环境感。”[4]133由大卫·索纳斯蔡恩的观点来看,母语是英语的观众此时应该能体会到强烈而真实的异国情调。假设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潘科的西班牙语对电影观众的理解与片中的苏珊都造成了语义上的中断,而威尔斯“布莱希特式”的美学追求却恰好通过电影中这些用不同语言进行的人物对话而获以实现。我们对电影叙事的连贯性与熟悉感被突然闯入的“外来语言”所暂停和陌生化,因而获得了一种“间离感”与虚构边境空间的真实感。
随着电影情节的推进,我们能发现潘科会以一种略带西班牙口音的英语与另一位“葛兰迪家族”的孩子对话。而在梅拉多汽车旅店中,潘科显然又用十分地道的英语口音给瓦格斯太太打电话。在这一连串的电影场景中,潘科的身份变得非常模糊且“不稳定”,我们很难确立潘科“真实”的声音,“而他看起来表演了一些语言行为,演绎出一种多重、变化、适应不同情况的声音”[5]201。类似的境况我们在昆兰拷问“嫌疑犯”桑奇兹的场景中也能见到,桑奇兹与瓦格斯、昆兰等人的交流亦不断在英语和西班牙语之间游走。
(二)“人声中心”的颠覆与音频技术的介入
希翁认为,作为“人声中心”的电影是一种“词语中心”的奇观。这就是说,电影中的人声对话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排他性与优先性。通常在一个声音环境中,我们总是先被人声吸引注意力,随后才会注意到这个场景中的风声、交通声、音乐声等。同时希翁还指出,人声的出现建立了一种感知的等级体系,其构成并包含了它所处的声学空间。而“《历劫佳人》则看起来恰恰是从被认为保证对话可识度结构的角度破坏了那种严格的等级体系”[5]201。换言之,在人声中心的模型下,潘科这个人物的“身份特征”通过各种差异性的对话在观众的感知中实现了某种转换与“跨越”。我们要从潘科诸多的“不稳定身份”中去搜寻其真正的身份,而“人声本身的中心性在这里充满着不可忽视的差异——表明听觉身份混合瞬间的声音行为”[5]201。这么看来一个稳定、“真实”的声音形象的话语便难以准确形成,不断转变的人物声音使观众难以捕捉到说话者真实稳定的身份特征,进而构建一个明确牢固的“人声中心”的听觉体系便十分困难。
此外,我们从潘科假装接线员改变其声音的表演中可以观察到,由音频技术的介入而实现的电影人物声音和身份的移位与改变在《历劫佳人》中多有展现。譬如,在电影结尾处,我们从瓦格斯与曼西斯窃听昆兰并用录音设备收集昆兰罪证的过程中便可看到,这里的录音装置使得人声与其身体分离开来,音频技术在此时让人物的身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位移和转变从而使其变得有些失真。在这个监听场景中,昆兰在讲话而瓦格斯在听,直到昆兰听到录音机里传出了自己的回声才意识到可能有其他人在附近。有意思的是,这时的瓦格斯与昆兰的躯体被录音装置所分离又被其所连接,而且“这个躯体由技术间接化了,声音与躯体分离,几乎变成它发生的工业化背景中无法分离的东西”[5]206。由此,我们从这种“技术间离化”的效果中再次直观地感受到了威尔斯为我们营造的一幅恢诡谲怪的“超现实声音景观”,这也体现出其对声音处理的独特美学追求。
三、《历劫佳人》的电影音乐:音乐的增值与隐喻
(一)“情感共鸣”的声音
在电影音乐所产生的增值效果中,由电影音乐对观众所引起情感共鸣的效果是我们通常能感受到的,这样的音乐我们称之为“情感共鸣音乐”。借由电影场景的风格节奏与呈现方式,恰当的电影配乐能直接参与到其对应场景中的气氛,以实现和谐的音画对位。希翁认为,音乐之所以能产生这样的效能是因为其利用了如喜悦、悲伤这些人们精神活动的文化编码。换言之,要实现精准匹配电影音乐与电影场景的情绪氛围而不产生突兀感,就需要我们能够正确地对音乐所包蕴的情绪色彩、文化内涵等进行精准解码。
电影中,当苏珊与新婚丈夫瓦格斯亲眼目睹了骇人的汽车爆炸后,苏珊被瓦格斯要求立即回旅馆休息,而他则先去调查汽车爆炸的原因。在苏珊返回旅馆的途中,电影选用的是极具墨西哥特色的拉丁爵士乐BorderlineMontuna,其曼波鼓点的节奏与管乐烘托出浓烈的拉丁美洲风情。此外,该爵士乐错落有致的节奏和着苏珊慌乱的步伐十分贴切地外化出她内心的焦虑与想尽快离开事故现场回到旅馆的迫切之情。随后,这首爵士乐又完美地预示在电影画面前景等候苏珊的潘科与四周混杂的人流所可能引发的危险,营造出略显紧张又极具戏剧化的情绪氛围。电影中有这样一幕:当疲惫的苏珊在梅拉多旅店拉开窗帘之际,吃惊地发现一群嬉皮士般的男女吵嚷着驾驶几辆汽车向梅拉多旅店急驰而来并飞快地经过自己窗前。这时画面的背景音乐选用的是热烈喧闹的TheBigDrag,电影配乐很好地表现出这群年轻人的放荡不羁,似乎他们正奔赴一场疯狂的摇滚乐派对。
(二)“非情感共鸣”的声音
有些时候,音乐与相应电影场景可能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似乎其相互漠视着对方的存在。希翁认为,这样的音乐通常是“非情感共鸣”的音乐。电影情节与这种持漠视态度的音乐情绪之间的对位往往是置于一个更加宏大和广阔的背景之上,“这些音乐来源中那些经过深思熟虑的轻松和天真,纵使音乐自己假装不引人注意,却已强化了角色和观众的情绪”[3]8。
在《历劫佳人》中,墨西哥妓女塔娜家的自动钢琴演奏的TheTana'sTheme便是一首典型的“非情感共鸣”的音乐。这首乐曲第一次是在昆兰调查了一家脱衣舞厅出来之时所出现,它似乎勾起了昆兰与塔娜的一段陈年往事,引得昆兰前去塔娜家与她相会。在影片中,曼西斯打电话给塔娜向其询问昆兰是否在她家时也出现过这首钢琴曲。在电影行将结束时,昆兰在塔娜家以及昆兰饮弹自尽后塔娜与警探交谈完转身走进无尽的黑夜,这首自动钢琴曲的配乐又先后出现过几次。虽然这首钢琴曲在电影中的几次运用所表现出的艺术效果都有一些不同,但它都与每次出现时的具体场景没有明确的关联,似乎只是一个理性的旁观者,抑或是一张仅代表塔娜身份的标签。可是,我们却通过这首钢琴曲加深了它在每个电影场景中留给我们的印象,认为它本就是这部电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此,希翁进一步谈到,像这样的漠不关心的音乐实际上与电影的“机械本质”有着同构性,它揭示出电影本身最为真实的“机械面目”,还召唤出情绪与感觉的织体的“机械结构”。
四、结语
在瓦尔特·本雅明所言说的“机械复制的时代”来临之后,现代社会经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于是我们开始重新审视与考查我们的感知形式。威尔斯用一种具有开拓性与实验性的声音美学策略颠覆了我们对电影声音的固有认知,建立了一种崭新的听觉感知形式。毋庸置疑,《历劫佳人》精彩绝伦的声音设计为我们带来了视听上极大的审美愉悦,也给电影研究者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声音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