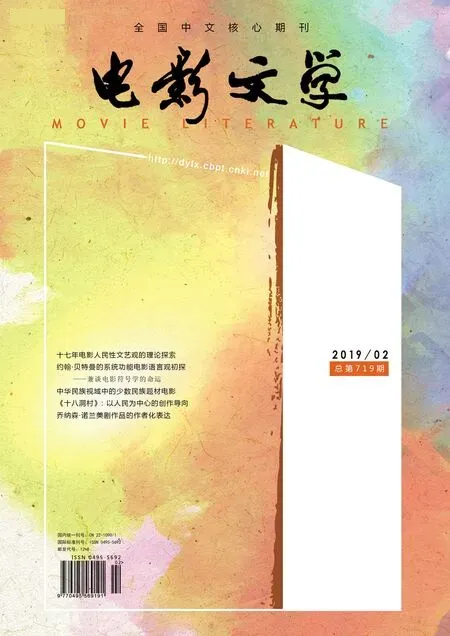电影《嘉年华》的主体构建与叙事呈现
戴思宇 吉 平 (陕西科技大学 设计与艺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21)
《嘉年华》作为一部典型的“叙述性影片”,它自身符号学叙事基调的形成与主体构建、叙事意象、叙事空间密不可分。导演文晏凭借细腻的女性视角,瞄准女性境遇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依靠人的外在形象和情绪表征,结合承载着叙事主体各种情感和欲念的叙事意象,构建出交织个人命运、原生家庭、男女性别、阶级意识的混沌空间。
一、叙事体系中的主体构建
女性的个体风貌和生存姿态作为独有的社会现象,是众多影视重要的创作素材,导演文晏也正是在这片创作宝地中打造了电影《嘉年华》的双套环式叙事体系。主人公小米小文的生活是相对独立发展的两个圈层,为了缝合主体构建间产生的叙事空隙,导演文晏将郝律师安置于双套环叙事体系的交叉部位,起到连接两位主人公生活的双向交流作用。另外,双套环式叙事体系分界点的建立,对应着两大阵营:刘会长、王队长、社会青年小建等人为代表的男性权力体系,他们是命令的输送方,要求女性在男性权威所辐射的范围中活动;小米、小文、孟母、莉莉等女性弱势群体,她们的生活已经被男性权力渗透,处处充满着消极的生活信号。导演文晏对这些不同年龄段人物的选用,也促成了主体人物多元格局的构建,进而也剥离出性侵案的实质——男性权力博弈下,女性被迫服从且饱受苦楚,正义公道的守护势在必行。
(一)男性权力构建:权威指令的发送
《嘉年华》中刘会长、警察、高官、医生组成的利益阵线,形成了负能量的集中营。刘会长作为性侵案的罪魁祸首,与《大红灯笼高高挂》中掌控一切权力的陈府老爷一样,以强权置身事外。即便正面镜头极少,“男人的权威性仍是一个缺席的在场者”[1],其命令式的腔调一出,强势地剥夺女性选择权的同时,也使男权同盟者有机可乘,颠倒黑白。诸位男性所处的行业虽然不同,但他们自私自利的举动与刘会长用财力置换自由的恶劣性质是高度一致的。这些涉事的男性都真实地生活在我们的视野中,他们既是恶势力的男性符号代表,又于广施淫威中用金钱和权力占据话语霸权。
(二)女性悲剧构建:情感生理的伤害
面对避之不及的男性恶势力,女性一方注定承受伤害。“黑户”小米,用超出同龄人的城府和成熟去求得生存,小文整日郁郁寡欢,天真无邪的笑容变为两位少女身上罕见的奢侈物。她们虽都予人以清冷的气质,细细一品还是大有不同。小文的“冷”中存有一丝纯真,可小米的“冷”,夹杂着冷漠和卑微之余,还不时地散发出一股忽强忽弱的孤傲之气。从小米对待性侵案一事先是冷淡,后又心虚躲闪的态度,小米情绪的复杂多变使得观众对她的内心世界捉摸不透。对于比小米年长的成年期女性——莉莉、孟母等人,观者则能从其鲜明的性格和生活状态中窥视到当代女性的底层生活风貌。穿着美艳、圆滑乖巧的莉莉惨遭男友小建出卖,落得“下辈子再也不要做女人了”的一声叹息;孟母的职业是舞女,性格较为暴躁,面对性侵案只能敢怒不敢言。这群被男性权力符码系统所操控的女性,愈是表面张扬,其内心焦虑和无力反抗的软弱意识,愈是快速得到曝光。女性主体自我麻痹、妥协不抵抗的懦弱意识一旦构建,被动服从和妥协迎合便会成为女性自保的首要选择,而这也使得大部分女性在遭受身心伤害后仍浑然不知,被冠之以“男权社会牺牲品”的标签。这种被丑化的符号削弱了女性的反抗情绪和行动能力,进而直接瓦解了女性自我拯救的力量。
(三)正面人物构建:公道正义的守护
性侵案受到权力发送者的拦截,侦破进展困难,小米小文的成长之路受阻。在此等困境中,导演文晏似乎感触到了某种正在觉醒的正面力量。于是乎,“新的主体构建作为一项自我赋权的重要行动”[2],自然而然地也就承担了反对现实恶势力、守护正义的使命。
就郝律师本人而言,她的身份设置近似于韩国性侵题材电影《素媛》里的心理医生。她的现身不仅仅是积聚影片的角色效应,更是呼应底层边缘群体中“缺位”的社会力量。郝律师除了专业素养极高、怀有仁爱公道之心,她的身上还流淌着一种可贵的双性气质。她每次出场都是一身西装搭配公文皮包,简洁大方中彰显着一种刚硬的男性气质。这种具有个性化特征的着装,契合律师职业的严谨特性,又暗示在男权社会,女性要想拥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像男性一样自立、自信。抛开律师的职业外衣,她又是一名普通的女性,有着不可多得的柔情。她本着尊重的原则,待小文如慈母般轻声细语安抚,对小米亦如长辈般教导和包容。导演文晏精心设置的郝律师一角,以男性恶势力的反对者身份现身,昭示自身对女性弱势力量的支持。
二、叙事意象中的意蕴营造
叙事意象是电影叙事艺术中极具包容性的影像符号,影像符号“能指”和“所指”关系的建立,物象与象征韵味的融合,有利于促成叙事意象外在特征与内涵表意的有机统一。在影片的叙事过程中,叙事意象首先对现实物象进行还原和再现,直观展示影像符号的“所指”。其次,叙事意象又是一“内心视像”,它通过对主体冥想和行为动作的真实观照,成功地具备了人性化的思想和观念,从而完成影像符号的“能指”。《嘉年华》中与主角紧密联系的梦露雕像、金色发套等叙事意象,面对来自主体人物强大的感情冲击,始终安静地承担着影像符号的表意功能,它们身为社会中“被看”的对象,化作欲望、情绪的符号指代陪伴在主人公的身边。
回顾影片里梦露雕像的第一次出现,导演文晏是借助主人公小米的视角来展现的。彼时,小米发现了梦露的高跟鞋和红色指甲,惊喜地在上面触摸、描摹,一旁的游人则把梦露雕像当作玩闹合影的背景。尔后镜头又多次顺着小米所仰视的方向,到达梦露雕像裙裾下方的私密处。这一处极具深意的镜头里,梦露雕像身上具有女性典型特征的生理部位被公开,而小米抬头、仰望、凝视,伸手拍照,一系列动作的发出,也直接展现了梦露身体的“被看”过程。“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3]在常见的影视作品中,女性的身体也常是“被看的对象”,男性往往是这种观看行为的主导者。导演文晏在《嘉年华》男性角色弱化、男性权力隐身的叙事背景中,一反以男性视角为主的叙事常态,将女性身体被异性所观照的传统设置转换成了身为女性的小米。从影片开头梦露身体被小米观察触摸,再到后期小米对莉莉身体部位的主动抚摸,“被看”与“被摸”动作的前后呼应,也喻示着物化的女性身体和实质的女性活体成为小米心中建构女性形象的参照物。然而迫于尴尬的“黑户”身份,正常的爱美之心成为不能见光的存在,小米把别人遗留的二手装饰物收藏起来,把对美的一切欲念与向往都搁置在自我的想象中。与母亲发生冲突的小文,深夜一人躺在梦露雕像脚下。两处简单的长镜头里,小文的情绪十分平静,梦露雕像保持其一贯的沉默。导演文晏用不带任何修饰的镜头语言来表现小文内心深处的颤抖和无助,颇有无声胜有声之效。
三、叙事空间中的符号呈现
“日常生活是一切活动的汇聚处、纽带和共同的根基。”[4]导演文晏以两位少女的日常生活为叙事重心,建造了从私人空间(家庭)到公共空间(校园、社会)的“两点一线式”的空间符号。在这两个关系错综复杂的生存空间中,“身份是处理意义过程的前提,自我是符号活动的产物”。[5]主人公所历经的原始成长环境关乎她们个体身份的形成,其后天的社会生活又最终影响到个体身份所做出的行为选择。因此,电影叙事空间作为主体人物活动、思想、情感的依附基础,它所关联的主体符号活动和叙事话语实现了对主体真实身份的呈现——小米的黑户身份,小文的离异子女身份。
(一)私人空间:“家庭”符号的缺失
电影《嘉年华》涵盖了三种原生家庭模式,第一类是以张新新家庭为代表的完整独生子女家庭,第二类是以孟小文为代表的离异单亲家庭,最后一类则是以小米为代表的信息不详、情况不明的“黑户”家庭。这三类家庭的集合是中国式家庭的符号特征,他们共性在于“家庭”的不完整,或是父母中有一方缺席,或是家庭教育缺失。
《嘉年华》中的父亲形象处于被弱化的层次,但他们对女儿产生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张新新的父亲为自己的事业,鼓励女儿拜刘会长为干爹,性侵案后又带着张新新屈服于凶手的金钱诱惑中;小文父亲是一个先抑后扬的角色,他曾在女儿小文的成长中缺席多年。初入观众视野,也是一派碌碌无为的作风,然而小文在绝望之际仍视自己的父亲为“最后一根稻草”的举动,使得小文父亲这一角色化为一种亲情符号回归银幕,转变成治愈和陪伴的温暖形象重新登场。反观《嘉年华》中母亲的形象,孟母对小文非打即骂,两人难以沟通且常常冷战;张新新母女向金钱妥协,充满着讽刺意味的同时揭示张母是男性权力下的臣服者;小米表面是最自由的孩子,实则是影片里最为孤独的一个角色。“三年前,我从老家跑出来,这是我待过的第十五个地方”,小米在不同的空间辗转,模糊的话语中透露着许多的不确定性和逃避因素,那个隐藏在她身后的不愿提及的家庭,是“空白”的。
以上原生家庭的种种恶况,破坏了少女们正常的成长路径。主人公小米、小文双双在成长的关键阶段失去父母的亲情关怀,她们所盼望的快乐和安稳总是遥遥无期,家庭内部的创伤致使两位少女的情感空间不断被压缩,与其相符的纯真无忧逐渐消失,最后直接促成小米、小文性格上的孤僻冷漠。
(二)公共空间:“社会”符号的混沌
对于家,少女们一度充满失望。她们急于挣脱现有的桎梏,幻想蜕去稚嫩的少女身份,并试图寻求某一种方法,在新环境中为自己找到暂时的解脱。校园本为自由纯洁的圣地,承担着教育和引导学生发展的使命。可《嘉年华》中的校园不似想象中美好,各种言语暴力和肢体暴力为主的霸凌现象盘踞于小文的校园生活中,加之单亲家庭的背景出身、老师的冷眼相待,小文的弱势性更为突出,因而极易成为被欺负的对象。随着小文单方面的反抗到男女双方的肢体冲突,再到小文被推倒在地和腿部伤口的特写,导演全程以一种俯视镜头给予展现,间接暗示成年男性对女性的嘲弄意识已蔓延至年轻的男性学生身上。同样与纯真校园生活形同陌路的失学者小米,则逃到一座海滨城市。“我喜欢这儿,因为这儿暖和,就连一个要饭的,夜里也能睡个好觉”。影片通过固定镜头和长镜头的反复使用,真切地表现小米瘦小身躯下所要承担的工作负荷。回视小米的生存境遇,边缘群体的卑微出身让她始终无法融入这里。年仅15岁的她,是这个表面温暖的海滨城市中真正的“他者”。
学校、医院等公共场域的不良作风,少女们日常生活的坎坷,无数问题的发生都是对社会符号系统内部男强女弱、利益至上、人际关系破裂丑态的鞭笞。男性权力不断彰显强化,促使女性在“被审视”与“被压迫”的痛苦之间不断游移,进而致使女性失去自身命运走向的自控权。在权力决定话语权归属、利益高于法律的社会背景下,以小米、小文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伤痛无处可掩,有冤无处申的状况更显渺小可悲,弱势群体的女性想要获得独立自信,拥有尊重和权益保障的愿景成为天方夜谭。
四、结语
《嘉年华》以少女个体的特殊境遇为主视点,连接其日常生活中所接触的各色成年人物,并透过这些主体人物的性格和行动表现,构建起主体人物的符号特征。此后,随着主体人物的位移开展,与之联系紧密的叙事意象,以积极的阐释作用现身,影片象征符号的意蕴得以传播至复杂的叙事空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