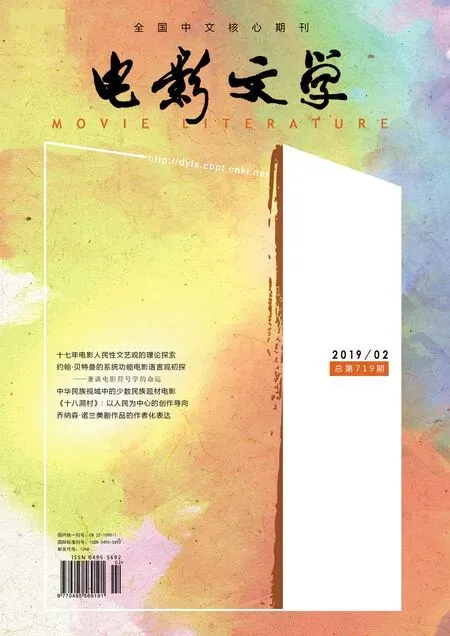电影《喊·山》对小说《喊山》的阐释研究
杜 娟 (天津师范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387;太原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喊山》是山西女作家葛水平的代表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2004年第11期),2007年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引发关注。一部小说的成功,往往会获得电影人的青睐。这部小说于2012年和2014年分别被改编成了电影《喊山》和《喊·山》,《喊·山》由80后导演杨子编导,曾获釜山电影节等多项大奖。
电影《喊·山》上映后,许多研究者已经关注到了这部作品改编后的差异及存在的问题,认为电影某种程度上未能与小说实现良性互动,与小说内涵有些偏离。但电影与文学的改编不能单从文学作品来看电影,应该从电影与文学作品的双重路径进行分析阐释,才能全面认识文学与电影的互动。本文从电影《喊·山》入手,来看小说《喊山》,探讨文学作品与电影改编所存在的差异及辩证阐释的双重路径。
一、电影对小说的改编
葛水平的作品以书写乡村世界为主,《喊山》也不例外。这是一部以乡村叙事为主的中篇小说,讲述了被拐卖的“哑巴”红霞,跟随丈夫腊宏逃到岸山坪,腊宏因意外踩到韩冲的雷管被炸死后,“哑巴”红霞与韩冲之间所发生的故事。小说直面现实,写出了以“哑巴”为代表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电影改编基本围绕小说的故事框架进行呈现。但在表现过程中,电影因其独特的表现方式进行了相应的改变。具体对比如下:
(一)电影对小说文本叙事的延续
小说之所以能够改编成电影,就在于两者对叙事的重视,都以叙事为核心。所谓叙事,“就是对一个真实或虚构的故事的讲述”[1],换言之,就是讲故事。电影和文学的核心都是讲故事,用不同的方式将一个好故事讲述给读者/观众,“将人不可言诠和交流之事推向极致”[2]。首先,电影延续了小说的基本故事情节,故事围绕韩冲和“哑巴”红霞展开,以腊宏的死作为其叙事推进的重要因素;其次,这部电影与小说都立足于乡村叙事来讲故事。从叙事空间来看,两者是一致的,小说与电影都以韩冲与琴花的“喊”为开篇,直接给读者/观众呈现了乡村的叙事空间,接着小说交代了“岸山坪”这个乡村区域,电影则用远视角的方式呈现出山区的空间状态。这种一致性让读者/观众能够感受到乡村空间传递的闭塞、落后,为人物的生存苦境奠定了基调;再次,从叙事技巧看,电影和小说同样用悬念来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小说文本一般用“召唤”结构,来唤起读者的想象,如《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安娜的神情为“生气的脸上”,何为“生气”?这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让读者来填充空白。《喊山》最后,作者写了韩冲入狱,“哑巴”红霞生活恢复平静,“屋外的阳光是金色的”[3],让读者有了想象的空间——她与韩冲的关系将何去何从?而电影《喊·山》最后以红霞成为嫌疑人为结局,也给观众留下了悬念,他们的命运如何?让观众自己去完成接下来的创作。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电影对小说改编时,以故事为基本依托,在叙事的人物、情节、技巧等方面都进行了延续。这种延续有助于强化和深化对小说文本的主题、叙事结构等多重理解。
(二)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变
1.从《喊山》到《喊·山》
电影对这部小说的改变中,首先是标题的变化。电影标题为《喊·山》,小说为《喊山》,区别就是分隔符“·”。从语言学角度来看,小说的题目“喊”与“山”构成了动宾关系,“喊”是发出的动作,“山”为“喊”的对象;而电影《喊·山》中“喊”与“山”不再是动宾关系,“山”不一定是“喊”的对象。这一不同让电影与小说的主题有了区别,小说是通过“喊山”这一具体的行为,表达了“哑巴”自我意识的觉醒,而电影的主题除此之外,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与开放性。
2.电影对小说情节的改变
从具体情节来看,在电影的叙述中,对小说的情节进行几处改动:一是电影一改小说中韩冲放置的雷管误炸死了腊宏,变成了“哑巴”红霞的阴谋,为结局做了铺垫;二是电影的结尾与小说结尾不同。小说的结局是韩冲入狱时,“哑巴”喊出了“不要”,哑巴成了红霞,生活恢复了正常,“屋外的阳光是金色的”[3],生活有了新的希望。电影中则是红霞举起“人是我杀”,将腊宏死的嫌疑转向了自身,电影此时还呈现了“哑巴”红霞与韩冲交往的画面,来展现她与韩冲的爱情,但结局如何,给观众留下了悬念。这是情节变化中最明显的两个地方。
3.爱情生活的强化
电影《喊·山》与小说文本相比,除了片名、情节的变化外,最鲜明的变化就是对爱情生活的强化。
小说结尾韩冲被捕时,“哑巴”红霞说出了“不要”,让小说达到了高潮。小说交代了“哑巴”不哑,而是被丈夫腊宏用钳子拔去了两颗牙齿,并加以恐吓,让红霞“失语”。至此,红霞不仅失去了自由,更丧失了作为“人”的权利——话语权,以至于红霞作为“人”的权利的彻底丧失。失语的状态再加上被拐的事实,加重了红霞的悲剧色彩,更是对乡村空间中女性悲剧命运的延展与强化。在福柯看来,话语受到了外在的限制,如权利和性,而红霞正受到这两种外力的压迫。葛水平在小说中更多展现的是对红霞在“失语”状态下生存的困境,最后的发声代表了这类女性能够成为真正的人,找回了权利,走出生命的苦境,这也是作者对这类底层女性命运进行的关照。
电影《喊·山》未能延续这一主旨,通过最后结局“红霞杀人”的转折,吸引观众。红霞之所以要说出真相,动机来自与韩冲的爱情,这直接显现了电影对爱情的强化。电影用了许多铺垫来讲述两人的情愫,如“哑巴”红霞在韩冲家对猫抚摸的瞬间。这些让观众在两人情感的推进中感知剧情,红霞与腊宏不合理的婚姻,成为她与韩冲之间情感关系发展的最合理化的因素。小说中,爱情成为红霞摆脱悲惨命运的力量;而电影中,爱情成为剧情发展的关键,也为结局的突转提供了阐释的空间。
不少研究者对《喊·山》的这些改编不太赞同,如边静《〈喊·山〉——历史与现实的进退失据》一文认为“从小说到电影(2016版)是一个市场化、庸俗化的过程”[4],还有的认为其脱离了小说文本,呈现了“消隐的乡村”“被想象的乡村”……这些观点值得商榷。电影在对小说文本进行改编时,有变化是必然的,因两者媒介属性与审美属性不同。我们看待电影对文本改编时,要认识到电影到文本的阐释作用。
二、电影改编与小说文本的阐释
小说文本的电影改编,是文学研究者和电影批评者都在关注的一个领域。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纷纷登上了电影银幕,枚举数例,如鲁迅的《祝福》《阿Q正传》、巴金的《家》、钱钟书的《围城》、杨沫的《青春之歌》、莫言的《红高粱》等。文学文本给予了电影素材,而电影对文学作品进行二次创造,许多文学作品正是因为二次创造才获得关注。如何正确看待电影对文学的阐释?这是值得思考和关注的。
(一)电影对文学文本的“忠实度”
电影改编的“忠实度”,是电影对小说文本进行改编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德国的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非常重视文本的“忠实”。他认为:“忠实不等于逐字照搬,忠实意味着:尽管对原作有所改动(部分是出于银幕改编的需要),改编作品仍然表现了一种保全原作的基本内容和重点……”[5]他认识到“忠实”一方面是故事叙事的忠实,另一方面是电影对小说文本中的“空白”进行电影化的呈现,这正是对电影改编和小说文本的辩证态度。换言之,电影在忠实于文本的基本故事外,可以对想象的空白进行二度创造。电影完全忠实于小说文本是不可能的,因为二者的媒介形式和呈现方式不同,改编自然也会有所区别。
电影和小说基本故事一致,从这一点来看,导演和编剧基本把握住了基本的“忠实”。对于文本的改动,《喊·山》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电影为了更好地与观众达成共鸣,在主题上进行了扭转,不再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而变为爱情的展现。张艺谋对《红高粱》的改编正是如此,改变了小说中生命、爱情、人性等复杂内涵,90多分钟的电影叙述中,选取了“生命”这一主题,刻意规避了多重主题内涵,易唤起观众。《喊·山》也是如此,这不仅是市场化的需求,更是电影表达的创造与选择。
(二)从电影来看文学的逆路径
在研究文学与电影改编时,研究者习惯性地从电影文本到电影,用小说文本来衡量、看待电影改编,这就容易进入误区,只关注电影对文本有多大的改动,忽略了电影对文本的阐释及补充作用。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作者B·瓦西里耶夫认为:“导演毕竟不是把一部作品本身搬上银幕,而是把他自己对这部作品的理解搬上银幕,即使一种不自觉的理解也罢。因此,所谓创造性改编——不是复述,不是转述,而是一种阐释。它力求达到两位作者的交融.从而产生一个新的世界——具有独创性的银幕世界。”[6]电影改编体现得更多的是电影对小说文本的二次阐释。
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读者在同样的小说中可能看到不一样的主题。电影在选择小说文本进行改编时,也要进行编剧和导演的阐释,这就可能带来与小说文本不一样的主题书写。《喊山》中,从哑巴“红霞”说出“不要”时,表达了作者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呼吁,但从电影的结尾再回归到小说文本时,也可以在其中找寻到红霞与韩冲隐现的爱情情愫,从这个角度来解读文本的主题也未尝不可。另外,电影的视觉叙述,让小说文本的抽象变得具体可感,读者对小说中需要苦思冥想的情感变成逼真的呈现,对予小说文本的空白进行了“召唤”和填补,《喊山》中,红霞是如何进行“喊山”的,电影给了答案,直观生动。从电影到小说的逆路径,可以看出电影改编的变化是对小说文本的一种补充。
电影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因其特殊的表现方式和审美效果,让观众不再进行艺术审美的膜拜,变成了直接再现,强调得更多是消遣性接受,这在本雅明的《机械复时代的艺术品》中有过精辟的论述。
三、结语
在以往对《喊·山》的研究中,研究者依旧以票房论英雄,票房低就意味电影改编的失败,这恐怕有些偏颇。有些电影不是票房可以衡量的,票房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如电影《喊·山》。首先,小说《喊山》本身以乡土书写作为立足点,这就决定电影的票房不会超越以英雄叙事、城市情怀等为主题的影片,受众相对较为小众。其次,这部电影属于文艺电影,票房从来不是文艺电影的噱头与追求。而艺术表达才是核心。最后,《喊·山》已经有电影《喊山》在前,这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观众的新鲜感。
通过分析,研究者对电影《喊·山》从改编角度进行分析时,往往拘泥于文本到电影的单一视角进行考查,忽视了电影到文本的逆路径,未能看到电影对小说文本补充与二度阐释。研究小说与电影的互生关系,应注重两者相互阐释的双重路径,辩证地看待其作用,《喊·山》就是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