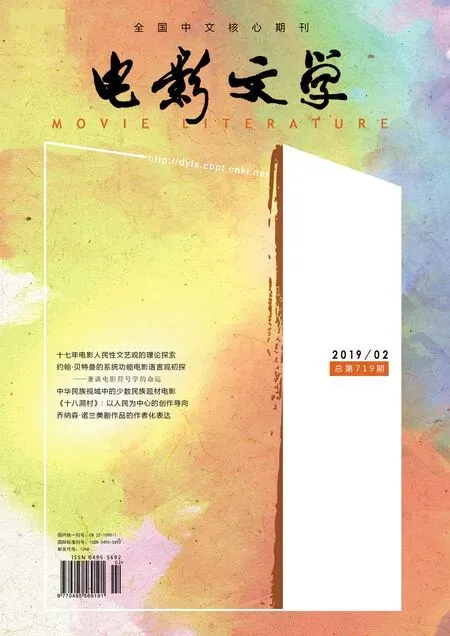微电影《筷子》的符号与文化解析
李 曼 黄 莎 (重庆邮电大学 传媒艺术学院,重庆 400065)
微电影最显著的艺术表现特性是见微知著,通过凝练的电影语言,能将大量“留白”的时空建构于观众的想象的感知之中。换言之,与传统的大电影以及多集影视剧相比较,微电影所具备的认知行为性质更加强烈。观众能否在短短数分钟的时长内正确理解影片的意义、体验创作者的主观情感、欣赏影片的形式审美价值,或者是感悟到微电影那没有言明却足以触发人无限想象的旨趣,都要从影片的画面、叙事和镜头影像所呈现的各种符号中去寻找答案。目前学界大都承认,现实中的事物与镜头里的符号不能简单等同,当影片里出现的各种符号倾于观众真实可感的东西(传统、历史、意义、文化等)时,其中所蕴含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已然超越了它们自身所指涉的科学实体,大都包含着人类丰富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符号学的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符号学家查尔斯·S·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将符号(英文sign,或译为记号、指号)界定为一种对象,这种对象对于某个心灵而言指代着另一对象。皮尔斯还指出了符号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如符号具有属于其本身的性质、必须与其所意指之物有某种真实联系,必须被心灵视为一个符号[1]。也就是说,符号有其特有的本性,亦因其纯粹的指示性与象征性而被人的心灵所感知、认可与接受。如此,符号自然作为“语言”,或者说是“电影语言”的客体,自20世纪出现的语言学转向以来,承载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吸引着众多电影理论家与制作者探寻的目光。而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与符号学分析的思潮,又标志着跨学科研究在电影领域攀上时代的浪潮,学者们着迷于用符号学的原理与方法来分析与看待电影符号所呈现出的文化现象与象征意义。一方面,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索绪尔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视角对符号做了系统研究,使符号学的研究越过以往对经验现象的分析,涉及对符号与意义关联更深的文化生活中的语言学探索,当先在文艺理论领域掀起了一股新的研究激情;另一方面,弗莱格的分析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与皮尔斯的实用主义哲学等均对符号理论做出了深入探究。尤其是皮尔斯所提出的符号理论更是力图使电影研究从语言学的影响中挣脱出来,主张电影符号研究不仅仅是考查一种实证性的意指表意的方式,更是对电影的“影像思维”所折射出来的,范畴的界定、认知、反思与现实的构成、呈现、赏鉴之间的多维关系的研探。在这里,本文试图借用索绪尔与皮尔斯与各具特色的符号理论来读解公益广告微电影片《筷子》(麦肯光明广告有限公司于2014年为央视春晚制作),进而阐述影像中的符号与文化现实的复杂联系。
一、符号学理论在微电影研究中的应用
对于符号的探索,自从意义被认定为是由语言创造和表达出来的“语言学转向”以来,便在电影影像分析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吸引着众多电影研究者的注意。作为现代语言学奠基者的索绪尔,他的研究重心在于剖析语言符号的结构,故其学说被称为符号学(semiology)。符号学理论广泛涉及电影表达层面的词汇、词义、语法、语言、结构等概念与问题。按照索绪尔的划分,语言现象略分为三组对立的概念:历时性(diachronie)与共时性(synchronie),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能指(signifiant)与所指(signifier)。在索绪尔看来,这三组对立结构里涉及的六个概念都很重要,是研究语言结构必须注意的问题,但重要程度却有明显的区分。在第一组对立结构中,索绪尔反对以往只着重对个别的、实在的、具体的语言现象的演变做时间连续性的、历史纵断面研究的理念,认为一个集体意识能够在特定时期超越对象的内容或意义,感知到语言系统并存的各项要素间诸如逻辑、接连、构建、心理等复杂的关系,转而主张语言结构研究须着眼于从整个语言系统的总体法则、各组成部分在结构、功能与诸要素同时并存层面上的关系,去厘析语言的结构系统本身。这组对立的关系,在微电影现象中,一部影片的镜头影像作为“言语”只能在其民族文化、语言结构中,直接的是在人们习惯了的电影语言表现规则中才能成为可以被认知和理解的东西。民族文化、语言结构以及电影语言的结构和法则是影片潜在性的本体,镜头影像乃至整部影片的影像叙事,则是对这种本体的具体呈现。如此一来,共时形态中的微电影语言,包括结构与法则在内,自然都被视为一种在形式上凸显的整体,凭借其在影片中展示的符号元素,组成一种足以用来描述或体现其文化的深层含义与操纵准则的“代码”。在第二组对立中,索绪尔将语言的整体系统视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而与之相对立、代表个人意志并对语言进行运用的言语则被视为语言行为的个体部分,因无法直接体现出社会文化意义而不能成为语言学的基本研究对象。如微电影中诸多镜头段落皆有的具体、独特、千差万别,甚至是对立的“言语”,但从宏观上来讲,它们具备共同的内在结构,这个相互关联的内在结构就是指电影语言的整个系统,因而具有符号的功能。所以,将索绪尔的理论应用于微电影中,研究者就不能生硬分离电影语言这个由语法、语义等元素构成的完整系统,而是去分析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并在这种关联、制约和对立中去确定背后的深层含义。所以,微电影语言中那些实在符号的闪现、叙事结构上的并存,以及镜头形式中的安排,展现在影像中时,实则是一个由结构组成的体系,而影片表现出的各种“言语”就是依靠这种“一般”于其中创造意义、价值与审美的系统。这个系统也正是电影研究者必须重视与探究的基础,它须在第一组对立里所强调的共时性层面中展开,唯有如此,研究者才可全面而综合地比较影片中出现的各种语言体系。第三组对立是能指与所指,即表现形式与概念意义。如果我们依照索绪尔的划分,在微电影中出现的符号有着声音、画面等介质,这便是符号的表层因素——能指;而由这些声音、画面或符号本身对应或指涉的意义、概念则为所指,二者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没有客观的本质上的联系。比如,在微电影《筷子》中频繁出现的主题符号“筷子”,在现代中文里叫作“筷子”,在古代汉语与日文中称为“箸”,英文又是“chopsticks”等。可以说,这些称谓就是能指,而所指则为由我国传向世界的、一种代表中华饮食文化的独特餐具。如何称呼这种餐具,则是由各国特定的语言习俗而定的,要理解符号的指涉功能,即产生意义的功能,还得回到符号本身中去考查它与别的符号之间的区别,如前述的同一概念(中华的一种餐具)与不同能指(筷子、箸)之间的差异。而在影片中,筷子这个符号与其所指的概念并无必然联系,二者的关系因而是任意的,观影者的着眼点不会放在这个物件客体上面,而是去探寻筷子在影像中所呈现的意义。秉着对共时性的尊奉,索绪尔的符号理论不会留意孤立、单个的符号,他所提倡的是对能指与所指间的关系、结构的探求,是去挖掘符号在电影语言中所创造的审美与意蕴。从索绪尔的符号理论来看,影片中被加上诸种表现效果的显在现象“筷子”,频频出现在各种场景之中,披着能指的外衣,却非一个独立实体,亦不是影片读解的核心;而“筷子”背后那些看不见的风俗惯例、相沿成习的规约或蔚然成风的规则、代码的组合,才是影片探寻的深层文化蕴意,这些皆与影片的创作者与现实客体无关。这也便是结构主义理论应用于电影分析的最为显著的观念。而进一步厘清表达层面的能指与符号分析层面的所指之间那种并不严格对应的结构关系,阐释其共时性聚合体的“聚合关系”与历时性结构段的“组合关系”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对立,还须借助符号学中其他一些理论。在这些理论中,皮尔斯的符号学主张从镜头展现的符号中去透视约定俗成的法则,求索屏幕画面中符号的意义所形成的集体意识与认知过程,为电影研究中探寻认知与现实、文化与审美、社会与个体、影像与现实间的真实关系提供了帮助。
在皮尔斯看来,符号中蕴含着观念和思想,但它们是依靠人们对符号的解释而达成的。这样,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二元对立,被皮尔斯加上解释项或解释元,扩充为符号与其对象在解释的关系中形成的一种真实的三元关系。皮尔斯认为,符号所代表的意义并不存在于人的直接感知里,它往往是一种习俗、一种集体心理、一种审美认识、一种文化沉淀对这一直接感知的解释,这些抽象观念是被具有物质属性的符号映射出来,因此它们的实质就是一种符号关系,而符号到解释为止才被赋予了意义或价值。如,《筷子》中“筷子”同时在不同的镜头段落中,指示出微电影制作者希望宣扬的“启迪—传承—明礼—关爱—思念—睦邻—守望—感恩”八个主题思想。每一思想观念都是由着上述三位一体的关系所确定的,观众看到的“筷子”就是一个感觉的符号,它依靠解释并与后续主题思想同存关系的解释而被赋予不同的文化意义。我们看到,在第一组镜头段落中,老人用筷子蘸调料逗喂婴孩的画面,便产生出婴孩(对象)—符号(筷子)—解释元(启迪)这组三元关系。而第二组镜头段落里,小女孩在家人的指导鼓励下学会用筷子,三元关系又转为小女孩(对象)—符号(筷子)—解释元(传承)。之后的解释循环接连阐明后续的主题思想,显示为种种不同的符号,象征出多样的文化意义。每一次的解释,“筷子”这个符号甚至是小女孩儿等对象便与主题思想等同起来,观众如其所是地理解镜头、体悟画面,将他们潜意识认知的符号本身与真实世界对应起来。所以,在微电影里宣扬的主题思想并不是观众的意识或认知对于一种抽象观念的直观认定,而是涉及诸种意义和丰富解释的一种文化理性。筷子这个纯粹的实在之物是第一性,而它与不同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第二性,当沉积于集体意识中的文化理性渗透进来解释之后,终将前两项联结起来并塑成微电影的镜头组段,连续表征出不同的三元关系。所以皮尔斯越过了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立足于一种更为切实的意指性。为使符号产生意义,这种意指就不会是任意的,如同影片中的老人用筷子让尚无明确自我意识的婴孩体味人生五味——意味启迪,家长教导小女孩儿使用民族特有的餐具——意味传承那样,筷子与不同的对象间确实存有客观真切的实在关系。
皮尔斯根据他所主张的客观实在范畴的三性(事物的纯粹存在,两个事物间的二元的或互动的关系,以及多个事物间的三元的或表象的关系),采用了三种三分法来划分符号或指号。第一种三分法是将作为一种实存的符号分为质的符号、单一的符号和法则的符号。在《筷子》中便是“筷子”这一符号本身了,它本身不具深义,但具化在影片中时,由传统习俗与集体意识所约定与认可,成为特别的或一般的类,便拥有了不同的意旨。第二种三分法是依据符号与所指对象间的关系,将符号分为图像、指示与象征。我国学者李幼蒸将之应用到电影语言之中,译为更贴近电影研究的术语:肖似记号、指示记号与象征记号。李幼蒸指出,肖似记号是指表达者与被表达者在外形上的相似。象征记号是指二者之间的意指性联系,是约定性和非“理据性”的。指示记号是指表达者与被表达者之间的联系,既非由于形似,也非由于社会习惯或约定,而是由于二者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2]。尽管李幼蒸认为肖似记号出现在电影中的频率最高,但《筷子》里象征文化传统的符号关系却是最为明显的。影片第三组段里的小男孩上桌准备用筷夹菜时被父亲阻止,教导男孩儿让爷爷先动筷,随后长者举筷说了祝福语,后辈们方才用餐。这一段中,筷子在外形上与其被表达的主题思想“明礼”毫不相似,更没有表征其相关的外在属性。然而影片画面具备一种含蓄的隐喻和意指的功能,将传统文化中敬老的普遍观念融进镜头表现之中,这就不仅指示出“筷子”与“明礼”之间共同具备的质,还借助社会规约与习俗,象征出筷子所意喻的深义。在此,“筷子”的“明礼”理念存于对画面的想象和暗示之中,生出不同于之前的“启迪”和“传承”的内涵,最终经过镜头画面的再解释,构成一种新的、特别的类质。正因为意义是构建的,所以符号总是阐释着另外的符号[3],根据不同的语境指涉、象征着不同的意义。而全片其余组段也正是借此类表现手法来展开的。第三种三分法是将符号分为对主题进行陈述的述位符号、指涉实存对象的命题符号与解释着在其解释方式中所显示的论证符号。这三大类划分在皮尔斯的符号理论中时常交叉组合,形成更多的亚类,扩充为更具丰富意味的符号分类体系。在《筷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类型的符号,也被应用于指示“筷子”这一符号所代表的文化意义的象征。但总的说来,“筷子”在该片里与它所指的八个主题观念都有着某种可比性,即带有相同的质,且有着真实的联系。“筷子”必须具备这种实际存在的物质属性、其所蕴含的深层文化意义以及指示性的审美价值,才会是实在真实的,因而也才能被观众所读解、接受。
二、微电影符号中的文化与象征
微电影《筷子》中最突出的符号自然是日常生活中观众再熟悉不过的寻常之物——筷子了。那么,筷子这一符号如何与其在影片中指涉它本身所具备的多重属性,分别对应、象征不同的意义而被观众接受的呢?这是因为,象征“借助法则和常常是普遍观念的联想去指涉对象,这种法则使那个象征被解释为指示那个对象。……它不但自身是普遍的,而且它所指称的对象也具有普遍的本质。因为它是一般的,所以它存在于它所决定的实例中”[4]。这即是说,微电影中的符号必须依赖于属性与意义之间勾连的文化逻辑与因果关系,才能显现出其内涵与价值。如在该片那八组代表中华传统美德的不同镜头组段中,每一个段落中出现的“筷子”就是一个质的符号,且只能借助影片的叙事、画面中的主题字幕以及表达深层文化含义的不同影像来指称一个主题思想。影片中交替地用筷子来描述、串联的八组主题是:用筷子让婴孩儿品味人生初味的“启迪”、教小女孩儿使用筷子而得的“传承”;让小男孩子学会敬老尊老的“明礼”;游子归家用筷子品尝家乡饭的“关爱”;在过世双亲的灵位前上筷祭仪所示的“思念”;增添一双筷子邀请孤老吃团圆饭的“睦邻”;小夫妻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准备小筷子的“守望”;祖孙俩用筷互相布菜所体现的“感恩”。我们注意到,筷子这个符号每次出现都体现出一种特定指向的质。如影片的第四大组合段中,在大雪天赶回家乡的男青年与其母亲的温暖互动,三年未回家的他拿起筷子夹食母亲所做饭菜,而其母亲则自豪又宠溺地说就知道他爱吃才做的这个菜。这组镜头于此时在屏幕上点明的主题词只能解释为筷子这个符号本质所指的意义——“关爱”。“关爱”这个质的感知,使得这位男青年跳闪出现在后续的段落镜头里,将头依恋地靠在母亲肩上时,他手中再次跃入观众眼帘的筷子便成为一种仅指示“关爱”这种观念的单一符号,它也只能解释所指对象的其时其义,并且受制于影像画面中所蕴藏的理念与主旨,在这个镜头段落中自然就无法指示出“启迪”“传承”“明礼”等别的主题思想。这便是运用筷子这个符号来指向诸命题的各类深层象征在影片中的应用,即用筷子不同的质来指向与之相应的不同对象。
如此,筷子这个符号便与它欲指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元素之间建立了一种实际不能观看、碰触、描绘,却是客观真实存在的因果逻辑关系。这种关系并非直接诉诸观影者的心灵显现,而是实存于文化沉淀之中,而符号在作用于人的意识、构建不同解释的过程中便将抽象的主观理念转化为客观实在的意义。这种意义具有精神性的指示功能,这也是皮尔斯所坚持的符号实在论的根本所在。更具体地说,人们为什么能够轻易解读筷子这个符号在影片中指示的诸类中华传统美德?便是因为筷子与“启迪—传承—明礼—关爱—思念—睦邻—守望—感恩”等质之间具有实在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抽象的又是真实的,且依靠不同镜头段落影像解释元,指向一种特定的社会、风俗、文化的意象。如在影片的第五组合段中有13个镜头,第1个镜头是旧金山华人街过年时街角的一处全景;第2个镜头是一位老人在窗后观看的近景;第3个镜头机位反打,中景补写老人的观看;第4和第5个镜头分别是老人独自翻看家人相册的近景与中景;第6和第7个镜头分别是老人接到朋友电话、相约夜晚聚会的中景与近景;在第8个镜头中,老人放下电话,远景出现他小孙女的相片;第9与第10个镜头是他为祖先灵位上香的全景与特写,而第11个镜头中,则大特写表现老人将一双筷子放在灵位前;第12和13个镜头中,老人给逝世的父母拜年,画面最后点出“思念”的主题词幕,显然是力图借助这组镜头来传达老人祈愿在精神上可以与逝者沟通、团聚的相思之情。若按剪辑技巧来看,这组段落的多个镜头组合与景别变化(2与3、4与5、6与7、9与10、12与13)显得略微有些冗长,显然是从多个角度去展现同一个动作,就如同将同一句电影语言描述了多遍那样繁杂。然而,第11个镜头的大特写却是神来之笔,筷子终于进入画面,发挥了其“论证符号”功能。即,通过华人普遍知晓的传统风俗,或是积于集体潜意识的文化心理,指示出老人邀请逝者用年夜饭的命题,最终将之化为“思念”的象征。在这个象征的含义里,包含着独特文化惯例的规约,它是体现一类文化象征的符号。身受中华文化洗礼的观众自然可以轻易理解并接受影片借用筷子传达的喻义,将之与“思念”的主题相连接。而不熟悉中华传统文化中有着遥祭祖先之礼的观众看到这里,也可以通过回忆前面的镜头中老人翻看相册、想念国内亲人的举动,来解读灵前上筷的祭仪,借助人类共通的文化心理与审美意识,至少能明白影片在这里指涉的是一个民族的一种特定的传统风俗,体会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即使已近人生终点,却依旧满怀眷念地缅怀双亲、牵挂故土的悠长情怀。至此,“思念”这种观念自身便成为一种符号,它不仅在影片中是一个对象,且与筷子这个符号产生的新质对应起来,在观众的思维中激发出新的感知,从而感受到筷子指示的“思念”符号的物质文化特性。
按照皮尔斯的学说,观念一旦达到意识时,二者之间的实存关系仍然存在。这是因为解释项可以无限延展,这就说明了符号的意义何以是开放的、不可穷尽的。而在每一次具体的意指实践中,解释项则决定了符号意义最终落在何处,且它也最能体现符号的文化规约性[5]。就以《筷子》而言,不同的解释元会产生新的指示符号,无穷无尽地象征出新的文化意义,而影片中不同影像的编排正好印证了皮尔斯所提的概念。这些意义是并存关系而非替代关系。首先,筷子是由两根细小的竹棍组成,不管它在影片中的尺寸宽度和外涂色彩有怎样的不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两根筷子协同配合才能自如使用的普遍观念已深入人心,不能分离的筷子就在无意间与“团结”或“团圆”等观念连接在一起了,组成了新的质。这种质的特性是恒定的,在逻辑上与理性上是真实的,不会因为新质的出现而泯灭。就像筷子在微电影的第七大组合段中指示年轻的父母对新生儿的期盼,希望能一块儿好好“守望”未来与其生命的延续时,筷子这个符号在之前指涉的“启迪”“传承”“明礼”“关爱”“思念”“睦邻”等实际存在的质与象征对应的关系一直刻在观众的脑海之中,并没有因新的观念、新的质在人意识中的形成而消失。所以,必须两根竹棍同时使用的筷子,是一个完美的符号,因为它为一种特有的文化观念达成了连续、合理的解释项,而且共时地让每一个解释元都拥有各自的意义。筷子这一符号就此成为种种象征,凭借影像画面的解释与字幕主题词的标志,构建起其成为符号的文化品质。因此影片的结构虽然极其简单,但影像符号的显现已然真实再现出如其所是、应被理解的诸种意蕴。其次,我们注意到影片的八组横组合段拍摄的是广州西关、上海长宁、福建永定、佳木斯东胜、旧金山唐人街、四川宣汉、济南历城、北京东城区八个不同的地点。它们之间的地理位置相隔很远,包括饮食在内的诸多地方文化亦各不相同,人物的身份、家中成员、经济能力、所受的教育程度也存有差异,但这八段中的人物皆居于或回归到同一处空间:家。这个空间对筷子符号的使用虽有一定的限制,但也更清晰地标志出它在这个文化场域中才具备的特定的品格。如果抽离“家”这个特定对象,很难保证筷子所指的“团圆”等文化观念还有此特性。加之影片中的八个小故事发生的时间都在国人最重视的春节前后,也就加强了筷子作为符号在特定文化体系中所发挥的象征作用。再则,筷子本质上具备的不能分开的物质性特征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联系是间接的,因为二者在表征上不存在酷似性。但皮尔斯认为对符号的解释源于社会习得的习惯,而符号的含义来源一种活动,这种活动由言语游戏来表达,而言语游戏则扎根于社会性和历史性上被确定了的生活形式之中[6]。在微电影的言语游戏中,扎根于这种社会、历史、生活的习惯,驱使影像勾勒出创作者与观众的意识中潜藏的观念,并借助影片传达的文化理念,以屏幕画面为媒介,最终以筷子这个符号为引,孕生出前述的观念。可以这样说,这些隐喻的文化观念是由人对筷子的不同感知而激发的,而影片中反复以各种景别和多个角度出现的各式使用筷子的行为,反过来又让人依靠镜头再现了这些观念。在影片第八组段镜头中,祖母用筷子给小孙子夹菜并送出祝福语,后者依样回敬,来回两次之后,四周众人笑口称赞,屏幕即刻跳出“感恩”的主题词字幕,以示小孙子回报祖母的关怀。在物理外形上,我们很难将筷子符号与“感恩”的观念联系起来。但影片的创作者将祖孙的互动,尤其是小孙子为祖母布菜并祝她长命百岁的影像记录了下来,创作者想要的就是这种体现回报的感恩之心。筷子于其中发挥了中介的功能,将小孙子的感恩之心展示出来,而最终的镜头画面就是创作人与观众想要看到的事实,满足了他们认知与体验的需要。可以说,筷子与“感恩”之间的逻辑事实与因果关系是因作者与观众对文化观念的感知、体会、理解与接受所引起的,而这些深深沉淀在集体意识之中的文化观念又先于一步,使人用镜头展现它。筷子就这样成为指示、象征、承载传统文化与美德的电影符号,依据其多质又相继串联的数种观念,将中华传统文化这根历经风霜的坚韧常青藤,绽放出的那一朵朵韵深又意美的花,描绘得尽善尽美。
三、由再现符号之外引发的审美价值
无论是探讨索绪尔所提出的“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还是着眼于皮尔斯添加的“解释项”或“解释元”,我们都可以看到,微电影的创作对符号与其指示之间所对应的社会、文化的观念及其表达形式,都极为注重。因为,其表征不仅指向现实世界中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还构成各种具备审美意义的独特的文化意象。微电影展现在观影者眼前的意象就此具备了假定的真实性与带有隐喻性质的象征性。《筷子》蕴含着浓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象与民族精神风尚,镜头表达更是透出特有的诗意情怀,以及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崇敬之心。叙事与影像中符号的运用独具匠心,使得符号与观念的再现、对应关系可以被观众轻易接受,艺术表现形式也激发出外在于符号本身的、足以触及心灵的美感。该片的第二组合段“传承”与第六组合段“睦邻”便是绝佳的例证。
“传承”中,使惯勺子的小女孩按妈妈的教导学着使用筷子。最初她无法自如操作,眼睁睁看着近在咫尺的佳肴却无法享用,因而急得大哭,连连摇头摆手说使筷子用餐不好。然而妈妈温柔地言说,中国人(吃饭)都是要用筷子的,并手把手耐心教导女儿拿筷子夹菜吃饭。当挂着泪水的小女孩最终颇为艰难地自己用筷子将菜夹到碗中并大口吃下去时,摄像机奇妙地移动,用略仰式的拍摄角度将近景转为特写,使小女孩微微侧抬的脸庞出现在屏幕最为显眼的位置。景别与视觉的变动使得所刻画的人物更显丰满、鲜明,观众可以轻易察觉到小女孩自然露出的微妙神情。这是一个充满无限希望、刚刚开始成长的生命,发自内心地对己身能力的认可,更是一种对民族文化延续的赞叹。潜移默化般的传承就发生在妈妈有意无意教会女儿使用筷子而后者小小骄傲的瞬时之间。小女孩手握筷子就如同联结了中华文明之源,她自豪满足又纯真可爱的神韵,随着之前滴落的不甘眼泪,与学习用筷不稳时滴到小下巴上的酱油,融进悠扬响彻的乐声里,极其可爱地润进了所有观众的心灵之中。筷子象征的“传承”的观念,就这样超越于物质符号以外,在承担指示功能的同时又成为一种审美符号的在场,感动着所有接受这种艺术编排与文化阐释的观众。反过来,筷子所指示的这种抽象性质的“传承”观念,便以更真实、更具诗意与生命活力的唯美感知,化为美的艺术表现形式;人们从古至今皆认可的传统文化意旨也因此转化为共同的心灵体验。这有些类似于我国美学家李泽厚所说的:“内容沉淀为形式,想象、观念沉淀为感受”。[7]
“睦邻”这一组合段更是表现了人性的关怀。在这段叙事的11组镜头中,我们体验到一段简朴却至深的大爱。画面组接极其简单,就是人丁兴旺的一家人邀请孤老一块儿过年,重复台词“多个人,多双筷子”以指示出其象征含义。然而画面信息的递进与故事的展开都显露着微妙的设计,以唤起观众的审美感知与共鸣。如,孤老在门前侧身打量邻居的子女和亲属接连进门时,眼里情不自禁露出的羡慕与寂寞,最后打算迈进家门的邻居在高兴之余突然想起什么,然后转身邀请孤老一块儿用餐;孤老倔强地拒绝说他已经煮了饭,邀请者顺着劝说知道他煮了饭,但仍真诚地用“多个人,多双筷子”的亲切乡话拉着犹豫的孤老进门;进门后,邻居的家属也用同样“多双筷子”的话热情迎接,打消了孤老的拘谨;餐桌上,当孤老看着邻居利落地摆上一双筷子,环顾四周的热闹场景,故作镇静地微微垂头、悄然抹泪时,相信每一位看着这个场景的观众都会忍不住在心酸之余又感温暖。尽管这个故事的时长很短,也没有别出心裁的叙述手法,但我们为什么会被深深感动,体会到一股难以言喻的厚重的美?那就是我们可以从“多个人,多双筷子”的台词与最后摆放在孤老面前的实物“筷子”所指的深沉情感中,真切感受到了一个情感被外化、象征了的审美符号。通过“筷子”,我们所体会到的这种审美情感不仅在屏幕上有如画龙点睛般映射了出来,还有如泉水般激涌喷发,有力地传达了出来。孤老抹泪的举止也成为一个在场的符号,同样蕴含着审美的性质与情感的真诚。这种性质代表着一种民族的深沉情怀与优秀品德的理想之美。正因为这种理想,“筷子”从单纯的象征符号提升至审美符号,展现出更为广阔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对生命的呵护,体现着平等友爱的大德之美,蕴含了中华传统文化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这种对生命的尊重与爱护的美,外化于“筷子”这个符号之上,诗意地象征出中华民族的纯朴、质美和对至善的向往。这种民族文化与生命道德理想的融合,也就铸就了真正的崇高之美。
观众在观影活动中得到了美的享受。而审美符号在观众的审美情感中起着主导作用,若有似无地激发着他们的想象、联想、思考,将其无意识接受到的道德感知转化为审美体验。“筷子”在让观众获得美感的瞬间,实则诱发出潜在于观众心底、平时较为淡化却彼此内在相连的普遍观念。它引导着观众的思想和情感,将象征与审美符号统一起来,使普遍观念在短时间内得以强化,由此孕生出更强烈的亦是人们早已习惯的精神联想。这样,“筷子”经过孤老的行为活动,在逻辑上演化成了人的思想的可能性、人之感觉的一种习惯性联想。而正是这种普遍性,超越了个体情绪的表露,成为一种能被所有人都普遍接受的情感。而这恰恰就是《筷子》通过微电影所具有的精练、简洁、“窥一斑而知全豹”等艺术特质,创造出的具有深厚审美意蕴的艺术形式,并由此剥离了“筷子”这个实物本身的实用功能,进而联合了“筷子”这一符号指涉的文化象征与审美意义,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本观念融进人们心中,终在影片中缔造出了“有生命的形式”,化为人类情感符号的创造[8]。这也正是该片能够在短时长播放中打动观众,使之获得美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