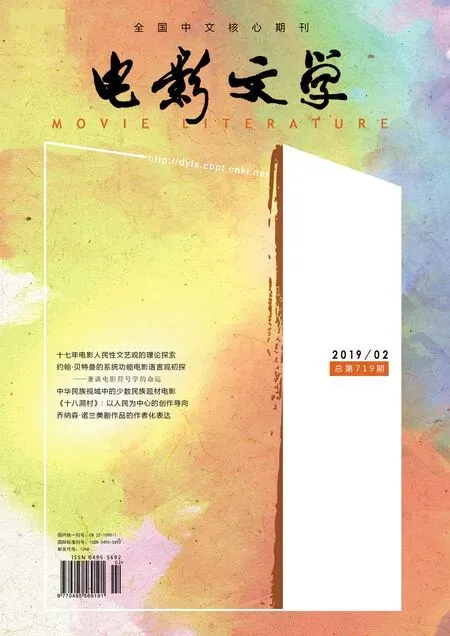“儿女的江湖”:贾樟柯电影的空间叙事
郭增强 杨柏岭 (安徽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影片《江湖儿女》基于时间、空间、人物的叙事跨度,主要呈现出斌哥和巧巧的情感轨迹、命运蜕变、精神走向。影片聚焦的“江湖”和“儿女”正如贾樟柯所言:“‘江湖’意味着动荡、激烈、危机四伏的社会,也意味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儿女’意味着有情有义的男男女女。”这里的江湖侧重于以故乡为轴心的底层空间,这里的儿女,侧重于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生命体验。贾樟柯电影所展现的“故乡”,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所在地,是凝结着心血和情感的心灵处所,是寄托着精神理念的理想家园。
一、“故乡空间”:贾樟柯审美经验的纪实影像
审美理念:日常生活的审美活动,交融着贾樟柯的“恋地情结”。“恋地情结”的出场路径与他的农业背景及生活经验有着内在性的缝合。“这样一种农业社会的背景带给我的私人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我愿意承认,并且一直非常珍视的。”[1]43基于故乡影响的缘由,以及对生活经验的珍视态度,他用审美的眼光,关照所拍摄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沉浸于筛选的空间之中,体验故乡空间氛围并与之对话。“要先沉浸十分钟,听这个空间跟你诉说,然后你跟它对话。”[1]110对空间观察和体验之后,是其审美想象与艺术构思:“我们应该证明家宅是一种强大的融合力量,把人的思想、回忆和梦融合在一起。”[2]对家宅(故乡)的观察、体验、构思后,使一系列的审美活动,蕴含着对故乡的“恋地情结”和现实关怀。“过去空间和现在空间往往是叠加的。……空间叠加之后我看到的是一个纵深复杂的社会现实。”[1]111正因贾樟柯对故乡空间的深刻体察,饱含着浓厚的“恋地情结”,引申现实的思索。他持续地把目光投向自己的家乡大同与汾阳,使他的故乡存活在纪实风格的镜像中。
冷静克制的运镜风格,记录着特定空间的时代印记。影片《江湖儿女》在故乡空间里,再现了简陋的居家环境、封闭喧嚣的KTV包厢、华灯闪烁的歌舞场、法制社会的大同监狱,有着那个时代浓郁的娱乐氛围和文化气息。在巧巧的家庭场所里,一系列中近景式的跟镜头,记录着人物谈话中的工人下岗危机,随着播音喇叭声流露出中国转型时期的煤矿危机。特定时代的生活气息还体现在娱乐休闲场所中。在大同棋牌室的封闭空间里,接近三分钟的固定机位长镜头的拍摄,泛黄的灯光、泛蓝的玻璃窗、烟雾袅袅、插科打诨,流动着生活的气息。在渲染的人情氛围里,也有欠账不还的矛盾冲突,显现出人际关系的亲疏冷暖,借用能指符号化的关公调解,展现出那个敬畏情义的年代,营造出快意恩仇、有情有义的人伦空间。流行音乐是那个时代的标记,伴随着《浅醉一生》的深情音乐响起,迪斯科舞蹈的欢快节奏、娱乐青年的狂热摇摆、忽明忽暗的华灯闪烁、激情狂欢的消费场所,表征着特定时代的流行文化印记。贾樟柯用冷峻的镜头对准了故乡的监狱空间。如果说关公是能指的道义象征,那么冰冷的手铐与紧锁的狱门则是规训和惩罚的法律秩序。伦理道义不能解决之时,是社会法制的运行之时,这也是中国法制社会“行驶”的时代痕迹。
电影空间系统的处理,不仅具有时代感,而且彰显了纪实影像的质感。影片《江湖儿女》的风格具有纪实性,在空间的处理上,符合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阐释的方式:“一是限于再现空间,并通过移动摄影使我们去感受,……”[3]影片的开场手持DV拍摄出纪录片质感,摇晃不定的镜头,粗粝感的画面,破旧的长途汽车,车厢内载着疲惫不堪、表情木讷的底层民众,镜头摇向靠窗的孩童,注视着慵懒的乘客,男女老少、底层人群。这样慵懒的人群、拥挤的车厢,是底层者的生存空间,再现了21世纪之初的时代气息和空间氛围。影片的纪实拍摄,贾樟柯还选取了那个年代拍摄的素材融入其中,映入眼帘的是画质粗糙的迪斯科的影像,记录着那个年代迪斯科舞蹈作为娱乐消费文化的盛行,也保持着影像风格纪实性的真实感。影片《江湖儿女》再现空间的处理方式,是贾樟柯电影一以贯之的风格。这种“故乡空间”的具有时代气息和纪实影像的方式,在其“异乡空间”有所延伸。
二、“异乡空间”:贾樟柯记忆场域的生命体验
贾樟柯电影中的“记忆之场”蕴含着对生命本体的关照。他将记忆根植于场所之中,使记忆与场所缝合;以无意识的流露和潜意识的沉浸促使叙事动机“起先我并不知道自己的内心深处有着一种强烈的叙事欲望。当我离开县城,汾阳的那些人和事一天比一天清晰”。[1]90他因其自身的离乡经历所拨动着内心深处的生命感触,去关注人的存在,去呈现生命的状态——“学会将滚烫的生命和真实的自我投放在自己的作品中”。[4]122贾氏电影的生命体验,是叙事主体的生命状态与叙事者的“记忆之场”相吻合的生命体验。贾樟柯在《今日影评·鸿论》中说:“三峡的人口密度,真的是摩肩接踵,房屋居住层层叠叠。人被压缩到窄小的空间里,人的活力便迸发出来。”他以镜像注视着“离乡”之程和“异乡”之地,呈现人的离乡处境、生存之艰、情感异化、命运蜕变、生命关照的美学理念。
三峡库区的记忆场域里,具有时代痕迹的生命感触。三峡水利工程的建设,是中国社会动荡、变迁、发展的历史记忆。世世代代居住于此的底层民众,面临着拆迁、搬家、远走,数百万的移民背井离乡。此时电影《江湖儿女》的舒缓的摇镜头独具匠心,大远景的画幅中,后景是远方的山峦,中景是长江客轮,前景是远走他乡的移民。镜头摇向离乡的巧巧,面色憔悴,迷茫无助,接着镜头转向三峡离乡的移民,表情木讷、神情茫然的近景画面。在如此黯然神伤的镜语体系里,是导演在关注被时代洪流裹挟前行的人,体察人的生之艰辛、离乡之痛。关注着人沉重的肉身还有人性涵泳的情感。
“异乡空间”中出现现代人情感破裂的因素:从物质利益驱动到人的隔膜与疏离。“异乡”在贾樟柯的镜像中往往是侵蚀现代人情感的容器。叙事的主体不是烟雾弥漫了眼就是物欲遮蔽了心;不是爱情的分道扬镳,就是亲情的恩断义绝。在《三峡好人》中奉节的郭斌,在物欲膨胀的驱使下和沈红劳燕分飞。到《山河故人》中的张晋生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他乡,因狂热追逐金钱,造成家的分崩离析。贾樟柯以往的电影中导致爱情与亲情断裂的罪魁祸首往往是金钱,而在《江湖儿女》中,关于情感的破裂不仅在于物质利益的驱动,还在于人与人的隔膜与疏离。最后斌哥与巧巧的情感破碎,不仅仅在于利欲熏心,而在于斌哥挽回做大哥的自尊心,更重要的是长达五年情感隔阂,缺乏彼此的交流与沟通,导致二者分道扬镳与破镜难圆。这样的情义之变,表征着人在时代的航程上,很难保持他的永恒性。正如贾樟柯所言:“不单写街头的热血,也要写时间对我们的雕塑。”在异乡里人难以经历岁月的历练,贾樟柯在异乡空间的拓展,延伸到现代人的情感空间,而这种在异乡的精神荒瘠,需要“返乡之途”寻找精神的慰藉。
三、“乡关何处”:贾樟柯故园情思的哲学追问
农业生活的成长背景、返乡之途的现实写照,或隐或现地透露出贾樟柯的美学理念与哲思。在山西汾阳的成长经历,使他的创作理念信条割不断“土地的联系”[1]43,从他的成名作《小武》到新作《江湖儿女》,不断地用洞察力与沉思度,关照社会快速发展中的故乡家园。在2015年返乡后的贾樟柯,深感时代与社会变迁之快、人际关系之紧张、情感交际之冷漠、人间情感与精神之危机;深深地思索单维度的金钱观,过度地依赖媒介载体,使人物欲膨胀而冻结了人性情感。在创作《山河故人》时,他敏锐而沉思地叙述道:“……以金钱为中心的单一价值观,伴随着这场运动出现在当代生活中的新科技,……我们忽略、放弃了很多本来应该属于我们的情感。”[4]206-207科技日新月异、媒介日益延伸,一方面给予我们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另一方面媒介载体侵蚀人的本体,促使现代人蜕变为“单向度的人”。这样焦灼的哲思,如鲁迅先生所说:“提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5]能读解这样“沉郁”的美学观念,也就能体验贾樟柯的影像;为什么有时晦暗不明,有时一镜到底地冷峻。他的电影不是粉饰生活麻醉人心,而是介入生活发人深省。
影片《江湖儿女》里,“故人返乡”后的空间叙事,延伸到了精神空间。在《江湖儿女》中,斌哥在返乡之途,已身患重病,与巧巧相遇已没有了昔日的爱恋,与兄弟相逢已没有了曾经的义气。斌哥的命运沉浮是“肉身的损伤”和“精神的幻灭”的综合写照,是男性身份的瓦解。而在“返乡”的女性形象中,《江湖儿女》中巧巧的女性形象由肇始依附男性,到经历情感抛弃、人心叵测、世事沧桑后,渐变为独立决绝的女性。其实,这样的“故人”身份,不管是矮化男性形象,还是强化女性意识,无论是弱化男性身份还是强化女性主义,都不是肉丰灵韵、精神饱满的人物形象,更不是健全的伦理道德系统。贾樟柯在现代人处于精神危机时,以“返乡之途”,试图寻找“精神家园”,找回完整的人性人格和健全的伦理体系。
“返乡”之后又“离乡”,“执意返回”却“无法真正返回”的形而上的矛盾,是对“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的追问、寻找、哲思。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阐释了现代技术的负面因素对人的异化,使人难以回归本真存在的精神家园,“只是此在作为其所是的东西而存在,它就总处在抛掷状态中而且被卷入常人的非本真状态的旋涡中”。[6]在《江湖儿女》接近尾声的组合段,斌哥“返乡”时巧巧用百度地图回应斌哥,“离乡”时,斌哥用微信语音告别,车站接人与告别,这是贾樟柯所要阐释的时代变迁,也是他所要呼吁健全的时代情愫。最具有传统的仪式感和最能传达人间的真情,却以媒介载体来承载本体的美好情愫和精神素质,让人深思“工具理性”对“人文理性”的侵蚀。“无家可归是安居的真正困境。”[7]更让人感到人生凄凉况味和精神家园流离失所的大孤寂感。还有以往贾樟柯的电影总会有“家”的存在,尽管家庭是破败的、家庭成员的关系是危机的,总是有子一代的出现,尽管子一代是叛逆的,或者迷失身份的。然而电影《江湖儿女》成了赤裸裸的“没有家的电影”“没有子一代的电影”。“返乡”本是对故乡的归根、对精神家园的找寻与认同,而“返乡”后已无家可归、无代可续,这又是怎样的凄楚与悲情。贾樟柯的电影蕴藉着一种中国美学“沉郁”的“洞察力”和“穿透力”,对人生世事沧桑的深刻体验,和对人生命运无奈的窥伺,以及对现代人栖息的精神家园的忧虑。观贾氏电影与体悟鲁迅的小说一样,“一种哀怨郁愤的情感体验,极端深沉厚重,达到醇美的境界,同时弥散着一种人生、历史的悲凉感和苍茫感”。[8]这样的美学境界值得每一个现代人去深深地思索,怎样“返乡之途”?如何“诗意栖居”?
四、结语
影片《江湖儿女》中呈现的“故乡空间”“异乡空间”“返乡之途”是贾樟柯的空间叙事架构。在“故乡空间”里,贾樟柯以个体经验,呈现纪实影像,镌刻着故乡,打印上时代痕迹,彰显着纪实风格。在“异乡空间”中,贾樟柯以漂泊生涯的生命感触,关注个体的生命质感,呈现时间对人的雕塑,记录人生的命运蜕变。“返乡之后”的活火山,没有了昔日的青翠欲滴,而是满目萧瑟,隐喻着精神家园的凋零,寄托着诗意栖居的涅槃再生。回到现实家园的贾樟柯,是在渴求一种“诗意栖居”的精神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