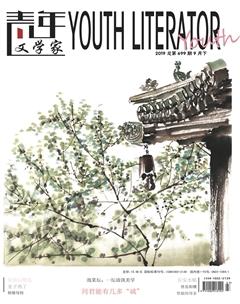《地下铁道》中的女性创伤记忆与美国黑人女性的身份重构
马行天
基金项目:本论文是云南大学第十届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当代非裔美国小说中的女性创伤记忆与美国黑人女性的身份建构》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8069)。
摘 要:《地下铁道》是美国非裔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的第六部小说,获得201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2017年普利策小说奖。小说讲述少女黑奴科拉不畏奴隶制的暴虐,在“地下铁道”众人的帮助之下追寻自由之路的故事。本文以小说中黑人女性的创伤记忆为切入口,运用创伤理论分析黑人女性在奴隶制下遭受的种族创伤、集体创伤、个体创伤、文化创伤和心理创伤,探讨黑人女性在种族歧视、男权主义、生活困境等多重压力下的受创经历,揭示黑人女性在这一过程中的自我迷失与身份重构。
关键词:奴隶制;创伤;《地下铁道》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7--02
引言:
科尔森·懷特黑德是21世纪美国非裔作家的代表人物,其创作题材广泛,备受读者和文学批评家的青睐。2016年,怀特黑德构思长达16年的长篇小说《地下铁道》出版,这是他的第8部小说,一经问世,便好评如潮。《纽约时报》称赞怀特黑德让读者忆起一代又一代美国人不畏艰险,不畏历史倒退的车轮,追求正义追求自由的决心。该小说入选美国奥普拉读书俱乐部推荐书目,奥普拉称:“我熬夜读这本书,心快跳到嗓子眼,几乎不敢翻下一页……我不得不停下来,细细体味我读到的东西,让愤怒和眼泪得到疏泄,而后再回到故事当中去。”小说获得2016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2017年普利策小说奖。怀特黑德运用冷酷的叙事风格,讲述了惨遭奴隶制压迫的黑奴少女科拉,搭乘秘密的“地下铁道”,逃出似人间地狱般的南方蓄奴州,一路向北,寻找自由的故事。小说以科拉的逃亡为线索,揭露美国黑奴历史和种族问题对个人乃至整个非裔少数民族群体造成的创伤与苦难。由于该小说的出版时间距今较短,国内对其的研究较少。本文将聚焦黑人女性的创伤记忆,揭示黑人女性在多重压力下的悲惨遭遇和对自我身份的找寻。
一、创伤理论
创伤理论是目前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研究涉及历史、哲学、心理学、文学等多学科的内容。创伤(trauma)一词最开始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医疗术语,在文学语境里特指创伤批评理论。20世纪90年代初,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吸收了弗洛伊德在前期关于歇斯底里症的研究结果,深入研究创伤经验的特征,首次提出创伤理论。造成创伤的事件具有“突发性”和“灾难性”,并通过幻觉或者其他闯入方式,如梦魇、闪回等反复出现,由此产生让创伤主体难以应付的“倒压性经验”。随着文化研究与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多元化,国外的学者们对创伤理论的研究转向更为广泛的领域。创伤记忆孕育了创伤文学,作家们运用集体创伤的成规,刻画描绘了各个遭遇创伤的人物,并通过这些形象,指代着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历史。
二、黑人女性的创伤记忆
从17世纪殖民时期起,种族主义成为美国社会的热点话题。黑奴制是最典型的种族主义形式,在这一制度下,奴隶仅仅是奴隶主商品交易的牺牲品。奴隶主随心所欲地剥削、杀戮和残害黑人,给黑人的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地下铁道》中,主人公科拉的创伤记忆源于黑奴制,她的外婆阿贾里从非洲大陆被多次贩卖到美国南方,一生在棉花种植园里辛勤劳作,最后惨死在棉花堆中。科拉从小就见证奴隶主压榨黑人奴隶,经历非人的待遇,她的生活从一出生便注定被禁锢在佐治亚州的棉花农场中。在被黑人同族的排挤与霸凌之下,她没能守住外婆留下的木屋和屋边的菜地,被赶进了放逐苦命人的“伶仃屋”,“伶仃屋”是科拉的创伤记忆的延续。从此,科拉的日子过得更加凄苦。对于黑人女性而言,留在心灵上的创伤比肉体上的伤害要更加刻骨铭心,即使在摆脱奴隶身份之后,她们依然无法摆脱心中惨痛的个体创伤记忆,这种创伤记忆会内化为精神上的自我责备与自我羞辱。值得注意的是,种族主义并没有随着科拉逃往象征着“自由”的北方而结束。在通过“地下铁道”逃到南卡罗来纳州之后,科拉以为自己彻底地摆脱了种族主义的魔爪,但事实是残酷的,她发现白人企图通过绝育来控制黑人的数量,同时将黑人作为医学实验和解剖尸体的对象。科拉这才意识到白人并没有停止对黑人的压榨,只是换一种方式榨取他们的尊严、自由和生命。[1]精神创伤是“受害人在极其恐惧的状态下遭遇某一惊人事件所产生的复杂感情,先前的知识结构无法为它做好准备”。[2]153科拉在得知这一真相时内心遭受重创,她不知道逃到哪里才能摆脱种族主义的暴虐,哪里才能是自由之境,她唯一能做的是继续逃亡。在奴隶制下,美国黑人群体遭受了多重的历史创伤,这一系列的创伤是在经历大规模集体创伤之下,几代人所积聚下来的情感伤痛,难以消除。
黑人女性,不仅要承受白人的种族歧视,还受到黑人男性的压迫。由于黑人男性无力抵抗白人奴隶主的压迫,他们就将奴隶主施加给他们的压迫、愤怒、暴力转嫁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身上,黑人女性不仅要承受压榨式的劳作之苦,还要承受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身心因此备受摧残。《地下铁道》以冷静的叙事语调大胆揭露男性对女性的迫害。科拉对母亲梅布尔的回忆再现了她在棉花种植园的不幸遭遇。她整天辛苦劳作,连临近生产也得不到休息,还惨遭黑奴工头摩西的威胁和强暴。摩西威胁如果梅布尔不顺从他,他便去找只有八岁的科拉。梅布尔只能“乖乖”顺从。在摩西这些黑人男性眼中,女人等同于牲口,你只要收拾他她们一次,她们从此就服服帖帖的了。[3]328男人对女人的压迫和强暴已经成为奴隶制下种植园的常态。在伶仃屋里,白色的男人和棕色的男人狂暴地利用女人的身体,她们的小孩生下来就发育不良,皱巴成一团。不断的殴打,打得她们脑子没了理智。她们在夜里一遍又一遍叫着死去小孩的名字。[3]19男性不仅对成年女性施暴,还不放过还未发育成熟的女性。科拉初潮后不久,工人们便把她拖到了熏肉房进行施暴,无人制止。[3]24在一次又一次的暴力行为中,黑人女奴俨然被男性物化成满足性欲和发泄愤怒的物品,长期的虐待导致她们的身心旧伤加新伤,心中早已生成无法愈合的创伤。她们的创伤不仅源于白人奴隶主的压榨,也源于黑人同僚的冷漠与不作为。
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迫下,黑人女性的爱变得异常甚至畸形,她们要么无法真正去爱,要么爱得太壮烈。母爱的缺失和变异并不是非裔母亲自身母性的沦丧,而是奴隶制的非人性造成的创伤。[4]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创伤理论的阐述,个体在年幼时期的生活经历对其一生的成长和生活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当个体受到的刺激超过自身所能承受的范围时,就会产生一种创伤感。个体在幼儿时期,各种需要的满足都要依赖母亲,母爱的缺失不仅会给幼儿带来永久性的创伤体验,还会给母亲的内心带来反复性的折磨。科拉很小就失去了母爱,她的母亲梅布尔在她十岁时不辞而别抛弃她逃往北方,科拉为此对母亲充满了怨恨,年幼的她独自面对奴隶制下残酷的生存困境,隐忍别人的诋毁与强暴。她见过男人吊在树上,任由秃鹰和乌鸦啄食。女人被九尾鞭打到露出骨頭。活的身体,死的尸首,通通在火葬的柴堆上受着烧灼。[3]39血腥的景象在她幼小的心灵上造成心理创伤,母亲的离去无法帮助她抚平创口。在科拉的记忆里,母亲梅布尔的形象是悲伤的。梅布尔总是“混合着同样的不情不愿,身体弯曲。“科拉没法子在心里把她拼合成一个整体。她是谁?她现在在哪儿?她为什么要离开她?连一个特别的吻都没留下。”[3]60-61卡鲁斯曾指出,最困扰受创个体的不是创伤性事件本身,而是她们对事件本身无法理解、无法接受的心理状态。[2]11科拉对母亲的描述反映出她对母亲的情感是复杂而又矛盾的,一方面,她不理解母亲的不辞而别,另一方面,她又渴望与母亲团聚,在逃亡的途中四处打听母亲的下落。悲剧的是,出逃的梅布尔并没有过上自由的生活。在逃亡之路上,她想起了科拉,母爱的天性呼唤着她必须回去,赶在第一缕阳光,赶在最早起床的人之前回到种植园。不幸的是,毒蛇咬伤了她,最终招泽池把她吞没了。科拉永远无法得知她的母亲放不下她,她对母亲的怨恨与误解也永远不会消除。凄惨的结局从侧面揭示了奴隶制是母女之间爱的缺失的根源,也是黑人女性遭受创伤的根本原因。奴隶制摧毁了家庭,剥夺了母亲和孩子之间爱与被爱的权利。
三、创伤的修复与身份的重构
记忆是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桥梁,通过传递,创伤记忆被转移或遗忘、复制或重构,先辈和后代之间不断地完成记忆的转化,这种转化是塑造家庭记忆的方式。经历过奴隶制惨绝人寰的压迫的黑人个体将自己的创伤记忆传递到后代的记忆中,不论后代是否亲历奴隶制,他们的记忆中都或多或少有关于奴隶制的创伤记忆,这些创伤记忆影响着他们构建非裔美国人的身份。当后代审视和构建自己的身份时,先辈所传递下来的创伤记忆就成为了后代的一种民族责任。一方面,后代所继承的创伤记忆和耻辱记忆有助于凝聚祖先坚持不懈、艰苦奋斗的精神,构建稳定的民族主体性。但另一方面,创伤成为个体和集体心理上挥之不去的梦魇,使其沉浸在过去的创伤记忆中无法自拔、迷失自我,难以找到未来的路。对于科拉来说,她在奴隶制下所经受种种创伤并没有让她就此屈服于的性别、种族和阶级等多重压迫,反之,她直面创伤,通过地下铁道,踏上一条寻找自我、追求自由的道路。在西泽心目中,科拉与其他奴隶不一样,当众人对遭受鞭刑的小黑奴冷眼旁观时,“只有科拉站出来。用自己的身体做了男孩的肉盾,代他承受主人的重击。”[3]263西泽相信科拉的善良、坚韧和敢于抵抗的精神将成为他们在逃跑途中的“火车头”,指引他们共同找到自由之路。创伤记忆对于黑人种族身份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奴隶制不仅是创伤个体的伤痛,更是整个美国非裔少数民族群体共同经历的集体创伤。科拉是不惧压迫的黑人女性的代表,她试图从奴隶制中挣脱,找到属于自己民族的自由之路。尽管追求自由的道路充满曲折,但是她已经做好准备,正以必胜的姿态勇往直前。
结语:
《地下铁道》以全新的视角勾勒出美国奴隶制下黑人女性的生存状态。主人公科拉不再是美国黑人文学中默默忍受压迫的黑人女奴,作为勇敢的黑人女性的代表,她直面黑人女性在种族歧视、男权主义、生活困境等多重压力下的创伤,走上寻找自由的道路。怀特黑德为小说安排了开放式的结局,科拉开启了新的逃亡之旅,虽然她不知道自己能否获得自由与解放,但是她知道自己将带着非裔美国少数群体的自由之梦继续前行。
参考文献:
[1]丁丽芳. 黑暗之光:解读《地下铁道》[J]. 现代交际. 2017(2):101-103.
[2]Caruth, C.1995.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M].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3]科尔森·怀特黑德. 地下铁道[M]. 康慨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4]李莉. 《宠儿》和《紫色》中的黑人女性创伤书写[J].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8(12):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