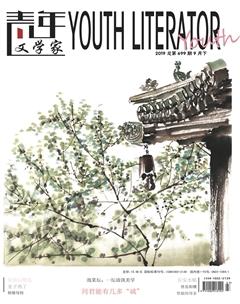从中原神话看“灵石信仰”
摘 要:民间信仰曾广泛地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灵石信仰”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在中原神话中表现突出,至今仍在中原地区的民俗事项里占据着一席之地。
关键词:灵石信仰;中原神话;女娲;大禹;黄帝;兄妹婚
作者简介:冀婕予(1997-),女,河南南阳人,毕业于苏州市职业大学,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27-0-03
人类的信仰纷繁驳杂,它表现在寺庙宫官的袅袅香火中,也显露于清真寺顶礼膜拜的仪式中,还体现在基督教徒对胸前十字架的虔诚祷告上。而在这些宗教信仰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民间信仰群体存在。中国民间信仰,承袭着远古的原始信仰,厚重地铺垫着整个民间文化史,广泛地影响和支配着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民间信仰包罗万象,不仅有对自然现象、自然物、自然力和各种动植物的崇拜,还有对幻想中的神鬼精灵的崇拜,同时也包括对超自然力和职司各异的神灵崇拜。
灵石崇拜是民间信仰体系中的重要组成。作为一种自然崇拜,它产生的年代十分久远。早在原始氏族社会,民众处于环境恶劣、生活艰苦而思维又不甚发达的社会低级阶段。原始初民由于能力所限而屈服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威力,在“万物有灵观”和“互渗”思想的支配下,头脑里幻化出各种信仰对象作为精神支柱,灵石信仰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
处于社会低级阶段的早期母权制社会主要以打猎、采集为生,在他们的意识形态里还不能把自己或自己的祖先与动植物、自然物严格区分开来,把石头奉为“石祖”就是其中一个表现。采集、打猎需要工具,而石的坚硬质地使它成为必然的工具材料,初民用它做成石器来获取生活资料。在环境险恶、毒虫肆孽的洪荒时期,石头也成了初民保护自身的武器。在原始思维中,石制工具和武器未被初民们看作是人造物,反而是被当作一种因其自身而在的存在,具有自我力量和某种神秘属性,成为支配人们意志的神灵。人们依赖于它,并以种种具有宗教性质的礼仪对它崇拜和信仰。原始初民与石头的密切关系还表现在“天然石洞是他们最早的居住地。这是因为“早期的人类缺乏建筑的技术和力量,故而常依赖自然形势获得居住空间,其中,岩穴曾扮演了人类襁褓的突出角色。……这种生存环境,经过原始心理的过滤、夸大、神化,很自然地进入神话,并在生存环境(岩洞或葫芦)与人种保存之间建立起神话的纽带。”[1]于是“石洞”成了母腹的象征,具有了某种生殖魔力。诚如台湾学者王孝廉先生所说:“古人把各种不同的石头看作是力量、生命、永恒、丰饶、信义、幸运的象征,从而形成各种不同时代的不同信仰文化形态,由此产生各种关于石头的神话传说和宗教仪礼”。
灵石崇拜信仰,在中原神话中的表现也十分突出。石块,曾被作为造人的灵物而被初民信奉为“石祖”,它也曾是改造世界、拯救人类的“圣石”。
一、以“女娲补天”神话看“灵石信仰”
女娲作为始祖神,最大的功劳莫过于“补天”和“造人”,而其中尤以“补天”在先。据众多文献记载,女娲补天所用的物品就是灵石中的五色石。《列子·汤问》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断鳖之足以立四极。”《论衡·谈天》篇:“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鳖足,以立四极。”《淮南子·览冥》篇:“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 断鳖足以立四极……”此外,《博物志》中也曾记述:“天地初不足,故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其阙(缺)。”
关于五色石的描述,在民间口头传承的女娲神话中虽各有所异,但其“石”的核心不变。在中原神话中,相关流传多集中在太行山的涉县、安阳县的清凉山和西华县的思都岗地区。河南大学中原神话调查组,历经数年调研采风挖掘出许多流传在民间的活神话。如在安阳县清凉山所采集的女娲神话:“女娲取来五个星星上的石头,炼成五彩石,才把天补好。”[2]涉县娃皇宫流传的“补天”:“女娲从漳河里捞出五色石子,熬化后一勺一勺烙成饼……”[3]民间口头还传有:“女娲补天时落下的石屑变为土,从而修筑了女娲城,城上常幻起五色朝烟。”这一切都彰显出民间对“石”的信仰。只有靠“石”所具的灵性,才能完成补天大业。
河南大学中原神话调查组,还在王屋山(属太行山系)采集到两处女娲补天所留的“遗石”传说。一说是在“天坛山”(王屋山主峰)下紫微宫西边的河滩里,“石头都是五色的。相传是女娲在这里炼石补天时剩下的碎石头”(据济源县文化馆魏平复讲述,采录于天坛山)。另一说是在王屋山天坛峰下的三叉洞,“三叉洞外面的西南角不远处,有两张席子大小的地面上,有许多色彩斑斓的碎石。据说就是王屋山的五色石,可能与女娲补天有关”(据当地人黄习瑞讲述,采录于天坛山)。由此,我们可看出“许多神话事件显然是以历史为依据的。……神话中的许多地点、人物、事件,据证明都有历史依据。”[4]
“在中原地区,与神话相关联的其他民俗事项很多,但主要是那些依附着神话的信仰民俗和由信仰民俗衍生出来的行为民俗,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三者互为表里、互为因果。”[5]女娲神话中的“灵石信仰”对后世的民风、民俗的重要影响也不可忽视。它依附着女娲神话派生出许多行为活动,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民间的“天穿节”这一行为民俗。明代杨慎的《词品》中记载:“宋以正月二十三日为天穿节,言女娲以是日补天,俗以煎饼置屋上,名曰补天。”民间将面粉、蔬菜等拌成汁以象征女娲将五色石炼化成的汁液,以示补天之事。在今天的涉县,当地群众去娃皇宫“朝北顶”时仍保留有烧“五色纸”的习俗。无论是“天穿节”或是“烧五色纸”等行为民俗,其产生皆源于女娲补天神话里的“灵石信仰”,属于模仿巫术的范畴。
二、以“大禹治水”神话看“灵石信仰”
原始初民相信岩石、巨石有灵性,认为大石可孕育万物,具有生殖能力。“灵石信仰”在“大禹治水”神话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石生人”和“人石互化”。《淮南子·修务篇》中曾载:“大禹之母狄得石如珠,爱有吞之生禹”。这就是一篇感石生子的神话。此外,大禹的儿子启的出生也与石有关,石破生启是“石生人”神话的变形和发展,包含着“人石互化”的因子。《汉书·武帝记》颜师古注引《淮南子》(译文)中,就有关于“人石互化”的记载:“禹治鸿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之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这是人变石的记载。而在河南登封县,中原神话调查组还采录到了由石变人的异文:“因啟思母心切,感动了中岳大帝,从而使化身为石的涂山氏复活。”
相信石头具生殖力的观念可能源于“地母崇拜”。“地母崇拜”是“生殖崇拜”的衍化形式。由于大地上可生产万物,故在初民心中,大地的丰饶和女性的生育往往被结合在一起。土地被视为生与再生的象征,被奉为“地母”,而石头则被当作大地神的代理象征也受到了崇拜,具有了神秘的生殖力。因此在许多民族中,不孕的妇女奉它为“石祖”,常去敬拜乞子。原始初民的自我意识薄弱,在他们的思维中,人和自然界(动物、植物、自然物)是相混淆的,且可以互相转化。于是,在大禹治水神话里,石可变人,人可化石。
三、以“黄帝神话”看“灵石信仰”
在黄帝神话中,“灵石信仰”表现最为明显的在于和“山崇拜”关系密切。“在中国民间信仰中,对山的崇拜往往和对石的崇拜相联。”[6]
《史记.五帝本纪》:“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在中原神话中,蚕神嫘祖死后化成了奶头山(现在新密市神仙洞外)。“她生前哺育子孙,将子孙问的事装在大石头里。谁如有什么愿望,可敲敲奶头山前的一块青石,如声响清脆,则可如愿以偿。当地人称它为灵石。”[7]在如今的密县天爷洞庙会上,凡是青年男女求婚的,老人们求子孙和求长寿的,都爬上去敲这块灵石。据古书载,黄帝为完成中原一统的大业,极重视人才,曾上崆峒山求广成子。棋盘山便是黄帝和广成子下棋时的棋盘所化,山下的下棋石也可谓灵石,据当地人说可帮助降雨、增收。后人还把神仙洞里那千奇百怪的钟乳石加以想象、附会,从而更加深了灵石崇拜的影响。
“石崇拜”和“山崇拜”的密切关联在“大禹神话”中也是存在的,如:“禹一怒之下,把妻子的头掉在河水里,变为一块巨石。她的身子还立在河岸上,后化为娘娘山,也叫梳妆台。”[8]
四、以“兄妹婚”神话看“灵石信仰”
有關兄妹婚的神话异文众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盘古兄妹婚和伏羲女娲兄妹婚。他们大多涉及通过占卜、滚石磨等手段来测“天意”,从而解决洪水后遗民再造人类的社会重大问题,其中的石磨成为了传达天意的最终决定性工具。如中原神话中的盘古兄妹婚,“咱俩弄上一对石磨子,我拿一扇从这山头往下轱轮,你拿那一扇子从那山头上轱轮。中间一道沟,往下滚,合住了就成亲,合不住,就算了。”[9]再如伏羲、女娲兄妹婚中,“咱俩往天上扔石头,石头合一块了,就得定亲。”[10]“老天在上,俺兄妹结婚,顺天意,磨就合为一盘,逆天意,两扇分开。”[11]从这些中原神话“兄妹婚”的内容中我们可看出,石的信仰和崇拜在人类的繁衍生存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意义。此外,“滚磨成亲”也表明了“灵石信仰”在新石器时代的发展、演化。
由伏羲、女娲兄妹婚所引起的“灵石具生殖力”的信仰对后世的影响,至今在中原地区仍有表现。如淮阳太昊陵显仁殿东北基石墙上的石窑,被视为女娲女阴的象征,这根源于在母系氏族社会已有的男根、女阴崇拜。这一石窑被称为“子孙窑”,源于伏羲、女娲兄妹婚。来庙会的人们以“摸子孙窑”,借石窑的灵性来求子嗣,属于“触染律”支配下的一种巫术行为。
在盘古山区大磨村(村名源于盘古兄妹占婚用的大磨),有一扇年代十分久远的大磨。当地在发生旱灾时,村民就把这扇磨支起来。他们相信,这样做之后不出三天,准下雨。究其思维实质,是想通过“接触巫术”的形式来达到祈雨目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兄妹婚神话里,帮助主人公躲过灾难的大半是石狮子或石子,可见在初民心中,因石具有灵性,所以可作通天之用,是天与人的中介。
纵观人类各民族史,灵石崇拜可谓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这一点在传世的典籍与文学作品中,亦显而易见。在我国四大名著中,“灵石信仰”多有体现。《水浒》里,梁山的一百零八将是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的化身,他们乃出自龙虎山的青石板下。在《西游记》中,主人公孙悟空是由东海神州花果山上的一仙石孕育而成。这一情节可追根溯源于“大禹治水”神话中所显现的“石生人”信仰。而“女娲补天”神话中的“五色石”在《红楼梦》里表现更为明显。《红楼梦》开篇的楔子中便写道:“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方二十四丈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蜗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下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这个被遗弃的顽石,正是小说的男主人公贾宝玉。贾宝玉就是这块灵石入世而化,他的一生际遇都与这块灵石有关。小说以灵石开篇,中间又以灵石联缀出许多悲欢离合、动人心扉的故事,最后再以灵石归去为全书作结。女娲是中华民族神化史上的一位创造大神,而《红楼梦》在女娲诸多功业中只选择了其中的“炼石补天”一节,并加以藻饰化,编织成似有还无的新的亚神话,这足以说明“灵石信仰”在后世的影响。
在 “灵石信仰”的影响下,古代文人形成了一种以石象征傲岸孤立、卓尔不群、坚贞不屈的人格精神。他们往往以石自居、引石自喻。《吕氏春秋·诚廉》中曾载:“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这正是文人以石自比的基础。再者,古之文人多有石癖,如米帝拜石;陶渊明、李白醉石;苏轼藏石、玩石,以奇石“雪浪”命名书斋;郑板桥以丑石自喻其风骨;曹雪芹之祖父曹寅也有爱石之痕。
历史在不断发展,人们的物质、精神需求得到了更多、更广泛的满足和填充,“灵石信仰”的功能也随着时代的变迁有所存留、增添、亡佚。但那些基于人类基本需要的功能则一直长兴不衰的保留下来——繁衍、平安、健康,它们是整个人类信仰史中不变的夙求。
参考文献:
[1]谢选俊.中国神话[M].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163.
[2]张振犁. 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M].东方出版中心,1998:29.
[3]张振犁. 东方文明的曙光[M].中原神话论东方出版中心,1998:38 .
[4]戴维.李明等(美).神话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86-87.
[5]孟宪明,程健君.民间神话[M].海燕出版社,1997:12.
[6]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M].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54.
[7]张振犁. 东方文明的曙光-中原神话论[M]. 东方出版中心,1998:117.
[8]张振犁.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217.
[9]张振犁,程建君.中原神话专题资料[M].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河南分会, 1987:33.
[10]张振犁,程建君.中原神话专题资料[M].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河南分会, 1987:102.
[11]张振犁,程建君.中原神话专题资料[M].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河南分会, 198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