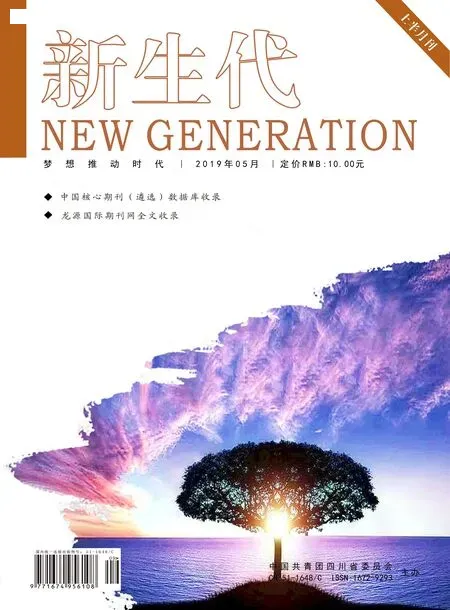彝汉动植物名词构词对比研究
张丽 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100081
一、彝汉动植物复合名词的对比
彝语和汉语一样,词的形态结构的特点,决定了它在类型学上的地位——“分析语”。【1】按内部结构来分,复合词可以有名词+名词(N+N),形容词+名词(ADJ+N),动词+名词(V+N),名词+动词(N+V),名词+形容词(N+ADJ)等几种形式;按构成成分之间的语义逻辑关系来分,复合词有联合式、偏正式、主谓式等几种主要类型;按构成成分的自由度来分,复合词的形式有自由词根+自由词根、自由词根+粘着词根、粘着词根+自由词根、粘着词根+粘着词根等四类。【2】本文以内部结构分类法为主,分别举例,比较彝汉动植物复合名词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特点。
(一)汉语动植物名词的复合构词形式
1.名词+名词
植物:土豆、蚕豆、鸽子花、老虎草、凤凰草、老鹳草等;动物:姜片虫、竹节虫、枯叶蝶
2.名词+动词
植物:羊踯躅、蛇灭门、鸟不踏
3.名词+形容词
植物:地黄、韭黄、竹黄、杏黄、茭白、花红;动物:竹叶青、树懒
4.形容词+名词
植物:黄瓜、苦瓜、黄麻、甘薯等;动物:乌梢蛇、黄蜂、黄雀、黑熊、棕熊、赤狐
5.动词+名词
植物:牵牛花、驱蚊草、捕蝇草、食虫草;动物:萤火虫、唤雨鸠、点水雀、画眉鸟、啄木鸟
(二)彝语动植物名词的复合构词形式
1.名词+名词
植物:豌豆ʂo33 no2(麦+豆)
豆芽no2 ne33(豆+芽)
动物:苍蝇ɦɔ11 mu33(绵羊+马)
蚊子 ɦɔ11 ʂo33(绵羊 + 蛇)
2.名词+动词
植物:接水菌mu33 ʑi2 ndo55(菌+水+接)
动物:萤火虫bu33 si33 to55(虫+点燃)
点水雀ŋa2 ʑi11 si55(鸟+水+渴)
3.名词+形容词
植物:黄豆no33 ʂo33(豆+黄)
糯米 tʂhe11 ȵo33(稻谷 + 粘)
新米 tʂhe11 ɕi55(稻谷 + 新)
动物:乌梢蛇va55ʂo33 na2(蛇+黑)
黑猪va55 na2(猪+黑)
(三)彝汉动植物复合名词构词对比
1.词素组合关系:如以上例子所示,汉语动植物复合名词的主要构词类型有五种,彝语有三种。彝汉语的动植物复合名词都有名词+名词、名词+动词、名词+形容词的构词形式,名词+名词的构词模式在两种语言中具有一定的数量优势。
2.语序的差异是彝汉语的一大区别特征,汉语是SVO型语言,所以在构词语序上,常常是修饰语或限定语在前中心语在后的结构,如“黄豆、老虎草、啄木鸟”;而彝语是SOV型语言,在动植物名词的构词上,常常是中心语在前修饰语或限定语在后的结构,如“黄豆、啄木鸟、红头菌”等。从动植物名词的内部构成成分角度来说,彝汉动植物名词主要有两种构词法,一种的简单的词和词的结构,如汉语“黄瓜、甘蔗、柳莺”,彝语“木耳、糯米、苍蝇”等;一种是词和词组的结构,如汉语“啄木鸟、爬山虎、捕蝇草、蛇灭门”等,其中修饰语部分“啄木、爬山、捕蝇”等为述宾结构,彝语“啄木鸟(鸟木啄)、接水菌(菌水接)、唤雨鸠(鸟雨咒)”中修饰语部分“木啄、水接、雨咒”为宾语在前谓语在后的动词短语,与中心语一起组成SOV的语序。
3.从有类和无类的角度来看,两种语言的动植物命名都有有类和无类之分。汉语有类动植物名词“黄豆、牵牛花、老虎草、竹节虫、画眉鸟”等均包含类指成分,无类动植物名词“龙眼、爬山虎、树懒、竹叶青”等不包含类指成分;彝语有类动植物名词“黄豆、桃树、点水雀、啄木鸟”等,无类动植物名词“木耳(鼠+耳朵)、仙人掌(水牛+耳朵)、苍蝇(绵羊+马)”等。
4.命名方式:从植物学的角度看,“双名法”是彝汉语动植物命名的重要方式,动植物名称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包含了动植物的形态型,另一部分则包含了动植物的形态、颜色、性状等方面特征,例如“龙爪槐、枯叶蝶”。
5.动植物词相互投射:表示植物名称的复合词许多是通过动物域投射到植物域形成,动物词汇加上动词或植物类属后,其词义不再具有动物词汇的意义,而是成为了植物名词,如汉语“爬山虎、羊踟蹰、蛇灭门、蝴蝶兰、鹰嘴豆、虎掌菌”,彝语“仙人掌、木耳”。同理,植物词汇加上动物类属或动物词后,其词汇意义不再具有植物词汇的意义,而是成为了动物词,如汉语“梅花鹿、枯叶蝶、鸟不踏”,彝语“野花椒、虎掌菌”。
二、彝汉动植物派生名词的对比
派生是常用的构词手段,派生的方式有加缀、重叠、变异、减缀、零后缀等,最常见的是加缀派生。加缀派生词的对比主要是在词缀基础上的对比,本文主要对比彝语汉语动植物名词的前缀和后缀。
(一)前缀
1.汉语的动植物名词前缀主要有“老、小、大、公、母、雌、雄”,例如:
老:老鹰、老虎、老鸹、老鼠
小:小麦、小米
大:大麦、大米、大黄
公:公羊、公牛、公鸡、公马
母:母鸡、母马、母狗、母牛
雌:雌鸟、雌蕊
雄:雄鸟、雄蕊
2.彝语的动植物名词前缀主要有:“a55、a33、a11、ʔo55”,例如:
a55:a55 khɒ33(艾蒿)、a55 nthi2(荸荠)、a55 va33(野山药)、a55 mo11 lə55(土豆)、a55 ŋɒ11(红薯)
a33:a33 tʂɚ55(喜鹊)、a33 dze33(鹞鹰)、a33 ɳo55(猴子)、a33 mɚ55(猫)
a11:a11 ȵo11(蜘蛛)、a11 tʂhɚ2(蜻蜓)
ʔo55:ʔo55 di33(狐狸)、ʔo55 ȵi33(水牛)、ʔo55 po33(蛤蟆)
(二)后缀
1.汉语的动植物名词后缀“子”,例词如下:子:猴子、兔子、鸽子、燕子、骡子、蚊子
2.彝语的动物名词常用后缀有“pu33、mo2、zo33”,例词如下:
pu33:公鸡ɣa33 pu33(鸡+公)
mo2:母鸡 ɣa2 mo2(鸡 + 母)、母山羊 tʂhi55 mo2(山羊+母)
zo33:小鸡 ɣa2 zo33(鸡 + 小)、小鸟 ŋa2 zo33(鸟 + 小)、小绵羊ɦo11 zo33(绵羊+小)
(三)彝汉动植物派生名词构词对比
1.现代汉语的词缀在数量上不算丰富,其中表人的后缀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表动植物的前后缀非常少,前缀只有“老、大、小、”等几个,其中“公、母、雌、雄”是表示动植物性别特征的转化派生,后缀“子”可同时用在动植物名词之后。彝语的动植物名词词缀也不丰富,名物化标记后缀较多,表人的词缀也多于动植物词缀,动植物前缀主要有“a55、a33、a11、ʔo55、ʔo33、ʔo11”, 后 缀 主 要 有“pu33、mo2、zo33”等,其中“pu33、mo2”是表示动物性别特征的转化派生;“zo33”是表达性派生,添加在动植物名词后,有指幼小的语法意义。在彝语中,表示动物性别的词缀比较复杂,特别是表示“公、雄”等阳性性别意义的词缀,在具体到某种动物时,常有不同的表达,例如“公马mu11 to2(马+公)、公山羊 tʂhi55 ɡɯ33(山羊 + 公)、公绵羊 ɦo11 lo11(绵羊 + 公)”。
2.彝汉前后缀的功能对比:藏缅语族语言的a前缀主要有构词、构形、配音三方面的功能。彝语的动植物名词“a和ʔo”前缀和后缀“pu33、mo21、zo33”主要有构词和配音功能,构词功能表现在前缀“a55 khɒ33(艾蒿)、a55 ŋɒ11(红薯)、ʔo55 di33(狐狸)”等词中,加前缀的词语中第二个词素单独提出来是无意义的,只有加上前缀“a55、ʔo55”后才有实义,表示动植物名称,前缀具有构词的功能;后缀“pu33、mo2、zo33”包含性别意义或幼小意义,与动植物词根组合指代包含性别特征或幼小特征的动植物,具有构词功能。配音功能表现在 “a33 ɳo55(猴子)”,其中 “ɳo55”作为词根,具有“猴”的意义,加上前缀后配成双音节。傅爱兰说“所谓配音功能,就是加a后使单音节双音节或四音节化在语流中富有节奏感。这种双音节或四音节词的‘音重’都体现为前轻后重型。因此,带a前缀的词既有节拍和谐,又有强弱和谐。这类带配音a的词大多数与词根意义相同。”【3】藏缅语前后缀构词和配音功能同样适用于汉语前缀“老、大、小”和后缀“子”的功能解释,其中前缀“老、子”突出的是配音功能,例如“老虎、老鼠、猴子、兔子、李子、竹子”等,加上前后缀配成双音节;“大米、小米、大麦、小麦”,中的前缀“大、小”具有构词功能。
3.语序更重要的类型学意义在于各种语序之间的蕴含关系,这种语序之间的蕴含关系反映的是语序类型相互制约的普遍性。受到语序类型的影响,在动植物名词的词序方面,SOV型的彝语中表性别特征和指小意义的 “pu33、mo2、zo33”等词缀在彝语中是后缀位置,为后置词;SVO型的汉语“公、母、雌、雄、小”等词缀在汉语中是前缀位置,为前置词。
4.在词缀化程度上,汉语的派生名词的词缀化程度不尽相同,其中前缀“老、大、小(大麦、小麦)” 和后缀“子”的词缀化程度比较彻底;“公、母、雌、雄、小(小狗)”的词缀化程度较低,还留有明显本义,主要功能是特征转指。彝语的动植物派生名词的词缀化程度比较规则,其中前缀“a55、a33、a11、ʔo55、ʔo33、ʔo11”的词缀化程度比较高;而后缀“pu33、mo2、zo33”等尽管为类词缀,但它们的词缀化程度较低,还留有明显本义,其主要功能是特征转指。
三、结语
本文重点关注彝汉动植物名词的内部结构,从复合和派生的构词角度简要地探讨了彝语动植物名词和汉语动植物名词的内部组合方式,然后用对比语言学的方法将两种语言的构词进行对比,总结了其差异和共性。主要差异有:第一,汉语动植物复合名词的主要组合类型有五种,彝语有三种。第二,在复合词的词序中,汉语主要是“限定语/修饰语+中心语”的语序,而彝语是“中心语+限定语/修饰语”;在派生词的词序中,汉语表性别或特征意义的词缀通常在前,彝语表性别或特征意义的词缀通常在后,汉语无实义的词缀可做前缀也可做后缀,例如“老鹰、兔子”;而彝语无实义的词缀一般只做前缀“a”。第三,彝汉语派生词均是指人词缀较多,指动植物词缀较少。
彝汉动植物名词构词的共性和差异源于地理环境和民族历史文化的影响,建立在彝汉动植物词语的命名理据、隐喻结构、构词特征、词义对应、语用表现、民俗知识系统综合对比之上的语言学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彝汉民族的认知特征,也有助于从不同文化角度认识动植物名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而且在第二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语言类型学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