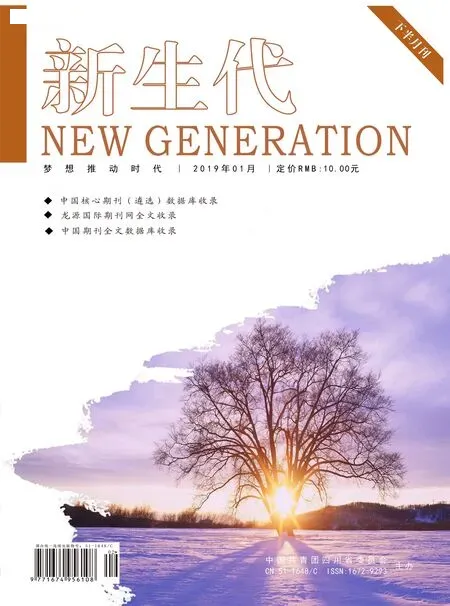水漫江城:1954年武汉大洪水亲历者余敦湖、周国香口述史
郭家麒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1954年夏秋,武汉市遭遇自1865年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大洪水。6月25日,武汉关水位突破26.30米的警戒水位。8月18日,武汉关最高水位达到29.73米,比市区地面平均高程高出5米多,洪峰流量达每秒76100立方米。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各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武汉人民全力奋斗,战胜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以上是《湖北日报》对于1954年武汉特大洪水进行的简报,寥寥数语,让洪水的来势之猛和抗洪人民之勇跃然纸上。
人生而有涯,经历过那场洪水的人们很多都已不在。为了探明武汉这座城市社会的变迁历史,为了深入了解这座城市的发展历程,更是为了复原几代武汉人的集体历史记忆,笔者对余敦湖和周国香这两位老人进行了关于1954年洪水的深度采访,探访他们洪水前后的生活境况。本文由两位老人的录音整理而成,除文章中插叙的转述文字,剔除了对话中重复的语言以外,都是对余敦湖、周国香访谈的真实记录,以确保其口述史的原真性。
那时的生活很造业,很苦
1954年,新中国成立不久,举国上下都处于新中国的建设时期,大多数平民百姓都是一穷二白,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很难解决。当时的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定量供给肉、米、面、油、豆腐、肥皂等,生活物资相对匮乏。据口述了解,一个人一年的油仅有两斤左右。南方供给米,北方供给面,蔬菜品种相对较少。
“我是1954年农历正月初四。当时我父亲有60岁,我母亲也接近60岁,往上有五个姐姐,五个姐姐已经出嫁了,就是已经结婚了。家里就剩我父亲,我母亲。他们本来没什么劳动力,我父亲提出来要我到武汉学徒弟。当时我只有14岁没到,因为我是正月初六生的,40年正月初六,我初四就来了,仅14岁差两天,学徒弟。其实是满了13岁,刚进14岁,学木匠。走了半年以后就淹大水。这时我又回乡里去了,回乡里去了以后呢,休息了一段时间,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水就退了。水退了,下半年以后我就来到了武汉。”余敦湖爷爷未满十四岁就要外出做木工学徒,年迈体弱的父亲和丧失劳动能力的母亲让他早早地懂了事,外出赚钱补贴家用。
“生活很造业很苦,要捡菜,喝井水。每天都是这样,那时候的水一分钱一担,一大桶。没有钱买,只能打井水,洗米洗菜。井水也是私人的,“华光染厂”,就在慈善左巷对面。我们在那里挑水,用铁桶在井里打水,然后再挑回来洗米洗菜。那时候不存在什么脏和不卫生,只要有饭吃饱就行了。后来井水成了绿颜色,井水烧出来的饭都是绿颜色的,我们就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一般井水是用来洗衣服的。后来就问华光南厂的,哪里的师傅就说他们是用井水来染布料的,水里有化工原料。所以化工原料就被我们这些打井水的吃了。我们家做小生意,卖浮子酒,卖小汤圆来维持生活。那个时候闹三反五反打老虎,打的那个运动特别厉害,所以这些商人也做不下去。那个时候每天都要死五六十个人,跳楼的,大资本家因为害怕就跳楼了。在这个当中我们做生意没有人吃,赚不到钱,就只能吃救济,那时候的救济只有三块钱。要是家里有人戴金银首饰,那就别想吃救济。我们读书的时候都没有钱缴学费,都是我的吴老师帮我缴学费,当时我说我不读了,我们家没有钱,那个时候还谈吃菜,什么都没有,就是一点饭就可以了。出行只能走路。我们家自谋生活,从这里走到同济医院,挑二十斤煤。在桶里就放二十多个小碗和汤勺。我父亲挑篓子、担子,我挑煤挑桶,我要从航空路挑水到同济医学院,晚上总到12点才回,我越走越打瞌睡。那个时候的路是一高一低,不像现在的路是平的,你挑个担子一颠簸,瞌睡就醒了。通常因为第二天还要上学,所以我那时候就喜欢下雨,下雨就不用出去做生意了。就那样去维持生活——今天买三斤米,吃完了明天赚钱再又来买三斤米,不是像现在这样一次买买十斤、二十斤、一百斤,没这样的。”周国香奶奶的家境不是太好,以做小本生意为生,当时“三反五反”、“打老虎”运动的开展,让她家的老主顾们一个个都不在了,这让她原本就捉襟见肘的生活雪上加霜。吃完今天还要操心明天,在这样的情境下,老人觉得不用出工的下雨天都是天大的恩惠。
即使在风调雨顺的年月里,上述的生活也是他们每天的常态。那洪水到来以后,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发洪水的时候我回老家了,师傅家的吃住是按计划的,当时发给的粮票之类也没有减少呢。政府也没有安置他们搬家,他们还是平和地过,房子没冲下去。我是水退了就回来了。我屋里一个师傅一个徒弟,我是徒弟。我的师傅是我叔叔,他请的师傅姓蒋。后来我在这里做,姓蒋的就走了。发洪水回老家老板提出的,没生意,吃闲饭,我吃了他就没吃的了呀,那我只有回去了,这个到底很简单的事,那我说吃饭不做事肯定好咧。没有人做桌子柜子,你说我在哪里干什么咧,水退了生意来了,我就回来了。”余爷爷告诉我们,洪水来的时候,为了减轻师傅家的负担,不吃闲饭,所以孤身一人回家去了。周奶奶告诉我们,“54年井涨水,我们房子的地板不是干的,一走就有一滩子水,水都冒到地面上来了。我们隔壁左右的都会踩出水,不只是我们一家。”左邻右舍都遭了罪。
一片黑压压的水
在访谈过程中,老人们提到,当时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片黑压压的水。在洪水到来之时,他们记忆里的武汉遭遇了这样的灾情。“汉阳的受灾情况……当时那还是有影响的。房子有的垮了的,要修,田有的淹了。他的返乡人员蛮少,我认识的万县的其他的没有,因为我们硚口这里严重些。再有的就是武昌的就不存在了。武昌没有被淹,它主要淹就是琴断口,现在我说,就是东德啤酒那个茬口断了,那个茬口断了以后,整个水就流到汉阳去了,武昌就不存在了,武昌的江滩没有垮。”
爷爷在回家的时候,发现往日通路的地方变成了渡口,还摆起了船,他讲出当时坐在船上的这样一段见闻。“在离开的时候最深刻的是……坐木船回去,沿路的屋顶啊,房子啊,都只露顶子出来了。汉阳那边淹的水啊,我只看到屋顶。人都撤离了,政府撤的,往高位子走啊,位置大概是在汉阳石湖。当时坐船票价记不清楚了,时间久了。船就在硚口码头搭的,在发洪水之前就有一个硚口码头,那是现在的金三角那条线。船夫在发洪水的时候赚钱的,当时是个个体户。一个木船,两个桨,土船。船夫在发洪水之前也是淌船的。坐船回去,坐木船回去蛮危险,里面5、6个人,小船毕竟有点浪嘛。14岁的时候,看到那个屋顶尖子啊,冒个尖子过去了,再冒个尖子过去了,再其他就是一片黑压压的水。”奶奶并没有地方可以去,她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后来没读书了,因为洪水涨得很厉害,把学校给淹了。没有上课了,就把我们居民安排到……那个时候不叫社区,叫居委会。居委会的主任就把我们迁到慈善会,那时候的雨下的很大。新路这里六角堤是淹水修的吧。淹水以前水就要往这边来了,汉正街的堤并没有倒,但因涨水都把市医院漫了,宝善堂那个水都吓死人了,水漫金山。后来政府要在这里做一道堤,水退了就把堤拆了。”回忆起那时的场景,奶奶还记得水淹到了哪里。“第一道堤,就是汉正街那道堤。第二道堤是新路,新路那一边的就用木船,现在叫划子。那一边就是水漫金山,走划子的,我们这一边还没有。汉正街第一道堤已经淹了,第二道堤的一边淹了。武广那边还没有,我们这边都淹了,中山公园也是。武汉地区的受灾情况比农村来说,还要小些。但是比民国三十年的还大。只有农村的人到城市来讨饭。 主要地方被淹的地方是天门、沔阳、汉川、黄陂、孝感等农村地区。武汉市区的话就是汉阳。原来就是靠月湖桥那边只要涨水就是一望无际。武昌还好,因为地势较高。汉口主要(淹的)是汉正街、从集家嘴一直到古田。”聊到这儿,老人们还回忆起当时鱼和粮票的故事。“54年汉口的鱼啊,满街都是。汉口的鱼,卖鱼的,不知道几多!那时候就是鱼多,因为涨水。那个时候人平(均)只有七块钱,没有钱买鱼。当时具体的政策就是吃鱼发油票,买鱼还给送油票,你买一斤鱼,就给一两油票。你买多少就给(相对应)多少油票。当时不发粮票,只发油票,都是计划的。但是涨水后鱼多了,就没有人买吃的,没有钱怎么办啊,那就卖鱼,买鱼就返油票。至于商家给我们的油票是政府补给商家,还是商家自己出就不清楚了,我认为是政府补贴给他们的。”
根据两位老人的口述,我们可以了解到,武汉大多地区均已受灾,其中以汉口最为严重,人们的生产生活都受到了冲击。
当时人们都团结一心抗洪
面对这样的洪水与困苦的情境,我们都为当时的社会治安、流民问题、社会舆论捏了一把汗,但两位老人却微笑着告诉我们并非这么回事。奶奶回忆,“当时民心很稳,好像思想都蛮纯的,没有动乱。没有蛊惑人心的谣言,因为那时候谁要说怪话,就是造谣、现行反革命、右派。谁都不敢说,那时候大人小孩的思想都蛮纯洁。”
这样的民风中,我们思索起那个遥远的年代,人人都一颗红心向太阳,虽然日子清苦,但是大家都朝着把祖国建设好的目标而努力。我们又追问起当时的抗洪救灾问题。爷爷表示因自己的年龄不够,当时无法参与抗灾。奶奶向我们讲述她当时抗洪的情景,“有组织抗洪队,由政府牵头。政府通知街道,街道通知居委会,要居委会下计划,比如你这里要去几个人,都集中去。抗洪的人主要我们社会青年(居民),一部分是社会青年,一部分是工厂的人。当时抗洪具体做的是那个担子,上面系三根铁丝,挑土筑堤。土是在农村的挑的。政府派火车把土从农村运过来。我想那时候还不是派车子,因为那时车子很少很少的。发洪水铁路轨道没有受影响。”奶奶告诉我们当时政府有组织抗洪队,社会青年广泛响应,于是大家带上粮票,有组织有纪律地浩浩荡荡坐上火车抗洪去。“火车,火车票是政府出的,我们只带被褥行李。有队长组织,我们社会青年由户籍带队(即派出所的管账),当时带队的是叫岳金毛。住在农村居民家,不要钱,大家是分散住的,你这里住几个人,那边住几个人。那些居民家没有受灾,是我们过去支援。吃食堂,自己做,街道组织、区里组织学野战军烧火做饭,有单独的人做。我们带粮票过去交,上面说要拿粮票买粮食。”回忆起抗洪的工作,奶奶向我们介绍了当时抗洪队伍的分工,以及抗洪时的工作情况。“工作主要是挑土筑堤。那个位置的土就不用火车运,本身就有山。男女都挑土,没什么细分工,是随机分的,工作大概有三四个月。三四月份回来的,回来后我就分到了粮店的工作。回来的时候武汉的洪水已经退了。要鼓舞士气那就表扬啊,比如用喇叭广播,谁刨的快啊,谁挑的多啊,那我总是得表扬。没有类似唱歌之类的娱乐活动,累的像鬼一样。不记工分,那时我们是义务嘛。”
淳朴团结的民风,一致抗洪的勇敢,这是那场洪水留给爷爷奶奶的记忆。
结语
时过境迁,当1954年的大洪水也成为了历史,成为了当代人们心里一个遥远的名词。但洪水留给那些亲历者们的,确是不可磨灭的记忆。洪水固然可怕,但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人民众志成城抗洪灾,齐心协力搞建设,困难在团结面前也就不堪一击了。当爷爷奶奶向我们口述这段历史时,我们了解了当时的艰辛,党与政府的努力,江城洪水的可怕和那辈人民的淳朴。
作为当代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我们理应负起责任,抢救有关那场洪水的记忆。这是江城的历史,这是那代人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