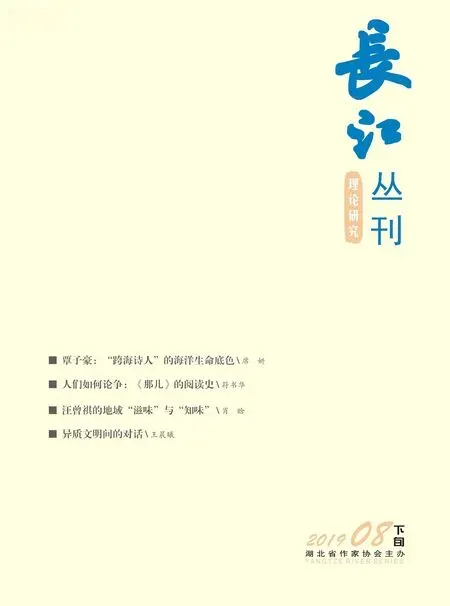覃子豪:“跨海诗人”的海洋生命底色
■席 妍/四川美术学院
覃子豪的涉海题材的诗歌作品占据他现代诗创作非常重要的部分,也使他获得了“海洋诗人”的称号。无论是其渡海经历,还是对海洋题材的开掘,都为研究其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故研究覃子豪的海洋诗创作以及其海洋隐喻,可发掘诗人渡海前后创作风格的内在转变,表现其诗歌创作中所流露的“隔海望乡”的原乡情结以及他对于自我生命的完成和诗歌技艺的美学追求。
一、早期创作的海洋向往与渡海经历
海洋与诗人覃子豪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紧密相关。1932年,年满二十岁的诗人出川到北平,进入中法孔德学院高中部学习,一开始便接触到十九世纪法国浪漫派诗人雨果以及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等人诗作。在孔德学院读书期间,覃子豪开始了新诗创作,并深受浪漫派与象征派影响。早在作者最初的创作中,海洋就成为了他诗歌中的重要意象,诗人写道:“我的梦/在静静的海滨/有海藻的香味/有星,有月,有白云……”(《我的梦》)这首诗以“梦”为题,以乡村和海洋对照,界定梦域之广远,渲染梦之声、色、气味,构成一个清新而忧郁的梦的象征。这首诗作于青岛,诗人在之后《海洋诗抄》的题记中曾回忆到北平念书后,每年暑假都会去海边,又指出烟台和青岛的海景最美。诗人更进一步表露出他的海洋情结:“自幼我就喜欢海,可是四川是群山所包围的一个盆地,没见过海,连湖也不曾见过,我却对海洋有一份恋慕与怀念之情。”巴蜀深处内陆,要见到海洋殊为不易,在《我的梦》中,不难判断催动诗人情愫的一端恰是这一片青岛的海滨,而另一端大概就是深处内陆的故乡。这一梦的“单恋”底色,或许正是这个漂泊在外的年轻人潜意识中思乡情地流露。这首诗最早收录在他与友人合编的诗集《剪影集》中,可以算作覃子豪海洋诗创作的源头之一。
在他的早期的诗歌中,诗人并没有将海洋作为直接书写的对象,但在他不同类型的诗作中,却不时呈现出大相异趣的涉海风景。例如《海滨夜景》中烟台的海滨路:“海滨路上荡着闲游的妇女/穿着绿色的红色的单衣/裸着双双的赤裸的臂膀/是海里漫游着的长长的银鱼……”鸦片战争后,1862年烟台开埠通商,走上半殖民半封建性质的城市发展道路;直到1932年,烟台有超过十个以上的国家与其发生贸易往来。故诗人敏锐地捕捉到海滨故烟台海滨迷离浪荡的氛围,具有强烈视觉效果的光影以及混合着舶来的爵士音乐、基督教堂傍晚的钟声——侧面展现出1930年代现代烟台海港都市的感官特征。而那些裸露着臂膀的慵懒、肉感、闲散的女性形象,成为现代海滨风景的一部分;同样,在《浴场》中,诗人亦将目光投向了熙攘的海滩:“每天都有许多游尸在海滩上徘徊……在黑浪里浮出……”诗人不加掩饰地流露出对“美国细腰女郎”和“意大利军舰水手”的轻蔑——原本洁净的海滩异化为现代化“浴场”,而横呈在海滩上裸露着的身体展示出一种奇异的陌生化效果,诗人视之为一种舶来的无生命的“艺术品”,赤裸着、提醒着诗人,一种源自现代文明和殖民历史记忆交织的屈辱感。如果将这首诗与他另一首《码头》联系来看,更能够清晰地看到缘海风景在现代世界中的变换:“千只/万只——中世纪的木船/疲倦地/靠在近代文明的码头上//腥味的水上/动荡地/闪着昨日的斜阳/白帆不见了/已被海风埋葬……”海洋不再是充满“海藻的香味”的幻梦,而是一个今昔重叠的历史时空表征:昨日的木船从今日的码头出发,曾经的白帆也在今日的海风中失去了音信,挣扎在半殖民半封建海洋上的讨海人,亦成为诗人同情的对象……这些涉海的诗歌大多创作于烟台和青岛两地,诗歌风格多受象征主义影响,运用暗示、烘托、对比等通感联觉的手法,展现出1930年代青岛海滨都市化,所带给诗人的西方光怪陆离的现代性的幻觉体验。但也不难看到,在轻微的迷醉之中,诗人侧身其中颓废彷徨的身影后,他敏锐地触摸到的中国的现实。作家流沙河曾评价覃子豪这一时期创作,难免有“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倾向,认为他诗中流露的忧郁、苦恼气息只是单纯狭隘的个人情绪,这固然有诗歌“横向移植”的影响存在,但却不免忽视了这些涉海主题的诗歌所包蕴的属于诗人的一种现实洞察力。又或许,这种存在于涉海书写中的洞察力,与他之后迅速转向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不无潜在的关联。因而也不能被忽视。当然,诗人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创作,主要还是耽于年轻生命本能的冲动,因为远离巴蜀故土的孤寂,搅扰着诗人的情绪,“一种恋情和怀乡病所混合的情感”便潆洄在诗人心中,触发他诗思。而怀乡情感的反面则是诗人不愿被禁锢的“行客梦”,正如他在《我不愿意停留》一诗中剖白道“赞美流浪”,这种渴望漂泊的心境或许也实出于他本就拥有的浪漫天性。
1935年,覃子豪从渤海乘船前往日本开启了他的留学生涯。在此期间,他切身感受到了留日中国学生的艰难处境。据覃子豪的挚友李华飞回忆,在日期间,覃子豪饱尝恋爱的滋味亦遭受失恋的打击,在甜蜜与痛苦双重刺激下,他的诗歌创作更加突飞猛进,那时的诗人在李华飞眼中是一个“充满激情和童心的性格人物”。但很快覃子豪就抛开了个人情绪,一水之隔的中国正深陷在抗战的泥淖中,牵动着海外游子的心。受到日本左联运动的影响,覃子豪于1936年在东京创办了《文海》杂志。自此他的诗歌创作转向了对抗战现实的关注。覃子豪也在诗论中谈及当时的创作方向的改变:“由于新环境的刺激,便从感伤的,幻惑的,孤独的感情中走向现实的世界。”这一时期,诗人虽未能创作出与海洋有关的诗歌,但在他后来的回忆中,这段人生经历仍然依托着海洋,并与现实产生了某种“共情体验”:“自离开四川、北平去到日本以后,我从山地之子一变为海洋之子。烟台,青岛孕育了我对海的意念。而极富岛国情调的日本,令我对海有更深的体验。我爱海,从未厌弃过。犹之我对恋爱永未满足一样。”不难看出,海洋内蕴于诗人的个人经历,甚至潜在地充当着他情感的催化剂,只是迫于战时的特殊境况,无心于海洋书写也可以理解。
“七·七”事变后,覃子豪及友人都相继回到上海,并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刚刚重返祖国的覃子豪,触目所见即是战时的海洋景象:黄埔江上巡行着无数军舰,而江岸边则挤满了饥饿与求生的难民,对比这外滩租界上立起的银行、买办公司等建筑,两厢对比下,“国破山河在”的现实更加呼之欲出。在《水手兄弟》一诗中,诗人以“水”自拟身世:“我是巴人/从瞿塘峡的险滩游过/到过巫峡的绝壁/从孩童的时候/就不曾恐惧险恶的洪波……水波给我的艰辛/我终于在苦难中长大/我立志要在祖国的海上/做一个航海的人……”。可见诗人对海洋的情感在抗战时期也是多重的:现实中,海洋是被掠夺和封锁的边境,这与他在黄浦江畔所见的“破鞋似的木船”以及“欧罗巴来的巨船”显然有所呼应。战时的海洋是禁区,也是斗争展开的核心区域,覃子豪也在诗中直接呼号,“中国的船不能越出中国的海岸/这是悲哀,这是耻辱……”。事实上,诗人在抗战时期也有意无意间将海洋纳入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中。他在1937年12月发表在《诗报》半月刊试刊号上的《伟大的响应》,便鼓动联合同胞一起抵抗日寇侵略。正如诗人所言,要以诗为“旗帜”,为“擂鼓”,为“呼号”,宣传和鼓舞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而有论者说,诗人此时的创作已经“由对敌人无比痛恨的静的情绪,升华到创作的灵感,化成动的诗行。”诗人在《真实是诗的战斗力量》一文中谈及,面对现实,诗歌创作的要义必须是“真实”,唯真实方能至诚,而真诚才可打动人心,启发众志成城之心意。颇具意味的是,诗人在这篇诗论中,特以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的“日神精神”来启发诗人要有太阳般光明永恒的意志与高蹈的理想主义激情。这一种升华的战斗情感无疑携带了诗人原有的浪漫主义基因,而“日神”意象,可视为火的形象的转述,故此,太阳与火虽然都具有一种热烈、光明的外在轮廓,但事实上却内蕴了一种冷静、适度、克制与肃穆的情感要求。加斯东·巴什拉以“理想化的火”来隐喻其辩证的两端:“点燃的火或献身的火,毁灭他人或毁灭自身。”对于覃子豪而言,诗人作为一名战士,固然需要“火”一般的热烈甚至倾向于自我毁灭的激情,但以海洋为代表的“水”的景色却构成了他诗歌创作中潜在的精神暗流,或者说,海洋在无形中已经构成诗人一个隐秘而丰富的心理空间。众水凝聚的海洋与万火之源的太阳,两者意象交缠在一起,构成覃子豪早期诗歌创作中,那种忧郁和激情交织的浪漫主义抒情风格。而海洋对诗人而言,既是私人的幻梦,也是现实中被封锁和突破的残岸断崖;既是历史的渔舟唱晚,也是现代的、破碎的浮木悲歌。故此,了解海洋触动诗人的诗情,从“水之来处”审视诗人的漂泊与游离,方能理解诗人抗战时期创作的火一般直面现实、战斗与反抗的精神内核,也更明了诗人去台前后,海洋般涓滴意念汇合而成的生命底色,这与之后他渡海而去的决然选择与生命回响,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抒情化的海洋书写与多重海洋隐喻
覃子豪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海洋诗抄》,《海洋诗抄》甫一出版,就迅速获得当时人,尤其是对新诗创作有兴趣的年轻人的喜爱。这本诗集更进一步加深了诗人与海洋的联系。可以说《海洋诗抄》不仅是诗人渡海后的个人体验,亦是他在异乡回首往昔,怀念故土,旋即深入自我的潜在精神空间。其诗歌风格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当时压抑的文学创作环境的反拨。
学界普遍认为,覃子豪诗歌创作的巅峰是在《画廊》时期。《海洋诗抄》重要性其实不亚于他之后艺术技巧上可能更加成熟的《向日葵》、《画廊》等诗集。换言之,人生和文学,两者本就是二而一。《海洋诗抄》所具有的内涵可能并不单纯是对海洋题材的集中书写,重要的是,这一系列海洋诗的创作,伴随着诗人在台最初几年生活以及在地认知,最大程度地展现出了诗人漂浪与抒情的心灵体验。覃子豪曾在《诗·生活》一文中写道:“心灵生活和现实生活的交溶是诗创造的原动力。”
1947年12月,诗人创作了诗《向往》,他在诗中表露:“我将重作一个航海者乘白帆而去/我将再在海上作无尽的漂流 /但我又不知道该去哪儿?”此时诗人并未指明他将要去台。而是在诗中流露出一种渴望远航的向往之情,他渴求寻找一个“理想的境界”、“自由的国度”以及“爱情与诗和音乐的疆土”。这与他 1946 年作的《倚桅人》似构成一种回应,身份不明的流浪者,倚靠着船桅,似在“寻找失去的希望”——这一孤独的形象如同诗人的自我投射。将大海作为归宿,是诗人背对战争后千疮百孔的现实一种无奈的选择,也是他作为一个诗人寻求精神疗愈,重建理想诗意国度的内在诉求。在最初的几首海洋诗中,能够看到诗人面对大海的喜悦、豪迈和旷达之情。例如《自由》:
“海洋啊!在你底面前/我了解了自由的意味了//我将赤祼着,像白色的天鹅/跃入蓝色的波涛//意志是鸢飞/思想是鱼跃//希望在无穷的远方 / 要学海燕,远征重洋。”
想象必以经验为尺度,经验是个人感受的总合。《自由》无疑是诗人真正自觉地将海洋纳入书写对象的开端。诗人被压抑的情感面对浩瀚开阔的海洋空间,无可遏制地宣泄出来,“鸢飞鱼跃”隐喻思想和意志的自由、开阔,体现出海洋对诗人情感和知性思考的触动。现实的海洋刺激着诗人敏感而细腻的感受,也启发诗人创造出了丰富而多元的海洋审美体验。可从以下两方面得到证明:
其一,诗人作为漂泊者(漫游者、旅行者),构建起海洋化的审美距离。诗人大部分海洋诗作于几个重要海港及外海岛屿。他曾表露“我在旅行中诗性最浓,诗的产量最丰”。旅行是人与一个地方或空间关系的审美化,也是一种有距离的自我审视。譬如为人所称道的《追求》一诗:
“大海中的落日/悲壮得像英雄的感叹/一颗星追过去/向遥远的天边//黑夜的海风/刮起了黄沙/在苍茫的夜里/一个健伟的灵魂/跨上了时间的快马。”
诗人面对太平洋的落日,产生了独特的审美距离和审美感受。诗人敏锐地捕捉昼夜轮替的刹那——夕阳“坠海”时如英雄般无声的沉重,孤星旋即“追去”的轻盈与迅速,一静一动之间,勾连起海天交接的广阔的空间感;海风刮起的不是海浪而是“黄沙”,更是将海洋与陆地(沙漠)两重空间并置,将现实的海洋与幻想中的大漠并置,将现实的岛屿和无法触及的大陆并置,唯一能超越时间,并跨越重重空间藩篱的,与其说是一个强健的灵魂,毋宁说是一种坚韧的意志,或言“追求”。然而诗人要追求什么,诗里并未指明,但诗中流露出的英雄主义气质,无疑揭示出诗人注视海洋的同时,将自我置于一个省思的地位。
无论环岛游历或是因公出海的暂时停泊,诗人到底也未能与他踏上的岛屿立下“契约”。故在他之后创作《骊歌》、《书简》等诗作,大多借海寄寓怀乡之情。1951年7月覃子豪因公出差到浙江外海的大陈岛,诗人隔海望乡,借“女郎”之口表达近乡而情怯,归乡而不得的忧愁:“一片蓝色的土地/在海的水平线上若隐若现//离你的家乡太近 /离你却如此遥远。”这一诗境,不难让人联想到余光中的《乡愁》和洛夫的《边界望乡》。正是从覃子豪始,“隔海望乡”这一独属去台诗人的乡愁体验,此后便成为一代又一代流亡者的集体记忆。归乡不得,诗人便“厌倦在海上流落”,要“去觅归路”(《虹》)。
其二,诗人一方面将海洋作为直观体认的审美空间,另一方面则是在文本中呈现出多元的海洋象征。覃子豪说:“我对海有写不尽的情感,要归功于象征派诗人给予我在表现技巧上的训练,我从象征派诗人中学到比喻、联想、象征,暗示等手法……从许多角度去看海,看侧面,半面的海,较之看全面,正面的海,尤富趣味。”例如《海的时间》:
“太阳是渔人的时计球/在海的辽阔的篇幅上/画上立体的时刻的蓝图//它用海波底色彩/表明气候的变换/它用白金色的直线/表示中午/又用红黄色的斜线/区分早晨和傍晚……”
诗人自道写出了“海的立体感”。他以太阳为焦点,将海视为一个立体的几何空间,以太阳白金色的直线、红黄色的斜线,构成中午、早晨和傍晚的“海的时间表”。海洋给予人无限广阔之感,在此无限漂浮的空间中,时间感被弱化,因此以太阳移动为坐标,以空间感知时间,是海上独有的记时方法。诗人从不同视角观察海洋,借空间视角的变换,暗示时间的感觉。而在《群岛》一诗中,诗人又运用对比和重复的视角,写出海天一色的空间感知:
“海上罗列的岛屿/像天上罗列的星辰……天上的云是海上的雾/海上的雾是天上的云/天上的群星闪烁是阳光中的岛屿/阳光中的鸟屿闪烁是天上的群星//我驾著一叶扁舟航行/沿著群岛错落的海岸/如同我航行在天上的/星辰与星辰之间的港湾。”
“海”与“天”相映,道出空间广阔透明之美;“海雾”与“云影”相谐,摹拟淡然渺远的云天之境;“阳光下岛屿”与“闪烁之星辰”相对,更以星辰之众,来暗示和比拟群岛散落、明亮之情态。整首诗句式工整,连用四句同位语,两相照应,如二手击掌,循环复沓,节奏音韵也模拟出海天相接的意境。
覃子豪在其诗论中强调,集中力量写一首诗,要选出最重要景色来刻画,要把景色和作者的情绪打成一片。因此,诗人不拘泥于写海的“宏大”视角,而是进一步将抒情化、情绪化的海洋,通过各种丰富而细微的意象加以展现。反过来,也即是将海的象征空间扩展到最大最广,包容一切细致与粗糙的可取之因素,超越单一的海洋特征,将一首诗的属海特质浓缩在最微小具体的事物,在一瞬间产生并击中属海的感觉。譬如《贝壳》:“诗人高克多说/他的耳朵是贝壳/充满了海的音响/我说/贝壳是我的耳朵/我有无数耳朵/在听海的秘密”;又如《岩石》:“奔腾的海 /美丽的,温柔的海/神秘的,令人沉迷的海……岩石,像一个哲人/在低头沉思/永远坐着 /面对海洋”;再如《临海的别墅》:“我临海的别墅/是猫一般的神秘……十年海上漂泊/我不曾回去/那蹲在崖山的黑猫”……诗人将海洋所具有的神秘性、哲理性的几种特点,都通过相关或相对的事物来加以提喻、暗示并且象征化。故而海洋诗则从单纯的意象之美,变为繁复的多重意象的联觉,对照互补,构成独特的海洋象征,也使得海洋诗在形式和内涵上,表现得更丰富,展现出海洋多样的形象。
覃子豪曾谈及海洋对于人生、情感、心灵乃至诗歌创作的重要性:
“森林、草原、河流、山岳,各自有其特性和美……我只有对海的印象特别深刻。豪放,深沉,美丽,温柔的海,比人类的情感和个性更为复杂,不能归入静的或是动的一种类型。它是复杂而又单纯,暴燥而又平和,它是人类所有一切情感和个性底总和,它的外貌和内在含蓄有无尽的美。……它摹仿人类的情感,而对人类的心灵却又是创造的启示。它充满著不可思议的魅力;比森林神秘;比草原旷达,比河流狂放,比山岳沉静,是自然界中最原始的祖先,也是给人类带来近代文化的骄子。”
诗人以为,海洋模仿了人类的情感和内心,而人类的情感和心灵却又受到海洋的召唤和启迪。可以想见海洋对诗人现实生活与内在精神产生的深刻影响。相较真实的地理海洋,诗人逐渐转向自身,现实之海也转化为其心理与精神的一种象征。他作于花莲的《花岗山掇拾》就显现出与他之前海洋诗创作路数颇异的精神向度:“花岗山上没有释迦牟尼的菩提树/不羁的海洋,是我思想的道路…没有人会惊讶的发现我的存在/我有不被发现的快乐……”
诗人朝向海洋的省思,与其视为一种“证悟”,不如说是一种自我距离化的书写。诗人在花岗山看海,但海不再是观察与审视的客观对象,它深入诗人流动的思绪,“苍白的沙漠是死了的海洋”,而“青色的海洋是活着的沙漠”,人类的原始的记忆和海一样,拥有不被了解的神秘与宽广,海洋与陆地(沙漠)空间,在时间变换与死生的循环中合而为一。身在异乡的诗人,不能追溯历史的记忆,也不被这片土地了解,故他“望海”、“观海”、“念海”,实则也是将自我陌生化,在一个如海一般神秘而陌生的空间中,诗人重新返回自身,并由此步入他朝向自我内部,更为圆熟,但同时也可能更为矛盾和抽象的诗意空间。
三、“抽象的海”:诗人的自我完成和超越
覃子豪的《海洋诗抄》作为一种人生与诗歌技艺的过渡,不可忽视它对于诗人的现实意义。海洋作为诗人以创作联接故土的精神空间,对其后期诗作也产生了潜在的影响。在历史断裂之处,覃子豪是否遭遇过现实与精神危机,很难从现实中加以考证和还原,但在其诗风转向所透露的神秘的讯息中,我们得以还原他后期创作的现代性感受。所谓没有产生经验的环境,就不可能有真切地感受;而没有对事物进行确然的描述,感受就是空洞无物的抽象概念。海洋并不只是孕育生机或者暗藏凶险的真实场域,一方面它是诗人情感归属的空间,诗人所经验的海洋空间为情感表达提供了修辞;另一方面,海洋涉及与诗人“在地”感受和其余事物关系的联接性,海洋空间对诗人主体意识起到了某种潜在的建构作用,与此同时,诗人也通过书写海洋,最终生呈出一个“新我”。
不少评论者认为覃子豪后期诗歌格调低沉,缺乏前期激昂的情绪和战斗的意志。贾植芳认为覃子豪从象征主义走向神秘主义,似乎陷入了一种迷惑、虚空的人生处境之中,但他也肯定这一转向的积极意义,“这是作者的内在精神世界与外部现实相抗争矛盾的结果,是对现实世界的抗议式的逃亡”。而诗人流沙河也认为覃子豪后期诗歌创作对“外物的关照少了,而内心的探索多了,被象征主义拖了后腿”。两者都认为《向日葵》与《画廊》集晦涩难入,为其走向冷凝、抽象感到不满。但覃子豪在谈这两本诗集时,也与《海洋诗抄》作了简单对照:
“第二本诗集《向日葵》不及《海洋诗抄》之受青年朋友欢迎,就是《向日葵》所表现的内容为较深沉,凝练;读时须加思考,方能领会其中意趣。而我的第三本诗集《画廊》较之《向日葵》所表现的更深,青年人或许不能普遍的接受。而我自己感觉近两三年来写的诗,更富人生的意味,更深入生活的核心。”
覃子豪是否真的回避了现实,他本人和评论者似持有不同的看法。在对《金色面具》一诗所作的自我剖析中,他曾如此表达他的人生主张:“若要去理解万物,必先理解自我……不理解自我和万物存在的意义,如何理解人生?”诗人去台之后,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更重视内心的探索,他不断对自我与外在世界的距离进行着修改,在诗歌艺术形式的追求上更加倾向个人化的自我表达,以至于流露出强烈的信仰意味。而向内在寻觅的过程,也是诗人对外在现实的一种反向投射。“金色面具”上流露出的那种不为人的本性、欲望所动摇的冷漠超拔的神情,那近于审判者一般冷酷而神秘的面容,恰为流离于异乡的诗人,呈现出命运中最“真”的一点。虚幻与现实,对于一位饱尝战火,多方流离,情感又敏锐丰富的诗人而言,似乎并无太大区别。正如他所言:面具是自我的对照,然而面具却已经超脱。诗人辩白道:“这位‘超人’诞生于我的生命发轫的深处。也许这‘超人’就是我,是升华了的我,超越了的我。是新我,不是旧我。”此时诗人所言的自我,是一个形而上的自我,一个在诗歌技艺的求索中所锻造的艺术化的自我。但诗人也意识到“即使是神秘、虚无、缥缈的感觉和感情,也不能离开人间的关系感受”。因此,诗人的自我是从他与现实人生的经验和与他者的联接而来,这“他者”也包括万物。若要求得人性中的真,便要祛除遮挡在“人性和物性的共通之处”的障碍。说到底,现实的变换如何不是幻梦?而梦如何又不是真的呢?故此,诗人有意识地追求并试图超越自我,虽然“金色面具”终究是假的,但诗人到底作出一个自我超越,自我更新的假设,展现出诗人在现实和追求间苦苦缠斗的心理。故他此时的诗风冷静、明澈,一方面呈现出早年冲动热情到达极致后复归平静的心态;另一方面,也是他对于历史现实的呐喊批驳,转向了对诗歌技艺的打磨和坚持。隔海分离的命运,就像他一样的这一辈流亡者的共同命运,在对抽象的自我的描绘中,诗人内心深处真正渴望的是一种相互联接的心灵的共鸣。诗人再度将情感寄托与海洋,而海洋不再是外部风景,或是单纯描摹的对象,而内化为诗人的思维律动和心灵和声,合二为一:
“啊!你在咏叹晨光中砰然一击,撞开了一曲交响,一树银花//银树千株,圆舞般的,起起伏伏,在黑岩上婆娑/花朵,带著如虹的幻惑的色彩,繁开又凋落/临风的水晶枝奏出玲珑的声响/一支终曲,凋落在绿玉盘中,溅出余音//梦境缤纷,变幻无穷……”(《海的咏叹》)
诗人形容海的浪潮声“超越悲欢”,“无损伤”、“无疲惫”且永不停息,甚至超越悲欢。而他个人则是寂寞的,面对海洋却感受到来自尘世的“鞭打”,实则在自我内心中沉浮,疗愈。诗人以多层暗示、隐喻、拟人、通感手法的运用,展现海浪的姿态、色彩,极富音乐感和韵律感。可以说,海洋是对诗人内在情绪和意志的具象化显现。诗人借海洋,不断潜入、倾听内心的声音,但最后无他,唯有一声“叹息”。在这追问更进一层,可看到海洋被人格化为某个不确定的对象,恰如“金色面具”,毋宁说海洋是“你”的化身,不如说,海洋是联接“你”和“我”情感与思想的路径。伤痕是共通的,寻求的完整恰是累积的伤痕;沉沉低回的叹息也是人生的一种咏叹。在《海洋诗抄》中,往往只能看到诗人与海洋空间两厢对照的情形,而从《海的咏叹》开始,覃子豪的海洋诗创作也进入了心灵无意识的内面。海洋也开始具有了更丰富、抽象的诗性色彩。从现实层面来看,诗人叹息着寻求自我的“跃升”,但依然被自我所牵扯,这大概是他现实处境的某种影射。
海洋作为诗人外部现实与内在精神的“联接物”,在整部《画廊》集中多次出现。值得玩味的是,这一“联接”,则多是通过“海”与“眼睛”的互喻来实现,例如:“海的眼睛凝视着南方燃烧的七月”(《火种》);“海睁开一只大眼睛/投七色回光于画廊”(《画廊》);“岛外之岛,海外之海的迷茫/说你的眸子也是迷茫的,像海/有云的忧郁”……在海洋上打开的视野,到诗人的后期,似抽象为一种空间的内外辩证。《画廊》中,诗人解放了他的想象力,体验到内外视角的翻转,例如《域外》:
“域外的风景展示于/城市之外,陆地之外,海洋之外/虹之外,云之外,青空之外/人们的视觉之外/超Vision的Vision/ 域外人的 Vision……”
“域外”是一个空间性的形象,它隐含着某条边界,是可见之物和不可见之物的边界,也是存在之物和遮蔽之物的界限,更是现实与超越现实上的事物的边界。显然在这首诗中,诗人追求的是隐而不显和海洋所展现的空间是一致的。但诗人在他的代表作之一《瓶之存在》里这样描绘:“似背着,又似面着/背深渊而面虚无/背虚无而面深渊/无所不背,君临于无视/无所不面,面面的静观/不是平面,是一立体/不是四方,而是圆,照应万方/圆通的感觉,圆通的能见度/是一轴心,具有万有引力与光的辐射……”内外的界限消失了,诗人构筑了一个圆融的诗意的形象。巴什拉曾指出:“浑圆的形象帮助我们汇聚到自身之中,帮助我们赋予自己最初的构造,帮助我们在内心里,通过内部空间肯定我们的存在。”诗人超越自我不是在现实中,而是在这“圆的空间”中。这是独立于宇宙之中的“美的存在”,融合了古典、象征、立体、超现实的梦境。巴什拉的“圆形空间”,与中国传统诗论中“物我交融”的象征性体验有着相似的结构。存在的事物正是不存在之物的显现,是不复存在之物的提喻和象征。覃子豪所追求的,恰好是一个需要借助诗歌象征才能复活的现实世界。
虽然覃子豪后期的海洋诗不多,但却与《画廊》等作品有着内在一致性。可以说《画廊》是诗人的借助海洋的眼眸所开出的诱惑之果,但它又何尝不是诗人晚年所遭遇的现实与自我危机的变相的宣泄。覃子豪创作的近百首海洋诗中,“水手形象”的塑造贯穿在他创作的不同阶段。对比《水手兄弟》、《我是一个水手》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关联:前者是从内陆到沿海,自叙身世的现实写照,克制而真诚,全诗充满着革命激情与反抗外侮的斗志;后者则是一种想象和情绪的无节制蔓延,将海洋与城市构成强烈而鲜明的对比,而人与海洋的关系通过水手形象建构而得以呈现。诗人从一开始渴望融入集体,到后来的个人出航,海洋所象征的被帝国主义禁闭的国土空间,以及这一空间召唤出的集体性力量,被逐渐由个人幻想的理想化国度所取代。海洋从民族主义的关照中退出,而成为充满异域风情、神秘而奇特的私人冒险乐园。这当中不免有诗人对充斥着阴险、虚伪、狡诈的现代都市文明的厌弃,更包含了一种诗人高蹈的理想主义的激情。而到《画廊》时期,水手形象成为一种普遍的超验的人的形象。正如覃子豪在《水手的哲学》中引用海德格尔的话作为题记:“从何而来,向何而往?”海洋成为一个飘浮而悬置的抽象空间,成为了诗人“神经末梢”上颤动着的存在的追问:
城市在薄雾中露现出美丽的面目/在地窖中隐藏了丑恶与狡黠/而伙伴们卸了重载,抛城市于船尾/去寻童话中七海的消息/水手的生活最雄辩/自己是雄辩的主宰/从不固定,永在奔进中/因为固定便是死亡/就这样没有纠葛的活着/就这样去逃避一个世界,追求一个世界。”
在海洋与城市的对照中,诗人毅然以过客的姿态鄙睨这看似繁华却寒热颠倒、无限疯狂的现代文明。这种现代性主体无处归依的焦虑,不能说没有现实批判的意味。但诗人始终选择甘当一个漂泊的水手,一个“悬置的人”。这当然和他在岛屿的在地经验有关,但逃向一个自我雄辩和自我主宰的人生,真的可能吗?抑或者是否真的存在一个可为“我”所掌控的自在自如的世界?这恐怕真的只能是水手的哲学,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洒脱之情,是诗人渴望超脱现世,但又无处归依的真实处境。在这种注定漂泊和寻求归属的两难处境中,诗人的自我形象进一步发生分裂:“我,进化中的原始/无需疑我,无须猜我,无须剖我/我是非谜之谜/非变调的感官/人岂能因我/而认识自己如此的存在/如此的形象?”(《Sphinx》)人面兽身的斯芬尼克斯,是诗人晚年对自我的认知,也是他对于普遍存在的“人”的认知。漂泊于海的现实经验最终抽象成为现代人的普遍存在方式。进化中的现代人,是如斯芬尼克斯一般自我分裂的半兽人形象,诗人注视着它,似乎也注视着他无法理解,充满悖论的人生,这无疑带有一种强烈的神秘主义倾向,但不能不视为他自我“悬置”后一种真实的人生体验。
四、结语
海洋是覃子豪创作的源泉,亦是他超越自我的现实场域。诗人在早期诗歌创作中,从浪漫主义的海洋抒情诗转向现实主义土地关怀;在渡海之后,重新开始书写海洋,表达思乡、望乡的羁旅之情;进而在后期诗歌创作中,海洋进入诗人抽象的哲思。从海洋诗创作的现实,可以想见诗人在异乡所遭受的现实和精神危机,这使他早年在北平求学时所受法国象征派的影响再度复苏并获得延续,甚至走向更为敏感超拔的艺术境界中。可以说,诗人后期逐步从生活实感上褪去,而致力于诗歌的美学探索,而对于诗歌技艺的沉迷,亦是他与外部现实联结的唯一途径。这种可能为人所诟病的选择,却反映出诗人真实的追求。尽管他并没有正面书写现实并有意制造了进入诗歌的障碍,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敢于批判现实的战斗力,但诗人终究还是意识到他作为一个诗人,背离现实之时亦是忠于现实之实。至少,他仍颤栗于“内在的海”,不断地自我审视,在离散视阈中,海洋方沉淀为诗人的生命底色,展现出他对于自我的完成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