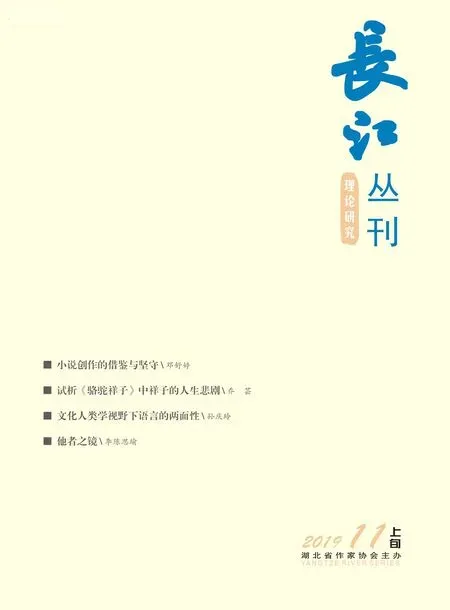资本批判与人性忏悔
——关于张炜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
■王春林
早在十多年前的2005年,作家张炜一篇名为《精神的背景》的文章,曾经在文学界引起高度关注,引起过一场比较广泛的争议。在那篇文章里,张炜所集中思考批判的,便是所谓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精神沙化现象:“由于对商品社会只是一种协调的依附的关系,市场就成为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某种权威,以至于非常害怕这个权威。这不仅是荒唐的,也是可悲的。过去是阶级斗争社会,知识分子最怕阶级斗争,一上纲上线,他们就慌了。因为不慌也不可能,把你赶到农场去就得了。现在的商品经济市场中,知识分子同样是没有丝毫的抵抗力。仅仅以图书市场为例,本来他们对于书籍是最有发言权和判断力的,可是一拿到市场上就没了主意。本来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平庸无聊,可只要是卖得好,有人立即就慌了,先是缄默,然后很快就跟上来,发出各种颂扬之辞。市场比起阶级斗争的威慑力,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商品经济时代就是这种精神状态。消费主义统领下的精神界必然呈现出‘沙化’现象,即精神的沙漠化。所以在这个所谓的经济发展时期,物质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揭露,人类最好的精神结晶,很容易就被纷纷抛弃。好像只有这个时期的中国人才重新发现了‘欲望’。实际上这个欲望不用我们发现,它一直是存在那儿的,只要有人就有欲望。欲望的力量,欲望的规律,它在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从来都是存在的,这很正常。”其实,对于市场经济所可能导致的精神沙漠化现象,张炜那不无偏执的警惕,更早在1995年前后,在市场经济刚刚开始萌芽发展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在当时那场特别引人注目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张炜就曾经和另一位作家张承志在一起被并称为抵抗市场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代表性作家。由此可见,自打所谓的市场经济在1990年代中期呱呱坠地以来,张炜对其所持有的一种批判与反思姿态,可以说一直就没有中断过。虽然说张炜这一方面的思想心得在他的很多小说作品中都已经有着近乎同步式的不同程度的体现,但相比较而言,他的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版),却毫无疑问可以被看作是作家这一方面长期专注思考后的一部集大成之作。
然而,在具体展开对张炜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的分析之前,我们却首先需要对这部长篇小说所集中表现着的当下时代的社会本质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关于当下时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表达过这样的一种看法:“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得资本在中国社会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促使中国社会很快地走向了资本主义化。然而,由于我们特殊的国情,与这种资本主义化相匹配的社会自由化理念却并没有能够变成现实。于是,一种姑且可以被称之为威权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就成为我们无法忽视的社会现实。在这样一种威权资本主义的时代,一方面是社会的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另一方面则是广大平民阶层的日益贫困化。贫富悬殊的尖锐对立之外,已经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应该如何进一步坚持下去?正处于十字路口且又矛盾重重的中国未来的发展演进路向究竟如何?所有这些问题,一方面是包括作家在内的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面对思考的,另一方面则也直接地制约影响着中国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威权的存在,非常明显地钳制着作家言说表达真实的限度。如何在威权圈定的范畴之内,最大真实地书写苦难依然沉重的中国,极大地考验着作家的艺术智慧。资本主义化的现实,很大程度上是所谓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一种结果。”假若承认笔者的上述判断存在着一定的合理之处,那么,我们所置身于其中的一种社会现实,自然也就是所谓的“威权资本主义时代”。尽管说笔者这种关于“威权资本主义时代”的论断,未必就能够完全获得张炜的认可,但在我看来,最起码,只有在充分认识到资本那样一种日益强化着的决定性作用之后,张炜以《艾约堡秘史》如此一部长篇小说的厚重篇幅来彻底清算批判资本罪恶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
既然张炜为自己的长篇小说设定的思想主题是对于所谓“威权资本主义”时代中资本罪恶的清算与批判,那么,小说的主人公也就必得被设定为当下时代的一位新兴资本家。事实上,身为小说主人公的艾约堡主人淳于宝册,也正是这样一位腰缠万贯的大资本家。关于淳于宝册所拥有的巨大财富,我们只需对他的私人府邸艾约堡略有了解便可推想而知。借用后来成为艾约堡主任蛹儿的目光,作家曾经对艾约堡展开过相应的描述:“倚山而建的小楼只是整个堡垒的几分之一,准确点说它的主体只能是这座山包,山旁的建筑也就等于它的前庭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挖在山石下面的私邸就像一个神话,更是一座迷宫,太过隐蔽与私密,即便是花上几天的时间,也无法将这个领地全部熟悉过来。”一方面,能够将一座山包挖空后用来做自己的私邸,的确说明着艾约堡主人淳于宝册所拥有财富的巨大体量,但在另一方面,虽然不知道张炜的如此一种艺术想象是否有真实原型所据,但在我的理解中,作家的这种艺术想象(尤其是还非得把一头名叫花君的花斑牛也牵到这座豪华无比的私人府邸中如同供神一般地养起来),不仅带有十分突出的暴发户性质,而且很显然是建立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之上。又或者,倘若联系张炜《艾约堡秘史》的书写主旨,那么,艾约堡本身的设计,其实充满着不可否认的象征色彩。如果把艾约堡所占据的那座山包理解为大自然的一种象征性存在,那么,以淳于宝册为董事长的狸金集团把如此一座山包硬生生地挖空,将其彻底改造为一座私人府邸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强大的资本力量对于大自然的严重破坏乃至干脆侵吞。从这个角度来说,艾约堡的设定本身,就可以被理解为整部小说的一种象征性预叙。因为,整部《艾约堡秘史》的主体故事情节,正是以淳于宝册为董事长的资本大鳄狸金集团,与大自然的缩影,也即以吴沙原和欧驼兰为代表的海边渔村叽滩角村之间的激烈碰撞与对抗。
作为一部旨在对资本罪恶进行深度批判的长篇小说,张炜在《艾约堡秘史》中把尖锐的批判矛头首先对准了淳于宝册的狸金集团。狸金集团的罪恶,首先表现在意欲侵吞包括叽滩角村在内的海边三个渔村以谋求所谓的入海口。这一点集中体现在淳于宝册与吴沙原的对话中。当吴沙原提出“三个村子一起兼并吗”的问题的时候,淳于宝册给出的回答是:“一起。这是狸金梦寐以求的。一个国家谋求出海口,一个企业也不例外。蓝色大海和白色沙滩,这样的景致很合现代人的胃口。”对于渔村被兼并后的未来情形,作家也曾经做出过相应的展示:“他知道对方一定随吴沙原看过了老肚带展示的规划图,甚至看过沙盘:西式小区、游艇码头、高级会所、现代泳场,当然,还有特意保留的一些海草房。”围绕着这个兼并方案,淳于宝册又进一步给出了两个方面的理由。一是强调这一兼并是所谓城市化进程的一部分内容:“老肚带说这是上级的统一规划,是城市化大格局中的一小部分,硬是摊到狸金头上了,也是我们的一大包袱。想想看,几个穷村子收进来,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兼并三个渔村,明明是狸金集团处心积虑的一种企业发展谋略,到了淳于宝册口中,却不仅被贴上了“城市化”的堂皇标签,而且还被说成是他们集团本来就不想背负的沉重包袱。如此一段失真话语背后所透露出的,正是淳于宝册这一人性构成相当复杂的人物形象生性中虚伪的一面。二是强调资本力量重要性的同时,为资本大唱赞歌:“你是知道资本的力量的,在这个世界上,它重新显出了无坚不摧的本质。四十年前它暂时藏了起来,但那是表面现象:如今它总算恢复了原形,露出了杀气。”虽然张炜并未交代故事的具体发生时间,但依据基本的故事情节来推断,当发生在当下时代无疑。倘若此种推断可以成立,那么,这段叙事话语中的所谓“四十年前”,就应该指的是1976年“文革”终结前后。这一方面,一个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就是,作为工业化时代亦即现代社会产物之一的资本,虽然在20世纪前半叶曾经一度非常活跃,曾经切实地推进过中国社会的演进与发展,但在1949年之后,在进入一个新的社会阶段之后,却很快地就被妖魔化,很快地就成为了一种臭名昭著的事物。此种情形,一直延续到1976年的那个时候,方才被宣告终结。正是从这样的一种历史事实出发,我们才敢断言淳于宝册这段话语中的所谓“四十年前”指的是1976年“文革”终结前后。尽管说资本之重新成为一种决定性的社会力量乃是1992年邓氏南巡讲话之后的事情,但它遭受巨大历史劫难后最初的复苏,却毫无疑问是从“文革”后起始的。正是在此后业已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资本渐次羽翼丰满,渐次“恢复了原形,露出了杀气”,重新显示出了其“无坚不摧的本质”。
其次,狸金集团意欲兼并叽滩角村等三个渔村的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以吴沙原为代表的叽滩角村人的坚决反对。为了达到兼并的目的,狸金集团真正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地使用了各种非法的罪恶手段。而且,依照吴沙原的说法,狸金集团在叽滩角村的所作所为已经算是很客气,算是给他留面子了。在其他村子里,狸金集团的手段会更加极端与残忍:“哪个村子里如果出了碍事的人,不出半年就会被解决掉,结局各种各样,都是很平常的。有一个村子出了十几个强人,他们一直跟狸金对抗,最后有的家破人亡。有一个村头儿受尽折磨还是挺过来,结果上边很快收到一封控告信,如今声名狼藉,村子也完了。”正所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狸金集团如此一种强劲异常的资本力量面前,一切都得乖乖让路。一旦试图反抗,那反抗者的结局便会特别凄惨。即使是狸金集团内部的工作人员,只要触犯了集团内部的某种禁忌,也会死得很惨。这一方面,那个被命名为“眼睛兔”的年轻人的不幸遭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眼睛兔”本来是淳于宝册传记的修改与整理者,只是因为喜欢上了集团被培训用来从事公关工作的一位小姑娘,结果却死于非命:“我按您的指示严肃警告过他。谁知道这家伙暗中一点都没停。结果就十几天的功夫,他搞上了一个女孩,小姑娘要死要活的。进了保安处哪有好事,那帮人的脾性……前天夜里人就过去了。”一个企业集团的保安处,就可以如此这般为所欲为地私设刑堂草菅人命,其无法无天飞扬跋扈的程度自然可想而知。
第三,狸金集团的罪恶,也表现在对自然生态环境所造成的严重破坏上。对此,吴沙原同样有着一针见血的揭露:“据我所知狸金周围的村庄没有不怕你们的,你们先后兼并了五六个村庄,这些村的人逃掉了好多,一些家庭也受到牵累。靠近化工厂的三个村子几年内患病率上升,其中癌症患者是过去的好几倍!有不少失踪的人,其中最多的是女性!全市最大的水源地被污染了,两条河里没有鱼,连草都枯了,治理三年没见一点成效。”
一方面不择手段地肆意吞并如同叽滩角这样的村庄,另一方面在随意草菅人命的同时却也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凡此种种,皆属于以淳于宝册为董事长的狸金集团这一资本大鳄在自身日益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现实罪恶。但请注意,由于置身于中国如此一种威权体制中的缘故,包括狸金集团在内的所有资本的积累与发展过程中,实际上都少不了与现实权力的结盟与联姻。质言之,只有在后者的强势支撑下,资本才会有如虎添翼的迅猛发展。这一点,在狸金集团的初始起步亦即所谓的原始积累阶段表现得特别明显。具体来说,淳于宝册人生事业的起步,始于村头儿的委托他兴办工业:“也就在这一年春天,三道岗村头儿陪一位公社领导找宝册来了。老人不顾一路疲劳,进门就对他说:‘小晌,咱老家要兴办工业了,这事全靠你!’”虽然叙述者并未作出明确的交代,但只要联系上下文的语境,我们即不难做出判断,淳于宝册人生事业的起步阶段,与资本这一曾经隐藏很多年的事物的初始复苏,基本上持同步的状态。又或者,联系“文革”后中国社会的实际演进过程,淳于宝册的兴办工业,其实也就相当于1980年代初期所谓乡镇企业的应运而生。最早,淳于宝册创办了一个小小的农机厂:“整整多半年的时间,宝册来往于工厂与三道岗之间。由于有李伯伯的支持,一座小小的农机厂在村里建立。”就这样,从农机厂,到化肥厂,再到食品厂、木器厂、建筑公司,淳于宝册的系列产业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
无论如何都不容忽视的一点是,在淳于宝册系列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老政委角色。虽然这位名叫杏梅的强悍女性口口声声离不开“战争”,但她的所谓“战争”不过是“文革”期间的武斗而已。在那个动荡不已的岁月里,杏梅所在的“磨盘山游击队”一个抢眼的功绩,就是从政治对手那里硬生生地抢出了一个身负重伤的高位领导。正是因为有过这种渊源,所以,这位名叫杏梅的老政委就与政治上层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与淳于宝册结识并决定加盟他的事业之后,老政委充分利用她和首长之间不无暧昧色彩的紧密关系,助力淳于宝册的狸金集团最终发展成为了一个经营范围辐射到很多方面的资本巨无霸。对于老政委所发挥的特别作用,淳于宝册曾经以形象的话语加以描述:“她认为我从事的既不是工业也不是商业,而是一场战争,身边要有一个‘政委’。我离开她心里空荡荡的,后来就开始想念,有时是半夜,一刻都不能等待,天不亮就急着上路,开了公司的快车。”同样借助于淳于宝册的自述,文本曾经对老政委和首长之间的特殊关系进行过准确到位的揭示:“新婚未满月她就领我去那个大城市见了首长,那个生了老年斑的大圆脸把我看过来看过去,从头问起,细细审查。我觉得这个人的眼神不对,私下里拷问老政委:你们到底有没有那种关系?她如实说‘没有’。耽搁了一会儿又说:‘如果你不介意,那我可以告诉你,首长摸过我。’我无比憎恶首长的一双手,它也生满了黑斑。回到老榆沟我们认真规划,制定方案:先是将三道岗的全部在此复制,然后就是设法扩大其规模十至二十倍。她表现出一股狠劲儿,说:‘先把那里掏空,它本来就该是你的!’我说这万万不能,三道岗是我的恩情地。她说最后留下一个空壳儿也算对得起他们。我当然没有照她的话去做,但终究还是对不起三道岗。如今那里的企业还在,不过早被我们狸金连骨头带肉吃掉了大半。首长给予了全程支持,他在咽气之前都是集团倚重的人。”这段话语的要旨,显然有二。其一,意在凸显老政委与首长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她们那不是暧昧但却胜似暧昧的关系,为首长全力支持狸金集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二,相比较来说,更重要的一点却是,老政委的存在,为淳于宝册和首长搭建了很好的桥梁。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老政委这样一个纽结点,所以也才有了淳于宝册和首长,也即资本与权力之间结盟关系的建构。毫无疑问,如同淳于宝册这样一位曾经被打入政治另册,曾经饱尝历史劫难的年轻人,之所以能够在遭遇了一个相对开放的时代之后,迅速崛起为在业界虎视眈眈能够称霸一方的资本大鳄,与老政委的存在,与以首长为象征符码的现实权力的鼎力相助,存在着不容剥离的内在关联。很大程度上,以淳于宝册为董事长的狸金集团与首长之间的紧密关系,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威权资本主义”这一社会性质论断的形象注脚。威权者,老首长也,资本者,淳于宝册或者说狸金集团也。正因为有了来自于政治权力的强力支撑,所以如同狸金集团这样的资本大鳄方才能够“横扫千军如卷席”似地在叽滩角村横行霸道肆意妄为。
以淳于宝册为董事长的狸金集团以上林林总总的所有罪恶,归结在一起,似乎正应了马克思曾经讲过的那句名言,意即资本是一种来到人间之后,“从头到脚的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很大程度上,也正因为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部《艾约堡秘史》中,与狸金集团这样的资本大鳄坚决对抗到底的,就是以村头儿吴沙原和民俗学家欧驼兰为主要代表的那个名叫叽滩角的渔村。首先,是那位带有突出民间社会身份的渔村守护者村头儿吴沙原。当淳于宝册信誓旦旦地强调吴沙原保护渔村叽滩角的目标已经达到,强调叽滩角村作为独立法人可以依据所谓的公司法进行自我保护的时候,吴沙原给出的却只是冷笑:“‘法’是很多的,就看谁来用。既然有这么多‘法’,两边的村子还是没能保住,他们交出了祖祖辈辈过活的地方,马上要拍拍屁股走人。用不了几代,谁还记得有这两个村子!你们各种办法都用上了,他们手无寸铁。你们夺走了土地,等于夺走了全部,现在,今后,一块儿给夺走了!”在中国这块特别的土地上,资本的力量其实是远远大于所谓“法”的。吴沙原所一语道破的,正是如此一种颇为令人震惊的社会现实。实际上,正因为吴沙原业已抱定了誓与叽滩角村共存亡的坚定决心,所以,淳于宝册才明确意识到狸金集团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对手。更进一步说,村头儿吴沙原之所以抱定了与狸金集团对抗到底的决心,乃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了类似于狸金集团这样的资本大鳄的真正原罪之所在:“流血,是的。二十年来死伤多少人,总能统计出来。过去有个词儿叫‘巧夺豪取’,今天已经过时了,因为太麻烦,不如‘豪取豪夺’。可以说狸金的巨大财富中,站绝大比例的都是不义之财!你们毁掉了水、空气和农田,还把财富转移到国外!可是真正的大罪并不是这些,不是……”那么,是什么呢?“是因为有了狸金,整整一个地区都不再相信正义和正直,也不信公理和劳动,甚至认为善有善报是满嘴胡扯……”一个资本大鳄的存在,在严重侵害大自然生态秩序的同时,竟然能够从根本上动摇诸如正义和正直、公理和劳动这样的价值理念,其原罪之严重程度,自然也就可想而知。因此,具有突出民间社会身份的吴沙原之所以要下定决心与狸金集团死磕到底,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护诸如正义与正直、公理与劳动这样的价值理念。
假如说吴沙原更多地携带有民间社会的特点,那么,民俗学家欧驼兰就很显然可以被看作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位代表。身为民俗学家,欧驼兰之所以要千里迢迢地离开繁华的京城远赴叽滩角村这样偏僻的海边渔村,正是为了完成她所承担的民俗调查使命。事实上,也正是在叽滩角村围绕民俗问题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在对诸如“二姑娘”这样的渔歌号子以及开海节这样的民间节日逐渐深入了解的过程中,欧驼兰不仅深深地爱上了叽滩角村这样虽然偏远落后但却充满自然与文化原生态意味的渔村,而且更是从文化与生态保护的思想价值立场出发,在叽滩角村与狸金集团的这场尖锐冲突中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叽滩角村一边。唯其如此,面对着淳于宝册,她才能够讲出这样一番义正词严的话语:“我一直想问您一句,又觉得这是狸金和村子的事情。我想说的是,海边这些历史悠久的海草屋全都推倒,那该是多大的遗憾!”既然欧驼兰早已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对峙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所以,当淳于宝册意欲重金聘请她为狸金集团的文化总监的时候,欧驼兰的态度便只能是毫无商量余地的断然拒绝。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与此同时,欧驼兰也对淳于宝册给出了可谓语重心长的告诫:“不过我想让您也记住,无论是我还是您,任何一个人,比起叽滩角这样一座历史悠久的渔村,都是十分渺小和短暂的。我们很小,很短暂,海和沙岸很大,它们对我们意味着永恒……”
只要联系“文革”后资本力量复苏以来的社会演进发展状况,我们就不难发现,吴沙原与欧驼兰联手与淳于宝册之间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所真切折射表现出的,正是中国传统民间社会与现代知识分子联手对抗新兴资本大鳄的一个形象化过程。或者更真切地说,如此一种艺术构思与情节设计,所充分反映出的,其实是作家张炜对于“文革‘后尤其是所谓市场经济时代以来中国社会本质的一种理解与认识。一方面,张炜认定,充满原罪色彩的新兴资本力量与自然和文化原生态之间的矛盾冲突,乃是当下时代中国社会诸多矛盾冲突中无论如何都不容轻易忽视的一种。另一方面,面对着如此一种长期令张炜忧心忡忡的资本原罪力量,作家很显然把与之有效对抗的力量寄希望到了民间社会和知识分子这样两种社会力量身上。尽管说张炜的这种观察与理解是否合乎中国社会实际仍然有待得到多方面尤其是社会学方面相关研究的充分证实,但最起码,张炜从自我社会生存经验出发所做出的这一判断,以及如同《艾约堡秘史》这样一部带有鲜明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其意义和价值不管怎么说都应该得到我们的理解与尊重。
然而,从自我的社会生存经验出发对资本进行不无严厉的尖锐批判,却仅仅只是张炜这部《艾约堡秘史》一个方面的思想艺术成就。无论如何,在强调小说社会价值重要性的同时,我们都不应该忽略小说更应该是一种深度挖掘勘探复杂人性世界构成的文体形式。作为深谙此道的资深作家,张炜对此自然心知肚明。关键的问题是,尽管说张炜对此早已心知肚明,但或许是因为面对着威权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大鳄来势迅猛内心过于激愤的缘故,我们注意到,在张炜包括《柏慧》《外省书》《能不忆蜀葵》《刺猬歌》等甚至包括茅奖获奖作品《你在高原》在内的一系列带有突出市场经济批判主旨的长篇小说中,作家似乎已经不再能够耐得下心来做细致深入的人性体察,更不用说再次企及他早在30岁的时候就已经在长篇小说《古船》中曾经有着很好表现的人道主义忏悔的思想高度。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迄今为止,张炜最具经典化意味的长篇小说,乃是他年仅30岁时创作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古船》。作为一部非常优秀的长篇小说,虽然说致使《古船》在当时普遍受到好评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恐怕却是思想层面上对于一种罪感意识的成功传达。具体来说,小说中罪感意识的成功传达,又与主人公隋抱朴形象的深度塑造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古船》中的隋抱朴是一个具有原罪感的人物,这个人物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古船》由于塑造了这样一个主人公,这样一个充满了原罪感的灵魂,使得作品弥漫着很浓的悲剧气氛和忏悔情调,这种罪感文学作品的出现,在西方不算奇特,但在我国,则不能不说是一种罕见的文学现象。”很显然,刘再复他们之所以要对《古船》做出高度评价,根本原因就在于罪感意识的充分传达。因为所谓罪感意识的传达,实际上意味着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抵达的灵魂维度与人性深度:“但伟大的忏悔文学,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认不认罪的问题,即不像教堂中向神和神的中介确认自己过失的问题,而是人的隐蔽的心理过程的充分展开与描写。正因为看重揭示心理的过程,读者才看到实实在在的灵魂的对话和人性世界的双音。”然而,尽管忏悔文学特别重要,但令人遗憾的却是,在中国文学中,忏悔文学是相当匮乏的:“也许正是中国文化缺乏叩问灵魂的资源,因此,和拥有宗教背景的西方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相比,中国数千年的文学便显示出一个根本的空缺:缺少灵魂论辩的维度,或者说,灵魂的维度相当薄弱。”既然如此,那么,《古船》中罪感意识的重要性自然就不言而喻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了对于罪感意识的成功传达,所以,《古船》才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多的真正具备了世界性因素的长篇小说,并获得了学界普遍一致的高度评价。
正如我们前边已经指出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尽管说罪感意识或者说由这种罪感意识而进一步导致的忏悔精神早在《古船》中即有着相当难能可贵的表现,但遗憾之处在于,在张炜其后的一系列长篇小说中,如此一种异常重要的精神线索竟然不知所以然地给断线了。所幸的是,到了他晚近的这部《艾约堡秘史》中,这种中断已然很久的人性忏悔的线索,却又令人倍感惊喜地开始重新浮出水面。具而言之,这种人性忏悔的精神内涵乃集中不过地体现在主人公淳于宝册身上。出现在文本中的淳于宝册,固然是一位资本大鳄,其唯利是图的本性无疑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但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一点却是,淳于宝册在疯狂攫取财富的同时,其人性世界的构成其实有着相当复杂的一面。
比如,从情感世界来说,淳于宝册是一位曾经饱受伤害的情种。这一方面,先后与淳于宝册发生关系的女性最起码不少于三位。首先,当然是那位带有突出毛遂自荐意味的一贯在淳于宝册面前强势无比的老政委。与年长自己五六岁的老政委相遇相识,正是淳于宝册的资本事业初始起步的时候。这位老政委也即杏梅不仅从外表上看是一位男性化倾向非常明显的粗壮女性,而且从其一贯的行事风格来说,她往往是生活的主动者。即如与淳于宝册情感的关系,她也是强势的,进与退的主动权始终把握在她的手中。更何况,依照前边的交代,在与淳于宝册结合前,老政委不仅曾经救过一位身居高位的首长,而且他们之间也还存在着某种难以言传的情感暧昧关系。一方面,淳于宝册资本事业的发展的确少不了来自于首长的强势助力,离不开老政委的存在,但在另一方面,在接受如此一位精神早已出轨的老政委为妻的过程中,淳于宝册情感上所受到的伤害,乃是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弥补情感世界曾经遭受过的严重伤害,所以也才有了蛹儿这样一位情感补位者粉墨登场的机会。虽然此前也曾经经历过两位男性,虽然蛹儿也不是什么处女之身,但很显然,与老政委的过于强势,与她的一贯飞扬跋扈相比较,后来才成为艾约堡办公室主任的蛹儿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温柔,就是逆来顺受。这一点,其实早在她与前两位男性的关系中就已经表现得非常鲜明。无论是那两段情感的开始,抑或还是结束,其始作俑者都是男性,而非可谓是“天生尤物”的蛹儿自己。又或者,作家之所以要拿出不小的篇幅来专门叙述蛹儿进入淳于宝册生活前的情感前史,根本意图就是要写出她这一方面的性格特征来。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淳于宝册之所以会日渐失去对蛹儿的兴趣,主要原因或许就在于她生活主体性的极度匮乏。唯其因为表面上接受过大学教育的蛹儿现代精神的严重匮乏,也才有了第三位女性,即民俗学家欧驼兰的令淳于宝册魂牵梦绕。毫无疑问,欧驼兰是一位有着自身强大精神主体性的现代知识分子。不论是她不惜千里迢迢地远离京城长期驻扎在叽滩角村进行民俗的深度田野调查行为,还是她那种捍卫自然与文化原生态的坚定意志,抑或最后面对狸金集团高薪聘请时的严词拒绝,所有的这一切,彰显出的正是她身为现代知识分子那样一种足称强大的主体人格。欧驼兰在淳于宝册的心目中之所以仅仅一面就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正因为在精神与情感上被欧驼兰彻底征服,所以淳于宝册方才不仅让雕刻匠将想象中的“二姑娘”形象雕塑成了欧驼兰的模样,而且还使出浑身解数意欲将欧驼兰收归到自己也即狸金集团的麾下。
再比如,从阅读和写作的角度来说,淳于宝册简直堪比一位作家。他之所以能够在书店中发现蛹儿这样一位“天生尤物”,与他长期形成的良好阅读习惯,自然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与阅读紧密相关的,自然就是淳于宝册的写作行为。关于淳于宝册的写作,文本中曾经不无嘲讽地做出过这样的介绍:“主人兴之所至大讲一通,旁边的速记员唰唰记下,然后交给秘书处,那里的头儿老楦子就有事情做了。他们一伙分门别类捋成‘理论’‘纪事’‘随想’,扩充成一大堆文字。”虽然有手下人捉刀代笔的嫌疑,但究其根本,一位如同淳于宝册这样的资本大鳄,能够把很大的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如此一种书写工作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见,他绝不同于寻常那些脑满肠肥的资本家。其一定程度上精神气场的存在,乃是无可置疑的一种客观事实。
但不管怎么说,最能够见出淳于宝册这一人物形象人性深度的,却仍然还是他那样一种其实很难称得上彻底的内在忏悔精神。淳于宝册的忏悔意识,突出不过地表现在他对狸金集团的排斥与厌恶中。淳于宝册的确是一个内心世界充满着自我分裂感的人物形象。一方面,是他殚精竭虑地顺应时代大潮,开创了狸金集团,成为这个时代的成功人士,成为资本时代的资本大鳄。但在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具有内在激情的诗人气质非常明显的嗜读者,他对金钱与财富,以及类似于自己这样一种疯狂攫取金钱与财富的方式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与厌恶,也自是合乎逻辑的选择。大约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遭受到吴沙原与欧驼兰的联手阻击,尤其是自己所钟爱的女性欧驼兰义正词严的批驳之后,淳于宝册才会有幡然悔悟的表现:“睡不着就看书,在笔记本上划着。‘这次海岛之行我不得不做出一个承诺,而后就是践诺,不然就成了“无赖”。’他写下这几句咬住了笔头,又加一句:‘不过我的承诺是向海神做出的。’他盯着这几个字,想到了半山上那座美轮美奂的建筑。”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此处的海神,在淳于宝册的内心深处,很大程度上意指他的精神偶像欧驼兰。唯其因为面对欧驼兰有所承诺,所以他才特别慎重地考虑如何才能践诺的问题。事实上,也正是在欧驼兰精神的感召下,在这样一种思考过程中,淳于宝册对于资本罪恶的认识方才有所清醒。质言之,淳于宝册的罪感意识生成基础上的自我忏悔,也只有在如此一种前提下才成为可能。
然而,欧驼兰的出现,只是淳于宝册自我忏悔的一种现实诱因而已。从根本上说,身为一位腰缠万贯的资本大鳄,淳于宝册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彻底的一种自我忏悔,最重要的一种思想基础,恐怕还是他早年在“文革”期间所遭受的不公正命运,以及在这不公平命运的过程中那些曾经对他施以援手的亲人们的可贵亲情:“他打发她走了,独自在湖边坐了很久。悲伤难忍,泪水全淌在心底,再过一会儿就要溢满呕吐。他知道这不仅是因为‘眼镜兔’的事。他突然想到了老榆沟那个黑夜,那座腥臭的老碾屋。他还看到了野椿树下老奶奶的白发。他闭闭眼,抬头望向西边的半山,在心里呻吟:‘老师,那是我为李伯伯准备的晚年居所,可他厌恶这里,走开了……’这样说着,泪水哗哗流下来。”曾经的小学校长李音,曾经对早年的淳于宝册有大恩。唯其如此,淳于宝册才不仅不远千里一定要去青岛面见李音校长的父亲李伯伯,以完成老师的遗愿,而且还在自己资本事业发达之后,专门在三道岗为李伯伯修建了一个居所。没想到,他的一番苦心却并没有得到李伯伯的认可。李伯伯毅然决然地拒绝了他的馈赠。对此,淳于宝册不仅倍感哀伤而且一直耿耿于怀。这种心理所最终通向的,正是男主人公一种难能可贵的自我忏悔。设若少了关于淳于宝册早年生活中李音、李伯伯以及老奶奶等相关人物的设定,那么,他成为资本大鳄后那种惴惴不安的忏悔心理的生成,自然也就会失却相应的艺术说服力。虽然说张炜在这部《艾约堡秘史》中关于淳于宝册自我忏悔的相关描写,其艺术的成功度较之于原来《古船》中的隋抱朴的确力有所不逮,但在当下这样一个资本依然在横行肆虐的时代,能够在小说中塑造出淳于宝册这样具有相当人性深度的资本家兼忏悔者的形象,其意义和价值无论如何都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