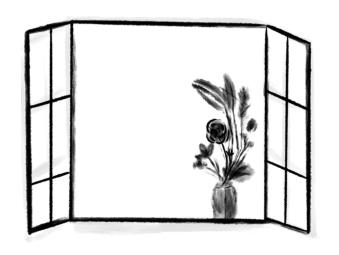一层塑料
二〇〇八年的冬天不是很冷,至少气温还未曾抵达零下二十几度的寒威。可是今年冬天屋子出奇地冷。本来十四五度的室温很是相宜,可是今冬的暖气似乎颓靡苍老,凉凉的铁片镀着生硬的棱角,冷冰得让人无语。塑钢窗的密封条也开始皱缩老化,北风穿过狭窄的缝隙,丝丝地渗进屋里,仿佛瞬间便填满整个空间。凉冰冰的寒意主宰了房间的温度,成为不可抗逆的主流。别人家的温度我没有探询,左右一个小区里住着,想来大抵如此。
喜欢午时前后的阳光,从东向西,缓缓映进室内,照耀着一地金光,一点一点,从这厢挪到那厢,从窗栏移到短墙,从短墙移向室外,然后,暖暖地,暖暖地 ,收拢一地碎金,慢慢退去,渐渐恢复一室清冷,仿佛从未曾来过,可你偏偏怀念它的暖,那么地短,那么地让人留恋。
午后的阳光依然明媚,却不再照进室内。阳光虽好,却也过时不候,稍纵即逝。
住在楼里,给窗户糊上一层塑料,其实是一种很憋屈的感觉。不比小时候,冬天到了,家家户户都会在窗外挡上塑料抵御寒风,十月过后,谁家若是早早挡上塑料,左邻右舍便望风而动,争先恐后的架势,好像晚一步便会被寒冷的冬吞噬。谁家若是十月里还不曾给窗户挡上塑料,大抵是要承受许多讶异的诘问与眼色的,虽然那是人家的事情,也会作为一项谈资传得远近皆知。比如,“前套房老孟家老早就糊上了,这家……”比如,“哎呀,那谁谁谁家,现在还没糊,都啥前儿了……”
那时,姜老太糊塑料的功夫绝对一流,一个人便可以包揽全局,量尺,剪裁,压条,钉钉,板板正正,中规中矩,前后左右难有望其项背者。不过隔壁吕家似乎也做得很好,姜老太常说那是一家会过日子的人。
那时时光很闲,人人都喜串门子,听老太说,小时的我闻香识门,到了饭点儿,常常脚一歪便没了踪影,跑别人家里去蹭苞米面大饼子去了。那时的邻居都很亲切熟稔,待我也是蛮好,虽然满口说着粗话,心肠却是地地道道的良善,就像杨家婶子,吃了她家的东西,如果我不回去坦白交代,她也不会过后向父母讨要人情,在她眼里,那不过是一个孩子单纯的喜好而已,无关其他。
那时空气很凉,屋子却是热乎乎的,尤其是火炕和炉灶,点起灶火烧一壶热水烤两个土豆、地瓜,窝在暖烘烘的炕头啃咬,真是一件惬意的事。穿着厚厚的棉服从冷飕飕的寒风里扎进屋内,把冻僵的手紧紧贴在炕上,室内虽不是温暖如春,从手心传递的热度却直达心坎,一股温软的暖意涌向四肢。那一刻,再冷的冬天也是温暖可爱的,哪怕是零下三十几度的酷寒,也挡不住内心蓬勃的热流。
那时的伙伴儿都很野性,打起雪仗男生疯狂女生野蛮,巾帼不让须眉,出门整整齐齐,很是淑女君子,带着一身冰碴儿回家,丢盔弃甲,十分地狼狈。有人为此受罚,有人因此挨打,大人行使大人的权威,小孩儿却坚守小孩儿的固执,冰天雪地里的团结,既锻炼了屁股的结实,也考验了孩子的诚信。那个时候,尽管队伍陆续减少,却没有一个人叛变组织,虽然胳膊拧不过大腿,却阻止不了孩子们心心相护的默契。
如今,我家的窗户也挡上了一层塑料,虽是透明的一层,终究有着淡烟薄雾的模糊,仿佛有什么阻碍了视线,让人不得畅望,心生怨念。姜老太说,那个卖塑料的生意可真火,塑料都涨价了,原本两块五一米,今儿个都卖到三块了。随行就市,水涨船高,原也无可厚非,可这塑料用来挡窗户,还是暖气楼里的窗户,怎么都觉着有点儿啼笑皆非。
姜老太对挡窗户这事儿还是比较热衷的。当九点的阳光越过楼层斜斜地歪进窗角,一抹橘红的光晕晃进视野,透过塑料,浅浅的,薄薄的,却那么有力和盎然,窗前仿佛岚霭闪烁,又似流光灼灼。冷硬的寒风吹鼓塑料的袍袖,却无法穿破它弹性的壁垒,仿佛被困在透明的结界,即便有通天彻地的嚣张也无丝毫用武之地,让人心情顿感愉悦。爬上窗栏的暖阳越发明媚灿烂,姜老太佝偻的背影披着明亮的阳光,从窗台这头挪到那头,再从窗台那边移到这边,像一幅流动的冬日暖阳图,暖暖地,静静地,那么地柔美,那么地温馨,那么地温情脉脉。
原来,没有什么可以遮挡眼睛的视野,就像这冬日窗外的风景和四射的芒光,只要换个角度就会呈现特别的美感,只要有心,再不济的事物也能感受到它的一丝熨帖与喜爱,何况生活处处充满始料未及的小确幸和有待发现的诸多美好。
这样的冬天,蛮好。
作者简介:孟柏宏,系吉林市作家协会会员,东方文学社社員,有诗歌、散文见诸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