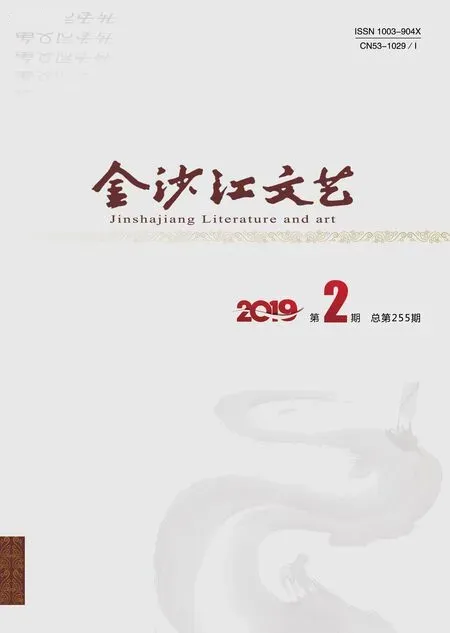植物六种
刘亚荣 (河北)
芝 麻
“耩!耩!耩芝麻儿!耩到头儿开白花。”耩芝麻是精细活,是慢活。芝麻种子籽粒极小,耩快了,苗会长得不匀时。所以啊,耩芝麻要老把式。
我写芝麻不是为了说耩芝麻,是无意中发现了芝麻的 “奇迹”。我从书上看到芝麻叶下汤面香死个人,就生了心,想尝尝芝麻叶的味道。那天回了老家,本来是采了点马齿苋炒了吃,孩子们都说,嗯嗯,不难吃。我受到鼓励,拿着塑料袋又去采马齿苋。老远发现一片嫩嫩的绿,很养眼。像芭蕉叶子的颜色,绿得喜人,走近了一看, “啊!芝麻!”葱绿的叶子,直杆上顶着一串粉白的花,还结了毛茸茸绿油油的角。
四处看看无人,两手飞舞,掐了一袋子芝麻叶。做贼一样跑回家,泡在洗菜盆里,看一盆水映出莹莹的绿。然后,极度夸张地给孩子们讲述我的偶遇。
然后,孩子们又听到我夸张地说;“快来看!泡芝麻叶的水,居然稠得像果冻!”为什么这样呢?
我只知道芝麻籽香,炒芝麻是坐月子女人们的健身法宝,它既有滋补作用,又有润肠功效。要知道,生活条件不好时,生孩子是件能要命的事情。鸡蛋芝麻小米粥是河北女人坐月子的最高待遇。
我素炒了芝麻叶,没有书上写的香,反而有股清苦味,但也不难吃。孩子们大呼难吃,以示抗议。连我炒的薄荷鸡蛋都受到了质疑,有的说 “像吃口香糖”,有的说 “像牙膏”。看来年轻人的饮食习惯和老一辈人不一样了。
我夏天极喜欢吃凉面,也是贪芝麻酱的香。还有涮羊肉,小料还是芝麻酱最对路。
我记忆里芝麻就是芝麻,和胡麻是两回事。可是书上说芝麻也是胡麻的一种,由张骞从西域带来。近年考古遗迹证明芝麻早在数千年前就出现在我国人的食谱中。这待遇,是考古学家的事情。
我要说的是,小时候家家都种几捆芝麻,换油,留着过年包饺子吃。那时候,一家人一斤香油能吃一年。有笑话说,一家人的香油吃了一年反倒多了。其实多啥呢,是面汤带到了香油瓶子里。我结婚时,大嫂子盛饭,我端碗,大嫂特意用筷子在我的碗里点了几滴香油。
打完芝麻的芝麻杆,我们老家叫芝麻秸,平时是舍不得烧的,留着年初一煮饺子。三十晚上,院子里撒上芝麻秸,踩上去,啪啪的响。老一辈人说,三十晚上,开始敬神,姜子牙封神时,没给他老婆留神位,所以这个神就四处串游,偷吃供品。她脚片子奇大,踩在芝麻秸上,啪啪响,就会被人们发现,放鞭炮轰走。芝麻长得很美,绿叶粉花娇娇弱弱的,却还能保家护院。
人们都说,芝麻开花节节高,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小时候,哪个村子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唱着 “耩!耩!耩芝麻儿!耩到头儿开白花……”的歌谣,在黄土地上用两个手指头耩芝麻儿呢。
荞 麦
我印象中,凉粉和荞麦本不相干。
卷着花边的白盘子里,盛着一些玉质的、牛子牌大小的东西,还有绿黄瓜丝和绿豆芽。零零散散的有几片咖色叶片,我知道这是阜平、行唐一带的炝香椿叶。我起初没认出牛子牌样的东西是什么。当地朋友说是凉粉。
凉粉?和我老家的山药凉粉不一样,和绿豆凉粉也不同。山药凉粉颜色发灰,绿豆凉粉发绿色。这是荞麦凉粉。这可真是稀罕东西,夹一块儿尝尝,少了脆劲,却多了粗粮的质感。吃过灰乎乎的荞麦扒糕,这凉粉长得可真好看,真像如今市面上流行的青海产白玉。荞麦凉粉中看也中吃。
荞麦是短命鬼。家乡人这么说,其实话语中透着爱意。潴龙河发水,冲了庄稼,只要能赶在立秋前一天,插上耩子耩上几耧荞麦,不几天,满地就长满了荞麦精灵。一个半月后,荞麦出落成大姑娘,一袭红衣裳,配着白花花的纱巾。风一吹,花枝乱颤,那一个美。这样的美是酸秀才眼里的美,庄稼人知道荞麦在大灾之年能救人命,能填饱肚子,能延续血脉烟火,这是庄稼人最朴素最本分的生存之道。
我在许由的箕山下颍水河畔尝到了荞麦凉粉,我不知道凉粉起于何时,这和许由有没有关系。我知道山药凉粉不会早于明代,那时候山药才传入我国。是谁第一个做的凉粉呢?这大概有多个答案,或者没有答案。我如果调凉粉,看相会更好些,滴上半勺岐山辣椒油,这色泽会平添几分画意。大热天吃上一碗,相当惬意。
很久不做饭了,看到街上新鲜的蔬菜眼馋,可是一个人能吃多少呢?常常扔东西。真想生在唐朝,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起码以胖为美。吃荞麦好,不增肥。
荞麦是好东西。虽然产量不高,但灾荒年能解饥荒。在诗人眼里是优美的田园 “雪铺荞麦花漫野,黛抹蔓菁菜满畦”,也是一幅画。家乡人猜谜 “三块瓦砌个庙,里面盛个白老道”。荞麦种子好看,三棱,荞麦皮是装枕头的上佳材料。在博物馆常常看到瓷枕,我感到很奇怪,这样硬实冰凉的枕头古人是怎么枕的,是裹上布,还是直接枕在上面?在瓷枕上睡觉,这可是个功夫。我的家乡蠡县出土过一个三彩的孩子样瓷枕,这形制比较罕见。
李时珍说 “荞麦南北皆有。立秋前后下种,八九月收刈,性最畏霜。苗高一二尺,赤茎绿叶,如乌树叶。开小白花,繁密粲粲然。结实累累如羊蹄,实有三棱,老则乌黑色。”说得详实,描绘得形象。我如果有块儿地,一畦种荞麦,一畦种蔓菁,朴素又诗意。
荞麦是贫瘠之地产物,一说荞麦,还有苦荞,大概登不得大雅之堂。听说有荞麦煎饼,我没见过。在电视上看到过碗托,山西地方小吃,听说在晋北碗托原料就是荞麦,平遥这边是白面做成,也叫 “碗秃子” “灌肠”。冷热皆宜。倒是喜欢荞麦饸饹,石家庄附近的行唐和无极的饸饹有名,听说无极饸饹制作方法是明末饥荒时由关中人逃难带来,经过改良形成自己的特色,如今行唐无极红事上还有吃饸饹的风俗。饸饹有很多种吃法,油泼、牛肉打卤、西红柿鸡蛋卤,羊肉蘑菇卤。我喜欢油泼饸饹,配点菠菜、油麦菜,绿豆芽什么的,热热的花椒油,泼在葱姜蒜末上,那个香,顶风可以香十米。至于羊肉蘑菇卤饸饹则更接近坝上的莜面栲栳栳吃法了。莜面和荞麦都属粗粮,现在却比麦子金贵。
荷花与藕
食堂里五彩缤纷的凉菜里边,加了用辣椒油泼的糖醋藕片,白生生的藕,酸辣辣的汁儿,脆生生,酸甜可口,简直好吃得没法说。
我自己偶尔也做糖醋藕片,莲藕去皮,洗净,切薄皮,过水,然后用糖醋汁拌,我为了好吃且养胃,常常会切一些姜末放进去,也算美味,清口,回味又有姜的味道。可与辣椒油泼的糖醋藕片相比,简直是小巫大巫的差别。
小时候虽然临河而居,但河里并不产莲藕,沿着潴龙河下行数十里地是远近闻名的白洋淀,村里人以前只说下水淀哩。爹小时候,河还是航道,顺风有张起的白帆呢。只在河岸不远处,生着两大片芦苇,青青的芦苇里有刘家祖先的坟,绵延了几百年了,从山西迁来,埋骨于此,在孟尝村生根,让我们这些刘氏后代和孟尝君有了地域上的联系。
只记得画的藕,当然不是齐白石画上那种。是藕粉盒上的藕,产自运河边的胜芳镇。人的饮食习惯来自于生活环境,来到市里后,在饭店吃过桂花糯米藕片、炸藕合,才知道,藕居然这样好吃,不仅有天然的清、脆、甜,还能香香的,让人回味。当然,我吃到的桂花糯米藕片,给人的感觉是甜甜的、糯糯的、脆脆的,带有桂花的香气。
我学会了做排骨炖藕块儿,藕切滚刀块儿,砂锅里宽宽的水,放排骨、花椒大料葱香蒜,大火十几分钟后,加入藕块儿。天慢慢黑下来,待得排骨香气四溢。关火。一锅清香可口的排骨藕块汤好啦,排骨粉嫩,藕块白生生,不失清脆,汤清郎朗,喝的人神清气爽。
听说,藕有八孔九孔之说。我生在北地,只见过公园里的荷花。藕是荷花的根。也听说,荷花的根分为莲藕和花藕,花藕是不能吃的,只是荷花的一种繁衍方式。从王祥夫先生文章里知道有种酱菜叫酱银苗,老北京人管藕的嫩芽叫做 “银苗”。
我在医院工作时,刘师傅在两个废弃的矮墩墩的大肚子水缸里种了几棵花藕,每到六月天,办公室都是香的,是那种清香气。沈复的 《浮生六记》中说,芸晚上把一小撮儿茶叶用纸包起来,放到晚上闭合的荷花芯子里,这样茶叶里就浸染了荷花的清香。我是为之赞叹,恨不生在水乡,摇着小船天天看荷花,吃莲藕。办公室外养着两缸荷花,荷花仙子一样在风中起舞,美得不可亵渎。只是因为这两缸死水,常有蚊子叮咬,也是一大烦事。想来世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
前年,去了衡水湖。雇了一条小船驶入荷花淀中,眼看着沉甸甸的莲蓬馋得要命。爱人多年前曾在武汉给我买来三个,一路颠簸,吃起来,早失了应有的清新气。摇船的师傅似是看透了我的心,停下船,掐了荷叶给我遮阳,一霎时,觉得自己变成了荷花仙子。他善解人意地扔过来几个带茎的莲蓬,我用荷叶裹了握在手中,半晌舍不得吃一个,倒是摇船的师傅说: “有啥舍不得,吃吧,只要湖在就有得莲蓬吃!”
考古发现数千年前人类的遗址中就有碳化的莲子,神话传说中,哪吒就是莲藕荷花铸就的神通广大小英雄。近日在读王祥夫先生 《四方五味》,书中有一幅插图是先生画的莲藕,葫芦状,一端是横切面,七孔,节间带黑茅根,旁边有一蜻蜓幼虫,我老家叫水蝎子,可吃。先生此画题字为 “晋阳湖多藕乡人多不食也。”晋阳湖边人守着藕这宝贝,却不吃藕,呜呼。
荷花被称为君子花,佛教也常用,被赋予神圣的使命。我的荷花连着藕与吃有关。
蓖 麻
蠡县人说的大麻,是蓖麻。
蓖麻这个蓖字是独一的,配得上蓖麻的洋气。
蓖麻确实是洋气的东西,叶子像巴掌,荷叶一样用带孔的茎秆顶着,不似一般花草的草香味。它的绿是一种独特的白绿,它的杆,带着节,竹子一样,还搓着一层白粉,像一个高高大大的外籍女子。
爹说,上世纪五六五七年的时候,刚修的潴龙河堤坡上,边边角角的地方,乌泱泱的都是大麻。边说边伸手比划着,两人多高,大麻籽一嘟噜一嘟噜的。这些大麻是护堤人种的,谁种归谁。青年团的小青年,要求进步又喜欢玩,想买乐器,没钱。换来了蚕籽,利用别人家的大麻叶养蚕。养蚕的地方也没有,就在咱们家北院,纪周晚上义务看着。姑娘们走到大麻地里,摘下头巾,掐些叶子喂蚕,大麻叶接济不上了,就捋榆树叶。大麻蚕刷啦刷啦地吃,小手指一般粗。那年的蚕茧结了几笸箩,卖了80多块钱呢,花12块钱置办了一个说西河大鼓的鼓,又买了金色的半月一样的说书板。
那时候养蚕都是义务工。一起说西河大鼓的人,有河北陈村的、堤内陈村的、宋岗的。咱们村主要是我和你大叔、老营叔,你姑父、你球哥。
我第一次听说蓖麻蚕。
小时候,北院种过半院子蓖麻。
下雨的时候,钻到伞一样的蓖麻下面,听雨 “哔哔叭叭”地打在叶子上。五六岁的小人,尚不知道雨打芭蕉和雨打荷叶的意境,调皮地折下叶子接雨,在地上划沟,引导水流向低处。蓖麻花有红的有黄的,蓖麻的花蕾小包子一样,蓖麻子长着刺,像刺猬,其实现在我会比方为板栗。起初,包裹蓖麻子的刺软乎乎的,变了颜色,就扎人了。
我家种蓖麻为了卖钱。每年这个小院种蓖麻或者苋苋谷的收入,够半年花销,有二三十块呢。
我记得,爹把蓖麻杆砍下来,我们找分叉的,两手捉着当小车,拉着弟弟玩。
蓖麻有与众不同的气质。它的种子也别致,黑麻或者灰麻、白颜色构成的花纹,胚芽的一头象脑袋。蓖麻子在笸箩里,像一窝正在睡觉的小东西,用手摸上去,光滑滑的好可爱。邢台的恒坤兄小时候玩过大麻子 “火把”,用铁丝把去壳的大麻子串起来,点燃,白白的大麻子冒着黑烟,豆大的火花,像萤火虫。爹说他小时候没油了,就砸开几个蓖麻子,用擀面杖压碎了擦擦锅,代替油炒菜。我前一阵翻资料,说蓖麻子八粒就能致人死亡。
当然,按照传统医学上是药三分毒的理论,蓖麻是入药的,作为泻药进入药典和药房,它的泄下作用比巴豆柔和,算是君子药。木集兄说,他舅妈用蓖麻子油线纳鞋底,用锥子在蓖麻子上戳一下,顺便把麻线也在上面滤一下。有了蓖麻子油,麻线穿过小孔滑爽多了。木集兄老家山东。我小时候,老家没有用麻绳纳鞋底的习惯,用自家纺的棉线,娘每扎一针,都在头发上划一下针,也是为了润滑。
张老师课堂上给我们讲蓖麻籽可以做飞机油。大概是指润滑油。
就在这个夏天,张老师遇车祸过世了。大概七十岁左右。我和保定工作的两位同学买了花篮给他送行。这个说话就瞪眼的人,老了,突然去了。没有孩子,没有老婆,灵前几个侄子侄女守着。他的床头,有两个相册,珍藏着我们小学时的照片。小学毕业三十多年,我竟然没有进过他的家,他自己没有家,跟着侄子住着,自己做饭吃。
前几年,在街上遇到他,曾许诺春节去看他。可是,我同学因为他的怪脾气不想去,我一个人也觉得不知道说什么,没去。又遇到他,翻着眼,怪我食言。有几次想去,又放弃。
张老师的窗台上下开着月季、串红和鸡冠花。没有泼辣的蓖麻。村里早没有人家再种蓖麻。
苋苋谷
苋苋谷的大名,我刚想起来——千穗谷。
它和野地里的苋菜,还有鸡冠花像孪生兄弟。
苋苋谷红梗的多,说红也不正确,接近玫红。叶脉也如玫红颜料描过去的一样,绿叶玫红梗,颜色上占了先。娘让我劈叶子炸 (焯水)菜吃,我偏心,尽量劈浑身嫩绿的苋苋谷。
菜地里的菜青黄不接的时候,苋苋谷叶子是上好的东西,开水焯了,蒜醋盐一拌就好吃,如果再泼上半勺油那就是人间至味了。可惜,那时候有点油味儿就不错。苋苋谷叶子给人软绵的感觉,又有嚼头,不似山药叶滑溜,没有马齿苋的酸味儿。
苋苋谷叶子好吃,但也不能过度。劈多了叶子,肯定减产。或者从旁边出侧枝,夺养分,结一些小穗子,影响主穗的产量。
这几年认得苋菜了,它的味道和苋苋谷一样好。最初吃苋菜在定兴县,那时我在医院上班,孩子暑假跟着爱人去了京郑线。倒休的时候,我坐绿皮车到定兴看孩子,小关带我去野地里采苋菜。麦子已出齐穗,那些白地 (指种秋季庄稼的地),种着长果和芝麻,长果秧子还盖不严地皮。这样的地里,长着一拃来高的苋菜。见到麦子有种欢天喜地的感觉。地里的蝼蛄、蚂蚱、蚂蚁,都让珠儿开心得要拍手,及至怕惊跑了蚂蚱,踮着脚走路。她不在意苋菜,更不知道妈妈的童年里有苋苋谷。苋菜被开水焯了,剁碎做了饺子馅。从此,苋菜走上了我家的饭桌。凉拌苋菜,浓绿的菜,白的蒜粒,鲜红的辣椒丝,配上几滴味极鲜、醋,是夏季开胃菜。冬季里,用苋菜加肥肉包饺子,是吃鲜呢。
定兴、京郑线、绿皮车和苋菜在一起。小关是满族人,和我没有一丝血缘,从保南到定兴,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我们和亲人一样。
我分析苋苋谷的大名,千穗与千岁谐音,符合中国人的意蕴,是不是借其长寿之意呢。1997年夏天,苋苋谷还小的时候,小关的爱人突然意外身亡。胖妞妞的小关,两个月内瘦得如同一个稻草人,风一吹都站不稳。时光不能倒流,千穗谷,千岁谷,只是一个美好的祈愿。
爹种庄稼很讲究,行距株距尺子量过一样。种出来的苋苋谷,犹如士兵列队。玫红梗的、浑身绿的,各有各的风采。仔细瞧,玫红苋苋谷的优势就出来了,个子大,穗子也大,火炬一样,苋苋谷粒也显得油光。
苋苋谷的种子,像半透明的玻璃做的,圆形,是做苋苋谷糖的好东西。小时候,走村串户的小货车上都有苋苋谷做的 “欢喜团”。苋苋谷爆成米花,用糖粘在一起,旋成圆形,点着胭脂和绿颜料。
上溯四十年,谁的童年没有 “欢喜团”呢。
爹在院子外的甬路边种了串红、美人蕉、对叶梅和鸡冠花。红梗绿叶子的鸡冠花顶着硕大的 “红鸡冠”。其实,我是很想尝尝鸡冠花叶子的。
蔓 菁
蔓菁这两个字很美。一看到它,眼前就漾起一片不起眼的蔓菁地。多少年没见过蔓菁了。
这次回乡给姥姥姥爷送寒衣,居然在大堤根杨树林下看到了它。我和妹妹猜测了好久,决定拔几棵看看。这叶子看着像萝卜叶,还布满了虫眼眼儿。我俩都认为是蔓菁。原因很简单,只有蔓菁才种在平地上,萝卜都种在肥沃土地的畦背儿上。且萝卜可是个招摇的主,挺着粗粗的腰,报功似的让人老远就能看到。蔓菁不是蔬菜园子里的大家闺秀,它餐风饮露,将天地精华暗暗地输送到自己孩子的身体里。
蔓菁的孩子就是它的根,手指头粗细,大多分叉,有环状的纹理,本白色,酷似人参,因此得到一个外号 “赛人参”。离我家乡不远的河间府,有个注解《诗经》的老人毛苌,他说,葑,须也。这葑是蔓菁的古称。
蔓菁的气味很特别,喜欢的视若珍馐,不爱的草芥不如。蔓菁煮粥,有一股呛人的中药味,和山药作伴熬的棒子面粥,我认为是不可多得的美味。山药黄橙橙的,蔓菁修理了须子,被巧手的母亲竖切做四瓣,白乎乎的颜色,露出发黄的纹路,看上去也不如山药美。虽然不美,但喜欢它的人一天不吃,仿佛没吃饱饭似的。这蔓菁和人也有缘分呢。
母亲病重时,北京的堂舅恰好回乡坐诊。养肺阴的方子,沙参、玉竹、天门冬、麦门冬、瓜蒌等等,我记不清了。堂舅特意嘱咐,多喝蔓菁粥吧。我特意查了蔓菁,别名一大串,形状也和我记忆里的蔓菁有天壤之别。我家的蔓菁,也许蔓荆二字最合适,形状如人参,也带有长长的须子,却和人参的命运有天壤之别。人参在条件最差的乡医院也被珍藏在茶色玻璃瓶里,蔓菁从地里挖回来,就随意地堆在墙角阴凉里,只图吃起来方便。蔓菁叶子长得也不起眼,只有下了大雨,才看出它也是绿色的容颜。它不占好地,边边角角,沙滩坡头是它的家。母亲每年在河边的 “蛤蟆洼”老堤头上撒下一些蔓菁籽,靠天意收成,每年也会收几筐头,配着山药度日月。贫瘠的日子,蔓菁微苦后甜的味道倒蛮似农家的日子。记得蔓菁总是和豇豆挤在一起,土绿的叶子更不起眼,只在深秋,人们收完了大秋,母亲背着铁锨筐头,到 “蛤蟆洼”去挖蔓菁。蔓菁叶子也舍不得扔掉,齐根切下来,挂在树枝上风干。这可是上好的东西。年前,开水泡了,配上大油,包成包子,如果年头儿好点,再切上几片肥油油的肉,那可是一咬满嘴流油的人间至味了。如今,想吃蔓菁馅包子,可是谁给包呢?母亲离开我二十多年了。
不知道蔓菁有没有延长母亲的寿命。我相信堂舅的话有道理,他是多年的中医。
堂舅和蔓菁结下了深深的缘分。几乎是无蔓菁不饱,他对我姥爷说,大爹,我一天三顿蔓菁粥都吃不够。一顿喝三碗呢。我那时候还年轻,想说,这蔓菁能有多少营养,穷人家的当家饭,还不如山药呢。堂舅回了北京,家里人去北京,会特意给他带上蔓菁。这蔓菁成了堂舅与家乡的使者。听说他临终时,还是吃的蔓菁粥。我想象着堂舅的样子,还原他喝蔓菁粥的画面:堂舅挥舞着筷子,挑着蔓菁吃得极快,且津津有味。吃罢,掏出手绢擦额头上浸出的汗珠,一脸满足。堂舅后半辈子,每年冬天能吃上最爱的蔓菁,临终胃里有一碗家乡来的暖乎乎的蔓菁粥,走在西去的路上,也算人生的一种圆满吧。
我写 《荞麦》的时候,曾说过,我如果有块儿地,一畦种荞麦,一畦种蔓菁,朴素又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