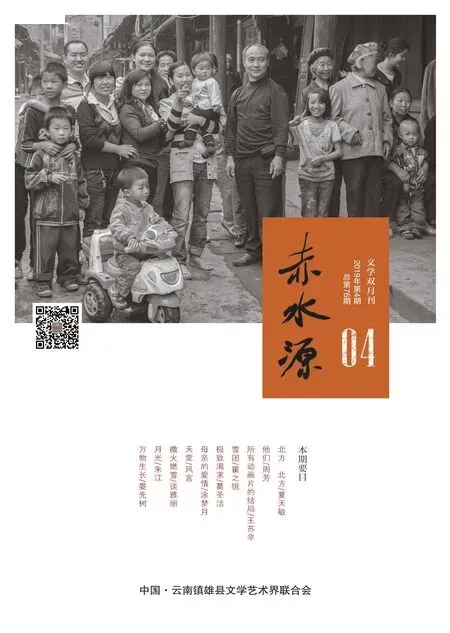予时光之书
杨家林
散文
立春前后
外面的风越吹越紧。
树木掉下最后的黄叶,路边的野草早已枯败。
等不到雄鸡报晓,我已在朦胧中醒来。只为目睹雪花绝世的容颜。
飘落的雪,像仙子的裙边,洁白而轻柔。亦像一把巨大的伞,遮盖世间的一切:狰狞可恶的面容,卑鄙肮脏的灵魂,泛臭的死水,开败的曼陀罗。
午夜,世界一片洁白,如初生的婴儿,唯有真善美。白雪覆盖的家乡在雾色中越显朦胧。耸入云端的罐子山模糊了,错落的村舍模糊了,一切的一切都模糊了。如梦似幻,虽无法触及却真实存在。存在于多年前那个立春的黎明,存在于漂泊许久的游子心底。
静寂的雪地里,万物正用尖锐的嫩芽或者锋利的爪牙刺破厚重的积雪,探向这个新世界。路上的行人,正试着用双手拨开眼前浓厚的迷雾,望向远方。
轻轻地捧起飘降的雪花和绕房的雾,把它们珍藏在我的指间,心底。在滚滚而去的尘世中,细细品味,悠悠怀念。
作别故乡
流水岁月,弹指挥间。
一束山间的阳光竟逼退了早春时节的寒潮,照耀在神州大地之上。
岩桥沟,像一颗镶嵌在流水与群山之间宝石,在阳光里闪烁着金辉。
一切都在等待,等待一束山间东来的阳光。消瘦的小溪,哗啦啦地流淌,把岁月的哀愁带去远方,溶解在烟波浩渺的大海之中,就像除夕夜家人团聚时的碰杯声,被匆匆时光带走。
阳光下,调皮的孩子脱下了厚重棉袄,迎风奔跑,欢悦的笑声惊醒了家门口那颗沉睡的老树。风中,老树抖了抖枝头的尘埃,尝试着伸直僵硬许久的脖子。
此刻,父母也走到了院坝,用那双昏花的老眼眺望晴空,口中念道:日是黄金雨是宝,五谷丰登少不了。
风悠悠地滑过树梢,灌满家乡的每个旮旯角落。我将心事付诸于风,倾听春天的故事。
在这样一个风和日丽的二月,心中纵有万千不舍,已只得折半截新柳,织一条柳带,挥手作别故乡!走向那个熟悉而陌生的远方,那个将谱写我春秋的地方。
桃花与鸟
初升的太阳,照耀着春日的大地,万物萌发,演绎着一场与梦的故事。
远山的草木泛着嫩绿,近处的几株樱桃花正在盛开,枝丫上的几只麻雀,翻啄着羽毛,像调皮的孩子。原野上渐现了老农的身影,爱美的摄影师扛着器材,不停地侍弄花草。空气中弥漫着春天的味道,大地上留满了春天的足迹。
我敞开所有的门窗,集一整屋暖春的空气,大口地呼吸。阳春三月,我们习惯性地谈起出去走走,看看来时匆忙的路。出去走走,不必像雄鹰那般翱翔蓝天,亦不必像候鸟那般往返奔徙,但可以像麻雀那般匍匐于田间,或者栖息于樱桃树枝头。
那些绽放的花,青嫩的野草,总能予以我新的期待和生命的启迪。静待花开花落,闲看云卷云舒,就像懵懂的少年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试着寻一处静谧的山野,有山亦有水。山不必太高,能看云海日出即可,水不必太清,能观水中鱼虾即可。在山脚涧旁搭一茅屋,在茅屋前后的空地上种几株樱桃树,在樱桃树的枝头饲养几只麻雀。
烦躁时,垂钓溪畔;闲暇时,看书作诗。岂不快哉!
五月末梢
阳光懒散地依靠在山巅,如彻夜未眠的人们,拖着满脸的疲惫。一阵滚烫的山风拂面而来,树叶轻舞,浅草摆动。
此刻,我仰望碧蓝的天空,寻觅一片走失的云朵,像游子眺望远方的故乡。顾不了山风把树叶吹得莎莎作响,把原野上的浅草刮得抬不起头颅,把不远处低头爵草的牛群的纤细的毛吹动。
踏步放歌已远去,一路风光尽忘我。青涩的野李子,稚嫩的猕猴桃,殷红的棠棠果,洁白的白米泡儿,足已让我垂涎三尺;还有那些零碎的不知名的花儿,如芳华少女在微风里起舞,荡漾出阵阵芳香,令我无从分辨。
这方山水之美,不可言啊!
五月的饕餮盛宴已让我醉身其间。
清凉的溪流扑哧扑哧地冲刷着两岸,带动着时间的轮轴滚滚而逝。来及细细品尝山间清流的甘甜,夕阳已将水中的身影拉得好长好长,夜幕已将剩余的时光遮掩。
在风中,我手捧一湾的清流,珍藏在五月的末梢。
立秋时节
夏日的暑气未觉消退,却已是入秋时节。核桃树上的秋蝉扯着嗓子地叫道:秋天来了!生怕忙碌的人们忘了。
阳光依旧微笑,风儿还是那么温柔,转眼又是一番景象。
远山不再像仲夏时那么绿叶盎然,却也不是深秋时那般五彩斑斓,开始有了层叠的美丽;眼前的成片玉米,在岁月和汗水的滋养中散发着成熟的味道。
一切皆如想象,却又超出了想象。
山间的雾色提前拉开了黑夜的帷幕,一场淅淅沥沥的秋雨滴落在青色的沟瓦之上,含浆待收的玉米正大口吮吸着上天的乳汁,以累累的穂回报辛劳的人们。
黄昏,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彩虹,远远望去,像一串挂在故乡脖子上的项链。
美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