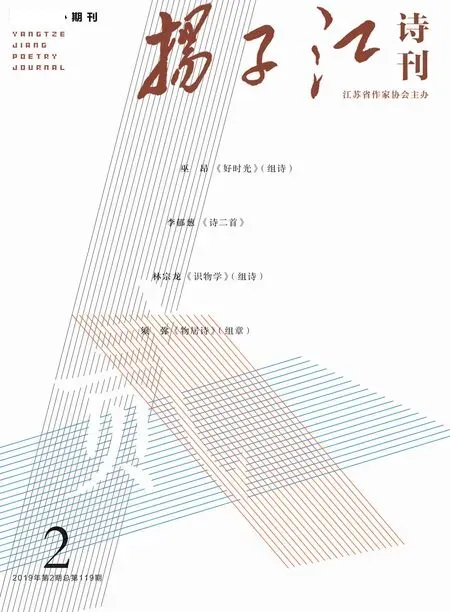落叶归根(组章)
宇剑
洋葱之心
如果灵魂有一扇窗,我就将所有光明献给独立的思想。
我赞美所有的生命神采奕然,我赞美所有的声音清脆动听,我赞美所有的味道如甘醴。我盘算着年轮,年轮盘算着轮回,轮回盘算着我,如此置换,我裹紧肉身,等待时间揭开我的真相,我的谜底,我的一切。
喟叹是多余的。
我安静地散发着光芒和热量。鸟雀啄我,风雨蚀我。我一如既往,在土地里勾践一样隐忍。我的思想正在接近文艺复兴,汇聚百家和弦,正在暗暗凝成一条冰河,它是一把带光的刀子,它是一颗无声的子弹。
我的心是异质的、禀赋的、独立的。
亲人们学会了打破砂锅问到底。亲人们渴求答案和结论。
他们在生命的菜地里捡到我,一层一层剥去我华丽的衣裳,一层一层认识我的密码。他们满含热泪迎接生活的幸与不幸,以及冷热。他们命名我是一尊洋葱。
思考清澈黎明的洋葱。
西红柿颂
西红柿,是秋天的礼物。她懂得哭泣和沉默,像我丰满的姐姐,温柔、和蔼、亲切。这其实是不够的,因为所有的褒义词在她面前,都为之逊色。
西红柿是生命的原色。
我的童年从那里开始,母亲的痛也从那里开始,这是家庭共同膜拜的颜色,共同领悟的生命重量。
秋天的菜园,只有西红柿面带阳光,她把最后的光芒散发,温暖乡村和冬天。
储藏是幸福的。蒂落是幸福的。
在艰难的日子里,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曾流过的汗,如同我记忆里的西红柿之酸。
我信仰生活的真善美。
我写诗感恩每一颗西红柿在秋天给予我和家人的美味,我们对着西红柿感慨,仿佛与生活、爱、诗歌相拥而泣。
葫芦颂
秋天不仅仅是高处的植物预约而来,它自带风雨和尘埃,它与一个字息息相关。
落。这个字独具匠心和诗意,独具温柔和高雅,独具现代主义的一切风流。
葫芦落地。这是多么自然的动作和行为,如同婴儿坠地,如同老人入土为安,生与死一念之间,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生生死死都是一个概念而已。阳光照耀着葫芦的表面,像是对一张脸进行辨认;雨水轻抚葫芦的周身,像是沉浸在瓷器之美中;大地母亲接纳自己的孩子一般,慈祥、温暖、和蔼。
岁月不居。
我在长安已是第三个年头,三年时间像是完成“落”这个动作的所有细节,一帧一帧。
生活不需要煽情,不需要矫揉造作,不需要多余的解释。它只要宽容和厚道,它只有一条通向真理的道路。
在奶奶的菜园里,我不如这只葫芦;在城市这浩瀚的菜园里,我更是不如一只葫芦。我只是卑微的个体,如尘土,如蜉蝣,如野马——
我努力模仿着一只高高挂在空中的葫芦,质感而美好。
只是内心空虚而寂寞,起风的时候,我就忘记了来时的路。
与白萝卜为伍
家父是赤脚医生,他赤脚养活了我们兄妹五个毛线团子一样的小孩,养活了母亲,养活了一家人。
春种秋收。冬去又春来。
一家人在时间这艘船上,航海。
一家人面对四壁,背诵祖上留下来的土方子,像铭记祖上的咒语和教诲,像为了草药和植物而生,像为了更好地活着而谨慎膳食,像雕刻生命的哲学。
我和妹妹背诵道:白萝卜,小人参,常吃有精神。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郎中开药方。九月九,大夫抄着手,家家白萝卜,病从哪里有?
妹妹哭着问:“吃了三十年萝卜的母亲,为何一身的病?”
父亲霎时,呆若木鸡。哦,更像是荒地里站立的一根白萝卜。
送走父亲最后一程,那是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五丑时,父亲从一个动词变成了一个名词,变成了一座坟。
我们一家人信仰了多年的药,那天失效了。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今我们兄妹五人,各自奔向各自的前程,背井离乡。
母亲叮嘱我们,萝卜抗癌,降福消灾。她声音很轻,很美,我隐约觉得那是父亲说过的话。
芫荽颂
跟随祖母种菜的那些年,我心有猛虎,细嗅的却都是香菜。
祖母的厨房,拥有着我所不知的五行学说、五味学说、五谷学说。
祖母带领我走在蔬菜的长短句上,寻找淡绿的词牌。
芫荽,这究竟是西施还是昭君的化身啊,她有一个美妙的乳名,她有一身浩然正气,蚊虫不近,如同英雄不近女色。
她仅仅是一道菜的点缀。这是成人之美的全部。
祖母耕耘着菜园,父亲耕耘着土地,我耕耘着贫瘠的文字,我们都需要一个点缀,一支画龙点睛的笔。
她独立成为一道风景。
她怀揣一把匕首,刺破了我们庸俗的嗅觉。
白菜颂
浮生如梦,我记忆里的白,有白马、白衣、白门楼。
白茫茫一场大雪淹没了贾宝玉的前程,白龙马驮着唐三藏西天取经,白毛浮绿水,这中间的白,都是乌托邦的白。
童年时期的白猫洗衣粉洗不掉儿时的无知。
白日依山尽。这中间的白,都是虚幻之白。
唯有白菜之白,不是真正的白,却有白的内涵。
人生如一场白日梦,明晃晃的。
我仰望白菜,是因为母亲把几大筐白菜送给村头的老拐子,救活了三个小妹妹的命。
那一年冬天风雪交加。一家四口,终日与白菜为伍。
世上其实没有伟大的事物,世上所传言的伟大,不过是与人方便。
眼睛是世界上最有温度的存在。
它看到河流的静谧,山岳的巍峨,它也看到白菜之白,不过是平凡人家的底线和根本。
土豆之命
恍若,是前世。一颗土豆落入我的命门。
让我领取平凡的二维码——土的箴言。
外省的友人常说我一日三餐离不开土豆、马铃薯和洋芋。
这些词汇是我苦命的兄弟,是贫穷的代名词,是生活的粮食,也是上帝的馈赠,丰富了我的灵魂和味蕾。
我麻木地活了二十六年。
在农村,我木讷如同一块带疤的土豆;在城市,我平淡如一盆乏味的土豆汤;在路上,我喋喋不休如烤焦的土豆片。
我像一个词语一样,站立在现实与理想之间。
我信奉的宗教是落叶归根。
是这样:一辆从农村开往城市的火车,轰鸣声不绝,我在内心里置换出另一个自己,去往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