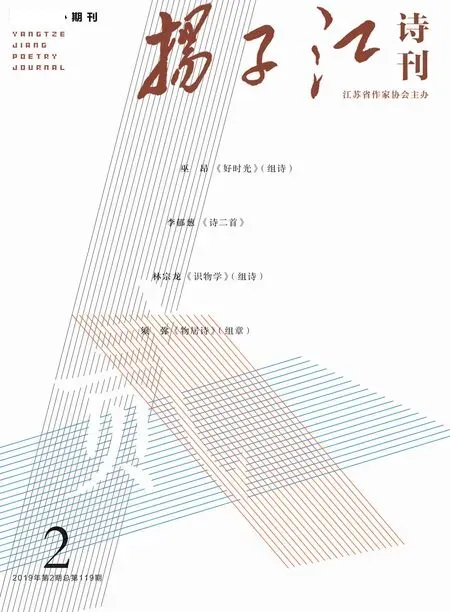识物学(组诗)
林宗龙
山中雾气
野猪在灌木丛拱出新鲜的土。
烧木柴的烟,从山中
那片毛竹林升起,
穿过它想穿过的禁地。
有一些我们尚未抵达,
当雾气弥漫在柿子树边缘,
一块散石从山谷滚落
并没有回声。但我们仍然相信
有着美丽斑纹的昆虫,
就像信任一种迷人的局限。
当在潮湿的墓园辨认完
身上长刺的并不是羊蹄甲,
或许我们将会从猎人的口中
获悉一头白羊
暴露在危险中的消息。
虚无的一种
他把皮球踢到一层楼高的屋顶,
一群同龄的孩子,
围在一旁欢呼,这虚无的一种,
在舍弃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时日。
傍晚,空气中烧桔梗的烟火味,
弥漫在芒果树周围。
几条街以外的花巷教堂,
会有祷告的母亲们,
从一棵羊蹄甲的底下经过。
七楼的阳台,我凝视着
逐渐变幻的云朵,那深沉的色泽,
我在一片敞开的湖泊见过。
它从不会消逝。
麋 鹿
也许,她有一双透明的翅膀,
当妻子从傍晚的教堂经过,
一条白色鲫鱼
被捕到岸边,横躺在空地
褐色的树枝旁。
湖面在一场风暴后,
平静得像一面婚姻的镜子。
她拒绝停下来,(已经没有什么
可以阻止她)
绕过棕榈和桉树,
她爱并痛恨的男人,
在湿地的中央。
她飞了起来,她摸到云层中
一片深渊的密林,
一只幼小的麋鹿,
正等着她,慢慢驱散它
周围的黑暗。
也许,那光就来自
她自己。
梦 记
从破碎的梦中醒来:
鸟的鸣叫是下水道的,
蒸汽机的轰响,
像从某种情绪抽离而出,
还有更多声音
不被认知。
我孤立并存在于其中。
风刮起时,
窗户砰砰响着。
一个小的秩序,
柠檬桉在保持沉默,
那不存在的反而在建造
更大的旋涡。
我存在并孤立其中,
陆地在移动,
挤压出湖泊、风暴和
我的母亲,以及那个
处在旋涡中心的回声——
“这神秘不是真的
要用一生来强调”
识物学
宝贝,这是“雪”。
羽毛那么轻的可疑之物,
你还未见过的,
它落在剧场外的椅子上,
医生,刚从那扇铁门
出来,涌向相反的街道。
这是“威严”,宝贝,
雪落到下水道之后
可能是黑的
你仍未确认的,
也许正储存在你父亲身上。
那是“火焰”,
一种转瞬即逝的洁白,
厨房风暴式的滴水声,
和我爱着你争吵中的母亲。
它落下来,甚至消失
并不意味着结束,
宝贝,这就是“生活”,
也可能不是。
在你触摸到之前,
它什么都可能。
闲散录
山中的鸟鸣,在两株木桃之间,
鸡蛋花的树冠,
像掌握了人类的语言,
在微微颤动。
清晨,和妻子说到的无目的,
是池塘边缘的青苔痕迹,
一只活过冬天的蝗虫在上面
爬来爬去。
那短暂,令人敬畏,
又充满露水沾在薄雾里的激动。
在边界找到黑暗前,
兰花丛间的一块鹅卵石,
像只鸵鸟,
斜躺在经验的光里。
哦。妻子的白鹭,
正飞过郊外的香蕉林。
妻子的手
“你的鱼尾纹”,妻子的手,
在我的眼角滑动。嗯,生活的
样子。我在接受不可逆的
改造:面对一面钟,现在是
妻子的手。“你的抬头纹”,
它滑动到我的额头,像笨重的
秒针,在做一场实验,
那迟缓的力量在教育我,
从来没有赞美,只是在我脸上
轻轻地抚摸,然后冲我说话,
“这是法令纹”,那里有你经历
的早晨和夜晚,有雾气
和屋顶,具体的树冠和
短暂的恒星……有妻子的手
留下来的气味,从深夜的漆黑中
伸过来 ,像一束从不停顿的
亮光,追着我要完成一次倾听。
虎头湾或其他
一片褐色的滩涂
多出几根耸立的瘦树干
散落在鱼排周围
海鸟有时会停下觅食
它尖尖的长喙在翻动什么
并不被我们察觉
黄昏将至,潮水即将漫过
裸露在外的礁石
当你弯身捡起一枚苦螺
是否惊异于那真正的声音
从陡峭的密壳里
寄居蟹伸出风暴式的钳子
像在搅动
居住于自然边缘的我
风暴眼
黑沉沉的乌云,
像父亲严肃下来的脸,
在车后座,我向老朋友说
“我们正驶向风暴的中心”
有什么重新被需要,
父亲的口吻,开始像雨的鼻息
落在一棵羊蹄甲上。
“孩子,去享受
那些少的事物。”
父亲不是别的,
是严肃背后,多出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