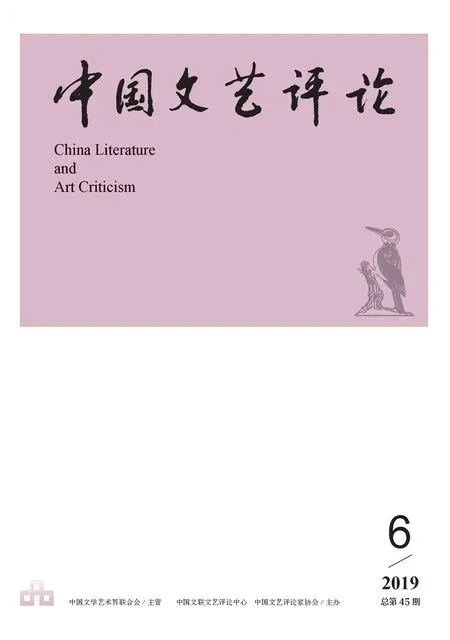机器的进化与工人生存情绪的改变
——从肖克凡的《机器》谈起
张红翠 张祖立
肖克凡发表于2002年的长篇小说《机器》,塑造了两代工人劳模的丰满形象和悲喜人生,讲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成长,以及新中国工业史的艰难曲折。小说不仅倾注了写作者的深情,也凝缩了故事人物的情感与精神,更有对中国工业化以及经济改革的深度关注与执着探寻。在诸多关于《机器》的评论中,理论家们集中对小说中以当代工业话题为核心的多重重要主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阐释。然而,当我们重新翻阅《机器》,总觉得现有的阐释让人有意犹未尽之感。原因似乎在于:绝大多数批评都将目光集中在小说的诗意化书写上,而对于“机器”及其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的非诗意化思索却少有关注。人类历史的事实是:工厂与工人的出现是与人类工业化历史直接相关的,人类工业化历史的根本动因是“机器”这一现代之物的出现。随之,以机器为核心组建起来的“人机”组合关系构成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主要动力关系。这一组关系是现实的,而这现实中甚至隐藏着某种触及人类终极命运的冷酷。因而,工业题材的写作必须在诗意化书写的同时,面对和思考人与机器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中人类生存的现实状态。然而,在当代中国工业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历数新中国工业化历程以及关注工人阶级成长命运的多,提问机器是什么、工人与机器之间关系的本质性状态的作品却很少。肖克凡长篇小说《机器》的出现似乎显现了一种突破,开始不自觉触及对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这一本质性问题的思考,透露出与诗意化写作并行的理性化意识。
一、问题的提出
在小说扉页,肖克凡对小说题目“机器”作了自己的解释:“人生就是一场运转。有谁愿意停下来呢?尽管停止也是一种生命状态,然而我们还是选择运转。”肖克凡的这段话是叙事者对叙事对象的诗意赋予,在这种诗意赋予中,写作者为中国工业化历史和工人阶级的时代精神乃至工人劳动的诗意化赋予奠定基础,甚至有评论者说,读完了《机器》顿生对机器本身的敬意。然而,我们认为,小说所表达出来的关于机器的隐喻远不止这些。因为,作为一种持续不断改变人类命运和生存方式的庞大的现代之物,机器与人类的关系远非诗意赋予所能完全表达。于是,经过仔细查找,我们看到在小说诗意书写的表层下面,埋伏了一条不甚清晰但却隐约可见的对于人与机器关系进行非诗意化审视的理性化线索。这条线索在小说中有具体可查之处,并且小说是在不经意的情况下通过它的主要人物——劳模第二代王莹——提出了这个重要的问题。
在进入东方制冷设备厂当工人之后,还未成年的王莹很快适应了工厂的生活,她对自己说:“我既然进工厂当工人就应当研究工厂这门学问吧?什么是工厂,什么是工人,工厂与工人是什么关系,机器与工人是什么关系……”年纪轻轻的王莹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质问题,这个问题的意义绝不在于表现小说人物作为女孩子却具有难能可贵的心智聪慧,更在于它触及到影响现代工厂工人生存情境和生命情绪的关键性问题。这个问题潜伏在小说当中,时隐时现,牵动着小说叙事的潜在意识,构成小说中与诗意化书写相应的另一条对位线索。尽管这一线索在小说中还表现为朦胧的、时断时续的隐含存在,而且在小说的终了,作者依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仍然显示了工业写作中宝贵的理性化的检视意识。这种意识体现了工业题材小说家以及工人群体,对于现代工人身份以及工业生存环境的、正在形成并将日益清晰的自我反思。
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日益成为人类劳作和生存的新的工业化环境,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也经历飞速演变。这种演变隐含着人类工业化过程的重要曲线,呈现的是人与机器之间的博弈以及这种博弈状态下人(工人)的存在品质及其对工作伦理建构的影响,也改变着人们对自身价值的理解,尤其影响着工人身份的具体建构。这些现实的工业化经验已经超出了《机器》叙事的内在范围,但又与之内在关联。在小说《机器》中,在诗意抒写的同时,肖克凡触及了人机历史关系变迁的关键问题,这种文本内在的回应使《机器》文本中的历史世界足以勾连小说文本之外的、当下智能化工业环境中生产线工人的生存景况与现实情绪。循着这种开放性的阅读,我们将进一步拓展《机器》的叙事视界,将阅读拓延至当代农民工诗人诗歌,并以此为契机,对《机器》没有展开的第三代工厂工人生存情景进行补充。或者可以说,本文的阅读和理解实质是以去诗意的方式重新阅读《机器》。
二、机器的历史:诗意书写的可能与不可能
要理解《机器》诗意化书写的内在可能,我们需要同时理解机器的历史及其对人的劳动情态的影响。机器是人类劳作的工具,工具贯穿在人类历史的全过程中。原始人类社会时期,人类的生产工具是十分简单的。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用简单的石头开掘劳作;进入新石器时代,出现打磨的石器;后来发明了冶金术,进入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出现铜制的工具和铁制的金属工具。随着电和蒸汽机的发明,人类进入现代工具时代,开始运用现代化工具进行生产和劳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机器”,是在西方工业革命后才逐步被发明和广泛运用的,是工具发展到科技高度发达时代的产物。世界上第一部工业化机器发明时,人们欢呼雀跃。机器之所以在最初给人类带来兴奋,是因为它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动力方式和生产方式。那个时候,人们恐怕还没意识到机器这一“庞大之物”同时也携带着将世界同质化在工业秩序中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在未来将不断改变着人类在世界中的生存关系。
回到《机器》。在小说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机器的这种力量和强大的意志。故事发生在中国工业化起步的重要时期,而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外族入侵的情况下被迫发生的。在当时的世界,生产机器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者地方工业化的重要动力和标志。所以,小说中日本的“东洋纱厂”在当时落后的中国故事里是一种特殊的符号,是现代社会先进的工业化标志,具有特别的吸引力。在《机器》一开始我们看到,16岁的牟棉花想尽各种办法过关斩将拼进东洋纱厂。与此同时,决意不做华昌机器厂少东家的白小林则投身东洋纱厂研究日本工业管理的内在机制。牟棉花为的是个人生存,而白小林致力的则是一个更加超越的工业化理想,为实现中国工业化做出个人努力,这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冲动在个体身上的表现。但是,不论是为了个人生存还是为了国家的工业化理想,牟棉花与白小林都是兴奋而急迫的,也都是趋向机器的,即接受机器的意志,这是现代人类共同宿命的缩影。
但是当机器环境成为人类普遍的工作环境的时候,机器带给人的则是持续的逼迫。这种逼迫首先是因为,机器日益成为生存必须的现实环境,人只有依靠机器才能求得比依靠土地更现实的生存。因为,土地圈占使得人们再难以依靠土地来获得生存,离开土地的人们要求得生存就必须进入以机器为动力核心的工业生产环境。牟棉花拼了命也要进入东洋纱厂,只是因为那样她可以吃饱。所以,当工人与工厂相结合的同时,在体会融入感之前他们体会的是分离——工人与原始土地、与血缘宗亲的分离。这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现实。其次,工业机器的普遍化将人类带入工业现代化的现实当中,工厂车间成为人类生活环境中重要的空间景观和工作景观。作为特殊的景观空间,工厂用严格的管理规定了现代人类基本的存在情境。然而,生命内在的对于归属感和安全感的需要,又迫使与土地分离之后的现代工人与工厂之间建立新的认同关系,即与工厂、与机器生产相认同,这种“认同”是工业现代性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随着这个问题的解决,现代工厂中工作伦理的建构才有可能,依托于工作意义建构而产生的工人身份的自我发现才成为可能。因而,对机器以及工厂的认同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弥合人与土地相“分离”而产生的“断裂”危机的弥合剂。而这一点是小说《机器》中关于劳模的伦理建构及其诗意化叙事赋予得以可能的第一个原因。
小说讲述了刚刚成为工厂工人的牟棉花如何在被惩罚的过程中,完成对现代工厂的理解,对工厂环境以及工作理性的认同,以及其自身作为现代工人的蜕变。第一天上班的牟棉花很快喜欢上了自己穿工作服的腰身,中午吃饭时也不舍得脱下来,于是就坐在棉花原料上,垫着围裙吃起午饭,结果却被白小林罚站,不幸冻掉了一个小脚趾头。牟棉花不服,反问白小林自己受罚原因,白小林异常冷静甚至冷酷地告诉她:“你犯了两个错误。一、棉絮是原料。你坐着棉絮吃饭侵害原料,罚站两刻钟。而围裙是工作服。你吃饭时间不解围裙违反规定,罚站两刻钟。”那种冷静得近乎冷酷的声音仿佛不是从白小林的嘴里说出来的,而是从一台台轰鸣的机器中发出来的。这件事看起来是现代工厂管理的一种严谨态度,但其透露的无疑是现代工厂中严苛的工业秩序和机器理性,这种理性秩序迫使新工人牟棉花不得不重新打量她的工作环境,迫使她严正地理解她的工作。由此,牟棉花开始了现代工人的身份认同,开始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作认同。这种认同意味着现代工人对生存方式现代化的接受。所以,在牟棉花、王金炳以及王莹两代工人不断绵延的伦理意识中,都有对工厂的认同、对工人阶级以及劳模伦理的深切认同:“工作一天光荣一天”(当然,中华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和担当也是这种工作伦理和荣誉背后的重要动力)。
作为第一代工业工人,牟棉花、王金炳们身体力行这种工作认同。在纺织工厂晕倒、被送进疗养院一段时间之后,心急如焚的牟棉花曾对女儿王莹说:“妈妈要是不能重返工作岗位,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妈妈要是不能重返生产岗位,还不如死了。”于是在身体稍微恢复之后,牟棉花偷回工厂重返机台,结果再次晕倒,可见她对工作的痴迷。这种认同我们在小说中看到很多次,这是一种工人精神,也是一种工人工作伦理的自我表达。最后,当在疗养院住了多年、临近生命终点的牟棉花于回家前一天的晚上,王金炳在电话里和牟棉花约定:“咱们早睡早起,每天吃了早饭我蹬小三轮车拉着你,咱们不逛公园不逛商厦专门逛工厂,工厂才是最好景致呢!”这些都诗意化地表达了牟棉花们把工厂当作家,把劳动当作光荣、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而在经济转制过程中,许多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破产的时候,王莹的东方制冷厂也破产了。王金炳伤感地说,“工厂破产等于拔了工人的根,工人拔了根怎么活?”这其中,有着工人对工厂几乎全部的爱和归属与认同。
劳模第二代王莹的工人经历进一步阐释了工厂和工人的关系:“过午的阳光排进窗户,送来秋意。被称为‘裙子队’的简报员们换了白衬衣蓝裤子,走出车间走进科室,忙忙碌碌行走在厂道上。王莹由衷地认为工厂就是自己的家。工人离开工厂就会成为无枝可依的小鸟儿。”而王莹的妹妹王凤“自从成了成衣车间缝纫工,王凤欢欢喜喜。工厂多好啊。清晨上班把自己的饭盒放到蒸箱里去干活儿。中午打开蒸箱,一只只饭盒散发着各种各样的香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中有他,融洽极了。下班洗澡,赤身裸体站在热水喷头下,理直气壮地冲洗着。结伴乘坐公共汽车回家,一路乐乐呵呵使你觉得社会主义处处有亲人。当了工人,王凤终于体验到追求人生幸福的含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工人对工厂认同的真实再现。工厂与工人结合成生命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这种结合其实是在现代工业时期才会发生的故事。
然而,现代工厂工作伦理并非一成不变,它也会受到挑战、发生变化。这种挑战的内在原因则在于机器系统的技术更新。也就是说,“机器”作为一种秩序系统的内在变化对工人的人生价值和工作认同具有决定性的塑造作用,机器技术更新决定着工人的工作认同、工作感受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机器》中关于工厂以及劳动和劳模的价值塑造和诗意化书写之所以可能的第二个原因是:小说故事发生在非智能化机器时期,而智能化时期的工厂中,这种诗意化赋予和价值认同就很难实现。这就涉及到机器技术更新与工人生存情绪之间的复杂关系。
三、机器技术更新与工人生存情绪的呈现
科学技术的不断更新,直接反映在以现代机器为核心而组建起来的生产系统中。现代机器和生产系统经历了由低到高、由相对简单到复杂先进的发展变化,而且速度越来越快。这些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与机器一起协同工作的工人们的生理和心理状态。也就是说,人类在几次科技浪潮中对机器施与的影响直接反应在工人的生产感受上,而这又潜在地影响着工人的工作认同以及自我的价值认知。
工业机器早期发展阶段,机器设备对工人工作情绪的影响并不深入——人的机器化和物化程度不高。因为机器运转系统还比较粗糙,动作衔接慢,机器生产需要更多的人力的参与。在参与机器运转的过程中,人往往需要依靠自己的感觉实现与机器的合作,逐渐地,人的感觉也越来越精准细腻。也就是说,当机器处于非智能化或低智能化的系统状态时,人的参与性和主动性相对高。可见,早期机器某种程度上对人而言具有激发作用,给人带来创造性体验,因此给人带来兴奋感和成就感、满足感和愉悦感。对机器的这种感受在小说中最鲜明地体现在牟棉花们可以把机器上的工作变为艺术以及王建设对机器的迷恋和人们对技术的倾慕当中。如前所述,这是小说实现诗意化书写的第二个条件。
小说以令人激动的诗意化语言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代纺织工人把工作变成艺术的美好过程:在一次纺织行业比赛中,牟棉花们沉浸在纺织艺术中,先是无锡国棉一厂的纺织能手,人称“巧织手”:“望远镜里,牟棉花看着‘巧织手’灵活的手指,好像不停翻飞的玉色蝴蝶,精巧轻盈,妙在其中。”当上海选手许金娣上场时,“她巡回看车,步履轻盈;她换梭装纬,姿态优美;她查看布面,身段潇洒;果然拥有‘挡车芭蕾舞’的艺术魅力。牟棉花情不自禁叫了一声好,差点儿欢呼起来。许金娣的操作真美啊,一台台高速织机化作一件件舞台道具,一个挡车女工竟然把这种又苦又累的机器操作变成一种又轻又柔的艺术表演,令人心悦诚服。牟棉花紧紧握着望远镜,忘了肚子里的孩子忘了自己是参赛选手,完全沉浸在‘挡车芭蕾舞’的艺术享受之中,久久不能自拔。”这段诗意化的叙事为现代工人的劳动赋予光环,而工作艺术化的过程则为现代意义上的工作赋予了一种内在意义:“它关注工作过程本身的手工艺技能——体力和脑力的运用”,现代工人“从工作本身而不是从其他不相干的领域或后果中寻找工作的原因。给人们带来满足的不是收入、不是解脱之途、不是地位、也不是凌驾他人之上的权力,而是技术过程本身。”同样,王建设从小就是一个机器迷,喜欢对各种大大小小的机器进行拆卸组装,参加工作后更是如痴如迷,开始“与机器的恋爱。”
以上情况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机器》中第一代工人牟棉花和第二代工人王莹以及王建设等所处的时代都是机器水平还相对较低的时代。查阅现代纺织业历史,我们知道,牟棉花们纺织使用的织布机应该是日本小岛家族织机换代之前的第一代织布机。日本第一代织机要追溯到“日本的发明王”、出生于1867年的丰田佐吉,他的一生可以说就是日本近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佐吉一生中最重要的、堪称是划时代的发明,是他在1896年完成的“丰田式汽动织机”。他发明的这台织机不仅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台不依靠人力的自动织机,而且与以往织机不同的,是可以由一名挡车工同时照看3至4台机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从时间推算,白小林深入研究的、牟棉花拼死进入其中的东洋纱厂使用的应该就是丰田佐吉发明的第一代织机。后来,小说告诉我们王莹刚参加工作的那一年——“我国第一台具有先进水平的韶山型大功率半导体干线动力机车在湖南株洲机车车辆厂试制成功”,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的线索。据中国韶山型电力机车发展史料,这一年是1958年。而这种机车在今天早就被淘汰了。这些背景信息告诉我们,小说中两代工人人生故事发生的主要年代是机器处于低智能化时期,而这才真正能够解释为什么牟棉花可以把机器生产艺术化,以及王建设为何可以在拆卸机器时那么入迷。换句话说,将工作艺术化,以及由之而为工作赋予内在的神圣化意义是有条件的,即机器的低/非智能化限制。
这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牟棉花们的纺织艺术以及王建设面对机器时候的兴奋感必然在科技浪潮的更迭中被超越,这一点白小林最清楚。如果说,牟棉花代表了小说诗意化赋予的叙事视角,那么白小林就始终代表着理性客观的非诗意化叙事视角,构成牟棉花叙事立场的一个对位。通过白小林,肖克凡在《机器》中有两次涉及到科技浪潮对生产过程的影响问题:一次是在纺织业技术比赛中,一次是在牟棉花回国后的家庭聚会中。
第一次,当纺织女工牟棉花参加比赛并沉浸在“挡车芭蕾舞”中的时候,白小林就向牟棉花传来一张纸条告诉她:“应当清醒,日本纺织业即将使用第二代织机了。”也就是说,机器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的(这证实了我们前面关于第一代织机的推测)。最初,牟棉花并不明白这意味着她沉浸在纺织艺术中的这种满足感和兴奋感不会一直延续下去。当机器的发展越来越快,机器运转的速度越来越快,工人的操作动作也必然要越来越快。这时候机器对人的逼迫就越来越明显,这就是现今机器高速度工作节拍对人的逼迫。对于这一点,后来的牟棉花已经有所体会。成为纺织行业劳模之后,牟棉花兢兢业业,不敢有半点含糊,生怕有人打破她创造的接线头记录,因此也极度疲惫。一天深夜加班回家的牟棉花一身疲倦地对丈夫说:“金炳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这样累吗?布厂织机实现高速化,从180转增到230转了。我呢,还要求扩台!速度越高我越扩台,从看九台车扩到看十八台车,这样产量提高百分之百呢!”这是牟棉花在机器全面高速化之前的最后一搏,事实证明,机器的更新换代是不会等待人的能力的提升,最后到王凤时代,织机已经换代,再不需要“牟棉花工作法”了。
第二次,在牟棉花从阿富汗回来之后的家庭聚会中,白小林也来了。他又一次不合时宜地告诉牟棉花:“日本工业的更新速度很快。据说我们国家也将更新织机。那么挡车技术指标全变了,接头速度失去可比性。就好比一辆马车创造的速度是不能拿一辆汽车相比的。你创造的接头记录成了历史,永远陈列在光荣榜上。……你总结创造的‘牟棉花工作法’也没了用场。织机提速,节奏动作全变了……”这无疑是告诉大家尤其是牟棉花:机器更替使传统的劳模变得不再可能。而当时,孩子们担心牟棉花受打击故意转换话题。后来我们看到,常住疗养院的牟棉花直至去世前一直都在做布鞋,她说是为了练习牟棉花纺织接头法。从诗意化叙事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令人动容的生命精神和劳动价值的高度体现,然而,从冷静而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何尝不是一种无知和可悲。
但是,白小林的两次提醒都被强大的工作精神和高尚的工人情感所遮蔽。这表明,尽管有白小林这一理性的非诗意化视角存在,但整部小说不可避免地在诗意化书写的进程中行进。这使得无论叙事还是小说人物都在面对人与机器之间关系的问题上罩上一层面纱,很难触及二者关系的现实痛点。这个痛点便是,在高智能化的机器系统下,无论是生产工人的价值体认还是工业写作的诗意赋予,都将面临危机和困境。小说《机器》并没有直面这个难题。这一方面表现在小说始终在较为单一的诗意化叙事线索上行进,并没有充分发展白小林的理性化线索。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小说中第三代工人故事的缺席(王莹的儿子和王凤的儿子是工人后代,但他们的人生已经开始有了别的选择——王莹的儿子是个网络游戏高手)。然而,中国的工业化现实回避不了这个问题。从中国工业化腹体中生长出来的、当代农民工诗人的声音正好可以让我们在延伸的视角中探讨被小说回避的现实问题。
四、农民工诗人诗歌写作——《机器》叙事的补充
今天,当我们走进更加现代化的工厂,一条条高度智能化的生产线便会展现在眼前,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站在生产线后面的当代工人,正在新的工业环境中体会人与机器的对立关系。在当代工人的生存情绪和工作伦理中,我们已经很难看到牟棉花时代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的光环,以及那些崇高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认同。他们已经不是牟棉花时代的工人,他们的生产环境也与当时大相径庭,但有一点,他们与牟棉花们一样,都是依靠机器环境劳作求生存的人,所以,从身份连带的关系上,他们可以被认为是小说《机器》中没有展现的第三代工人群体。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生命故事很少被今天的文学写作所关注,但是,当代农民工诗人的诗歌却让我们听到了生产线工人生命内在的真实声音。他们的故事和书写恰好可以作为《机器》的延伸,让我们完成对《机器》的阅读。 当代农民工诗人几乎都是生产线工人或者曾经从事过生产线生产,他们有矿井机电检修工,有服装厂工人,有电子车间工人。在他们的诗歌中,我们看到高智能机器环境下工人生存的现实。苏北工人绳子在《工厂啊工厂》中表达了与牟棉花们心目中完全不同的工厂形象和工厂经验:“天天在其中行走因此 会变得麻木和迟钝……你最好收拾好自己最好忘了你自己是谁。”在这里,工人已经难以形成与工厂之间的内在认同。在郑小琼的诗作中,随处可见的是她对工厂以及机器生产线的异议:“我说着这些多刺的油腻的语言铸铁——沉默的工人的语言……疼痛的 饥饿的语言 机台上轰鸣着的欠薪 职业病断指的语言 生活的底座的语言 在失业的暗处……正如年轻女工无助的眼神或者厂门口工伤的男工他们疼痛的语言颤栗的身体的语言……”这里已经没有了把工作艺术化的工作体验和可能。
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当代工人所面对的机器的高智能性。因为,智能化机器时代,自动化程序为机器设备增加了本来没有的柔性和思维,机器具有越来越高的人性化,即机器具有了高度思维性和感觉性等人性特质,能完成更精密细微的高难度工作。机器替代人的部分越来越多,随之,人的参与性就变得非常低而有限,工人劳动日益被简化为单调和乏味的简单动作。而且,随着机器节拍的精准和高速,人的工作节拍也被要求不断提速。这时,人只能感受到高速机器的催促和追赶,感受到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的被机器驾驭的附属感。所以,高度智能化的生产线上的工人,既很难有崇高的工作认同,也很难能够从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获得满足感。并且,现代生产车间的条件管控也越来越严苛,往往是恒温恒湿的隔绝自然的人工环境,由于严格的防尘绝缘要求,在一些特殊生产企业的精密生产线上,工人工作往往需要穿戴静电衣帽等。当工作者的身体被理性一致地管理甚至被强行一致地包裹时,工作者作为“人”的独一性和整体性也被取消了:车间里,只有认不出谁是谁的工人,而没有“这一个”。许立志的诗歌《流水线上的雕塑》以及《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都表达了在生产线上劳作时候的生命感受。这种感受似乎表达了另一种工作哲学:“获得或保有一份工作不再是一种挑战,而是一种无奈。”爱迪生曾经说:“地球上的一切工具和机器,不过是人肢体的知觉的发展而已。”这句名言用在早期机器时代或许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智能化机器时代,在机器与人之间关系发生逆转的情境下,这种判断显然不准确。
当然,农民工诗人的生存情绪之所以与小说《机器》所展现的上世纪50年代到八九十年代中、工人高扬的主人翁意识和集体情感相距甚远,除了机器的智能化发展这一重要因素之外,还与另一个因素有关系,就是经济体制的转换。当代的工人已经不像传统工人那样属于国家职工,有终身制的荣耀,他们是合同工,而不是工厂集体的主人,都是工厂的过客。这种工作关系的不确定性使得当代工人既获得了无限的机遇,但也增加了生存的漂泊感,以及身份认同的焦虑感。
所以,如何安慰当代工人漂泊的灵魂,是全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文学写作无疑是这一关怀中最为生动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认为工业题材的写作依然有价值,应当在时代历史中前进,并且认为文学创作者应该去“注视”这一部分被忘记和旁置的后工业生产的“承受者”,我们则需要自问: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工业建设中所展现出来的、拼搏忍耐的奉献的工人精神如何激励智能程序控制下的现代生产线工人,如何救赎他们被奴役的精神和灵魂,如何为他们提供文学应当有的道德关怀,如何在想象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与他们站在一起?工业题材的小说家们该以怎样的目光打量和描述今非昔比的工业生产线上的劳作者,并对他们的生存作出真正具有关怀性的理解和关注?这是当下时代中工业体裁写作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
从大的背景来看,兴盛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工业题材写作在绵延至21世纪最初几年之后有所萎缩(其间自然有多种复杂的原因)。但是在人工智能几乎弥散到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的时候,工业题材的写作恰恰可以在这个关联的领域中开拓出新的视点和可能。因为,文学的使命既面向社会也最终归向自身。与工业机器进化相关联的人工智能问题已经是闯进人类面前的越来越重要的生活现实,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对人类未来的命运究竟喻示着什么,这其实是个未知数。无论是人工智能被人类驾驭着帮助人类奔向更高的文明,还是人在很大程度上被人工智能所取代,都势必使得人和人工智能关系即人机关系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人类可能从来没有像这时那么在乎对人工智能和人自己进行伦理的反制和预设,从而达到人机关系的平衡。未来的工业文学将表现的是人机同场互动的奇异场面(或就是平常场面),作家还将不断地强化着人(包括工人)的主体意识和价值引导,作品甚至还将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色彩。兴许,一个全新的工业文学将走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