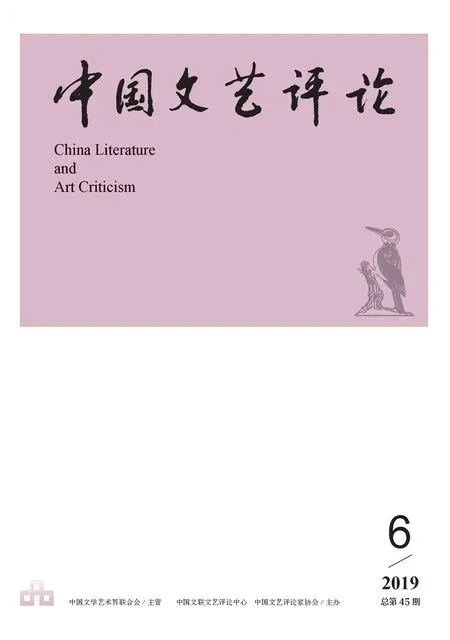论纪录剧情片对“虚实”的跨界与坚守
牛光夏 成亚生
纪录剧情片(Docudrama)作为纪录片和剧情片的混合体,是一种打破边界、虚实相生的影视艺术形式。美国电影理论家简妮特•斯泰格对它进行了具体描述:“纪录剧情片,就如同它的名字所表示的那样,是一种将‘纪录片’与‘情节剧’混合在一起的再现模式……‘纪录剧情片’大多采用主流电影和电视中的标准戏剧模式用以完整地再现历史”。德国纪录片界更是对纪录剧情片提出了两项重要评判标准:“一方面,作品要有很好的事实基础、采访跟进以及史料调查;另一方面,要有高质量的表演水平,情景再现必须达到能够在电影院播出的级别”。相较于常规意义上的纪录片,纪录剧情片中的戏剧因素和虚构成分都有增加,它用讲故事的方式对来自真实生活的原始素材进行艺术化的处理,使其矛盾冲突更为集中和紧凑,从而拓展了纪实性语言之外的可能空间。本文从纪录剧情片的历史渊源入手,旨在廓清它的外部特征和内在结构,并就纪实性坚守与故事化表达的具体呈现及二者彼此融合的运作策略进行探讨与分析。
一、纪录剧情片的外延突破与叙事结构
在纪录片的发展史上,纪录剧情片中标志性的人物扮演、情景重现等创作手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弗拉哈迪时期,他的影片从“一开始就体现出了在纪实与虚构之间的创作理念,它具有了故事性、情节性和抒情性”。在其经典之作《北方的纳努克》(1922)中,弗拉哈迪就对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习性进行了建立在真实基础之上的叙事化处理,如让他们演绎祖辈用渔叉猎杀海象和海豹的场景,为了采光在削去一半的冰屋中摄取纳努克一家表演起床的镜头。20世纪30年代,约翰•格里尔逊首先提出“纪录片(Documentary)”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他所领导的英国纪录片学派遵循这一理念,部分影片对现实的处理采用了搬演、再现、重构等故事片的手段,如《漂网渔船》(1929)中,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不可能用水下摄影完成的海中鱼群段落,被猜测是在水族馆之类的场所摄制而成;《夜邮》(1936)则将火车车厢拉到摄影棚,打灯布光后拍摄了分拣邮件的段落。由此可见,在纪录片的发轫之初,它与剧情片的界限就是含混不清、极具模糊性的。
这种模糊性在1980年代末出现的主张“虚构”的新纪录电影中被进一步放大。此时兴起的“新纪录片已经在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归复到当初没有太多拘束的起点,戏剧化、表演乃至其他形式的虚构和故事化再一次占据了优势位置”。它们不再一味苛求比尔•尼科尔斯所谓的“严肃话语”,而是以拍摄故事片的规则和标准来要求自己,运用情节剧式的创作手法对部分假定情境进行风格化的搬演和再现,如《浩劫》(1985)、《细细的蓝线》(1988)、《罗杰与我》(1989)、《超码的我》(2004)、《生于妓院》(2004)。在此发展语境下,表述行为型纪录片、第一人称纪录片、自我治疗纪录片、动画纪录片等亚类型纪录片陆续登上历史舞台,当然也包括纪录剧情片这一融合纪录片与剧情片、真实与虚构、纪实与表演的新型影视艺术品类。出现了英国BBC的《失落的文明》(2002)、《诺亚方舟》(2003)、《失落的古城市》(2006)、《古罗马——一个帝国的兴起与衰亡》(2006)、《关塔纳摩之路》(2007),美国的《标准流程》(2008),德国的《出于对德国的爱——捐赠丑闻》(2003)、《大洪水之夜》(2005)、《施佩尔和希特勒》(2005)等代表性作品。这些片子在取材自真实事件、尽可能完整复现历史的基础上,通过穿插剧情再现、演员扮演、场景重构等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化形式,将事件过程与人物关系图谱更加紧凑而鲜活地呈现出来,增强了作品本身的可看程度与趣味性。
从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进程来看,自改革开放前注重宣传报道与国家话语传递的政治化纪录片时期起,到改革开放后至1990年代初确立人文观念、宣扬民族精神的人文化纪录片时期,再到1990年代中后期尊奉纪实理念和百姓意识的平民化纪录片时期,故事化的创作技巧一直都处于边缘位置。但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各类平民选秀节目、明星真人秀、快节奏情节剧等极具狂欢性质的电视产品充斥于屏幕并具备较高收视率的泛娱乐化时代背景下,纪录片这种单纯讲求纪实、复现日常生活的影视艺术形式显然不占优势,进行故事性创新已如箭在弦上。于是在西方纪录片创作理念的影响下,《复活的军团》(2004)、《故宫》(2005)、《圆明园》(2006)、《大明宫》(2009)、《外滩佚事》(2010)、《迷途》(2010)、《大案终结者》(2013)、《旋风九日》(2015)、《河西走廊》(2015)、《家道颖颖》(2019)等一批采用搬演、真实再现、三维动画等虚构性手法以突破传统题材样式视听语言局限的纪录剧情片陆续出现,并由于具备引人入胜的戏剧冲突、扣人心弦的悬念设置、多线叙事的故事情节等娱乐化因素而受到观众的欢迎和市场的青睐。如系列片《家道颖颖》第一部《回家》,围绕开往青桫镇的绿皮小火车上发生的故事,聚焦古镇改造、城乡贫富差距、代际隔阂等转型期中国较具普遍性的现实问题,在现代工业文明与团结友爱、邻里互助、心系集体等中华传统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中彰显人性的真善美。与传统纪录片不同的是,在《回家》中观众可以在剧中看到跌宕起伏的剧情内容、撩人心弦的悬念设定及个性鲜明的角色形象等故事片常用的叙事手段。兼具纪录片和剧情片的特性与优势,使《回家》一经推出实时收视率达0.8%。
二、本体属性——纪实性与内在真实的统一
19世纪20年代,被萨杜尔称为“第三先锋派”的城市交响乐电影悄然盛行于欧洲各国,它们反对纪录片的故事化创作趋向,提出了“非戏剧化”“非情节化”等观念和主张,认为构成纪录片的关键要素是“纯粹的运动”“纯粹的节奏”和“纯粹的形式”,并促成了《柏林——大都市交响曲》(1927)、《桥》(1928)、《雨》(1929)等诗意型纪录片。而在形态和手法多元化、观众细分化的现代纪录片创作中,这种非戏剧化叙事的理念已不再适用,但其所秉持的记录现实生活、还原日常面貌的纪实性内核,仍应是当前纪录片严格坚守的价值底线,当中也包括纪录剧情片。
首先是通过对真实人物的访谈以弥补部分内容的缺失、推动情节发展,亦有助于强化片子的客观性、真实性和现场感。而且借助对普通人的采访及他们真情流露的口述,更能引起观众的文化共鸣和情感共通。在《回家》的片头与片尾就穿插了对K422次列车长蔡明华、K165次列车长王巧芬、医护人员史明洁等人的访谈。他们声情并茂、绘声绘色地对自己所经历的真实事件进行描述和回顾,使观众身临其境般重新体验事发当时的危急与紧张。而贾樟柯导演的《二十四城记》(2008)则通过对国营420厂工人大丽、小花、宋卫东等的口述访谈,展露出在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普通工人的生活环境和心理状态的变化。其中由专业演员所扮演的部分采访对象均有真实人物原型,他们朴实自然的表演辅之固定长镜头、黑场过渡、巡礼式空镜等纪实性语言,使得影片极具纪实感和生活气息。德国导演雷蒙德•莱就提倡纪录剧情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是采访,必须在采访的基础上发展剧情故事”。美国新纪录电影的代表性导演埃罗尔•莫里斯更是将采访视作他制作电影时必不可少的手段,认为采访是“让我的纪录片之所以成为纪录片的原因之一。那是一种属于现实的元素”。在其代表作《细细的蓝线》中,借助剧情片的叙事策略和戏剧化的视听语言来采访嫌疑人、警察、证人、法官等不同对象,构成了一种“罗生门”式的叙事结构,打破了纪录片和剧情片之间的壁垒。其次,利用相关文献资料、历史影像等纪实手段也是加强纪录剧情片真实感和权威性的一种上佳谋略。导演周兵曾摄制了《梅兰芳1930》《敦煌》《外滩》等剧情性较强的纪录片,他所坚持的创作宗旨就是“在文献上对历史的忠实和在活动影像(含声音)上对历史的虚拟”。
正所谓“见微知著、以小显大”,纪录剧情片在叙事过程中还注重通过生动传神、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来彰显自身的纪实性和真实感。且由于需要对过去事件进行再现处理,重建细节也是纪录剧情片不可避免的重要问题。细节即是全片的“情节点”和“亮点”,有助于刻画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心理、推进情节发展和升华作品主题。如《迷途》中,全国解放后潜伏在内地已达八年之久的国民党高级特务郑蕴侠,在参加工厂召开的控诉大会时满脸虚汗、精神恍惚,且在回答问题时脱口而出“有”这一国民党军人惯用语的细节,就真实体现出他因害怕被发现真实身份时的紧张心情,也为之后他趁慌乱连夜逃跑的情节做好了铺垫。然而“模仿性叙述注重再现真实人生,讲究细节逼真,但也会因为拘泥于真实细节而流于琐碎”。纪录剧情片在构建细节时,既需要依托有据可查的历史事件与场景片段,也需要制作人在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创作原则的基础上,以情节发展的客观需要为前提发挥一定的艺术想象,通过合情合理的细节刻画展现震撼人心的画面表现力和情绪感染力。
作为文化融合、媒介融合语境下出现的一种把真实与虚构相融合的片种,纪录剧情片在坚守纪实性内核的基础上,运用搬演、重构、再现等剧情片的故事化手段是一种顺应国际纪录片领域发展趋向的创作策略。因为“受国际纪录片界创作趋势的影响,剧情化风格和工业化制作逐步成为主流媒体的创作手法和趋势。”20世纪90年代初,以美国所谓的直接电影风格为指向标的纪实美学在中国盛行一时,在其熏陶下出现了关注社会边缘人物的新纪录片运动,他们的片子采取不介入、不干涉拍摄对象和拍摄环境的制作方式。这种影片常常浮于表面记录,缺乏深度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实际上,纪录片的创作不是一味地为纪实而纪实,更不是简单复制现实,而是通过描绘现实去体悟事件背后具备生命力的人性关怀。
对内在真实或艺术真实的追求应是任何艺术作品的终极目标,创作者按照符合生活内在逻辑、彰显生活本质同时又具有审美价值的原则,对来自于直接或间接经验的生活真实进行筛选,重新组合和结构。纪录剧情片以纪实性和内在真实的统一为其本体属性,它不完全照搬自然流动进程中的生活现象,而是在创作前期深入生活进行素材的捕捉、收集和观察,创作中通过演员贴近生活的扮演、对真实事件和具体场景的再现等手法触达内在真实,以富有创造性的表现形式来反映社会现实。
三、框架建构——故事化与戏剧化的再现
故事性的建构方式贯穿纪录片的发展始终,不论是《北方的纳努克》所采用的引发悬念的手法,还是《持摄影机的人》《柏林——大都市交响曲》等城市交响乐纪录片以一天为时间线的记叙模式,乃至德鲁小组的直接电影擅用的“危机结构”的框架,更不用说以“纪录片可以而且应该采用一切虚构手段与策略以达到真实”为创作理念的西方新纪录电影。而随着科技手段和纪录片类型形式的日新月异,作为新兴品类的纪录剧情片便兼收并蓄了前者的特点和自身的创新,囊括了诸如搬演、真实再现、悬念设定、非线性叙事、背景音乐、情感化的叙述方式等剧情片中的元素。
以演员扮演、搬演为主的“真实再现”可谓是纪录剧情片在构建叙事框架中所必不可少的一种艺术手法,尤其是对过去真实事件和历史片段的情景重现,它是“一种虚构的、类似影视剧中的扮演的方式,对时过境迁的重要情节进行扮演,或者运用光影、声效、造型,再现特定历史性时刻的情况”。作为一种从虚构类作品中借鉴过来的叙事技巧,真实再现丰富了纪录片的表现形态,增强了趣味性和视听感。如《大明宫》运用搬演、3D特效等手段再现了建造大明宫的情景,将这一巍峨壮观的古代宫殿群落真实直观地展现在观众眼前。《河西走廊》则以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10个重要时间节点为叙事中心,在历史资料相对缺失的情况下,借助演员搬演、情景重构的方式带领观众领略了河西走廊从汉代至今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和文化演进,再现了诸如张骞出使西域、发现玉门油田等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塑造了鲜活真实的历史人物。这种再现方式摆脱了传统历史文化类纪录片为了解读历史而一味地采用文献、历史图片、口述等固有模式的束缚,不仅拓展了影像表达空间而承载更多内容,也使其更加生动形象和耐人寻味。但是它必须遵循的原则是:“‘再现’的东西必须以‘真实’为前提,不能虚构……还有就是再现得像不像、巧妙不巧妙。如果使用不当,劳民伤财不说,对作品来说也是大煞风景、弄巧成拙”。
悬念设置是纪录剧情片在故事编排和节奏把握上的重要手段,由悬念产生的悬而未决感、疑惑感及未知感也是纪录剧情片能够把故事讲得精彩曲折、引人入胜的关键要素。讲述邓小平1979年访美期间所发生的故事影片《旋风九日》就借用了惊悚悬疑片中常见的叙事技法如手持摄影、粗粝画质、快节奏动镜来结构影片,尤其是邓小平在美国险遭遇刺那一段落,配以声效、光影的渲染和动画形式的部分还原,充分营造了当时惊险紧张的悬念氛围。此外,对于人物在危急关头因恐惧、担忧、欲望等本能反应而做出的选择与行动的伦理考验更是成为悬念设置的基本内容。如《回家》中最大的悬念就是春燕能不能顺利产子、火车上的一众乘客能不能按时归家过年。解决这两大问题要面临一系列接踵而至的困难和抉择,此时对片中主要人物及其他乘客的人性和伦理道德的考验就成为吸引观众继续收看、紧扣观众心弦的一把利器。
与此同时,纪录剧情片不同于一般纪录片单一的线性叙事,多采用故事片常见的多线叙事或传记式叙事模式。在《回家》中有两条明显并置的情节线,一条是小火车上归心似箭返乡过年的青壮年乘客,另一条是古镇上匆忙准备着百家宴、等待家人归来的妇孺老人。片子通过交叉蒙太奇使两条明线同时展开、时有交集。此外,还有些许暗线穿插始终,如充满误解、心生嫌隙的廖家父子和林家母女的和解;即将退休的火车司机刘承光与自己的职业旅程及工作伙伴——绿皮小火车的告别;替地产开发商牵线搭桥的谢家盟反省悔悟、意识到“亲情重于金钱”的觉醒。而《外滩佚事》则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用人物传记的故事体记录历史,并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向观众讲述赫德、叶澄衷、杜月笙、周璇、李香兰等人在1843年至1945年间发生的传奇故事。其中,将外滩拟人化的处理不仅把上海滩的视觉形象塑造得更加真实立体,也更易于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和思绪认同。
由于具备故事化、戏剧化、表演性较强的特质,纪录剧情片在演绎较为敏感或重要的历史事件、领袖人物和政治议题时的发挥空间及可操作性更大,它在复现这些人物和事件的过程中,往往采用搬演、采访、字幕、特技等手法使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产生一种“间离感”和陌生化效果,即不再单纯地陷于类似直接电影所呈现的表象真实之中,而是充分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想象代入,并冷静、理智地分析片中事件的虚实性。如《外滩佚事》就借助黑白和彩色的画面来区分历史与现实,使观众清楚明了影片中的虚构情节和表演成分,而不至于迷失对真相的探索。
四、运作机制——边界的“融合”与底线的坚守
作为一种交叉性、跨媒介艺术品类,纪录剧情片在坚守纪录片的客观真实和进行剧情片的艺术虚构时,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使两者有效地融合为一,同时又要坚守住“真实”这一底线。在迈克•雷诺夫看来,“纪录片与剧情片之间远非壁垒森严,不通骑驿。恰恰相反,二者不仅在形式技巧上难分彼此,在表达机制上也本无不同”。即它们并非是两个完全泾渭分明、毫无关联的存在体,而是“深陷彼此”,于叙事方式、修辞技巧、视听语言等方面都有许多相似之处,如都具有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基本叙事结构,及伏笔、冲突、重复、长镜头、蒙太奇等表现手段。此外,纪录片和剧情片的主题与核心都是“人”,都通过展现人的生存状态、精神世界、命运发展及文化积淀来向观众传递某种信息、理念及价值观。这些外在表征和内在结构上的相似相通也为纪录片与剧情片的互相借鉴、融合渗透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纵观电影发展的历史进程,纪录片与剧情片成功融合的一个著名流派就是20世纪中叶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将叙事性与卢米埃尔影片的纯纪录性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有着持久意义的电影风格”。如罗西里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德•桑蒂斯的《罗马11时》、德•西卡的《偷自行车的人》都借用非职业演员、实景拍摄、自然光效、固定长镜头等纪实手法讲述了一个个映射时代、发人深省的精彩故事。此外,剧情片和纪录片界限逐渐模糊的趋势也可从导演或制作者的身份转变上窥见一斑。如“新德国电影四杰”之一的沃纳•赫尔佐格提出了“诗意地凝视”的纪实理念,并拍摄了《灰熊人》《白钻石》等纪录片;詹姆斯•卡梅隆在《泰坦尼克号》上获得巨大成功后着手进行关于海底世界的高成本纪录片《重返俾斯麦战舰》《深渊幽灵》《深海异形》等的拍摄;制作了《X射线》《守望者的观点》等纪实影片的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也开始拍摄剧情片;伊朗导演阿巴斯则将固定长镜头、静观式记录方式等纪实美学手段嵌入其剧情片《面包与小巷》《特写》中;贾樟柯也在摄制了一系列剧情片后拍摄了《东》《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等带有一定剧情色彩的纪录片。他们将剧情片的常用艺术手法运用于纪录片的制作中,又将纪录片的纪实美学渗透进剧情片的具体运作中,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两者的融合与发展,也为新世纪初纪录剧情片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纪录片与剧情片跨界融合的内在实质是真实与虚构的相融相通、并存共生,真实和虚构“如同分别朝着地球的南北极航行的两艘航船,在到达极点后开始贯穿两极,朝着各自方向演进的纪录片与故事片开始出现合流趋势”。这也是纪录剧情片需要面对和处理的基本问题。作为纪录片在文化融合、审美多元化时代衍生出的新形式,纪录剧情片并不追求极致真实,而是大量运用搬演、再现等虚构性手法进行叙事,甚至于其故事化外延在视听感受上要重于纪实性内涵。但区别于完全建立在虚构基础之上、极具后现代色彩和娱乐属性的“伪纪录片”(Mockumentary),纪录剧情片仍会借助取材自真实事件的情节、社会演员的加入及人物采访、影像资料等纪实手段的有效运用来坚守传统纪录片的真实底线和纪实原则。这种坚守基于对纪实精神的秉持和对情节创制、演员表演的良好平衡,优秀的纪录剧情片要以“很好的事实基础、采访跟进以及史料调查”“必须审慎而真诚地展开采访与设计剧情”为保证,并进行多次回访和核实,使编写的剧情忠于事实,与生活自身的发展逻辑相吻合,以此来提高影片的真实质感和可信度。
五、结语
随着纪录片市场化、产业化及观众收视需求的多样化、个性化程度日益加深,传统纪录片需要不断做出改变和调整以顺应时代发展的走向。不同风格和类型多元化共存与共荣的格局,是中国纪录片必然的发展之路。不论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望长城》一改之前主题先行的专题片特征,确立以纪实理念为主题风格的突破;还是《生活空间》将电视纪录片栏目化,并提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口号标语的尝试,都拓宽了纪录片的生存空间和领域。20世纪末21世纪初兴起的融纪录片与剧情片于一体的纪录剧情片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纪录片的外延。不同于追求“未经操控的现实”的直接电影和排斥剧本、演员等虚构元素的真实电影,更与纯粹“画面+解说”的格里尔逊式纪录片大相径庭,纪录剧情片既坚守了传统纪录片的纪实性内核,又进行了故事化的创造性表达。它不复是“现实的搬运工”,而是藉由职业演员或社会演员的搬演再现及其他故事片的艺术手法来代替自然主义、形式主义的刻板记录,超越了一般纪录片的表象真实。尽管近些年“纪录片的春天来了”的欢呼常有耳闻,但不容回避的是,长期以来纪录片在传媒市场中处于受众面小、“缺席的在场”的尴尬境地,在当前竞争激烈的传媒生态环境下,纪录剧情片这种于虚实之间跨越彼此边界的融合与坚守,相较于纯粹纪实的纪录形态而言,从受众接受心理层面更符合人类爱听故事的天性,是亲近更多观众、赢得更大市场的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