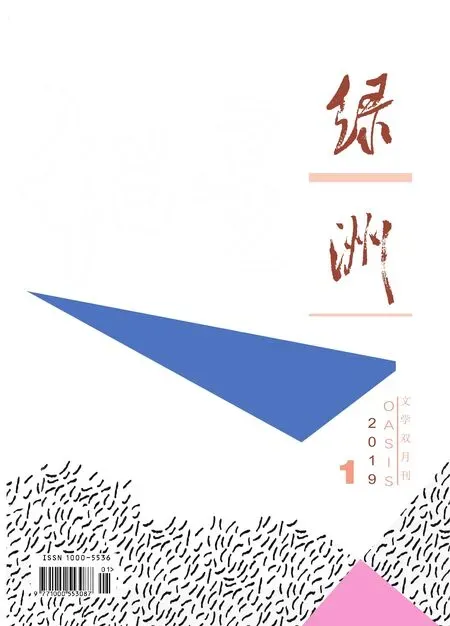翔鸣兄弟,一路走好
李金昌
昨天刚飞到西安,忙于筹划集团公司设在曲江南湖边上的陕甘运营中心的开办事项,突然接到好友原新疆作协常务副主席赵光鸣先生的电话,说虞翔鸣先生走了!顿时,我感觉呼吸几乎停止、大脑一片空白……
我与翔鸣结识于三十年前,即1988年初春,当时我在哈密兴办了砖厂,生意十分红火,里里外外忙得团团转,上午签合同卖砖,下午骑着摩托车去工地收款,中午走到哪里随便吃个炒面什么的,天黑才能回家。那天回家时,看见一个陌生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他起身同我打招呼并介绍说自己是兵团绿洲杂志社记者,叫虞翔鸣,专程从乌鲁木齐坐火车来找我,想了解一下个体户的事。聊起来才知,他上午十一点就到了,那时还没手机之类的通讯方式,就一直等到了天黑。他说已和我的夫人拉了半天家常,对我经营个体砖厂的一些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后来我们边吃饭边聊,他年长我一岁,也坦诚地说了一些自己的家庭情况。我们两人都是地富子女,非常时期在老家受尽歧视,万般无奈当盲流进的新疆,命运相似谈起来便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于是越聊越投机。好在他还有哥哥与二姐早前进疆也在兵团有工作了。那时关内到处不收人,我听人说新疆能吃饱,便逃荒要饭一路往西,经过四十多天才落脚到新疆哈密了。晚上我们俩睡一个大床,好像有说不完的话,几乎说到了天亮。第二天上午,他便坐火车回乌鲁木齐了。
不久,他在《天山》杂志上发表了报告文学《砖比血还红》的长篇文章,我拿到杂志反复看了无数遍,他把我想说又不敢说的,把我埋在心里的痛苦及遇到的心酸事全部写出来了。我打内心对他的文采及记忆力佩服得五体投地。那时节没有录音设备,他当时拉家常也没有用笔记,竟然把我回家的途径、泾河流经的走向,特别是把我老家的村庄大寺坳村黑山李家也一字不落完全记在了心里并写了出来,尤其我小时挨饿的种种细节也写出来了,比如“我上初中时父亲咬在嘴里嚼了一会的馍吐出来让我又吃掉了”。不光我看到流泪,很多读者特别是六十年代受过饥饿的人看到都会感动不已。
第二年,我离开新疆前在乌鲁木齐又见了他,我把上次见面后的经历及经营受阻不得不回老家的事又告诉了他。他接着又写了《砖和血一样红》的续篇。他的这个报告文学系列,在当时引发了舆论大喧,很多报纸以“改革开放的能人被逼离新疆”为题进行了报道。根据他的两篇报告文学,新华社记者兰学毅写了长篇通讯《砖王沉浮记》,引起了全国媒体关注。《中国建材报》记者张红在《中国建材报》头版头条一连发了十几篇关于我的报道,部分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栏目选播,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震动。改革受到阻力、个体户受到打击,无数人发声。迫于形势,兵团派工作组到原籍接我回疆,给新疆挽回影响。当时的兵团政委郭刚亲自接见并征求我的想法,当听到家已搬回老家女儿高考耽误后,破格特批女儿在兵团财经学院上学,兵团纪委将我所在的团场的场长免职、政委撤职。之后,我又一次见到了翔鸣先生。他说没人再敢给你经营设置障碍了,你还是回哈密吧,我因太过伤心,砖厂也捐给了国家,便执意回了原籍。
五年后,女儿大学毕业分配在乌鲁木齐工作,一个女孩子独身在新疆,我们老两口不放心便回来租房陪伴女儿。那时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已传遍全国,八级累进所得税制已取消,后来,我又放胆在乌鲁木齐搞了房地产开发,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企业已发展成跨新甘陕三省区经营、资产数十亿、员工上千名的集团化民营企业。这期间我和翔鸣一直在交往,他时不时还以我为题用舆论给我打气,并经常在一些场合向媒体朋友们介绍,说我是赚钱的“魔术师”!并暗暗收集我经营及生活的各种素材,在2012年他写出了近四十万字的纪实文学《并非一个人的背影——李金昌传》,真实记录了我的大半生艰难经历,也是中国近半个多世纪社会生活的缩影,引起了新疆文坛的一片赞誉。新疆文联、新疆作家协会专门举办了作品发布会,国内文学界一些大家也发表了评论文章给予了极高评价。后来,他又去了我在咸阳投资的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进行了实地调研,前年还和赵光鸣副主席去我平凉兴建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以及我出生的村庄——泾川县高平镇大寺坳村黑山李家调研,顺道游览了国家旅游名胜崆峒山,当时的精神状态十分好!
我们两人性格都不张扬,也都不善言辞,旁人看来我们是一般朋友,其实我们亲如兄弟。在乌鲁木齐三十多年的交往中,我们每年总会有几次聚会,每个礼拜都会打电话,凡家里重要事项都互相诉说,征求解决方法。每当个人住院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对方。我几次做手术他都最先问候(我做手术大都在北京等外地),他几次住院我都是第一时间去探视。
他虽然只上过初中,但天赋极高,又肯用功,先是在团场被抽调搞新闻宣传,后来当编辑,最后担任了《绿洲》杂志社主编,兵团作协常务副主席等职。除了文学创作外,他闲暇时写书法,尤其爱好收集古钱币。从文革后期乌鲁木齐有了自由市场后,每个周末的时间他几乎都消磨在花鸟市场旁的古玩摊点上,他可以说是新疆古钱币收集最多的人,特别是对新疆红钱每一种类都有收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新疆另一钱币收藏家因家里有急事把自己收集的红钱出手转让,他知道后第一时间去商讨,竟然花十几万全部买了过来。这几年退休后,他几乎整天整理他的钱币,编号、查索发行年号、书写标签。我见他过于一门心思喜欢,就把陕西一领导送我的一套陕西古代钱币大全的藏品也送给了他,他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去年,我回关内过春节前又邀他和一些文化界朋友提前聚餐过年,那天他一改以往破格喝了一点酒,精神格外兴奋,席间欢声笑语。为了助兴他还唱了一段我听不懂的家乡小曲,还唱了一段草原歌曲。虽然音调不准,但他内心中那股豪放强悍之气也令人震动,赢得在座的朋友一片掌声。过完年我在平凉市场停留了一段时间,又前往西安筹建集团陕甘运营中心,一直到六月份才回新疆。他告诉我住院的消息后,我立即赶到军区总院,见面后使我大吃一惊,一个好端端的人一下变得面黄肌瘦。我们畅谈了许久,他说坚持一定要把关于新疆的钱币的那本书整理后出版,完成夙愿。说到病情,他说这种病非常疼痛,疼得他几乎难以忍受,只有一种进口药才能止疼,8000元只能维持一个疗程(二十天)。回来后我立即给他打了两万元,让用完后我再给打,谁知不到半个月他竟然毅然决然地说走就走了!人生如此短暂,生命如此脆弱,转眼兄弟阴阳相隔,这怎能不使人肝肠寸断,这让我如何接受这样的残酷现实。他的义气、才气、勇气,他那种含而不露、爱憎分明的文化性格,那种对学业的专注精神,永远永远都是后人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