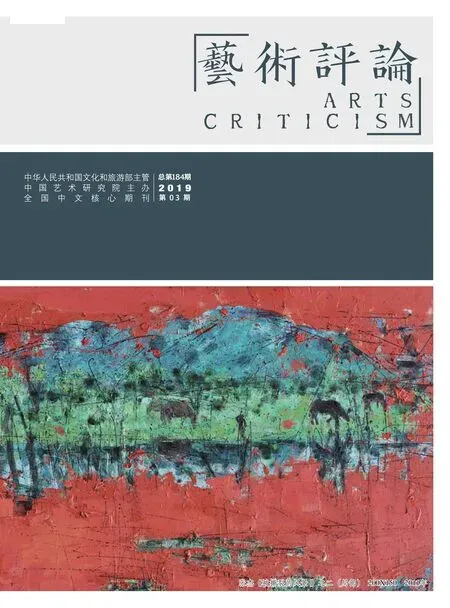说豫剧新崔派
——杨奇《新崔派艺术论——张宝英舞台艺术论》序
廖 奔
安阳市艺术研究所杨奇先生写了一本《新崔派艺术论》,论述豫剧名旦张宝英的舞台艺术,邀我作序,并希望我谈谈对戏曲流派的见解。豫剧大师崔兰田的崔派艺术我是熟悉的,她的女弟子张宝英在一生实践中继往开来、发扬光大,逐步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表演风格,杨奇称之为“新崔派艺术”。“新崔派艺术”产生在安阳,让我从安阳说起。
安阳是著名的七朝古都,今天以殷墟和甲骨文著称于世,安阳殷墟遗址和中国文字博物馆都是中华早期文明的象征物。但早期安阳和豫剧(河南梆子)却一直没有发生太多的联系。我们知道,早年河南梆子唱腔有祥符调、豫东调、豫西调,是以黄河南岸一线的开封、商丘、洛阳为中心的。处于豫省北部的安阳却和谁都挨不上,以往安阳是唱怀调、大平调为主的。而最早作为“豫西十八兰”之一成名的崔兰田,就是唱豫西调的,前半生多在洛阳、西安等地演出。但由于1951年的一个因缘际遇,崔兰田来安阳巡演,引起轰动,随后安阳市政府挽留住了崔兰田。崔兰田在安阳一扎就是五十多年,在这五十多年里,崔派艺术炉火纯青。崔兰田培养出一批徒弟,最有成就的就是张宝英。张宝英有幸成为崔兰田的第一个徒弟,也是时代的因缘际遇。大跃进时期崔兰田招徒,因出身贫苦收了张宝英。张宝英从此跟定崔兰田,一跟几十年。
张宝英早年多方打基础,闺门旦、刀马旦甚至彩旦都是常演的行当,国庆 30 年献礼演出《对花枪》时她甚至扮演了带头盔的老旦姜桂枝。1979年香港金马影业公司拍摄电影戏曲片《包青天》,她在竞演者中脱颖而出担纲主角秦香莲,一炮打响,使“河南秦香莲”饮誉了香港和东南亚,她也从此开始集中饰演青衣角色,塑造了众多“青一色”的舞台形象——陈三两、窦氏、柳迎春、赵艳荣、尤二姐等,演出了《桃花庵》《卖苗郎》《秦香莲后传》《洪湖赤卫队》《红云岗》等代表性剧目,在崔派传人中博得“第一青衣”之誉,后又在《寻儿记》里把老旦孙淑林演活了。张宝英严遵师训,博采众长,在保持崔派艺术精华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行腔特点,大胆吸收了秦腔、曲剧等姐妹剧种以及歌剧的发声方法,形成独特的演唱风格。她创造出的新腔真假声运用自如,韵味浓郁、声情并茂,既有崔派神韵,又有时代气息。她把“塑造新人物,创立新风格,向观众奉献自己的拿手好戏”作为座右铭,以在舞台上塑造性格鲜活的人物为第一目的,几十年来追求不息,创作了一批主题鲜明、风格独特的代表剧目,培养了一大批追随其演唱特色的传人,逐渐形成一个新型的豫剧流派“新崔派”,产生极大影响。古都安阳,为孕育了豫剧新崔派艺术而骄傲。
崔派艺术的特长是哭戏,发扬光大了豫剧青衣唱腔悲戚激愤的特点。崔兰田早年的艰难生活经历使她同情孺弱,常常在唱腔中宣泄自己对底层民众的一腔同情,也宣泄自己的一世悲愤。崔兰田在舞台上创造出一系列典型意义上的中原式悲剧,通过“以情动人”的手段把这种悲剧化入了真切感人的唱腔,感动了千千万万观众。张宝英继承崔派艺术,首先就要在哭戏上下功夫。但她最初扮演秦香莲时缺乏情感共鸣,导演杨兰春谆谆启发她:“文革”中,你是斗争对象,爱人关进牛棚,你连孩子面都见不到。你就不想孩子?孩子就不想你?想到秦香莲、自己以及普天下的苦命人,张宝英不禁悲从中来,感情闸门一下子打开,唱出了催人泪下的一腔幽怨和悲愤。经过长期的磨练,作为豫剧崔派艺术的优秀传人,张宝英不但会唱、能哭,更善于融情入理、按情行腔。她的体会是:“用真挚的感情、真实的生活感受和传统的表演手法融合在一起,才能抓住人物,通过唱把人物的心情表达出来。每用一个花腔、咬字、喷口、哭泣、换气的部位都要考虑到人物。”能够根据自己的条件进行继承创新,张宝英促进了崔派艺术不断向前发展并使其充满活力。
我向来不认为流派仅仅体现在与大师唱腔的“相似”上,这是世俗的理解,是戏迷对大师留恋与眷顾所形成的特定社会需求,他们通过音声甚至相貌举止的“像”来怀念大师。虽然是人之常情,却有害于艺术的发展。流派指价值观、审美观、美学风格的一致或接近,而不仅仅是指技法的相同度,如单纯以后者为追求目标,就会走入死胡同。齐白石说:“学我者生,像我者死。”豫剧大师陈素真也说:“传统的优势恰在于她拥有不断自我更新,可经历百代而不衰的深根厚土和历史渊源。”如果早期拜梅兰芳为师的程砚秋跟着乃师亦步亦趋,何来京剧四大名旦和程派!如果早期拜过唱豫东调的陈素真为师、自己唱豫西调的崔兰田也跟着乃师亦步亦趋,又何来豫剧五大名旦和崔派!
其实张宝英学艺崔派初期,也曾刻意模仿崔兰田的演唱技巧和韵味,崔兰田发现后,说出了另外的见解:“不要死板硬套地模仿我,在像不像我上瞎下功夫。你和我的嗓音条件不一样,我是大嗓,你是小嗓,你没那道腔。你要用我教你的方法,根据你自己的嗓音条件去演唱。怎么唱得舒服、唱得好听悦耳,你就怎么唱。”这是大师从长期实践中悟出来的深刻艺理。但不要徒弟像自己,而要根据先天条件去揣摩最适宜的演唱方法,怎样体现流派呢?通过剧目和人物形象体现,通过对特定对象的独特表现力体现,例如崔派的哭戏。大师们都有自己经受考验和淘洗的看家剧目,并且研琢出了对这些剧目最恰当的表现方法。后学者要去精心研琢这些剧目和方法,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是对流派的最合适解释。如果把“像不像”作为流派的首要也是必要条件,只能让学生邯郸学步、自我为牢,只会模仿不会创造,就压抑了创造性。加上每个人的天然条件不同,外貌、形象、气质、步态以及嗓宽、音高、气息、声量不同,个体差异会影响模仿的成色,影响学生的情绪和成绩。甚至,天然条件优异的学生去孜孜模仿老师通过后天努力纠正先天不足缺陷的方法,就事倍功半、逆水行舟了。
流派亦须追踪时代发展而变化,后来者不能只不越雷池一步地搬演前辈保留剧目,而应根据时代的需求创造自己新的作品和人物形象,有创造就会有突破。张宝英在继承流派和不断创新的过程中,根据自己的先天条件对崔派演唱吐字、发音、行腔技巧实现了扬弃,使之既有鲜明的崔派特色,又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她因而既是崔派的忠实继承者,又是崔派的变革发展者,实现了对崔派艺术的“创造性继承,创新性发展”。
张宝英大成了,创立了自己的“新崔派”风格,成为当代豫剧十大名旦之首、“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豫剧代表性传承人”。我们则从中体会到了艺术传承发展的历史辩证法。
还在崔兰田担任安阳豫剧团团长的时候,团里来了一个文字秘书,他叫杨奇。杨奇长期在剧团工作,陪伴在崔兰田和张宝英身边,随时留心记录揣摩她们的剧目、唱腔、人物形象、表演艺术,几十年不间断地为之撰写评介文章,把崔派艺术及其发展演变轨迹摸了个透。担任安阳市艺术研究所所长之后,杨奇开始了对崔派艺术的系统研究,形成一部部成果。《新崔派艺术论》就是这些成果中新出的一部。这些历史际遇,既是崔兰田和张宝英之幸,也是杨奇之幸。我还想说,这难道不是安阳之幸、豫剧之幸?
于是我们就又有了这本谈豫剧新崔派艺术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