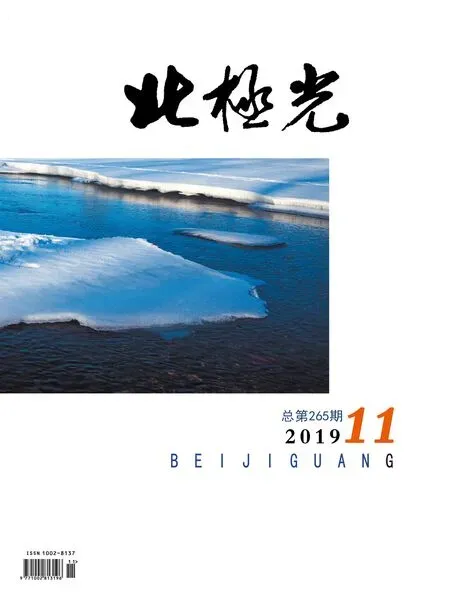糊纸盒的奶奶(外一篇)
王 娟
七八十年代,梅城居委会总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副业,如绣花、糊纸盒、缝纫、竹编等手工活。这些手工劳动大部分是没有生产车间的,一般是干活的人将半成品拿回家完成,然后在规定时间内交回成品。这样的工作主要是分给没有正式工作的家庭妇女,让她们挣些钱。
市民路12号有位纸盒奶奶,姓蒋。她住在老屋的厢房,脸盘圆润,有着沉静气质。我住进老屋时,她五十左右岁。
蒋奶奶是湖南人。她的丈夫瘦高,帅气,书生模样。他们是外地落户到梅城的。政府分给他们两间房。
听老屋的人说,蒋奶奶过去是大家闺秀,裹过小脚,没有工作,蒋爷爷没生病时,靠蒋爷爷的工资生活。爷爷生病后,日子拮据了。蒋奶奶为了给爷爷治病,卖掉了隔壁一间老宅,还在居委会找了份糊纸盒的活,一边糊纸盒,一边照顾蒋爷爷。
糊纸盒的活儿技术含量低,收益也低。蒋奶奶别无选择,只能糊纸盒挣点钱。夏天在厅堂糊纸盒,偶尔会有弄堂风穿过,可以避暑。冬天却挡不住寒风,厅堂阴冷。蒋奶奶除了双手长满了冻疮,脸颊上也长了冻疮,即使戴着帽子,围巾,脸上还有冻疮。蒋奶奶脸上的冻疮在来年春暖花开时才慢慢褪去。
纸盒爷爷得的是不治之症。我到老屋的头两年,还能见到爷爷在天井下晒太阳,面色蜡黄蜡黄的。后来他卧床不起了。
我小时候帮着蒋奶奶糊纸盒时,曾闯进他们的卧室。卧室光线暗,蒋爷爷见我进来,侧着身子,边咳嗽边招呼我。我站在爷爷面前,呆呆看着他。家人把我从纸盒爷爷的房间拖出来,告诉我以后不准进蒋奶奶的房间。家人不让我到不干净的地方,担心被传染上疾病。
我还是经常去蒋奶奶家,并称呼她:纸盒奶奶。市民路12号,从门屋进来,穿过两个天井,有一个后门。纸盒奶奶家的侧墙就是后门。从后门绕出去是东门街。弟弟妹妹每次来蒋奶奶家,会缠着我一起玩捉迷藏。游戏规则是以后门为界,不能出了后门。弟弟妹妹特别喜欢躲在纸盒奶奶家,用堆成小山的纸盒当掩护。纸盒奶奶乐意让我们串进串出。她有时看我着急,会眯笑着朝弟弟妹妹躲藏的角落打个眼神,给我暗示。
虽然纸盒奶奶喜欢孩子,但她膝下无子。听院里的人说,他们曾抱养过一个女儿,养女对养父母的感情不深,长大后极少来看望纸盒奶奶。
纸盒奶奶不像老屋里的其他居民那么喜欢聊天,也融入不到大家的闲聊中。她一个人默默地糊纸盒。纸盒爷爷在病床上躺了一年多离世了。当时他的棺材放在老屋二进的过道上。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棺材。
不久,纸盒奶奶又重新开始糊纸盒,糊纸盒的木板台面又架起来了。纸盒爷爷走后,原本安静的纸盒奶奶更安静了。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她摔了一跤,摔坏了腿。居委会工作人员隔三岔五地送来半成品,然后把成品的纸盒拿走。
我没事时,还帮蒋奶奶糊纸盒。我把糊纸盒当成趣事。纸盒奶奶与我交流的话不多,只是经常会停下手中的活小憩,怔怔地看着我,笑着,过了片刻继续干活。
纸盒奶奶靠着一把高凳,两手撑着,移步地生活在老屋中。
记不清过了多少时日,当我再次去看望她时,天井下的过道已是空空的了,过道里曾经布满纸盒和浆糊的味儿,在空气里也散得一干二净。
记忆中的陆篾匠
我第一次到市民路12号时,陆篾匠年近五十,高瘦黑黝,戴着眼镜,斯文,很精干的样子。陆篾匠当过兵,抗美援朝时荣获三等功。七十年代退伍后,分配在梅城的新安江电表厂。
七八十年代的梅城是个工业小城市,城市该有的设施一应俱全。除了公园码头客运站,电视台、俱乐部、文化馆之外,梅城还有三所小学,两所初中,两所高中,一所大学,两个医院,两个电影院,以及很多工厂。七八十年代的梅城,人丁兴旺,商旅云集,是许多转业军人首选的安置地。
那时在梅城谋生的东阳人不少,磨剪子的、爆米花的、弹棉花的、补锅、补鞋、做蒸笼的……街坊邻居看见手艺人,都会说是东阳人,也不管是不是真的东阳人。陆篾匠也是东阳人,自带手艺,一把篾刀,随了半辈子,一点不丢东阳人的脸。
市民路12号,二进靠左,第二间厢房是陆篾匠的家。他退伍时是单身,政府分给他一间房,二十几平方米。他结婚晚,老婆是东阳老乡。他三十八岁才有了第一个孩子,后来又生了一儿一女。一家人住这么小的房子,显然不够,他没有向政府再争取一间,只在自己的房间外用竹篾围了一间当厨房。孩子到了学龄期,他老婆带着三个娃回东阳老家了。
虽然我与陆篾匠在老屋见面时间少,但丝毫不影响我对他的敬重。我每次遇见他,都喊他:篾匠爷爷。他笑呵呵的抚过我的头,说我是听话的娃。
到了夏天,陆篾匠就会忙碌起来。午后,老屋的天井廊下有苇帘放下,底端用竹竿支着,可以挡住透过天井泄下的阳光。苇帘内是三五个在厅堂过道乘凉,或手作的邻里,有人洗洗刷刷、有人窃窃私语、有人忙着手上的针线、也有人摇着扇蒲打瞌睡……修补篾席的陆篾匠,也是其中一员。偶尔一阵穿堂风拂过,陆篾匠会停下手中的劳作,迎风深呼吸,那个舒心惬意的表情,不是现在空调房所能体会的。
陆篾匠修得最多的是那些年数久了,或保管不当,篾席边角受磨损以及篾条断裂的席子。请陆篾匠编织新篾席的也有,却很少。
我小时候不理解,常问奶奶为什么不重新编一张篾席,后来才知道从前的大多数人,一生也只睡一床席子。而经日积月累的篾席,三伏天能让人感觉冰凉舒适。
每年夏天,谁家的席子坏了,一定会出现在陆篾匠的手中。陆篾匠是爽快人,没有二话就应允。下了班,或者逢上休息日修补。陆篾匠自家空间小,就将席子平摊在家门口二进的厅堂过道上,或蹲,或坐,汗衫湿背,一丝不苟的修补。极薄的篾条在粗糙的双手中来回穿梭。损坏的篾席经过修补后,若非新旧篾条色差大,接缝处是完全看不出痕迹来。修补好了,陆篾匠将席子滚筒收起,绳子扎三道,两头和中间各扎一道,给邻里送去。
慢慢地,陆篾匠会编修竹制品的手艺从市民路12号传了出去,周边的邻居们也开始让陆篾匠帮忙修补篾席和竹制品。
陆篾匠一如既往的和善,一件挨一件地完成。也不时会有左邻右舍端着麦饼、饺子之类的面食来感谢陆篾匠。陆篾匠连声谢过,笑得腼腆,并叮嘱邻里下不为例。
不修补席子时,陆篾匠下班后会被老屋里的其他男主人找去打牌。三个人打,从不赌钱,输的人戴个草帽,或者用报纸剪成条状,当胡子贴起来就好。输得越多,胡子越多。胡子越多,笑声也越多,常常引得院里人过去围观。
我也经常凑进去看院里的各种热闹,还喜欢看陆篾匠编织篾席的样子。手工编织的篾席和竹器编织物,在过去的年代似乎司空见惯。老人们也常说篾刀拿得起,不怕没柴米。如果陆篾匠只是个篾匠,或者他只是个退伍军人,也许日后不会这样被怀念。偏偏,陆篾匠是个有手艺的退伍军人,在物质匮乏的年代里,生活再清苦,陆篾匠也从不赚取老屋居民的柴米费,所有的修修补补都是免费义务,年复一年。
而今,时代进步,生活好了。许多渐行渐远的老手艺,只能在记忆里重现。每当和孩子讲起市民路12号的故事,总不忘陆篾匠,不忘他在老屋二进的过道上修补席子的健朗身姿。天井外斜照的光影,映在他写满岁月泛着油光的侧脸,忽明忽暗,偶一抬头,陆篾匠笑容通透。
——吃饭、当官都和席子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