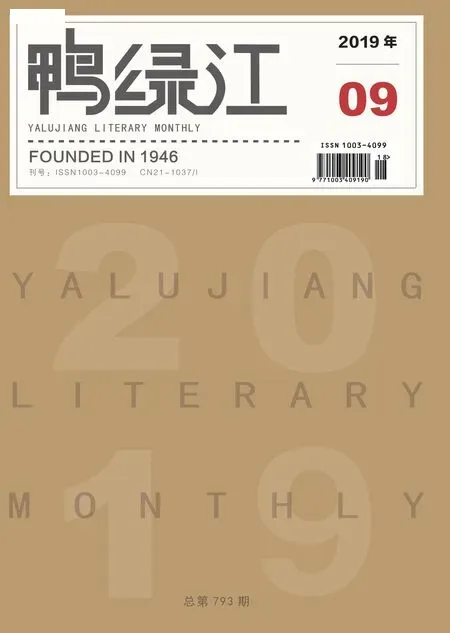短诗八首
扬 臣
弥勒佛简笔画像
可以眯起眼睛。痴男怨女
看不透的,绝口不提。
有人一意孤行,有人难得糊涂。
你不爱朝拜,只喜欢画像:
白纸柔软的一面,一定经得起碳素笔
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
纵然有一天化为灰烬,
轻风过后,尘将归尘土终归土。
回笼觉之梦
黎明,是你喜欢的坐骑。
它的蹄声,应和我起伏的心跳。
启明星退进你的眼,太阳还没有跳出我的地平线。
栖息在你喉咙的那只鸫鸟,唱起我熟悉的歌。
而左右摇摆总想着障目的阔叶,
让我看不出,更猜不透你。
顺着你的尾间,我伸出右手,
像断桥,搭在焚山后四处飞扬的灰烬里。
在叫花鸡铺子前
以插队的那人为界,食欲分两节:
前面稍短,
后面比排的队更长。
把买鸡肉换成预支明天,
换成受难,
或者赴死。
那么今天,现在的我,
就是那个在时间序列里插队的人。
与停在水泥柱上的蚱蜢对视
如果我是它,睁开所有隐性的复眼,
能否找到一条出路,绕开对面的严阵以待?
不回头,是否也可以躲避
某个同类率领一群影子的穷追不舍?
如果闭目、缩腿,收回的触角
是藏在午后冰冷的阴影里,
还是从洒向阳光的汗液里收集盐分呢?
镜中取魂
晚上千万别照镜子,会把魂吸进去。
小时候常听奶奶这样说,
我才不管,那个叫做魂的玩意。
如今,出门前,我习惯于匆匆揽镜自照。
镜中取魂,给自己充点精气神的气。
大嘴梁风口的小麦和罔草
小时候,我喜欢拔毛胜过割麦,
更讨厌拔草。
滚烫的开水泡一分钟,顺手拔几下,
不管家鸡野鸡,都能显出美味该有的样子。
大嘴梁风口的坡地,一颗麦种只长一棵矮苗。
抓不拢,再有力也没处使。
而除草剂打不死的罔草,使出吃奶的劲,
还是不能连根拔起。
如今,我远离麦田,
但怀念罔草,如怀念鸡毛。
海的肺音听诊练习
坐在椰树的阴影里,听诊器对准海面。
太阳反射光在水面的撞击声,是难以判断的杂音。
贴到地上,你听到一片落叶最后的告白,
与蚂蚁急促的脚步声不同。
伸进海里,你终于听清地球深处的呼吸:
汩汩有力,起伏不定,它像小时候爬山的自己。
汽笛声不肯停下来
窗外的鸟,有一声,没一声。
远处,船舰的汽笛,突然长鸣不已。
早晨如懂事的婴孩:安静,孤独,
完全不去回想,临睡前大人们的训斥。
我也记不起,昨晚梦里做过什么?
直到翻出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汽笛声
还不肯停下来。
出门,去海边,突击检查,来一次真的。
几只船像无辜的墨点,
滴撒在画布蓝灰色背景里,随风起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