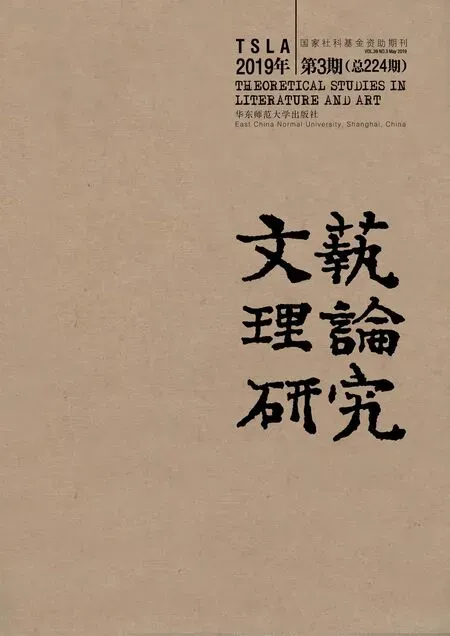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的历史生成与当代发展
陶水平
一、问题的提出——何谓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
本文所讨论的“中国艺术精神”论是20世纪中国美学和文艺研究的一种重要美学思潮和文论形态。它滥觞于晚清民初,提出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确立于五十年代以后的港台并播撒于海外,复兴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作为一种特定的学术指称和自觉的理论追求,“中国艺术精神”论是五四之后一批具有深厚民族精神和文化情怀的学者的美学追求,旨在校正五四新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重建中国现代文化精神和美学精神。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正式诞生于抗日战争的民族危难岁月,以阐扬中华文化的生命精神、振奋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为己任。“中国艺术精神”论以现代新儒学生命本体论哲学(或价值形而上学、现代心性哲学、现代人生哲学)为哲学理论基础,是一种以中国美学史和艺术史研究面貌呈现的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研究的理论建构形态。在“中国艺术精神”这个学术旗帜下,聚集了大批优秀的人文学者,取得了大量极具原创性的理论成果,至今已形成了一个绵延百年的中国现代人文学术新传统,并成为近年来我国当代文艺学和美学界的一个学术热点。
作为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上一种令人瞩目的美学理论形态,“中国艺术精神”研究史论结合,融会中西古今之学,激活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生命活力,为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转化、西方美学的中国化以及中西美学的会通创造了宝贵的学术经验,也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不断回望和创新的学术资源。关于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的研究,目前已有孙琪《中国艺术精神:话题的提出及其转换》(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刘建平《东方美典——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宛小平《港台现代新儒家美学思想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专著研究,并涌现了不少论文讨论这一话题。其中,王一川、章启群、张泽鸿等先生的论文都很有代表性。鉴于目前的研究往往限于不同侧面,本文力图对这一美学思潮和文论传统的学术谱系、历史语境、哲学基础、理论内涵、理论特质、理论价值及其当代发展等关键性问题进行整体式理论图绘,以期推进中国艺术和美学精神问题的研究。
二、晚清民初“中国艺术精神”论的先声
晚清民初是一个文化急剧变革的时代,在晚清民初文坛“经世致用”的文学功利主义大潮中,少数先知式的思想家认为自强图新首先应是民族文化精神的振兴和国民精神人格的挺立。正是他们最早提出文学的精神建构问题。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思想巨子最早认识到,立国之本在于立人,欲立其国,必先立其人。文学艺术和美学哲学在提振国人精神的立人伟业中具有重大作用,他们可谓是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的先声。例如,梁启超提出文化上的元气说、哲学上的惟心说、文学的新民说和趣味说,阐明文学与人格精神的关系,开启了文学精神追求的价值取向。例如,他在《国民十大元气论》(1889年)一文中明确提出:“求文明而从精神入,如导大川,一清其源,则千里直泻,沛然莫之能御也。”(267)梁启超还在《惟心》(1899年)一文中化用佛学,提出:“境者心造也。[......]岂有他术哉?亦明三界唯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隶而已。苟知此义,则人人皆可以为豪杰。”(361-62)随后,王国维在《文学与教育》(1904年)一文中明确提出:“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王国维,第三卷 63),并先后撰著研究屈原的文学精神、《红楼梦》的文学精神和戏曲的文学精神。在《人间词话》(1908年—1909年)中,王国维更是以“境界”释“精神”,指出:“故能写真景物、真情感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王国维,第一卷 142)鲁迅更是强调人的“精神”与人格独立之极端重要性,“精神”一词在其《文化偏至论》(1907年)和《摩罗诗力说》(1907年)等早期论文中出现数十次之多。鲁迅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恃意力以辟生路”,开启“二十世纪中国之新精神”,促进“国民精神之发扬”(“文化偏至论”,鲁迅 49)。他赞美卢梭、拜伦、雪莱等诗人的启蒙思想和浪漫主义精神,赞扬尼采的生命意志说和易卜生的个性解放说,主张“剖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文化偏至论”,鲁迅 39)。鲁迅指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其繁华物质文明只是现象之末。(精神之)本原深而难见,(物质之)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鲁迅 50)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鲁迅盛赞西方浪漫主义诗人为“精神界之战士”“精神界之伟人”,并呼唤中国现代精神界之战士的诞生。鲁迅强调,文学审美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自振其精神而绍介其伟美于世界”(55—93)。以上梁启超、王国维、鲁迅等先驱对人的精神和文学精神的阐扬成为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的先声。
三、宗白华与方东美: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的正式提出者
最早明确提出“中国艺术精神”这一理论术语的是五四之子宗白华。宗白华是五四时期著名诗人、编辑和学者,经历了一个从西学向国学嬗变的思想历程。宗白华在《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1934年)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哲学如《周易》以‘动’说明宇宙人生(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正与中国艺术精神(如谢赫的‘气韵生动’)相表里。”(105)在此之前,另一位同样沐浴五四文化并具有诗人气质的现代新儒家方东美发表了《生命情调与美感》(1931年)一文,阐述艺术美感、生命情调与宇宙人生观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在《哲性三慧》(1937年)一文比较中西文化的诗性精神,同年还在《中国人生哲学概要》学术演讲中阐发中国艺术精神。因此,宗白华与方东美同为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理论的提出者。以下稍作具体展开。
1.宗白华的“中国艺术精神”论。探索中国文化的精神向何处去,是宗白华毕生的学术旨趣和艺术追求。作为五四之子,宗白华的学术思想和文艺观念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生成的,并随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认识的深化而不断发展。从宗白华早年多篇论“少年中国”社团和《学灯》办刊思想的文章中可以看出,宗白华在青年时代就树立建设中国新文化精神的抱负。中国现代学者很多研究中国哲学和文化精神的文章都首发于其主编的《学灯》,而且经由宗白华亲自撰写编后语予以推介。宗白华青年时就酷爱哲学,早在1920年赴德国留学之前就着力研究西学。22岁时曾写下长文《欧洲哲学的派别》,对西方哲学有精细的研究,尤其醉心于叔本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康德的唯心哲学,批评唯物论哲学想从物质中推求精神思想的原理根本不能成立,赞美希腊和欧洲文学艺术描写“动象”、表现“动”之生命的艺术审美精神。早年的宗白华,写了很多研究新诗、新文化、新艺术、人生哲学、精神文化、精神人格的精彩论文。在《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1919年)一文中,宗白华指出:“我们现在对于中国精神文化的责任,就是一方面保存中国旧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大庄严精神,发挥而重光之;一方面吸取西方文化的菁华,渗合融化,在这东西方文化总汇上建造一种更高尚更灿烂的新精神文化。”(102)宗白华认为,将来世界新文化一定是融合东西两种文化的优点而加以新创造的,这融合东西文化的事业以中国人最相宜。我们要有进化的精神,这是少年中国新学者真正的使命和事业。总之,这奋斗创造的最后鹄的,就是创造具有新生命、新精神和新国魂的“少年中国精神”。在《看了罗丹雕刻之后》(1921年)一文中,宗白华写道:“艺术是精神和物质的奋斗[……]艺术是精神的生命贯注到物质界中,使无生命的表现生命,无精神的表现精神。”(309)在德国留学期间,宗白华发现了“东西文化对流”的现象,对中国文化的伟大价值有更深的认识,因而更加注重中国古典文化研究。1925年回国之后,宗白华执教于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重镇(学衡派发祥地和现代新儒学学术重镇)国立东南大学,曾与方东美共事。期间,熊十力还在东南大学讲授过《新唯识论》,这些都激发了宗白华对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研究。宗白华在文章中还多次提到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自己的影响。在《艺术学(讲演)》手稿(约写于20年代末)中,宗白华即已认识到:“凡一切生命的表现,皆有节奏和条理,《易》注谓太极至动而有条理,太极即泛指宇宙而言,谓一切现象,皆至动而有条理也,艺术之形式即此条理,艺术内容即至动之生命。至动之生命表现自然之条理,如一伟大艺术品。”(548)三、四十年代,宗白华写了大量研究中国古典哲学、文学、艺术尤其是音乐和绘画美学的文章。宗白华高度赞美魏晋的自由人格精神和唐代的文化进取精神,尤为阐扬中国古代乐舞艺术精神,认为乐舞艺术是人的内在生命和宇宙生命最为直接、具体和生动的流露。1939年,宗白华在《〈黑格尔及其辩证法〉编辑后语》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易》也是一部动的生命哲学,所以它的方法也是属于‘辩证法’的。”(245)宗白华对中西哲学精神的系统研究见于其《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这部未刊稿。关于这部手稿的写作时间,学术界有不同认识,这又关系到对宗白华美学思想嬗变历程的认识。笔者发现,宗白华写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艺术精神研究的系列美学论文,与这部《形上学》手稿观点一致、互为表里、相互印证,表明二者写作应在同一时期或略有前后。可见,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宗白华的美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贯通“道”“艺”、创构艺术意境论的阶段,强调艺术家精神涵养对于艺术创造之重要性。在宗白华看来,艺术意境正是中国文化中壮阔幽深的宇宙意识和生命情调的象征和显现,是中国古代艺术家生命精神和宇宙大生命精神的生动表征。宗白华的中国艺术意境论与其中国哲学形上学研究相互发明,相得益彰。宗白华《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1946年)一文则是其四十年代研究中国美学精神的一篇重要专文,更为鲜明地显示出中西艺术精神融合的价值取向。
2.方东美的“中国艺术精神”论。现代新儒家方东美的艺术精神论是建立在其“生生之德”的生命哲学本体论基础之上的。方东美的“生生之德”生命哲学是柏格森“创化论”、怀特海“生成论”与中国传统儒道易佛生命哲学融会贯通的产物。在方东美看来,中国美学是一种生命美学,即创造“生生之美”,体现“生生之德”。文学艺术所表达的“生命情调”,本质在于普遍生命之大化流行和创造不息,在于盎然生意与灿然活力。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方东美通过广播向全国青年发表关于中国人生哲学的系列演讲,在抗日炮火声中阐扬中国文化精神,以激发国人的民族精神与抗战信心。其中,深刻地阐扬了中国文化中“美的艺术精神”,强调先哲“人的精神气象能与天地上下同其流”的雄健精神。方东美认为,中国古代先哲视宇宙为一大化流行的生命,兼有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且是浑然一体的,不像西哲往往把它们截作两片。因此,中国先哲的宇宙观可谓“万物有生论”(不同于西方“万物无生论”)的宇宙观。把宇宙和人生打成一气来看,人与宇宙大化浩然同流,是中国哲学的一贯精神。中国人的宇宙观究其根底具有道德性和艺术性,故为价值之领域。总之,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乃是广大和谐之生命精神(《中国人生哲学》 18,19,22,38,39,172)。方东美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上最早阐发孔子与庄子的艺术精神,赞扬孔子的生命创造精神和老庄的大生命精神,对后来的唐君毅、徐复观有直接影响。方东美认为,美是人类创造欲的表现,一切艺术都是从体贴生命之伟大处得来的。中国艺术家直透内在生命精神,化为外在的生命气象。中国艺术所关切的,主要是生命之美及其气韵生动之充沛活力,它所注重的不像西方艺术那样仅是表现孤立的个人生命,而是注重全体生命之流所弥漫的灿然仁心与畅然生机,从而体现了中国艺术独特的人文主义精神(《中国人生哲学》 55—58,193—203)。抗战后期,方东美发表了影响深远的《中国文化中之艺术精神》一文,进一步阐扬中国文化精神以振奋国人的民族精神。
因此,本文认为,方东美与宗白华同为“中国艺术精神”理论的提出者。在宗白华和方东美那里,中国的哲学、文化与艺术都是极富生命精神的,生命精神既是中国哲学的精神,又是中国文化和艺术的精神。宗白华与方东美为同学和表兄弟的关系,二人都学贯中西,都有深厚学养,都深受五四新文化影响,都有深厚民族强怀,都具有诗人气质。宗白华著有《流云小诗》和《三叶集》,为五四时期著名哲性诗人;方东美创作旧体诗词一千余首,并结为《坚白精舍诗集》出版,被誉为“一代诗哲”。他们在学术上相互影响,思想旨趣多有投合。追求哲诗交融互摄、重视周易美学并强调“生生之美”是他们的学术共性。所不同者,方东美更侧重于哲思中见诗意,更强调“生生之德”(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生命本性或内在创造力),强调感悟宇宙人生的普遍生命本体,即生命情调、美感与宇宙的合一。宗白华则更侧重于诗意中见哲理、于诗艺中见大道、于艺象中见艺境,更强调“生生之理”(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生命节奏或条理),强调“道器合一”或“道艺合一”,在艺术象征中领悟生命节奏,以乐舞美学精神为中国古典艺术精神的文化本原和最高理想。作为“一代诗哲”,方东美更注重艺术的生命本性和价值研究,贯通艺术、宗教和哲学;作为一代美学骄子,宗白华进而还注重深入探究艺术样态和形式,贯通美学和艺术学。再者,宗白华对文化的理解更为广义,涵盖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而方东美所理解的文化更侧重精神文化。方东美强调万物有生、万物含生,强调艺术是表达“生命存在的灿溢精神”,因而方东美的美学研究更加强调中国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性和艺术的精神价值,更加注重阐扬艺术的生命精神和生命气象。宗白华则更注重通过建构艺术意境论来阐扬中国艺术精神,认为中国传统艺术意境、艺术精神与“道”的关系最为密切。总之,宗白华与现代新儒学的关系是一位自由主义诗人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其中,在哲学上,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尤其是方东美的现代新儒家哲学对宗白华有重要影响。在美学上,宗白华对方东美和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徐复观以及后来的文学批评家李长之等人影响更大。
四、唐君毅与徐复观: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的理论确立者
在宗白华、方东美明确倡导“中国艺术精神”研究之后,现代新儒家唐君毅、徐复观等人相继展开中国艺术精神的系统研究,“中国艺术精神”论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1.唐君毅的“中国艺术精神”论。唐君毅明确提到宗白华艺术审美精神论对他的影响(《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206)。而且,唐君毅对魏晋美学精神的认知和赞扬也受到宗白华的直接影响。唐君毅的中国艺术精神论研究主要见于《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53年)、《人文精神之重建》(1955年)等著作。这些著作都辟专章论述中国艺术精神、礼乐精神和文学精神,深刻揭示了人的精神文化的生命之源和价值之源,阐扬中国文化的整全性价值和人文精神指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与宗教得到道德精神与艺术精神的灌注,未来中国文化应进一步融摄西方的科学和宗教精神,进而提出了中西文化精神的互摄、会通与融合等论题。
在此以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为例稍作展开论述。该书系统阐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起源、演进、哲学基础、艺术呈现以及未来发展等论题。唐君毅指出:“中国之艺术文学之精神,皆与吾人上述之中国先哲之自然宇宙观、人生观及社会文化生活之形态,密切相连者。艺术文学之精神,乃人之内心之情调,直接客观化于自然与感觉性之声色,及文字之符号之中,故由中国文学、艺术见中国文化之精神尤易。”(195)进而论之,中国古代各门类艺术的精神亦相互涵摄,无不可以令人悠游其间。每种艺术之本身,皆有虚以容受其他艺术之精神以自充实其自身之表现。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学艺术之精神异于西洋文学艺术之精神者,在于中国文学艺术具有优游之美,皆可使人的精神入乎其内,游心于其中。令人心与之俱往,人的生命精神涵育其中。因而中国艺术不仅是审美感知或观赏的对象,更是吾人整个心灵藏、修、息、游之所在。所谓“藏修息游”既是一种心物交融的生命体验,又是一种自由活泼的精神境界。中国各门类艺术都具有令人藏修息游的艺术境界,中国艺术精神亦即往来悠游之精神(202—215)。中国艺术虚实相涵,皆可令人的心灵悠游往来。“故吾人谓中国艺术之精神在可游,亦可改谓中国艺术之精神在虚实相涵。虚实相涵而可游,可游之美,乃回环往复悠扬之美。”(204—205)中国艺术为生命精神提供安顿归宿之所,心灵生命得以相互亲近和感通,进而提振人的精神力量,开拓人的心灵境界,艺术因而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显然,唐君毅所阐发的中国艺术之悠游精神是对孔子、庄子等先哲的“游于艺”“游心万化”等审美精神传统的现代转化。随后,唐君毅进而在《人文精神之重建》一书中具体阐发了孔子和庄子的艺术精神,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艺术精神为道德的艺术精神,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艺术精神为纯粹的艺术精神。这可谓先于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阐扬孔子艺术精神和庄子艺术精神。唐君毅认为,归根结底,中国艺术精神植根于中国人的人格精神,从自然美、器物美、艺术美到人格美,乃是人的生命精神上升之路,也是道德自我或心之本体的不断超越之路。
2.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中国现代艺术精神论的标志性著作。在现代新儒家当中,徐复观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前半生投身军政,后半生献身学术。1943年,拜熊十力为师,退役向学,一生著作数百万字,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尤其是艺术精神、文学精神的现代转化。其中,《中国艺术精神》(1966年)是徐复观系统研究中国艺术精神的主要代表作,也是20世纪中国学者第一部专门以“中国艺术精神”为论题的专著,是中国现代艺术精神论研究领域最具标志性的学术成果之一。
徐复观与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师友致力于建构儒家形而上学体系不同,而是通过思想史、文化史、艺术史的现代疏释和体验领悟,阐扬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艺术精神,以期开出儒家文化的新生命。徐复观认为,道德、艺术、科学是人类文化中的三大支柱,西方文化强在科学,而中国文化在道德、艺术研究方面更为优越、更有价值。不仅有历史的意义,而且有现在和将来的价值。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心的文化”。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人生价值的根源即是在人自己的‘心’”。《易传》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道”为天道,“器”为器物,而“形”指人的身体。由于人之心在人的身体之中,“所以心的文化、心的哲学,只能称为形而中学,而不应讲成形而上学”(《心的文化》 211-12)。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论正是建立在其“心的文化”(“形而中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徐复观对中国古代心性哲学和道德精神的阐发集中体现在其《中国人性史论》(1963年)一书中。徐复观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奥妙。在《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之中,徐复观明确提出,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发端于、奠基于由孔子和庄子所开显的两个典型。
徐复观认为,孔子艺术精神的生命本源在于“仁”,彰显在孔子的乐教(诗教)之中。孔子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揭示了儒家人格成长的艺术之路,体现了对音乐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达到了仁与乐合一的精神境界。由此,孔子建立了“为人生的艺术”的典型,完成了美善统一的人格精神建构。究其奥妙在于,艺术植根于“仁心”这一生命的根源处。孔子乐教所推崇的“大乐必简”和“无声之乐”,更是达到了与仁合一的人生至纯、至净、至和、至静、至美的生命最高境界和艺术最高境界,成为先秦儒家最高最完整的艺术精神。因此,孔子是中国历史中第一位最明显而又最伟大的艺术精神的发现者(《中国艺术精神》 4)。战国之后,雅乐衰而俗乐起,孔门艺术精神趋于汩没。但是,孔子的艺术精神并未消失,而是在后世诗经学、文心雕龙和古文运动中得到了体现和展开。
徐复观认为,如果说孔子的艺术精神植根于“仁”,那么,庄子的艺术精神植根于“道”。“老庄所建立的最高概念是‘道’;他们的目的,是要在精神上与道为体,亦即是所谓‘体道’,因而形成‘道的人生观’,抱着道的生活态度,以安顿现实的生活。[……]他们所说的‘道’,若通过思维去加以展开,以建立由宇宙落向人生的系统,它固然是理论的、形而上学的意义;此在老子,即偏于在这一方面。但若通过工夫在现实人生中加以体认,则将发现他们之所谓道,实际是一种最高地艺术精神;这一直要到庄子而始为显著。”(《中国艺术精神》 42)老庄在他们思想起步的地方,并无艺术意欲,更不曾以某种具体艺术作为他们追求的对象。但是,从他们的修养工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去看,则不期然而然地归于艺术精神。因此,当庄子从观念上去描述他之所谓“道”,而我们也只从观念上去加以把握时,这“道”便是思辨地形而上学的性格。但当庄子把它当做人生体验而加以陈述,我们对这种人生体验而得到了悟时,这便是彻头彻尾的艺术精神(《中国艺术精神》 43—44)。徐复观指出:“庄子所追求的道,与一个艺术家所呈现出的最高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同。所不同者,艺术家由此而成就艺术地作品;而庄子则由此而成就艺术地人生。”(《中国艺术精神》 49)老庄否定世俗浮薄之美和世俗感官快乐,追求最高的“大美”“大乐”和“大巧”,使人的精神得到自由解放。这种自由解放即“心斋”“坐忘”之心,庄子称之为精神,亦即是艺术精神主体。庄子的精神境界是一种“体道”“与天为徒”“入于廖一”“与天地万物相通”的“游”之境、“独”之境,庄子的艺术精神是一种既“虚、静、明”又“弘大而辟,深闳而肆”的自由精神,是一种纯粹、整全、自觉自由的纯艺术精神,庄子因而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再发现者。
总之,孔孟之心为仁心、亦即尽性知天的道德心;而老庄之心则是体道之心、虚静的艺术心。一如自孔子仁心到孟子提出四端之心,中国古代艺术的道德精神得以澄明;自庄子提出虚静之心,中国古代艺术的自由精神亦得以自觉。孔子是中国艺术精神的第一位发现者,庄子则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再发现者,亦即是纯艺术精神的发现者。由孔子所开辟的艺术精神在后来“文以载道”的古文运动中得到生动表现,而由庄子所开辟的纯艺术精神主要在后来的山水画艺术中得到了最为纯粹的表现(后者是前者的独生子)。庄子与孔子一样,依然是为人生而艺术。儒家成就的是道德的艺术人生,而老庄思想所成就的人生是虚静的艺术人生。因此,为人生而艺术才是中国艺术的正统。不过儒家所开出的艺术精神,常须在仁义道德根源之地有某种转换。由道家所开出的艺术精神,则是直上直下的,成就的是纯艺术精神(《中国艺术精神》 114—18)。可见,徐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研究,达到了现代新儒学的中国艺术精神论研究的最高学术水平,同时也把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影响深远。
五、“中国艺术精神”论在大陆和海外文学批评界的播撒
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的提出和确立,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强烈反响。首先是在大陆的文学批评家中得到响应,青年批评家李长之率先提出“文学批评精神”这个理念,并贯彻在其文学批评实践之中。此后,“中国艺术精神”论在港台文学批评家、海外华人文学批评家和海外汉学家那里得到响应,陈世骧、高友工以及王梦鸥等人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都深受“中国艺术精神”论的影响,共同形成了“中国艺术精神”论谱系中的批评家范式,与“中国艺术精神”论谱系中的美学家和艺术学家范式(宗白华)、哲学家和思想家范式(方东美、唐君毅、徐复观)在理论形态上鼎足而立。换言之,大陆批评家李长之、台湾批评家王梦鸥以及海外华人批评家陈世骧、高友工等人的文学批评都体现了一种批评家的艺术精神理念,成为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的理论播撒。限于篇幅,本节仅对李长之的文学批评精神论进行简要评析。
李长之深受德国文化影响,重视文学批评的美学精神研究,其所写的美育研究和文学批评论文以及西方艺术理论译著曾多次得到宗白华的好评。1940年,青年李长之在《释美育并论及中国美育之今昔及其未来》一文中,对何谓美学精神、何谓中国美学精神及其对中国美学的未来期待等问题发表了重要观点。李长之指出,美学关系于形而上学。美学的真精神是在反功利,在忘却自己,在理想之追求。这是成功任何大事业所必不可少的精神。中国古人把宇宙视为一个生动活泼、生生不已的伦理世界,生活于这个世界的人在俯仰呼吸之间,与宇宙大我息息相通,从中感到了生命力的洋溢充盈。因此,中国古典美学精神即是生意盎然、氤氲不息的生命精神。孔子即是这样一位富于古典美学精神的大师。然而,“现代人的精神已浅薄脆弱到了极点,生活不过是耳目声色之欲,所看宇宙自是干燥而枯窘的空气而已,石头而已,灰尘而已”(《李长之文集》第三卷 165)。李长之对未来中国美学提出了很高的学术期待。他指出,文化教育是使人类全体或分子在精神上扩大而充实,美感教育则为其中最重要之一种,甚而可谓是最符合教育本义之一种。铸就新人类,建设新国家,离不开新美学。新美学不是简单继续古人的美感教育,而是建立在新的形而上学基础上的新人文主义美学(163—72)。显然,李长之的这个美学思想是对蔡元培、宗白华和方东美的审美人格教育思想和艺术生命精神理论的发扬光大。李长之还著有《德国的古典精神》(1942年)一书,深入阐发了德国古典主义文化精神。李长之指出:“我常说,我有三个向往的时代和三个不妥协的思想。这三个向往的时代:一是古代的希腊,二是中国的周秦,三是德国的古典时代。那三个不能妥协的思想:一是唯物主义,二是宿命主义,三是虚无主义。[……]我所谓的三个可向往的时代:希腊,周秦,古典的德国,尤其是在这三个时代中之正统思想,可说都是理想主义。”(151—53)李长之所说的“理想主义”即是一种人本的、热情的、艺术的、完美的文化理想精神。而且,李长之倡导美学精神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灌注和运用,提出“批评精神”这一理念,认为“文艺批评最要紧的是在‘批评精神’”,并著有《批评精神》(1942年)一书(《李长之文集》第三卷 3)。在该书中,李长之呼唤伟大的批评家及其批评精神,认为文学批评乃是批判家批评精神的流露和应用。李长之将批评精神释为一种灌注在文艺批评中的理想精神,并以“感情的型”作为批评活动的最高文艺标准论,并由此展开具体的批评实践,撰写传记批评专著,阐扬中国文学史上司马迁、陶渊明、李白、鲁迅等作家的伟大人格精神。
六、后五四文化与现代新儒学:“中国艺术精神”论的形成语境与哲学基础
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的兴起,应置于五四新文化、后五四文化和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整个大的时代文化思潮和精神嬗变史中加以考量。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是19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历史急剧变革的产物,是对19世纪末以来西方列强科技文明、物质文明强势侵入中国的文化反应,是20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因应传统文化危机所作出的一种文化对策,是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重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转引自《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327,361)。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前所未遇的深刻危机。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民族共同文化遗产问题上,晚清民初中国知识分子作出了不同的学术思考和文化选择,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界的偏于西化的文化自由主义、偏于俄化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偏于国学的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潮。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两大思潮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潮,现代新儒家作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在后五四时期兴起,介于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和其他传统主义之间,旨在探索一条折中的学术路径,希冀在文化危机中重建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
发端于1915年《新青年》(后改为《青年杂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中国现代青年为主体的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将中国近代启蒙思潮推向了新的高峰,用陈独秀发表于1916年《青年杂志》的一篇同名文章的话来表述,即“吾人最后之觉悟”(陈独秀 175),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现代社会。五四新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性改造和整体性变革。五四新文化思想巨子们接受了西方进化论,将中西文化理解为“新与旧”“落后与进步”“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的关系,宣称应“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适 153),主张通过激进变革来“破旧立新”和“弃旧立新”,彻底摈弃传统文化,全盘学习西方文化,以期通过输入西方新学理,再造中国新文明,因而奏响了20世纪前期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最强音。但是,五四巨子的思想偏至也是现代新儒家所不认同的。正是这些偏至之处引发了后五四时期现代新儒家的文化新保守主义兴起,他们对五四新文化做出反思、批评和矫正,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做出新的构想,表达了一种不同于五四的文化现代性新诉求。
作为一种后五四文化,现代新儒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保守主义,不把传统与现代化视为水火不相容的关系,而是认为儒学与西学、儒学与科学、儒学与现代生活可以协调和融通。现代新儒家大多有深厚的西学功底甚至是西学专业出身,他们“援西入儒”,将西方生命哲学、德国精神哲学和现象学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化的“返本开新”和传统文化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走出中国文化面临的困境,同时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暴露的西方现代性诸种弊端。因此,现代新儒学不同于其他文化保守主义,实现了对一般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超越。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发现并阐扬被清代朴学所遮蔽的宋明理学的现代价值,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文化,以期重建中国现代新文化,使之成为克服中国现代文化危机的因应之道,是现代新儒学最根本的学术旨趣。现代新儒家的“生命哲学”(“生命形而上学”)“天人合一”“内在超越”“道德理想主义”“返本开新”“以新内圣开出新外王”等文化理念,都是现代新儒家对传统儒学现代价值的彰显和阐发。因此,现代新儒学与五四新文化一样,同属20世纪中国现代文化的范畴。与《新青年》文化先锋一样,现代新儒家思想巨子也是中国文化现代性建构不同面向的重要开创者。因而现代新儒学不是曼海姆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也不是艾恺意义上的反现代化思潮。现代新儒学是一种新传统主义、新保守主义、新心性主义、一种具有中国智慧的新现代性哲学。以现代新儒学为主要代表的后五四文化对中国现代艺术精神论的理论建构,起到了直接的引领和激发作用。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正是在后五四文化和现代新儒学影响下兴起的,属于整个后五四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新儒家生命哲学奠定了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的哲学本体论基础。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的理论生成,得益于五四新文化和后五四文化(尤其是现代新儒学)的滋养。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与之相互发明,成为现代新儒学在中国美学研究中的生动呈现。从总体上看,现代新儒学是一种诗性哲学。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借鉴了现代新儒学的生命哲学,受到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方东美等现代新儒家的生命本体哲学(价值形而上学)的深刻启迪。现代新儒家对宋明新儒学“内圣”之学(心性之学)“接着说”,并将其创造性地转化现代生命哲学和精神哲学。其中,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所阐发的以“意欲自为、生命直觉、调和持中”(63)为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哲学和人生哲学,张君劢《人生观》与《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1923年)所阐发的区别于科学的“主观、内在、直觉、自由意志”的新玄学(33—40,61—120)尤其是熊十力《新唯识论》(1932年)所阐发的“辟翕成变”“生生不息”“天人合一”(170—74)的生命哲学以及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1937年)所阐发的“生生之德”(165)的生命哲学等,对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影响深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即是现代新儒学哲学在中国美学史、中国艺术史领域的具体展开。现代新儒家对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哲学精神的研究与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研究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构织了中国现代人文学术史上一幅精彩而壮丽的精神画卷。
七、“中国艺术精神”论的历史地位和理论特质
“中国艺术精神”论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独特的理论品格。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乃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校正,是后五四时期对中国现代新文化的一种重建,是中国美学现代性建构的一个重要面向,因而也是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论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五四新文化巨子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弱项,强调引入西方民主和科学,这是其巨大的历史功绩。但是,五四先锋彻底地反传统,又有伤很多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而且在学理上陷于偏颇。其一,失去民族文化的本根和主体,所引西学焉能生存?其二,仅把西方文化归结为民主与科学,忽视接引西方的哲学文化(形而上学)、宗教文化,造成对西方文化认知的欠缺。殊不知,哲学精神与宗教精神从来就是西方文化之根本,如英国近代文化巨擘马修·阿诺德主张德性与智性并重,高度阐扬西方文化的“两希精神”,认为宗教精神与科学精神缺一不可;尼采则阐扬希腊文化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尤以酒神精神为根本。不仅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如理念论)与宗教文化(如基督教)成为西方古代的文化支撑,西方近代人文主义哲学和理性主义哲学是西方近代的文化支撑,而且形而上学也仍是西方现代文化的承诺,形而上学与宗教文化在西方现代和后现代时期仍在与时俱进地发展。然而五四新文化巨子如胡适、陈独秀等人都认定西方宗教文化和形而上学已被科学摧毁,因而胡适信奉“实证主义”,陈独秀主张“以科学代宗教”。这显然是一种片面认识。现代新儒学的兴起,正是对五四巨子上述两个偏差的校正,以期对中国现代文化进行重构。文化即生活样态或生活方式,而文化理念则是文化之道,没有文化“理念”和精神之“道”支撑的器物、科技、制度都只是偏于一般的“术”而已。正是由于五四新文化一味崇尚科学与民主,以之为宗教(或以之代宗教),失落了最高的文化精神理念,因而激发了现代新儒学的兴起,意在激活被掩抑的宋明理学心性本体论,力求以心性本体涵摄民主与科学,开辟现代中国人的文化理念和精神之道,回答中国人的生命价值之源和终极生存意义问题。有论者指出,美学在中国的使命从一开始或许就是超载的,而不仅仅是一门纯粹的美学学科。“中国语境里的‘美学’从确立之初就改变了其在西方学科体系中的疆界,而泛化为修养之学、性灵之学、上升为智慧之学和形而上学,贯通了艺术之道与人生哲学。”(吴志翔 2)诚哉斯言!如同19世纪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认为文学批评乃是生活批评,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者也同样不是在纯美学的意义上理解艺术,而是把艺术理解为人的生存方式和民族文化精神的感性呈现方式。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者倡导人生的艺术化和艺术的人生化,阐扬一种大美学观、大艺术观和大文化观。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心性体验为其核心,在此基础上贯通天人、道器,贯通自然、艺术和社会人生,旁及古人关于修养、教化、感悟、性情、精神、性灵、趣味、神韵和境界及其诗性话语。因而“中国艺术精神”论是20世纪中国美学和艺术研究领域一种有着独特现代性品格的理论形态,是一种以中国美学史和艺术史面貌呈现的人生美学、人文美学、人格美学、生命美学、体验美学、文艺美学、本体美学、超越美学或形上美学。
归根结底,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是为了追寻和建构现代中国人的精神价值和生命意义。“中国艺术精神”论不仅是对五四时期陈独秀“以科学代宗教”说的反拨,同时也是对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说的某种回应。陈独秀等人崇尚西方的进化论和科学主义,陈独秀在《再论孔教问题》(1917年)一文中提出:“真能决疑,厥惟科学。故余主张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253)显然,陈独秀对科学抱以无限的信心,使之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形上学之尊贵。与之不同,蔡元培先生则认为,人的精神作用有知识、意志和情感三种。由于科学进化的作用,宗教遭到科学的瓦解,因而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蔡元培认为,美感教育乃是从现象世界的美丽形式感抵达实体世界或形而上观念世界尊严感之津梁,因而倡导以理想之光和崇高之美来引导国民精神。蔡元培指出:“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蔡元培 5、68—71)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开创者们,显然不认同陈独秀的科学至上的观点,而是认同、响应和发展了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强调哲学精神和文化精神的重要性,因而高扬中国文化重道德、重诗性的优良传统,阐扬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和道德精神,以挺立的人格精神来涵摄科学技术,纠正“科学万能”的科学主义崇拜之弊端。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者大多在审美形而上学或艺术本体论的高度来阐发中国艺术精神,其中融会了艺术的感性、智性、德性、诗性和神性等多重精神蕴含。
由此,可以见出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自身独特的理论特质。作为后五四时期兴起的中国现代美学的一种重要理论思潮,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体现了自身特殊的学术旨趣与精神追求。有论者指出,“中国艺术精神”研究实为20世纪中国美学理论的一种重要审美范式(刘建平 10)。这是有相当道理的。本文认为,艺术精神植根于哲学精神和文化精神。艺术精神是在审美形而上学和艺术本体论意义的精神追求。艺术精神虽与哲学本体论息息相关,但又不是理论化的本体论知识体系,而是活生生的生命精神,是本体论的体验形态、感性呈现与鲜活性存在。艺术精神是人类不断追求文化创造和追问人生意义的生命精神,是人类生生不息地追求真善美终极价值的自由超越精神。中国艺术精神则是中华民族在自身生存本体论基础上的精神追求。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是一种以历史美学和历史诗学(或曰中国美学史和中国艺术史)面貌呈现的中国现代美学本体论和艺术形上学,所探究的都是关系到中国现代美学和现代艺术的根本理念(如艺术的生命本根、精神之道及其生动的感性呈现)等核心问题。一如德国古典美学在德国近代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在20世纪中国文化现代性建构、现代民族精神建构和民族新文化建设中同样发挥了重大作用。
八、“中国艺术精神”论的当代发展与理论创新
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为20世纪中国美学史写下了辉煌篇章,它不仅彰显了中国艺术审美精神自身独特的优秀价值,而且在中西比较和会通中重建现代中国人的意义世界和精神世界,对中国文化发展提出很多有价值的构想,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和宝贵的学术经验,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现代学术新传统。同时,其理论不足也激发了今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超越。
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不仅在港台和海外得到发展,而且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学界得到复兴和发展。从李泽厚等人的感性经验论哲学美学到中国当代文艺美学,都体现了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的学术传承与拓展。例如,李泽厚的新感性美学思想明显受到现代新儒家“中国艺术精神”论的影响。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李泽厚就率先研究现代新儒学,肯定其继往开来、应对挑战的理论价值。同时提出,“内圣”不仅是道德,而且还应包括整个文化心理结构,包括艺术、审美等。李泽厚认为,“从孔子开始的儒家哲学基本精神即是以心理的情感原则作为伦理学、世界观、宇宙论的基石”(310)。李泽厚融合现代新儒学、康德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并加以综合创新,在“美学三书”“三大思想史论”等著作中提出“儒道互补”“乐感文化”“天人合一”“积淀说”“新感性美学”“情本体论”“儒学四期”等理念,可谓对现代新儒学美学思想的继承和超越,是对“中国艺术精神”论的创新发展,成为新时期以来我国哲学美学所取得的最具影响的理论成果。继李泽厚之后,中国当代美学、诗学和艺术学领域,出现了不少研究中国文学精神、中国美学精神、中国诗学精神、中国文论精神以及中西美学和艺术精神比较研究的优秀著作。近年来,“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更是成为中国执政党在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文化理念,中国美学和艺术精神研究成为中国当代美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领域。当代中国文艺美学更是接续了“中国艺术精神”论的学术传统,注重艺术形上学和审美本体论研究,以建构当代人的精神家园为学术追求。对此,笔者已撰文讨论,兹不赘述。
毋庸讳言,“中国艺术精神”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缺陷。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断裂使得传统艺术精神成为一个和现代中国人的现实生活、生命情感失去了天然联系的瑰丽幻影”(刘建平 8),这确为警醒之论。“中国艺术精神”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传统艺术精神,而是对传统艺术精神的现代阐释和现代重构。中国艺术精神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的联系问题乃是至关重要的。“中国艺术精神”论的现代意义,取决于它能否和如何参与中国当代艺术生活乃至世界当代艺术生活的精神建构。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在探究中国上古艺术精神和中国中古士人艺术精神方面成就斐然,但对于中国近古艺术精神尤其是明清市民艺术精神则关注不够。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艺术精神”论暴露了自身的理论局限性。借用英国文化研究的术语,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普遍存在着文化主义(或文化至上论)的局限性。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对艺术精神与社会结构的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之复杂性、互动性也关注不够,亦需要超越。今人需要追问的是:如何认识中国文化自身的批判性?如何认识中国艺术精神的批判性?孔子尚且发明“诗可以兴、观、群、怨”的艺术价值论,这一“怨”字表明,反思精神和批判精神理应成为中国艺术精神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日新之谓盛德,中国艺术精神与时代精神血脉相连。早在一个世纪之前,素以文化保守主义者著称于世的辜鸿铭即在一篇学术演讲中预言:“我深信,东西方的差别必定会消失并走向融合的,而且这个时刻即将来临。虽然,双方在细小的方面存有许多不同,但在大的方面,更大的目标上,双方必定要走向一起的。”(149)王国维更是倡言:“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王国维文集》第一卷 71)百年前的中华学者尚有如此胸襟,今人更应奋发有为!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的理论遗产对于克服现代性社会工具理性单向发展的片面性,弘扬当代文化的人文精神和崇高品质,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论的深度和高度有了,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拓展中国艺术精神的当代性、丰富性与广度性,是当代文艺美学应特别用心的。应当立足于新的时代和全球化语境,扎根于当代生活的鲜活经验,挺立一种新时代的审美主体性和审美人格精神,吸纳和转化当今新技术革命的成果,参与当代世界艺术精神的对话和建构,推进当代中国艺术精神的创新发展。
注释[Notes]
① 见于宗白华在1921年一封写给朋友的书信《自德见寄书》,《宗白华全集》第一卷,第320页。
② 关于该文作者,或谓方东美所作,因而收入方东美文集中;或谓唐君毅所作,因而收入唐君毅文集中。笔者持第一种观点,认为该文为方东美所作。
③ 唐君毅在此前的《道德自我之建立》(1944年)一书提出,人的道德自我即是人的至善之心或心之本体,一种追求真善乐(真善美)之本心。该书有专节讨论人的“精神之表现”,认为求美是人的生命精神和理想精神之表现,见该书第56页。
④ 陶水平:“深化文艺美学研究,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江西师范大学学报》3(2015):11—21;陶水平:“铸就文艺研究的精神之鼎——试论文艺美学的精神建构价值”,《江西师范大学学报》6(2018):3—14。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蔡元培:《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Cai,Yuanpei.Selected
Works
of
Cai
Yuanpei
on
Aesthetics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1983.]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253—56。
[Chen,Duxiu.“Re-Discussion on the Education of Confucianism.”Selected
Works
of
Chen
Duxiu
.Vol.1.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3.253-56.]方东美:《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方东美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303—18。
[Fang,Dongmei.Modern
Chinese
Academic
Classics
:The
Volume
of
Fang
Dongmei
.Shijiazhuang: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1996.303-18.]——:《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 - -.The
Chinese
Philosophy
for
Life
.Beijing:Zhonghua Book Company,2012.]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兴涛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Gu,Hongming.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
.Trans.Huang Xingtao,et al.Haikou:Hainan Press,1996.]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卷四。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151—64。
[Hu,Shi.“The Significance of New Thoughts.”Anthology
of
Hu
Shi
.Vol.4.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151-64.]李长之:《李长之文集》第三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Li,Changzhi.Selected
Works
of
Li
Changzhi
.Vol.3.Shijiazhuang: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6.]——:《李长之文集》第十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 - -.Selected
Works
of
Li
Changzhi
.Vol.10.Shijiazhuang:Hebe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
[Li,Zehou.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Beijing: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85.]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Liang,Qichao.The
Complete
Works
of
Liang
Qichao
.Vol.1.Beijing:Beijing Publishing House,1999.]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Liang,Shuming.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Their
Philosophies
.Beijing:The Commercial Press,1999.]刘建平:《东方美典——20世纪“中国艺术精神”问题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
[Liu,Jianping.Oriental
Beauty
:A
Study
of
“Chinese
Artistic
Spirit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ijing: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2017.]鲁迅:《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50—54。
[Lu,Xun.Grave
.Beijing:The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1980.]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Tang,Junyi.The
Spiritual
Value
of
Chinese
Culture
.Jiangsu: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6.]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Wang,Ermin.The
History
of
Thought
of
Modern
China
.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2003.]王国维:《王国维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Wang,Guowei.Selected
Works
of
Wang
Guowei
.Beijing: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ress,1997.]吴志翔:《20世纪的中国美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
[Wu,Zhixiang.Chinese
Aesthetics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Wuhan:Wuhan University Press,2009.]熊十力:《新唯识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
[Xiong,Shili.New
Doctrine
of
Consciousness
.Shanghai: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2008.]徐复观:“心的文化”,《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211—16。
[Xu,Fuguan.“The Culture of Heart.”Collected
Papers
of
the
Chinese
History
of
Thought
.Shanghai: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2004.211-16.]——:《中国艺术精神》。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
[- - -.Spirit
of
Chinese
Art
.Shenyang:Chunfe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1987.]张君劢 丁文江等:“人生观”,《科学与人生观》。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33—40。
[Zhang,Junmai,and Ding Wenjiang,et al..“Philosophy for Life.”Science
and
Philosophy
for
Life
.Ji’nan:Shandong People’s Press,1997.33-40.]——:“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61—120。
[- - -.“Re-Visiting Philosophy for Life and Science,and Reply to Ding Zaijun.”Science
and
Philosophy
for
Life
.Shandong:Shando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97.61-120.]宗白华:“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98—112。
[Zong,Baihua.“The Origin an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ainting.”The
Complete
Works
of
Zong
Baihua
.Vol.2.Hefei:Anhui Education Press,1994.98-112.]——:“中国青年的奋斗生活与创造生活”,《宗白华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92—105。
[- - -.“Chinese Youth’s Struggles and Creations for Life.”The
Complete
Works
of
Zong
Baihua
.Vol.1.Hefei:Anhui Education Press,1994.92-105.]——:“看了罗丹雕刻之后”,《宗白华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309—315。
[- - -.“After Seeing the Sculptures by Rodin.”The
Complete
Works
of
Zong
Baihua
.Vol.1.Hefei:Anhui Education Press,1994.309-315.]——:“艺术学(讲演)”,《宗白华全集》第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542—82。
[- - -.“Art (Speech).”The
Complete
Works
of
Zong
Baihua
.Vol.1.Hefei:Anhui Education Press,1994.542-82.]——:“《黑格尔及其辩证法》编辑后语”,《宗白华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245。
[- - -.“Editorial Afterword ofHegel
and
His
Dialectics
.”The
Complete
Works
of
Zong
Baihua
.Vol.2.Hefei:Anhui Education Press,199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