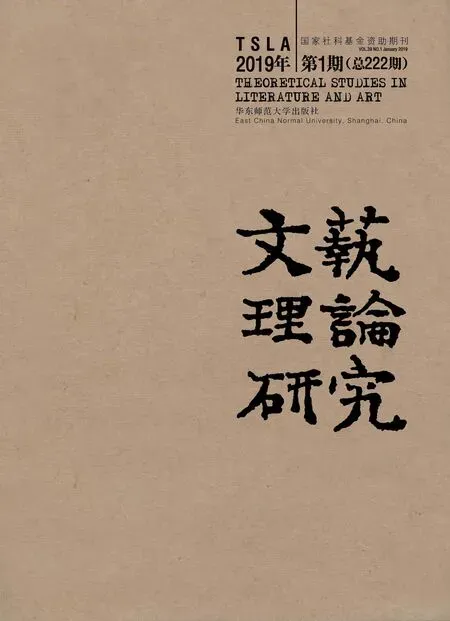何以流行,如何经典?
——市场运作视角下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媒介价值评估功能初探*
石 娟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发生、发展再到繁荣,与印刷资本的介入和以技术引领的大众传媒的出现及繁荣密不可分。可以说,百年中国通俗文学现代性特质的根由之一便在于文学与大众传媒的“合谋”。由此,以上海为中心,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了鲜明的市民大众文化特征,尽管这些特征受“大众”在不同时期文化素养及文学接受要求、认知水平的限制而不断发生着流变。而近现代通俗文学每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便是在大众传媒的渲染下,以“流行”的方式,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中,呈现出来的“默默的强势”。(范伯群60)这一切,归根结底在于那只“看不见的手”——与大众传媒相伴相生的通俗文学的生产与消费机制,以及由该机制必然带来的近现代通俗文学备受指责的“金钱主义”“趣味主义”“享乐主义”之种种。然而,时隔半个多世纪,当时备受指责的“金钱主义”“趣味主义”的部分作品中的优秀之作,在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认同的同时,也终于得到学界认可,成为经典,进入现代文学史。貌似悖谬的种种现实背后,实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文学与媒介之间施展魔力,彼此调适,使它竟然可以备受上至学者名流、下至贩夫走卒的一致推重,促成百年以来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一次又一次之“热”,深刻影响了各时期作家的文学创作行为、文体形式、文本内容,以及读者的阅读接受行为和观念,乃至社会的文化风尚……问题在于,在通俗文学的流行文本与经典文本之间,印刷资本与媒介在其中承担了怎样的使命?发挥了怎样的功能?在文本生产过程中,它们与文学活动各方究竟如何协调、牵制、冲突、让步,使得文本在问世时即可一鸣惊人,进而不断制造流行,使一个貌似粗糙的文本,能够穿越时空,成为经典?在梳理这一系列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回答一个问题: 何为“文学经典”?通俗文学经典与新文学经典之概念界定能否同一?若不能,差异何在?因为只有厘清了这些问题,接下来的讨论才能回归通俗文学本体。
时至今日,“文学经典”的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已有理论成果中,主流意见大致分为两类,朱国华先生对此进行了系统规约,他认为: 一类为“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一类为“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117—28)“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与卡尔维诺的“文学经典”观相似,认为经典的构成条件根源于文本内部美学的、思想的等等质素。而由于所有定义为经典的文本自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本质主义经典化”存在种种漏洞和缺陷,难以自圆其说。在此基础上,基于外部质素的“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应运而生。从泰纳(Tyner)、佛克马(Fokkema)、考尔巴斯(E.Dean Kolbas)、法兰克福学派(Frankfort School)再到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文学经典产生的条件与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捆绑到一起,而中国的文学经典发展实践也同样证实: 文学生产消费机制与经典的形成的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明代禁止私刻传布小说戏曲的出版政策恰恰成为明初经典作品出现较少的一个关键因素(陈大康135—82)。但是,如果文学经典的判断抛弃了内部质素,仅从外部条件来规约,显然同样会陷入另外一种逻辑暴力。朱国华先生条分缕析,最后得出结论:“我们今天的文学经典,是通过各种不同的经典化机制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获得其特权位置的。”(126)可见,文学经典的结构化原则根本无法通约,评价标准必须在其产生的特定历史语境中予以辨析。但是,无论文学经典产生的历史语境如何变化,无论评价标准是基于文本内部还是文本外部,如下几方面都应该被视为确立一部文学经典的必备条件: 1.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2.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独创性(包括类型的、叙事的、审美的等)。3.具有阐释的多义性(如学术的、媒介的、思想的等)。但由于历史语境以及接受对象的不同,通俗文学经典与纯文学经典之间存在一条根本性的差异: 通俗文学经典是“雅俗共赏”的,纯文学经典则有许多是“俗不能赏”的,如《百年孤独》《等待戈多》、鲁迅的部分作品,等等。从文学生产和消费的角度来看,在通俗文学范畴内,“雅俗共赏”又可以实现最广泛的“流行”。
那么,百年来,在“流行”与“经典”之间,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生产与消费机制通过何种方式在雅俗之间寻求平衡,它们又是如何协调彼此间的张力,使其中的优秀作品得以穿越时空限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的多重选择中,做到多元兼备?而以此为前提的百年中国通俗文学价值评估标准将如何认定,又会形成怎样的风景?
一、市场运作: 一种方法和视角
已有研究表明,中国近现代文学最为突出的载体变革,即报刊的出现。报刊突出的时效性特征,使得近现代以来依托于报刊媒介生成的几乎所有的文学文本,从酝酿、策划、创作、发表、传播,再到消费和接受,都有一种极为活跃的生产行为显著地贯穿始终——文学的市场运作。事实上,文学的市场运作行为并非始于近现代,它随着商品经济及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印刷技术的发展而出现,早期几乎完全集中于图书的生产与流通领域,且多以“广告”形式为主。现有研究表明,唐代便已有为招徕客人前往购买而打出的书业广告的雏形。至宋代,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书业广告从形式到内容都有了重大突破,形式和位置都非常灵活,或印在扉页,或印在序后卷末,字体也多粗大醒目,周围饰以种种花边栏框,以吸引读者。内容上,广告文字大量增加,用语也更加讲究,已具有吸引读者产生购书欲望的功能。到了明代,除了在封面设计、字体、装订等方面大幅改进外,已经有书商为了吸引顾客而找人在书前写作大量序跋了。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文化市场运作行为,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标志性变革: 1.它主要基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之后因载体变化而产生,以企业为单位而开展,内涵与古代私人刻书有本质的不同。2.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出版变为以在报刊上连载为开始,经过读者阅读检验之后再修订而出版单行本。无论从创作模式还是文本内容来看,都与古代直接出版单行本的单一形态有根本差异。3.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文化运作行为是全方位、立体且多角度的,涵盖了从报纸、期刊、图书到电影、广播、电视等多种媒介,形式更为丰富,推广的介质和形式更为多样。总的说来,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市场运作,专指由编辑/出版商发起,以赢利为目的的各种文学/文化生产活动,既包括编辑/出版商的策划、组织、编辑、推介行为,也包括读者与作者、编辑,读者与读者,作者与编辑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以及在市场运作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现象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应该说明的是,“市场运作”这一文学/文化生产领域的概念,不限于某一种媒介,无论是纸质载体(如图书、期刊、报纸),还是视觉图像载体(如电影、电视)声音载体(如广播),只要是以赢利为目的的,由出版商、媒体人发起的文学/文化组织、生产、出版、推介及互动等种种活动,一般都属于市场运作范畴。
应该说,文学进入现代之后,市场运作成为必需环节,任何一部作品,都需要依靠此环节才能走向读者,在现代生产消费机制环境中完全没有广告、宣传以及编辑介入的作品,要想走向最广大的读者,几乎难以想象,当然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假如有,也必定是小概率事件。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以市场为生存命脉,相对于新文学而言,市场运作行为展现得更为丰富,也更为活跃,通俗文学几乎所有的文学活动都发生在市场运作行为的全过程中,文学载体与媒介——大报副刊、期刊、小报、单行本、视听传媒,文学活动的各方——出版商、编辑、作家、读者乃至于诸多流行过并最终经典化的文学文本、文学活动、文学事件、文学形象……无不与此息息相关。按照热奈特的说法,从文学广告到序跋再到编辑点评,一切都有效地“包围并延长了文本”,有力地“保证了文本[……]在场、‘接受’和消费[……]”(转引自金宏宇3)因此,以文学的市场运作为手段进入文学文本生产与消费研究,就是在梳理、还原、剖析文学活动的历史现场,并从中发现通俗文学自身的活动规律、价值体系和评价标准,以此作为对裹挟于资本和媒介活动中的作家及其创作活动的评价依据。厘清每一部通俗文学文本参与市场运作的各方之间的关系、各方在文本中的功能和对文本的贡献、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发展轨迹,还原它们的本来面目,确立不同媒介文本的评价标准,它们对于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对于现代的吐故与纳新,以及作家在资本裹挟过程中的幸与不幸、坚守与退让、气节和情怀、得意与失意,都有待以文学市场运作问题作为理论出发点,各个击破。这是近现代通俗文学的独特性、复杂性所在,却也是近现代通俗文学研究中极富魅力之处。
二、报刊—单行本—视听传媒:从“流行”到“经典”之生成
以大报副刊、期刊、小报、单行本为主体的纸媒以及以电影、广播为主体的视听传媒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作用与功能,在21世纪以后的研究中,无论在史学还是文学著作中,已多有论述,它们共同建构了自晚清到民国中国市民社会令人炫目的文化场域。媒介的逐利目的,使文学以生产和消费的名义,摆脱旧有的“雅爱搜神,闲则命笔”的“自娱”功能,迅速担负起描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重任,在“消闲”“趣味”“娱乐”等种种表象下,在此消彼长的生存竞争中,通俗文学独有的现代性特质,在市民大众从“阅读”到“观看”“收听”的漫长岁月里得以确立。报馆、书局、电影院、电台这些文化资本企业,以合作共赢的方式,参与了通俗文学从“流行”到“经典”蜕变的全过程。其中,小说文本的生成具有典型意义。
(一) 大报副刊、小报、期刊: 通俗文学“流行文本”之生成
作为一部流行文本,所有的阅读“热”,都发生于报刊连载小说之时。如果我们把通俗文学作品从流行到成为经典视为一个完整的周期,那么,通俗文学与纯文学作品最大的不同即在于: 近现代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的“流行”绝大多数都是从报刊开始的。“流行”本身,即是读者对文本的阅读选择和价值评判的同一。而我们要关注的,则是读者所要选择的文本,究竟如何生成。
印刷资本的介入,报刊文学的出现,改变的不仅是文学叙事模式(如何写)、创作观念(为谁写)和发布媒介(如何发布)的问题,它更使得一个完整的文学活动由传统的“作者-读者”的“创作-接受”二维模式变为“作者-编辑-读者”的三方参与,因了编辑的介入,读者的意愿、编辑的意愿,不同程度地在文学文本中得以呈现,晚清到民国时期令人炫目的新与旧、雅与俗、传统与现代等种种令人炫目的时代景观,在以市场为生存条件的生产与消费机制下,在如上种种变革中,得到了丰富的书写。同时,报刊的出版发行方式,使得经历过“十年辛苦不寻常”的长篇小说一变而为“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创作者既没有时间也无心“优游删润,以求尽美尽善”,这倒也成就了“十日之内,遍天下矣”(解弢116)的广为传播之景观。随着近代市民阶层读者群的崛起,报刊连载小说以迥异于新文学的“与世俗沟通”之浅近平易视角、“单日畅销书”的叙事变革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宣传运作,沉潜到市民读者的价值评判、文化选择和生活观念中,促成了记录“今社会”的近现代长篇通俗小说的兴起和繁荣。
作为周期最短的出版物,清末民初所有的连载小说,一般都首先在大报副刊、小报和期刊连载。连载过程中的受欢迎程度,不仅可以决定连载小说的篇幅和体量,还决定了连载之后作品的走向。张资平《时代与爱的歧路》在《申报·自由谈》被黎烈文接手后果断腰斩,而周天籁在《东方日报》连载的《亭子间嫂嫂》却由计划中的四五万字一口气写到七十万字,累得作者几乎要“筋疲力尽而昏倒了”(二版),连载结束后仍受到出版商的关注并在极短的时间即出版了单行本。这一切,都与读者的阅读选择密切相关。一部小说是否流行,报刊的发行量是一个直接的指针,而更为直接的反映则体现在广告上。《啼笑因缘》仅连载一个多月,要求在《新闻报·快活林》副刊版上刊登广告的商家络绎不绝,最多的一天,在三分之二的版面上竟然刊登了7个大类18个广告。问题在于,这类报刊连载小说文本的“流行”是如何生成的呢?
由于媒介不同,个中原因有所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原则,那就是小说在连载过程中的读者反应会决定故事将讲到怎样一种程度。可是,由于资本基础、载体形式、周期以及媒体背景的差异,三种媒体对于连载小说“流行”的生产行为有很大不同。大报副刊由于很长一段时间内连载的故事数量有限,且拥有雄厚的资金基础,加之副刊主编具有一呼百应的号召力,所以作品在连载前、连载中甚至连载后,编辑、读者都能够积极参与。《啼笑因缘》连载前,主编严独鹤对“超等名角”张恨水“肉感的”“武侠而神怪”的指引,每日连载内容片段的精心设计,连载期间严谔声在读者中发起的多次调查,乃至后来张恨水的答复以及《世界日报》的改写,再到后来三友书社单行本的出版,都有编辑的全面介入,更不用提严独鹤凭借个人影响力在“快活林”的直接点评和间接推荐。但是,小报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由于小报难有大报那样雄厚的资金基础,加之版面受限,所刊广告十分有限,多数以内容赢利为主,不能也不敢只寄托于某一部未完成的小说,而是选择几部小说同时连载,以吸引更多的读者。与大报相比,稿源相对不足,所以小报连载小说编辑的介入程度没有大报副刊编辑那样深且明显,这就使得小报连载小说的流行常常带有很多偶然性因素。而期刊连载则又完全不同。与报纸相比,期刊周期较长,编辑的时间相对从容,参与的方式也更为多样。《江湖奇侠传》在《红杂志》连载之期,主编施济群除了在“编辑脞话”中有意识地加以推介外,更在连载过程中不断点评,使“施评”成为与小说同时呈现的一大亮点。而《红杂志》的老板沈知方更是深谙生意之道,不仅亲自登门拜访向恺然,还利用文化市场的生意眼,帮向氏谋划转向武侠神怪题材写作,并在《江湖奇侠传》连载之初就充分预见了市场之热,更充分利用杂志与图书版式的相近性,采取期刊与图书捆绑销售的策略,为了单行本出版方便,每个故事常常没有结束便戛然而止,甚至有时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完就告结束。且每一期《红杂志》上的《江湖奇侠传》部分单独排页码,字体字号也是当时单行本小说的通行标准,出版单行本时,不必重新排版,只要把杂志相应部分加印若干套,加以装订,贴上印好的封面,单行本便出来了。一套举措使《江湖奇侠传》从连载到单行本出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在读者中生产“流行”,保持热度。不过,这样印行的单行本并非“经典版本”——《江湖奇侠传》的经典版本应是后来也由世界书局出版的、经不肖生修订的版本,回目、内文与连载本都有差异。(叶洪生10—12)
时效性是报刊区别于单行本的显著特点,而报刊媒体必须在市场中求生存的属性,使得它必须在“公共空间”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努力担负起服务、沟通、引领的角色。传统长篇小说与现代报刊媒介的通力合作,使报刊连载小说这一现代文体得以诞生,时效性与“当下言说”市民文化心理需求的契合,满足了书局和报馆作为印刷资本对利益的最大化诉求。伴之而来的,就是由此而外化的“一种普遍的形式”,以及由这种“普遍的形式感”衍生出来的具有“一般性”和“渗透性”而非个性化的文学及文化现象,也即所谓“流行”(转引自高宣扬1)。报刊小说连载的形式和目的,皆是为了服务于流行文本的生成,此过程中受众在报刊编辑、出版商诸活动的推动及影响下,对文学的关注、参与与臧否的现场感和当下性,更成为现代都市的“传奇”记忆,深刻地改变了文学创作进程,并进而促成了一种新的创作关系——作家、编辑与读者三方参与的共同创作,以及新的叙事模式——以作家为主体的显叙事和以编辑、读者为主体的潜叙事之共生。这一切,都彰显了报刊连载小说以及近现代中国通俗文学最有意味的现代性特质。
(二) 单行本: 经典化之雏形
经典化是一个过程,穿越时空,进行多重的意义阐释,是经典化的两个必要条件。经读者阅读选择后流行的通俗文学文本,出于逐利目的,出版商(书局、出版社)会迅速对其进行二次生产,即出版单行本。无论是《留东外史》《江湖奇侠传》《荒江女侠》,还是《秋海棠》,几乎所有深受读者欢迎的报刊连载小说,单行本出版速度都极快,甚至有的出版商会为了一部热销小说而迅速成立出版机构,最极端的非《啼笑因缘》莫属。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单纯的逐利行为,但这种行为背后,却隐含了通俗文学生产与消费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 单行本是文学经典确立的必经之路。
从连载版本到单行本,阅读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出于满足读者连续阅读的需要,书商在从连载到单行本的形式变革过程中,会对作家有所要求,而由于报刊连载的时效性要求,作家难以对自己的作品精心打磨,也愿意对受欢迎的文本予以修订。因此,在单行本出版过程中,出版商与作家都有对原作进行修订和改写的愿望,并利用这一契机进行修订,使叙事、人物、脉络更符合单行本阅读需要,更重要的是,这一改写行为使一部长篇连载小说的结构和叙事不再因“单日畅销书”而显得杂乱不堪,可以借此成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别具匠心的故事。区别在于,不同作品,作家和出版商介入的程度有所差异。三友书社出版《啼笑因缘》,从连载结束到正式出版不过一个月左右时间,现所存该书各种版本,底本几乎均为三友书社版,而该版就是《新闻报·快活林》连载本的集成版,尽管在修订的一个月期内,《新闻报》也曾多次征集读者意见,但它并非作者本人认可的最终修订本。张恨水在《世界日报·明珠》上连载的《新闻报·快活林》改写《啼笑因缘》版,才符合他的个人意愿,才是他最终想要呈现给读书界的经典化文本,不幸的是,这一版本却因版权之争而胎死腹中(石娟166—70)。因此,对作家个人而言,一部作品能否流行,主动权掌握在读者手中,他无法控制,也不能预判,但是,对于要流传后世的作品,优秀的作家是有所追求的。也因此,出版商将报刊流行的连载版本改为单行本出版,在将文本进行二次生产以实现谋利目的之外,从文学活动的角度而言,对于文学现场中优秀作品的留存以及之后接受史家的评价,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这些流行作品,也恰恰因了这样一种方式获得了进一步修订和完善的可能(当然也包括修订得并不成功的作品)。不难看出,读者的阅读选择、编辑/出版商的二次运作、作者个人的进一步加工,是报刊连载小说走向经典的必经之路,而单行本的形式,恰恰为优秀的报刊连载小说穿越历史时空提供了可能,它使小说得以摆脱报刊载体难以保存的局限,以一个完整的面貌接受一代又一代读者的阅读和意义阐释,从而一步步走向经典。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启蒙运动的生意》中称:“启蒙运动存在于别处。它首先存在于哲学家的沉思中,其次则存在于出版商的投机中——他们为超越了法国法律边界的思想市场投资。”(3)市场对于启蒙运动如此,对于文学活动也同此。台湾大学梅家玲女士在呈现包天笑教育小说之社会影响力这段史实时即曾指出:“文学或社会的现代化原就不只是单一的、进化论式的线性发展;革故鼎新的理想追求,有时反而在保守传统的作为、在追求商业利润的过程中,得到意外的实践。”(116—17)在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的单行本出版中,作为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最有力的竞争对手,被称为“第二号书业”的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在其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世界书局的沈知方和大东书局的沈骏声,对于通俗文学特别是单行本的出版,贡献甚巨。《江湖奇侠传》的一纸风行,《浮生六记》的出版,类型小说及其代表作家的出现,文学商业“竞卖”模式的提出……这些日后留在通俗文学史中的诸多事件,都与两个书局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书局对通俗文学作品以谋利为旨归的诸多运作行为,从根本上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的走向,以其具体的文学实践,参与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对于以报刊为主要载体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报刊之于文学文本的功能在于提供了某一时间段内“流行”的“公共空间”,而单行本却使这些受到大众读者认可的畅销文本得以穿越时空实现“流传”,并为使它们成为经典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不难看出,现代出版—媒介业所以成为“经典”生成之动力即在于,它必须“广种”,但也必须“精耕”。
(三) 二度创作: 经典之确立与延续
中国近现代通俗小说多经由报刊连载、读者的阅读选择,再到书局组织单行本出版,与此同时,或在其之后,电影、评弹、说书、戏剧、戏曲等大众艺术形式会对受欢迎的作品以原作为蓝本进行二度创作即改编,这些改编或发生在作品大热的历史现场,或发生在作品大热的身后数十乃至数百年间,所有的行为,均由商业资本介入,直指赢利的目的,却又与启蒙运动一样殊途而同归,在穿越时空的文本阐释及价值实现过程中,实践着经典的再造。问题由此而来: 所有指向接受的文本改编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何在?
作为对文本内容的二度阐释,以满足不同受众需要为目的的改编行为具有鲜明的“文本兼性”: 一方面,改编行为首先是对原作的接受,却比一般意义上的读者接受更深入。一般意义上的读者接受是阅读的终点,绝大多数接受行为不具有再呈现的功能;二次改编接受的过程却是使原作面向更多受众的起点。在接受时,原作的复杂性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并以新的话语方式进行阐释,这些话语方式,有些是媒介的,有些是时代的,有些是意识形态的……长篇小说作品之中的多义在此环节中得以继续开掘和再度阐释,这些阐释和二度创作,由于受目的、定位、改编者的艺术水准、资本干预、时代风潮等因素的介入,取得的成就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 成功的二次改编,都可以使作品面向不同时代的受众,使其文本意义和价值得以再阐释和呈现,生命力得以延续。由于报刊连载小说篇幅多数较长,以情节取胜,而情节正是一个个相互之间关联密切的故事形成的“珠串”,每一个“小串珠”即高潮均可成为改编的优秀题材。近代以来的优秀改编作品如《空谷兰》《啼笑因缘》《火烧红莲寺》《金粉世家》《荒江女侠》《秋海棠》等莫不如此,而当代根据金庸、古龙、琼瑶等人的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作品,更将这一理念进行了充分实践。颇为极端的例子当属《火烧红莲寺》: 1928年,明星公司老板张石川抓住契机,将《江湖奇侠传》中的一节改编为电影《火烧红莲寺》,一把火连续烧了四年,尽管从第二集起就抛开原作天马行空,但仍是连续拍摄了十八集方告结束。然而,对于《江湖奇侠传》这部作品而言,故事的多义阐释并未到此结束,紧随其后,连环画《火烧红莲寺》、各大报纸广告版上的“火烧”系列电影海报,频繁呈现于20世纪30年代民国武侠文学生产场域之内,彼此映衬观照,以文化生产的名义,构成一个时代的武侠奇景,并辐射后世。与此同时,成功改编之后的视听作品,又促成了新一轮阅读热,穿越时空,使当年那些尘封在故纸堆中,与历史现场相观照的报刊连载作品的生命力在百年之后得以延续。如果说历史上的读者从报刊连载小说中读的是“今社会”和“眼前事”,百年后的读者欣赏的,恐怕是经过时间淘滤之后沉淀下来的历史、情怀、风格、文化和传统,以及作家穿越百年的叙事魔法和语言艺术,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及的“报刊-单行本-视听传媒”的“流行”到“经典”的实现通道并非线性的单向行进,有时单行本与视听传媒的二度创作常常是同时进行,甚至是三方同时进行,即报刊连载与单行本出版再到视听传媒的改编几乎同步,比如《江湖奇侠传》分集的单行本出版几乎就与《红杂志》连载同步,再如金庸小说的“旧版书本版”,而到了数字时代的当下,三方同步行进早已成常态,即媒介融合或IP运营,在此基础上构成的另一类文化商业景观,令人目不暇接。作为文本意义再阐释的方式之一,改编只是作品确立其经典地位的路径之一,与学理阐释、读者阅读的个体阐释等共同实现了对长篇连载小说的多义解读。而改编行为最直接的影响即是它成为文本走向流行的推手之一,从这个角度讲,改编此时具有多重功能: 一是使作品走向流行;二是使作品成为经典的多义阐释手段之一;三是使作品与读者之间因时空跨度而产生的陌生与冲突得到弥合。
事实上,除去媒介和技术因素,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作品从流行到经典生成的主客观因素还有很多,如时代风潮、文艺政策、观念变革,等等,但在诸多因素中,由于新媒介特别是报刊的出现,使得媒介形式与生产方式在文本流传的诸多因素中,显然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左右文本生产及消费能否流行乃至经典的关键力量,正如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所预言的那样:“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18)即后来的传世之语:“媒介即讯息。”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媒介生产与消费之关系和文本功能的角度予以展开,以窥通俗文学经典生成无限可能之一斑。而以今日的眼光看来,对于优秀的连载小说而言,报刊连载的时效性是一把双刃剑。它第一时间获取了小说的读者评价,推动了小说文本“流行”之态的生成,同时却也使得小说在面世时的种种先天不足成为必然。单行本出版在某种程度上对其进行了调整和补充,并使作品以整体的面目得到留存,为未来的阐释和发现提供了可能。至视听传媒具有“文本间性”的二次改编的深度接受和再阐释,文本的内涵和外延均得以延展,并为作品在不同时期赋予新的阅读价值和阐释意义,使作品的多义性得到相对丰富的呈现,经历了时空的淘洗,作品的经典价值和经典地位,终得确立。对于报刊连载小说而言,形式与内容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互文性,载体形式冲击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却也增加了小说文本的叙事容量和叙事张力。而文化资本的全面介入对于小说更为深刻的变革在于,它改变了传统小说创作中作家成长的方式、创作与接受的关系、文本的结构方式以及文本的接受形态。而这,是又一个内涵丰富的课题,有待在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
(本文在成文过程中,得到了徐斯年先生的悉心指点,特别致谢!)
注释[Notes]
① 唐至德二年(757年),成都卞家印本《陀罗尼经咒》首行印有“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字样。唐咸通二年(861年)前,长安李家刻本《新集备急灸经》书前有“京中李家于东市印”字样等。虽然属于“版权页”,却也未尝不是印刷者的自我广告。见肖东发: 《中国编辑出版史》(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70页。
② 宋刻《诚斋先生四六发遣膏馥》目录后的牌记云:“江西四六,前有诚斋,后有梅亭,二公语奇对的,妙天下,脍众口,孰不争先睹之。今采二先生遗稿灱于急用者绣木一新,便于同志披览,以续膏馥,出售幸鉴。”见肖东发: 《中国编辑出版史》(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72页。
③ 见《新闻报》副刊《快活林》1930年5月1日第十七版。
④ 这主要出于“粗放”,即为了赶时间、节约成本而不遑加工,也是为了出“同步”单行本。石娟:“民国武侠小说的副文本建构与阅读市场生成——以平江不肖生《江湖奇侠传》为核心”,《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016): 127—38。
⑤ 按: 那时印刷,先要检字、排字、打校样、校对、定版,然后打出“纸型”,用以浇成铅板,上机付印。“同步策略”不必重复前述流程,节约成本,缩短周期。
⑥ 本文仅针对晚清民国时期的媒介形式予以讨论,进入20世纪末至当下,则表现为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电子媒介。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大康: 《明代小说史》。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Chen, Dakang.History
of
Ming
Dynasty
Novels
.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0.]罗伯特·达恩顿: 《启蒙运动的生意: 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叶桐、顾杭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
[Darnton, Robert.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
édie
1775-1800.
Trans. Ye Tong and Gu Ha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5.]范伯群:“在‘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多元共生新体系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9—61页。
[Fan, Boqun. “Keynote Speech on the Academic Seminar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and Diversified Symbiosis System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Modern Popular Literature (Illustration Edition).”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Diversified
and
Symbiotic
Chinese
Literature
.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9.59-61.]高宣扬: 《流行文化社会学(第2版)》。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Gao, Xuanyang.Popular
Culture
Sociology
(The
Second
Edition
).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5.]金宏宇: 《文本周边: 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研究》。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
[Jin, Hongyu.Text
Periphery
:A
Study
of
Peritext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14.]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1年。
[Mcluhan, Marshall.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 Trans. He Daokuan. Nanjing: Yilin Press, 2011.]梅家玲: 《教育,还是小说?——包天笑与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说》。台北: 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Mei, Jialing.Education
or
Novels
? - -Bao
Tianxiao
and
Late
Qing
-Early
Republican
Education
Fiction
. Taipei: Rye Publishing Cite Cultural Business Co. LTD, 2006.]邱健恩:“自力在轮回: 寻找金庸小说经典化的原始光谱——兼论‘金庸小说版本学’的理论架构”,《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7.1(2011): 2—11。
[Qiu, Jian’en. “The Samsara of Independence: A Quest of the Origin of Jin Yong’s Classic Novels.”Journal
of
Suzhou
College
of
Education
27.1(2011): 2-11.]石娟:“《啼笑因缘》的两个版本——《新闻报》与《世界日报》之间的一段公案”,《新文学史料》3(2010): 166—70。
[Shi, Juan. “Two Editions of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New
Literature
Historic
Material
3(2010): 166-70.]解弢: 《小说话》。上海: 中华书局,民国八年(1919年)。
[Xie, Tao.Novel
Criticism
. Shanghai: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19.]叶洪生:“答顾臻弟问有关《江湖奇侠传》回目内文真伪及版本等事”,《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6.3(2010): 10—12。
[Yeh, Hongsheng. “A Reply to Gu Zhen’s Questions about the Genuine Chapter Subtitles and Contents and Editions of Legend of Yung Ching.”Journal
of
Suzhou
College
of
Education
26.3(2010): 10-12.]周天籁:“亭子间嫂嫂外传(二)关于写这篇外传的话(下)”,《东方日报》1941年4月2日。
[Zhou, Tianlai. “Biography of the Lady in the Pavilion (Second Part) and Remarks about Writing the Biography.”Oriental
Daily
News
, 2 April 1941.]朱国华: 《乌合的思想》。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年。
[Zhu, Guohua.Thoughts
of
the
Crowd
.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