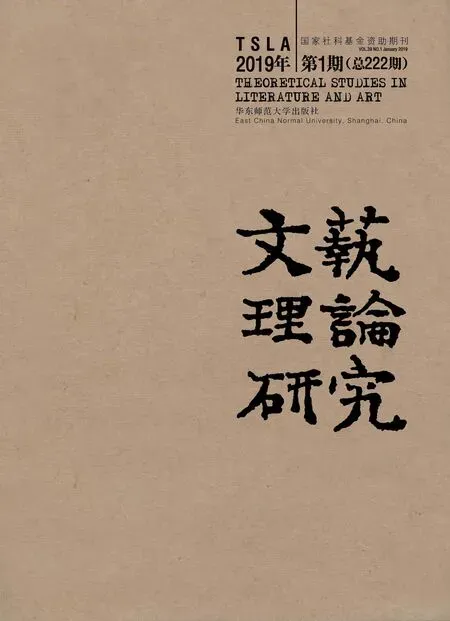福柯理性批判话语的深层路径及其“后理论”引题
刘 阳
福柯的理性批判话语首先集中于他对人类疯癫史的知识考古研究,也包含在他有关人类酷刑、监狱、惩罚制度以及性现象等主题的考察中。始终需要弄清楚却迄今其实仍还具有推进空间的关键问题,是贯穿上述考察的“理性压抑非理性”这根主线究竟摆出了理性与非理性的怎样的学理关系?尤其是,考虑到福柯在《疯癫与文明》等重要著作中频繁使用“非理性”一词、却似乎始终未及较为直接地对它与“理性”作过内涵的界说,辨析其理性批判话语的深层路径便不仅有必要,而且将能使人从中感受到一个微妙而关键的转变。让我们从考察福柯前期的理性批判话语开始。
一、前期“非理性”: 从“外在于理性”向“反理性”逐渐缩换
福柯大致从四个阶段来依次考察人类疯癫现象的演变。这四个主要阶段包括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17世纪以后、19世纪以后与20世纪以后。出现于它们中的、被福柯每每统称为非理性的疯癫,其具体内涵有无法被简单处理的复杂性。早在文艺复兴时期,麻风病业已消失,疯癫被人们从美学角度看待并由此成为了审美对象,即“自由地显示疯癫”(《疯癫与文明》70)。其显著例证就是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的文学作品,它们中包含某种无恶意而不乏浪漫色彩的,关于智慧的领悟与启迪。以下这段论述是福柯研究者时常援引的:“如果说知识在疯癫中占有重要位置,那么其原因不在于疯癫能够控制知识的奥秘;相反,疯癫是对某种杂乱无用的学问的惩罚。如果说疯癫是知识的真理,那么其原因在于知识是荒谬的,知识不去致力于经验这本大书,而是陷于旧纸堆和无益争论的迷津中。”(26)“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被福柯指认为是陷入了迷津的疯癫,因为它骄傲地夸大了理性主义,由此形成的试图包举生活世界、却实际上脱离了生活世界的学问观念,其荒谬性恰恰需要被堂吉诃德式的疯癫所“惩罚”。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癫,是与真理有关的想象。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看似失常之举,并不必然收获人们自以为站在合法立场上所发出的嘲笑,事情的真相可能正好是颠倒的,一位斗士与风车奋勇大战而浑不在意世人的嘲讽,高呼“宁可勇敢过头而鲁莽,不要勇敢不足而懦怯”(塞万提斯105),只为“执著地把正义的信念保持下去”(曼古埃尔170),不合常规的例外状态隐含着证伪常规的真理性力量。可当进入17世纪后,疯癫慢慢开始被从经济角度把握,被看成是需要通过劳动改造加以抑制与纠弹的情况。禁闭所把精神并未失常的违法者、流浪汉与染有恶习的游手好闲者等一网打尽,在强制性劳动中试图对其实施精神与肉体的全面束缚,疯癫开始遭到仇视,事实上的精神错乱者,连同若干精神正常者,都被目为“精神不健全者”而逐渐受到一种特殊制度的裁处(《疯癫与文明》57)。到19世纪,疯癫进一步又被从道德角度加以规训,被认为需要得到教化。精神病院成为企图矫正作为道德失误的疯癫现象的机构,矫正使疯癫不再引发恐惧,沉默与匿名都是疯人的症候,这就是思想异端愈来愈被视为疯子而受到排斥、打击的时代。而20世纪以后,疯癫终于成为医学观照的对象,包括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内的学说,承担起了对其进行治疗的任务。总之,与疯癫自身的性状(假如有的话)无关,疯癫史是一种沉默的考古学历史,是疯癫被说(建构)成了何种内涵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理性扮演了渐趋深化而无孔不入以致无往而不胜的压制者角色。因为按福柯,这四个主要阶段出现的疯癫症候皆被人们视作非理性,受到着理性的程度越来越深的压抑。粗看起来,理性压抑非理性的结论似乎至此就可以完成了。但福柯不止在一处耐人寻味地指出“即使它们能从社会表面将理性和非理性分开,它们依然在深层保留了理性和非理性相互混合及相互交流的意象。”(《疯癫与文明》196)如果理性与非理性在福柯的本意中并不泾渭分明,而有着更为复杂的情况,那就得来细究理性与非理性,尤其是非理性在福柯心中究竟指什么。福柯点明了“造就非理性的两种主要人类经验形式”,即“激情和语言”(182): 前者“认为疯癫在本质上是激情”;后者则“认为疯癫是谬误,是语言和意象的双重虚幻,是谵妄”(173)。这意味着非理性在福柯笔下至少具有两种不同的指称。对后一指称来说,“非理性的基本特征是谬误和梦幻,即盲目”(149)。这种非理性涵盖的是上述四个阶段的后三个阶段,主要涉及罪孽与道德过失等需要得到惩罚、规训的情形,但福柯指出,这些情形都是供观看的东西,成为了有别于文艺复兴时期自由地显示疯癫的“有组织地展览疯癫”(70),即被运作于一套套权力话语中的“真理重建术”说成了梦、幻觉与谵妄,以致“疯癫的含义就是非理性”(185),其话语运作实质被福柯总结为“使疯人和有理性的人相遇的具体环境已预先确定了非理性的失败”(236)。被这种话语权力所确定的,是非理性的消极的一面: 混乱、无逻辑、缺乏秩序等。较之于它,对前一指称来说,非理性却具有积极的一面: 展示与揭示真相。这种非理性,涵盖的则是上述四个阶段中的第一个阶段。世人眼中的疯癫,毋宁说是一种独特而难得的清醒。它当然也因诉诸激情而不排除某种与梦、幻觉与谵妄的交叠,但更有意义的是蛰伏在这些表象后的深沉而富于意味的上升性潜质。福柯敏锐地洞察到了这种潜质,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模糊不清的存在,西方的理性才达到了一定的深度”(3)。这表明两点: 其一,表面外化为疯癫的这种激情,在范围上确实不归属于理性,而归属于理性之外的区域地带,在这一意义上,疯癫诚然是非理性的;然而,其二,处于理性之外的这种疯癫又顺应着理性,甚至有助于深化理性,在深度上不逊色于理性而具备同样的上升特征,与理性从而存在着兼容的空间。堂吉诃德看似失了常的疯癫行为,隐含着庸常之辈难以企及的追求理想的热情,饱含的情感与向往理想的直观,实则都兼容着理性。这种既非理性又实际上能容于理性的疯癫,与米兰·昆德拉笔下包法利夫人的“傻”(愚蠢或天真)同工异曲,实为文学的深厚母题(如艾萨克·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反而是诸种有意无意压抑这种疯癫的力量,比如仰仗知识观念一味嘲谑堂吉诃德的庸众,相形之下披着理性外衣行疯癫之实,使事情倒过来沦为了看似合法的文明的疯癫。理性压抑非理性,由此鉴于上述复杂情形而无法一概而论。
从上述初步分析可以看出,福柯其实还原出了被理性所压抑的非理性的不同内涵,这种压抑沿循着把“非理性”从“外在于理性”逐渐微妙地缩小与偷换为“反理性”的深层路径。后两种内涵的共同点自然是非理性。区别在于: 前者不属于理性,却与理性相容;后者不属于理性,且与理性相斥。观察到这个初步结论的我们会同时审慎地想到,出版于1961年的《疯癫与文明》毕竟尚是福柯前期的代表性作品,其所还原出的以上深层压抑路径,应该说集中代表了福柯前期的理性批判话语,那么,它与福柯后期理性批判话语呈现为何种关系,有否在后者中进一步得以深化与推进,是我们极感兴味而不能不继续详察的重要问题。
二、后期“非理性”:“反理性”内涵得以强化
集中代表福柯后期理性批判话语的重要文献,首推其1978年5月在法国索邦大学所作并正式书面发表于1990年的演讲《什么是批判》以及稍后完成的《何谓启蒙》。这两篇前后顺承的作品围绕康德的启蒙观展开讨论与反思,必然触及对理性的重估。它们共同指向康德著名文章《答复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运动?》问世近两百年来的一个未被人发觉的盲点: 启蒙运动赖以将人从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使之变得成熟的理性,仍可能是权力的变种。这就值得对18世纪以来的启蒙理性——其得以形成与发展的时空恰好处于福柯上述疯癫史描述里的后三个阶段中——的性质重加审视了。
福柯发现,当康德以古典哲学的思维方式强调理性将人从不成熟状态提升至成熟状态时,他实际上暗含或者说预设了基于“一般德性”的“某种更普遍的律令”,而让人联想到牧师型的拯救—服从(屈从)观念模式。这种相信依据良心的指引便可在进步论意义上化不成熟为成熟的做法,被福柯与15、16世纪发生的“如何治理”“治理人的艺术”这一基本问题域关联起来思考,认为其“始于历史上社会治理化的巨大进程”(《福柯文选Ⅱ》178),并终于在警惕与反思中设想其为统治艺术的某种翻版。福柯由此不无犀利地指出,“对康德来说,自主根本不与服从君主相对立。”(《福柯文选Ⅱ》179)他特意提醒人们留意,康德的原文是一篇报纸文章,其客观上蕴含的特殊诉求是亟需得到观察的。包括实证科学的自信、国家系统与国家主义的发展在内的错综因素,似乎使这一从知识角度提出来的由启蒙理性设计的理性结构在表象之下埋伏有与之密切相关的压制机制,残存有自然法的观念痕迹,而令它在变了相的合理化进程中与权力仍相合谋,仅仅成为了一个被福柯称作“作为认知的历史模式之合法性研究”(《福柯文选Ⅱ》189)的,以指出错误与虚幻(真/假、已建立/未建立、合法/非法)为满意目标的合法性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令福柯生疑之处在于: 它是否忽视了历史维度或者说限度?
福柯对此交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一种有意无意相信在历史界限之上存在着超历史的拯救性合法力量的做法,无论如何是与一种权力背景暧昧地相伴随的。就像无法轻言崇高的确切所是,因为那可能沦入话语权力编织成的无形网络。如果启蒙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拉开帷幕的,它在深层次上依据并心向往之的理性便不再天经地义。福柯追问道,“那些过度的权力,那些治理化的出现,不是应由理性本身负起历史责任吗?治理化由于得到理性的论证,理性的责任更加不可推卸。”他从而试图把思考方向扭转为“对自以为是的理性及其特定的权力效果的批判”(《福柯文选Ⅱ》181—82)。这接续与强化了他前期理性批判话语的指向。启蒙是要使人摆脱非理性状态而走向理性,这句笼统而看似没有疑义的愿景表述其实包藏着福柯式的秘密。想要走向的这个理性目标既然在实践中因失去了历史界限而变得让人仰视以及反过来以接近牧师的姿态引人驯服,它的对立面便只能是反理性,在这里,“非理性”的内涵同样被不知不觉地(因为无法径直断言其为蓄意地)置换为了“反理性”,因为它客观上被认为没有接受那个无界限的理性力量与前景的规训,那个无界限的理性,相应地也便是变了种的合理性(权力的牢笼),依据福柯所示,康德以及沿循康德这一思想路线前行的后康德主义者(包括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些人物)展开如上启蒙实践时,表面上用理性去帮助受众脱离非理性状态,实质却是把受众框定为需接受理性合法化规训的对象,这由此便仍走在了反理性得以强化的老路上,与福柯前期理性批判话语得出的观察结论是前后承接的。
如此,接下来摆在福柯面前的棘手问题便是: 当还原出启蒙理性仍在某种程度上与权力背景相伴随,意识到现在该自觉拆解这一被掩藏了数百年之久的隐性符码时,作为还原者的福柯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假如任何试图用理性启蒙他人与自身的做法都必然暗含着权力的规训,那么福柯此刻不也正在试图从正面揭示出一种希望令人们相信的真相?他将如何保证自己的这套揭示性话语不重蹈权力背景呢?这个未及在《什么是批判》中充分展开的重要议题,紧跟着便在《何谓启蒙》中被福柯明确坦承了出来:“如果局限于这一类始终是部分的或局部的调查或检验,是否有被我们可能既未意识到也无法控制的更为广泛的结构所左右的危险呢?”(《福柯集》540)对此,尽管福柯提出了四条自辩理由(能力与权力的关系悖论、同质性、系统性与普遍性),其辩解显示出的某种勉强与无力却不难被感到,例如所谓同质性寄希望于人在从事上述拆解、还原活动之际自觉相应地“更改游戏规则”,便难免流于理想化的乌托邦筹划而显得语焉不详。纵然如此,一方面对此路向的深入剖析已超出本文的论旨,另一方面,虽然遗留下解决问题的未竟空间,却首先指出问题的要害,这也仍是根本意义所维系。事实上,福柯为此而指出了一个方向,那就是一反合法化老路,代之以凭考古学、策略与谱系化为标志与关键词的以历史与实践的关系考察为旨趣的事件化(Eventalization)观念与方法。
这种观念与方法在《什么是批判》的最后已得到了某些探讨,更为正面详尽的论述出自福柯一篇尚未得到汉语翻译的访谈录——《方法问题》。在那里福柯认为事件“不作为一个习以为常的事实或意识形态后果”而现身,即不“把分析对象归诸整齐、必然、无法避免与(最终)外在于历史的机械论或者说现成结构”,而是归诸“构成性的多重过程,”(Burchell, Gordon, and Miller 76-78)准确揭示出了事件化观念与方法的建构主义实质。语言在活的使用形态——话语中存在,话语是符号的区分,而符号的区分进而塑造着现实中各个个体的位置,即带出着现实的区分,被话语区分出的,表现为差异关系的现实中所必然隐伏着的这种(不等)权力,建立于“语言结构”(《疯癫与文明》235)之上,正是它赋予知识以建立在符号操作基础上的正当性证明或曰名义,使之成为在表象上实现自己的充满景观与仪式感的“建构艺术”(《规训与惩罚》188),从而改变对象在真空中不证而明的传统观念,实现其客观性。因此,一个对象被权力建构,归根结底是被语言符号所建构,去说一种知识对象即用语言去形成这种知识话语,语言的符号系统性质使之同时替代对象,将它置入符号的区分关系中加以理解,如何区分,往哪个方向具体区分,就形成了建构行为的具体话语条件,事件的发生从而便是个体对自我在具体环境中的受限性的主动展开,它使福柯的理性批判话语在揭示对象以祛魅的同时不至于自我取消,而仍获得了自己的位置。就是说,福柯保证自己这套揭示性话语不重蹈权力背景的一个做法,是不遮掩这套话语的权力隐秘来源,而从正面将这套话语的生产过程还原为一个事件——个体对一种知识对象的建构决不超时空地进行,而总受到自身所处于其中的一系列具体复杂的话语条件的限制与影响,其建构过程是一个事件。这样,福柯提供的走出上述“被我们可能既未意识到也无法控制的更为广泛的结构所左右的危险”(《福柯集》540)的方案,就是语言。这正是学界一般认为被康德所忽视了的维度(这样说当然并非苛责身处认识论时代的康德必然得承载语言论时代的主题),它的根基与端口是索绪尔发动的语言论转向。富于意味的是,福柯点出的这个方向并没有被由他奠基、稍后兴盛的“理论”运动走通,后者仍未从实质上跳出合理性(详后文分析)。
结合前后期理性批判话语看,福柯图绘出了这样一条理性压抑非理性的深层路径:“非理性”逐渐被从“外在于理性”缩换与强化为“反理性”。那么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微妙内涵转变呢?这就既得了解后两者各自的具体意识成分组成及其与理性的关系,也得了解两者在诉求上所针对所非之理性究竟是什么。这就会发现,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是词的歧义(“理性”一词承载的不同内涵)造成的,尽管相关学理在福柯充满独特行文风格的叙述中颇为清晰。需要进一步沿循福柯自身运思的踪迹(即如上所说的“激情和语言”),来勾连并适当反思相关概念的学理基础,以深入理解他所观察到的这个重要走向。
三、相关概念的学理基础:基于福柯自身运思踪迹的勾连
对应于福柯在疯癫史中划分出的第一阶段,非理性指外在于理性(arational),即不是理性也不反理性。不是理性,是因为它的范畴坐落于一片与理性不同的疆域。不反理性,是因为它虽然不属于理性范围,却又在某种程度上仍能与理性兼容,呈现为与之不互斥的心意能力。或许因此之故,法国的福柯研究学者弗雷德里克·格霍指认疯癫“与理性产生关联”(格霍6),产生关联,也即兼容。福柯所指认的能对理性产生积极促进与深化作用的堂吉诃德式疯癫,就是这种外在于理性的意识成分。一方面,从表层看,疯癫首先是一种情感,如前所述是福柯自己所说的“激情”,作为“疯癫的专横”(《疯癫与文明》24)动力的情感(emotion、feeling),毫无疑问是解读“外在于理性”的一个相关概念。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从深层看,我们能在福柯出版于1966年的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其前后期理性批判话语桥梁的《词与物》一书再次对《堂吉诃德》的论述中察觉到,疯癫“表达了对世界的凶兆和秘密的领悟”(24),实际上是一种“产生了诗歌和癫狂的面对面”(66),在想象中追求相似性而未被后来的同一性与差异性范式所轻视的(65—66),从而与柏拉图《伊安篇》中的迷狂以及普罗提诺《九章集》中的直觉一脉相承的直观(intuition)。直观,是解读“外在于理性”的又一个相关概念。这两个相关概念都在学理上有其植根。基于福柯自身上述运思踪迹的思想史勾连,有助于我们深入看清“外在于理性”这种思想方式的实质。
先看情感。作为感性引起的内在感情,情感与感性这个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有关。感性首先既非理性又兼容于理性,呈现出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情况更复杂的性质。对此,至少有以下两个证据。(一)从字面看来,感性似乎应当是与理性相斥的一种心意能力,近代欧洲大陆哲学中著名的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主要就是在此意义上界定感性的。这派学者将认识划分为朦胧认识与明晰认识,又在明晰认识下进而分出理性的明确部分与感性的混乱部分,其让低级阶段的感性认识上升至高级阶段的理性认识的诉求很明显,感性在此无疑是非理性的。然而,同一时期的鲍姆加登创立感性学(美学),却着眼于与理性认识相平行的感性认识的完善,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感性在此又不反理性,相反具有相当于理性的直观能力。因为感性作为人通过感官感知表象的能力,先天地具有空间与时间这两种直观的形式(康德42—43),感知到的不是自在对象本身的知识,而是涉及了观念的表象,康德对感性的界定便是“通过我们被对象所刺激的方式来获得表象的这种能力(接受能力)”(康德25),它因此兼容于理性。(二)感性在近代思想中的这种两重性,进入现代后又获得了新的命运。尼采尽管激烈反对理性,但他把非理性的出路定位于肉体,在克服主(思维、主体)客(广延、客体)二元论的同时仍滑向着身(精神)心(肉体)二元论,未及考虑到,肉体对于精神意识这一主体来说仍是客体,因而仍未动摇“精神唯一地维系于主体”这一二元论模式的出发点。这种局限,实际上便是将感性片面地视为反理性的产物。接着尼采往前走的关键,于是在于还原感性中并不反理性的一面,即在于证明肉体(此时便已不能再称肉体,而应称身体了)本就具有某种主体性,比如肉眼并不作为单纯被动接受外部信息刺激的感觉器官而出现,相反本就具有完形的视觉思维能力,这才可能真正克服身心二元论而超越形而上学。我们已知道尼采之后二十世纪思想的一大研究焦点就在这里,身体现象学沿此倡导的身体—主体,便为艺术活动的真理性提供了有力支持。
由于根源于感性,情感便相应地既非理性又兼容于理性,呈现比我们通常以为的情况更复杂的性质。这也至少有以下两个证据。(一)既然作为源头的感性具有如上两重性,情感相应地也有反理性的性质以及不与理性简单斥离的性质。前者不难在无意识、梦境与幻觉等同样离不开情感支配的反理性活动中直接找到证据。后者的典型证据则首推康德。他联结审美判断力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的依据,是证明崇高的热忱情感与人的思想境界及其道德律有关,《判断力批判》第23节便明确指出,崇高是理性概念(康德称之为“理念能力”)的表现,崇高判断中类似于宗教心境的情感,就允可了情感中理性因素的合法存在。(二)到了现象学那里,广义的生活世界接纳着在明见性中本真存在着的、现实的意义,这则是情感与理性共生的思想新背景。海德格尔在批判逻辑之“思”的同时,指明“克服流传下来的逻辑并不是说要废弃思而只让感情统治一切,而是说要进行更加原始,更加严格的与在相属的思。”(海德格尔123)杜夫海纳发现,人们在感知审美对象时已摒除对外部客观世界的留恋,而直接感知到呈现于面前的真理,真理蕴含在高度展开了的感性中,“它绝非一种无组织、无意义的感性,而是按照严格的逻辑展开的、述说着自己的感性”(杜夫海纳38),对之他称为“情感逻辑”,认为审美对象形成了一个协调统一的独特世界,其统一性不来自从外部可加以把握的理性逻辑,而“来自仅仅服从情感逻辑的一种内部凝聚力”(杜夫海纳216)。根据这些学理论证,就不能以常识性成见来判定情感与理性相对立(这的确是学界迄今仍每每存在的一种简单化处理),看到两者的兼容,或许才更有意义也更顺乎晚近学术进程。
再看直观。它又称直觉,同样既非理性又兼容于理性。这也至少有下面两个证据。(一)在一些情况下,直观明显是反理性的,这时我们着眼的是它内部那种拒斥建立在概念、判断与推理模式上的逻辑推导的特征,应该说,克罗齐著名的“直觉即表现”学说,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直觉的。新时期以来国内的诸多学术讨论将直觉视为理性的对立面,依托的意义背景应从此端来观察。不过,从广义观之,起源于拉丁文“观看”(intueri)的直观却是兼容于理性的,因为它可以具备直接把握整体,一览无余地洞见真理的能力,如康德所说“凡是能够在一切有所思维的行动之前作为表象而先行的东西就是直观”(康德47),其包括作为本源直观的智性直观与作为派生直观的感性直观。我们平常也说“第一感觉(直觉)重要而深刻”,这时我们的学理视野是从普罗提诺、托马斯·阿奎那、康德到胡塞尔与雅克·马利坦等思想家所持的直觉观,它涉及不借助逻辑推导却直接抵达事物真相、实现本质直观的心意能力。(二)尤其是康德区分联想与想象,认为前者是再生的,后者则是生产性的与主动的,它“起着合成引擎的作用”(Hall 151),进入“想象力与并非概念却与此同时以原初面目出之的知性的和谐状态”(Rogerson 37),行使先天直观能力以达成“想象的综合”(Heidemann 213),此时得以实现的主观合目的性是“面向全人类而普遍的”(Insole 155)。柏格森称这种兼容于理性的直观为“最高形式或最高水平的智力或理性”,以此来区别于“被降级为抽象的、失去人性的逻辑的理性”(祁雅理40—41)。法国现代宗教哲学家雅克·马利坦则称这种最高形式的理性为“智性”与创造性直觉,相信“不仅存在逻辑的理性,而且也先于逻辑的理性存在着直觉的理性”(马利坦66)。这便纠正了认定文学艺术反理性的尼采式理解,而为文学艺术在深层始终运作着的直观理性,提供了学理支撑。
对应于福柯在疯癫史中划分出的后三个阶段,非理性则指反理性(irrational)。依据福柯的还原,17世纪后的疯癫被不断建构为梦、幻觉与谵妄等似乎都与生理上的头脑混乱有关的情形。反理性,指与理性不相容而无法与之实现合作与并存的、排斥理性的心意能力,其主要涉及的具体内容包括无意识(unconsciousness)、梦(dream)、幻觉(illusion)以及一些虽无法令人感觉到,却在实际上刺激并引发回答反应的阈下知觉(subliminal perception)甚或其他本能欲求等。这三阶段中遭到禁闭、教化与治疗的疯癫者,包括后期福柯所认为的接受启蒙权力规训的个体,其疯癫并不是客观自明的,大量情形表明他们不仅在多数情况下保持着正常健全的思维与精神状态,而且从不乏第一阶段中那种积极促进与深化着理性的,具备揭示性的启迪力量的疯癫,只不过如今被权力(即如前所述福柯自己说的“语言”)一步步说成为患上了无意识,尤其是梦境与幻觉等症状的生理疯癫。非理性至此的内涵确实被缩小与悄悄地偷换了。原因在于,如果保持第一阶段那种兼容于理性的疯癫,社会秩序的统治将会受到愈来愈多的威胁,这些威胁,自疯癫者看来乃是正常的思想表达,自试图维持一种秩序的统治者看来却不利于统治的实施,而在不便正面压迫的情况下,后者便把前者本具有兼容于理性一面的疯癫不动声色地运用一套套话语编织、建构成生理疯癫,通过这类话语策略来强化规训,认为非如此不足以巩固权力的统治,即用话语策略来凸显与塑造疯癫的有可能反对理性统治的一面,这就把原先仅仅外在于理性的非理性给偷换成了反理性。
外在于理性与反理性的上述微妙差别,根源于理性(Reason)性质的复杂性。福柯勾画出的理性压抑非理性的人类思想进程,实质是把非理性从“不一定反理性,仅仅不同于理性”一步步偷换为“反理性”的过程,这是对原本具有两种客观内涵的对象注入自己的特定意志,则其所认为不应被反的理性的性质便浮现了出来,那就是主要起规训作用的理性,即福柯在不少地方称为“计算原则”(《规训与惩罚》101)或“精心计算的强制力”(153)的狭义的理性(Rationality)。它作为理性的狭义表现,主要涉及分析与推理——这实际上是试图去征服对象的规训性力量——的理性,是福柯描述的“西方理性进入了判断的时代”(《词与物》82)的证明,由此引发现代思想重新恢复其内涵的冲动,比如在诗思中重拾对存在的领会。依据程度的不同,合理性的积极一面是发展出了认识论成果(自然科学),其消极一面则是控制欲的凸显。因此,外在于理性,针对的是Reason。反理性,反(针对)的则是Rationality。前者顺应、配合与深化着完整的理性。后者所反的、狭义化了的理性,则是合理性。福柯顺次还原出前者与后者后所形成的上述理性批判话语,因而指向了理性(形而上学)逐渐得以强化的方向,合理性作为其强化标志可谓余响不绝。
四、“理论”在这一深层路径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福柯上述理性批判话语还原出的最后一站是精神分析学说。这是被晚近理论家醒目归入“理论的现代运动”的“理论”(Theory)(Birns 46)。伊格尔顿等人在讨论二十世纪文学理论的著述中每每将直接影响了拉康等理论家的精神分析专章化,更是我们熟悉的事实。看起来,在理性的强化之途中,“理论”扮演了某种推波助澜的角色?对此福柯并不否认,他是这样说的:“精神分析学用被观察者的无休止独白双倍强化了观察者的单向观察。这样,既保留了旧疗养院的单向观察结构,又增添了一种非对称的相互性,一种无回应的新的语言结构。”(《疯癫与文明》235)循其理路,像精神分析学这样的“理论”将疯癫置于权力的观察之下并建构出反理性成果,奥秘无非是善于发明“新的语言结构”,其包括“精神病学,尤其是犯罪人类学以及犯罪学的重复话语”(《规训与惩罚》19)。在这一过程中弗洛伊德“重新组合了疯人院的各种权力,通过把它们集中在医生手中而使它们扩展到极致”(《疯癫与文明》260),不仅精神分析学如此,进而言之,“理论”皆然,诸如“性落入了话语的掌控之中”(《性经验史》17)而逐渐产生出各种性别理论等情形,都成了可推导的题中之义。结合上文的分析,从福柯的叙述踪迹看,“理论”就应该成了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的同谋与推力。
然而,福柯自己难道不是“理论”运动的奠基者之一吗?我们知道,包括精神分析学说在内的“理论”滥觞于语言论学理。语言被索绪尔证明为是不直通事物的符号(替代品,即表征系统),其可理解性取决于符号在共时性结构(索绪尔称为言语链)中的可区分(差别)性,建立在区分基础上的符号的横向毗连与纵向对应共同创造着意义。作为替代品的符号不等于原物,却赋予原物以意义,沿此开启的语言论思想在逮住形而上学要害的同时,推动自明性范式向建构性范式发展,带出了二十世纪后期文学理论研究的新焦点:“理论”。因为符号的区分是语言的具体使用——话语,区分必然带出位置的差别(不等),说出现实中的等级,行使话语权力。“理论”的兴盛因而不仅是语言论转向的结果,而且与福柯沿此推进的奠基直接相关。斯图尔特·霍尔在《表征》一书中,将从索绪尔到罗兰·巴特的语言学诗学路向以及福柯的政治学路向完整界说为文化研究的内外因,准确道出了“理论”与福柯在语言论上的渊源。而语言论转向的根本意义,在于破除传统形而上学有关语言及物的符合论信念,去批判与超越它。这也是语言论的根本贡献。按这一学理寻绎,“理论”在本性上就是超越形而上学的。它之所以反对自明性(后者被乔纳森·卡勒称为常识性观点),是因为自明性掩盖了深层结构而成为合理性的来源: 取消情境而指向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在揭穿形而上学的要害——掩藏深层结构这点上,“理论”成就非凡,应该说对合理性作出了深刻反思。从福柯引发的这种实际影响看,“理论”就应当是与合理性无缘的。
问题于是出来了: 一方面成了合理性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旨在批判合理性,“理论”看似矛盾的上述两方面,似乎置福柯于奇妙的位置,即被自己所批判的对象拥护为了先驱,这该如何得到解释?其实这个表面上的矛盾,恰好道出了从福柯理性批判话语中延伸出来的意味:“理论”对合理性的批判是否彻底呢?这得看它自己是否从根本上化解了被它设置为批判对立面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分岔,否则它的批判就仍可能引发追问,而为合理性的变种留下可能。正是在这点上“理论”显示出了某种困境。
如前所述,深层结构不与表层结构平行相向,而始终存在着落差,这已被证明为是语言或者说话语的本性。因为我们看到的貌似自明的表层结构,无不是符号在深层进行精心操作(区分)并由此产生出位置差别的结果,一个符号在言语链上被安放于此位置而非彼位置,唯一的理由是要与别的符号相区分,至于如何区分,往哪个方向区分,并无必然道理可言而完全是随机的,但当它被安放于此位置并进而固定化后,便形成了话语权力。可见,只要用语言说话,就避不开深层结构的支配。这一来,离不开语言表达自身的“理论”,岂非也有一个被深层结构所支配并伪装成表层结构的问题?换言之,每当它试图从正面建构一种意义时,它总同时伴随有一种背后的话语权力因素在解构着它。即当它声称“形而上学自明性需要得到批判,因为它掩藏着深层结构”时,这句话的意义若想被从正面建构得合法而变得成立,就必须同时承认表达着这一意思时的它不具备某种深层结构,从而不至于因自己也需要得到批判而取消自己陈述这句话的资格。但这是做不到的,除非这句话不是语言,不是话。这的确是哲学严格思考问题的方式,就如美国著名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对相对主义者的质疑那样:“但是一个人如何可能前后一致地
坚持一个使得一致性概念变得无意义的学说呢?”(普特南183)同理,一个人也不可能在承认自身受制于深层结构的情况下主张“深层结构需要被揭露”。这样,依托于语言的“理论”如要实现意义建构,便不能不仍暂且掩藏深层结构,非如此不足以避免自我解构的命运。这是一种权宜的宿命。“理论”由此面临着有趣的悖论: 想要去解构别人的自己,始终却也存在着被别人同时解构的隐患。那么能否靠“理论”自身来突破这一悖论呢?为了不动摇自身得以成立的根据,它自然也是愿意在这点上积极营求的,即如果“理论”能在揭露对象深层结构时主动袒露出自己也同样处于深层结构中这一事实,使意义的建构不再困扰于同时被解构的隐患,当然最好。可“理论”仅凭自身无法达成这一点,因为我们很快发现,它的深层结构在符号区分中被二元化为了“说成”与“被说成”这两个固定的位置,即在不断的相同操作中重复着同一张底牌: 语言论。福柯正确地点出“弗洛伊德则回到疯癫的语言层面”(《疯癫与文明》185),是否疯癫,与对它的说法有关,沿此以进的拉康心理分析理论对自我—他者在横向轴线上的关系的凸显,更是语言论(一个符号的合法性,存在于与所有不是它的其他符号的区分中)的后果,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各种身份族裔理论,都是被这个共同的背景相继催生出并蓬勃兴盛的“理论”景观。美国学者杰森·波茨与丹尼尔·斯托特在出版于2014年的一部新著中形象地指出,“理论”虽能废除君主(monarch),却仍显著而固执地趋于“君主演替模式”(the model of monarchical succession)(Potts and Stout 3),这一模式就是语言论。从积极的意义来说,这让我们体会到了西方理论学术在学理脉络上有根有容的连续性。反过来的消极性,则是深层结构底牌因不断重复而变得理想化与不可经验,留下了被解构的隐患。德里达指认道,形而上学的症结在于“当场而且立即独立于经验主体性事件和活动的——这经验主体是追求理想对象的——理想对象无限地被重复而始终还是同一个对象”(德里达95),这启示我们,隐匿于各种“理论”背后的那张语言论深层结构底牌,因不断重复而使“理论”的运作常常看起来像是一种按部就班的,有固定线路可循而逐渐失去了具体可经验性的在场手法操作,与意图论发生了合谋: 操作惯性在重复中积累成了不变的意图,“说成”与“被说成”这两个位置被二元固化,与意图—效果模式合流。正如以色列学者伊莱·罗纳在出版于2015年的重要著作《事件: 文学与理论》中提到的,德里达解构在场的理由就是“程序性的相同反复”(programmed repetition of the same)与“固定的仪式过程”(fixed process of the ceremony),它们中和(neutralize)了事件的独特性而使之失效,故值得解构(Rowner 119)。迄今仍不绝于耳的指责“理论”热衷于拿理论去套作品与现象进行机械生硬嫁接的批评声音,实可谓为此而发。
可以重复操作的不是人,而只能是物(工具)。这与“理论”的外现形态——重复性的解码活动是一致的。自同一张语言论底牌出发,“理论”意在拆解自明性现象中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伪一体性(想想罗兰·巴特对建立于深层结构基础上的“纯逻辑现象”的符号学批判),这种拆解行为出于还原真相的意图,而理所当然地拥有及物(“真相”)冲动与指向,为的是通过揭露引起人们“原来如此”的恍然大悟感,从而是一种解码行为。客观上依托不及物的语言,主观上却重复着及物的意图论冲动,这个深层悖论才决定了上述表层悖论。物是二元论的产物,取道于合理性,不断重复操作,所依据的理性在性质上从而是合理性,它无意于上升与超越,而将眼光聚焦于不同主题内容在同一操作程序中的代换,形象地演绎着“合理就好”(“说通便行”“搞掂即可”)的字面义。所谓工具理性等分类意义上的理性,形象地表明物的工具性,也是合理性具体展开于其间的序列以及现代思想对理性进行批判的靶矢。“理论”以超越合理性为题中应有之义,却囿于重复解码的及物冲动而仍落入合理性。福柯看似留下了无尽悬念的论述,因而触及了复杂的真实。
看来,“理论”一方面如上所述,尚未从根子上摆脱合理性,另一方面又已融于语言论的必然发展进程而无法回头重新来过,它只能在现有情况下寻求自我更新之道: 既承认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在话语中的必然并存与分岔,又不让这种分岔流于解构性力量,而是努力来尝试使这种分岔创造性地行使对意义的建构。“理论”之后,可以认为是在这一语境下展开的新议题。怎样做到这一点?直接的回答当然是反思合理性对理性内涵的窄化,并进而引导其逐渐恢复与重新上升为完整的理性。这个带有抽象色彩的愿景,需要落实到具体操作实践中,即改变理性思维支配下不断重复操作深层结构底牌的做法,而同时改做两件事: 既承认并给出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的分岔(即承认语言形成的话语权力区别于从外部介入的意图性权力,也即承认语言的本性);又确保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在分岔中能并存,以使解构中有建构(即不让语言形成操作惯性,也即避免将符号的区分关系固定为二元位置以致重新与意图—效果模式或曰意图论合流)。
这意味着,让语言不去做及物的事(因为及物的事是语言也可能想做的,科学语言就有此倾向,这实际上是语言的非本真状态;底牌不断重复而成为操作惯性,即形成了意图,也即变成了去做及物的事),以免不断变陌生为熟悉(解码的快感或者说满意感正由此而生),而是顺从自身不及物的性质,不以任何理由与事物发生固定关系,却作为符号系统积极替代那试图令人熟悉的物(对象性存在),从而不断产生变熟悉为陌生的话语效果。顺从自身不及物的性质,即主动地(这三个字很重要)替代(而非传达)原物,这出自对未知的可能性的主动需要,而需要的主动产生便同时是情感的产生,它直接导出替代的后果: 想象与虚构——去替代原物不就是在情感中去想象与虚构出一个新“物”吗?而情感、想象与虚构的结合不是别的,正是文学。也就是说,语言对自身不及物本性的顺从,与感性、情感与直观(按胡塞尔,本质直观=个体直观+自由想象)等外在于理性并深化着理性的意识成分有关,这些意识成分典型地集中于文学,形成的是文学的思想方式,如同福柯所列举的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的作品那样。在此意义上,“理论”便值得积极吸收文学的思想方式而走向文学。虽然这不排斥研究者仍可以从深层结构角度祛魅式地研究文学,但符号的区分关系在文学中不再固定为二元位置,相反在区分中继续与不断地无穷区分,凸显自身话语构造以葆有无穷的陌生化活力,从而令深层结构支配下所可能产生的话语权力保持相互的制衡,在相对意义上走出合理性,又的确是客观事实。让“理论”在合理性操作中逐渐迈出更新自我的第一步(当然还不是全部)——吸收外在于理性的、文学的思想方式,因而至少是隐含在福柯自己的理论书写中的潜质。在一个不甚引人注目之处他曾表示:“如今是亟需通过虚构(fiction)来思考的时候了,在过去,这是思考真理的一种方式。”(Foucault 12)在理论叙事学的创造方面作了很好示范的福柯,引发了“理论”之后,或者说方兴未艾的“后理论”的文学走向的议题。探察福柯理性批判话语深层路径的最终意义,也就在这里。
注释[Notes]
① 就此而言,一项虽令人生畏,却深具意义与价值的学术工程,是将康德三大批判重新奠立于语言论视野,进行充满难度与现代色彩的“批判哲学的语言批判”(即纯粹理性的语言批判、实践理性的语言批判与判断力的语言批判),其成果的艰辛实现可望开出康德研究新境界。
② 有学者“想用小说原本技巧,打败小说”(栾贵明: 《小说逸语: 钱锺书〈围城〉九段》,新世界出版社,2018年)第2页,也是出于对小说创作自身是否隐伏有自我解构因素的敏感与兴味。
③ 基于此,情感、想象与虚构等虽也属于文学的性质,却非文学的根本性质,它们都派生于语言这一文学的根本性质,语言的创造性活动从而也才是文学的本义。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Burchell, Graham, Coli Gordon, and Peter Miller.The
Foucault
Effect
:Studies
in
Governmental
Rationality
.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Birns, Nicholas.Theory
After
Theory
. Peterborough: Broad-view Press, 2010.塞万提斯: 《堂吉诃德》下册,杨绛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Cervantes Saavedra, Miguel de.Don
Quixote
. Vol.2. Trans. Yang Jia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7.]祁雅理: 《二十世纪法国思潮》,吴永泉、陈京璇、尹大贻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7年。
[Chiari, J.French
Thought
in
Twentieth
Century
. Trans. Wu Yongquan, Chen Jingxuan, and Yin Day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7.]德里达: 《声音与现象》,杜小真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年。
[Derrida, Jacques.Speech
and
Phenomena
. Trans. Du Xiaozhe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9.]杜夫海纳: 《审美经验现象学》,韩树站译。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
[Dufrenne, Mikel.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s
. Trans. Han Shuzhan.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6.]Foucault, Michel. “Maurice Blanchot: The Thought From Outside.”Foucault
,Blanchot
. Trans. Jeffrey Mehlman and Brian Massumi. New York: Zone Books, 1990.7-60.福柯: 《福柯文选Ⅱ》,汪民安编。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Foucault, Michel.An
Anthology
of
Foucault
Ⅱ
. Ed. Wang Min’a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 三联书店,2012年。
[- - -.Discipline
and
Punish
. Trans. Liu Beicheng and Yang Yuany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
[- - -.Foucault
’s
Anthology
. Ed. Du Xiaozhen. Shanghai: Shanghai Far East Publishers, 2004.]——: 《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 三联书店,2012年。
[- - -.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 Trans. Liu Beicheng and Yang Yuanyi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性经验史·认知的意志》,佘碧平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 - -.Sexual
Experience
History
. Trans. She Biping.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
[- - -.Words
and
Things
. Trans. Mo Weimin. Shanghai: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1.]弗雷德里克·格霍: 《福柯考》,何乏笔等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Gros, Frederic.Michel
Foucault
. Trans. He Fabi, et al.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7.]Hall, Bryan Wesley.The
Post
-Critical
Kant
:Understanding
the
Critical
Philosophy
through
the
Opus
Postumum
. London: Routledge, 2015.Heidemann, Dietmar H..Kant
and
Non
-Conceptual
Content
. London: Routledge, 2013.海德格尔: 《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6年。
[Heidegger, Martin.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 Trans. Xiong Wei and Wang Qingji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6.]——: 《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 三联书店,1999年。
[- - -.Being
and
Time
. Trans. Chen Jiaying and Wang Qingji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9.]Insole, Christopher J..Kant
and
the
Creation
of
Freedom
:A
Theological
Problem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年。
[Kant, Immanuel.Critique
of
Pure
Reason
. Trans. Deng Xiaoma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4.]曼古埃尔: 《阅读日记》,杨莉馨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Manguel, Alberto.A
Reading
Diary
. Trans. Yang Lixin.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6.]马利坦: 《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刘有元、罗选民译。北京: 三联书店,1991年。
[Maritain, Jacques.Creative
Intuition
in
Art
and
Poetry
. Trans. Liu Youyuan and Luo Xuanmi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1.]普特南: 《理性、真理与历史》,童世骏、李光程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Putnam, Hilary.Reason
,Truth
and
History
. Trans. Tong Shijun and Li Guangche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5.]Potts, Jason, and Daniel Stout.Theory
Aside
.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4.Rowner, Ilai.The
Event
:Literature
and
Theory
. Nebraska: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15.Rogerson, Kenneth F..The
Problem
of
Free
Harmony
in
Kant
’S
Aesthetics
.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8.——以福柯知识考古学三种认识型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