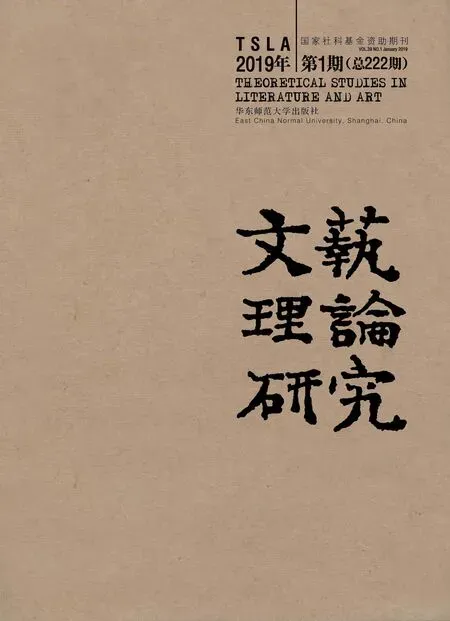“文章”经国与“作者”自觉
——《典论·论文》原文学批评的话语建构
张岳林 杨 洋
一、《典论·论文》“文学自觉”说批评中存在的问题
近20年来,学界质疑《典论·论文》的“文学自觉”说不断,以致影响对《典论·论文》文论价值的评价,这与此前肯定其为“文学自觉”说的观点形成了反差。何以学术界对同一文献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影响深远的“文学自觉”说何以仅是“有感而发”的命题?质疑“文学自觉”说的学理基础是否无可置疑?中国文论不依外来理论观念的价值究竟在哪里?这里涉及的问题显然无比重要。但从根本上说,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方法变化的结果。
鲁迅当年提出“文学自觉”说(504),显然是从西方文学观出发的,他是有批评的自觉意识的。那个时期西方纯文学观对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了根本的影响,无视这一根本文化背景,也是说不过去的。有趣的是,今天学人质疑《典论·论文》的学理依据仍是文学独立、审美等西方纯文学观念。那么,同样的理论出发点,何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从学术思想发展来说,鲁迅的命题是建构性的,而今人的质疑是解构性的。其本质仍有相通之处。换句话说,这都是“以西律例”(刘勇强109)的结果。虽然,我们承认西方文论具有理论的逻辑性,恐怕也不应忽略中国古代文论自身传统的自足性、原创性。
同时,梳理质疑“文学自觉”说的观点,我们还发现存在另一“以今律古”的现象,这主要是以今天对文学的理解和认识来批评古人的文学实践。其中最典型的是立足文本对作者原意进行考证的讨论。研究者以今天的文学观为参照,对曹丕时代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并申言这些结论是曹丕的原意,这显然是“以今律古”的结果。
从逻辑上说,所谓回到作者本身,终归也只是一种阐释方法。按照现代阐释学的观点,作者本意是不可还原的。文本一旦完成就具有自足的意义,而有待于读者的解读。这一说法当然有割裂作者与文本之嫌。如果承认作者的写作具有自己的语境,则问题在于,作者的言说有一定的对象,但又会涉及普遍的原理。加之文本一旦完成,又会形成自己的话语系统。关键是,今天要求回到作者的语境,仍是以现存资料为基础的(原始资料多少都有散佚,《典论》本身即不完整),与作者写作的原始语境未必是一回事。作者的阅读储备,面对的问题,与触发写作的契机,与今人的文本考证逻辑很难是一致的,甚至从思维逻辑说,存在相反的可能性。即使这种考证大体与作者写作状态重合,以此语境(作者同时期的文献资料)理解作者,则作者的独特性何在(即以普遍性去理解特殊性)?因此,语境还原只是理解作者写作的基础或参照。然而,多数研究者把这种参照当成或代替了作者的原意。
由此显现的第三个问题是,由于研究者的立足点不同,选择的材料不同,这样得出的结论难免对原文造成割裂,从而使得研究对象碎片化。如《典论》写作时间问题,有无针对性、针对谁的问题等等。甚至有的论文指出曹丕最看中的不朽文章是徐干的《中论》,以此否定曹丕的文学(诗赋)不朽认识。这显然是两极化的思维。最看中,不等于对其他的否定。“融等已逝,唯干著论,成一家言”(《典论·论文》238)这一既羡慕又不乏遗憾的表述(担心自己能否不朽),显然不是否定文学不朽。否则曹丕自己就陷入既知“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却又“以己(徐干)之长,相轻所短”的文人相轻的通病了。其实他对诸子的文学写作的评价是相当高的。如王粲“长于辞赋”,刘桢五言诗“妙绝时人”,陈琳“章表殊健”,阮瑀“书记翩翩”。虽然《又与吴质书》说:“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俊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未及古人”与批评“贵远贱近”似有矛盾,但能说明《典论·论文》观点的调整。)(237)但因“书”是私人信件,带有曹丕个人的艳羡,而论文是公共话语表达,而且七子并称,言徐干“粲之匹也。”(235)这显然是一体视之的。关键是,这类完全逻辑化、学理化的论证、考辨,使得鲜活、浑融的原文了无生气。
第四个问题是《典论·论文》写作目的的针对性与一般文学原则问题。在《典论·论文》写作目的的讨论中,指证其写作目的是针对曹植集团的或建安七子的大有人在。“事实上他是怕别人染指自己的权力而向邺下文人集团尤其是曹植一派提出的安抚与告诫: 文学也是建功立业,且能身后留名,当官没有什么意思,只能享乐一时,死了也就完了,你们要安心于舞文弄墨,不要急于争权夺利。这显然是一位初立太子训导群下的口气,并非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真正意识到了文学的崇高地位。”(徐正英28)但是,这类观点只考虑了其目的的消极意义,而忽略了曹丕立太子后论文的积极意义。即如杨修、丁仪兄弟等可以直接杀掉,何用专写一篇论文以示告诫。而把《论文》写作置于争太子的高潮阶段则更不可思议。“修临死,谓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为坐曹植也。”(陈寿419)连杨修都意识到曹丕立太子,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还谈什么争太子的高潮或对曹植等的劝诫呢(连曹植都想除掉)?
当然,从文本本身言,说针对建安七子是有依据的,说针对曹植集团则属背景联想(还存在自相矛盾: 既要求曹丕论文理论提纯,又认为其论文别有指涉)。问题是即使《典论·论文》针对建安七子立论,恐怕也不能仅以这七人为曹丕的写作目的。因为,作者具体的针对性和一般文学原则之间不可能完全重合。即使作者有写作具体的针对性,也有在流传过程中的思想增值,和文学普遍价值的参照。“文人相轻”“文气”“作者”“四体八科”等等显然是文学的普遍性问题。因此,《典论·论文》的价值更应该置于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来看。“《典论·论文》劝导邺下文士改变文人相轻的陋俗,用文章为曹魏统一大业服务。”(孙明君39)这类说法的价值在于,看到了《典论·论文》隐含的政治目的,但却以今人的学术眼光把其视为负面的价值。这自然不能完全彰明其意义。
第五是断裂的进化论眼光。视之为“文学自觉”是进化论的眼光,而质疑其“文学自觉”也内含着对其非进化论的批评。凡此都是一种断裂论,而忽视了曹丕论文的历史传统。
与此相关,是《典论》的写作时间问题。以现存资料考察,《典论》写于曹丕为太子时期是最可靠的。且不论后来是续或补《终制》,卞兰所见《典论》应是包含《论文》的。建安十六年为五官中郎将、丞相副时期说和黄初年间说,皆属对材料做了有利论点的处理。如“融等已逝”一语即可否定《典论》写于建安十六年之说。但论者以“大概”推测语气和唐代文献来否定建安时期文献的完整性,认为这是曹丕的感慨,非原文,其方法本身就需要质疑(也不符合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做出的“虑祥而力缓”的评价)(610)。《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曰:“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彫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朗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士,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彫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陈寿88)这里“初在东宫”应是基本时间节点,“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虽然会有一个过程,但是绕不开这个节点的。重要的是,这决定着曹丕写作的身份。
检讨这些问题,是希望揭示古代文学研究中今人方法的局限,即对今人批评方法本身的批评。跳出既定的观念、方法,尽可能贴近古人的思想、文化、文学语境,从古人的问题来理解古人的问题,而避免先入为主的方式造成对古人完整性、浑全性的割裂。即在中国文学传统完整的现象与现代学理逻辑的断裂间,寻找贯通的多重联接。由此从曹丕时代的问题来看,“文学自觉”与“不自觉”都不是曹丕关心的问题。“文”“文章”“文学”“文气”“文体”“论文”等等问题,都涉及文学,但又都不止于文学。因此,把其看成作家论或文章学论,显然都窄化了其内涵。其显现的包容性、浑全性、多义性,自是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特征所在。
二、“文章经国”的话语体系与“作者自觉”的论述轴心
(一) 建立在国家意识基础上的“文章经国”的话语体系。从曹丕写作《典论》的太子身份来说,国家意识应是他的基本出发点。而思想史上,随着尊王、一统等战国以来超越七国地域概念的大一统国家概念的成熟,法家以及汉代贾谊、晁错、陆贾、董仲舒等人的思想,都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刘劭曰:“建法立制,强国富人,是谓法家,管仲、商鞅是也。”(118)邦国观念是秦汉以后日益突出的社会意识。曹操本人就具有突出的法家思想。“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 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举贤勿拘品行令》166)故《三国志·武帝纪评》中说:“太祖[……]揽申、商之法术。”(陈寿39)事实上曹操礼、法并用,重霸术、法刑,常提桓、文故事,对他们以霸政、霸术,尊周攘夷,挺立国家、王室权威的做法表示认同。其《让县自明本志令》就明确说道:“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陈寿23)对此,有学者认为:“东汉覆亡之后的三百六十九年酝酿着一个大问题,牵涉整个国家从头到尾的重新组织,不仅曹操不可能预测,即作史者如陈寿及裴松之也仍没有看到演变之全豹。”(黄仁宇58)“我们从长时期大眼光看来,秦汉的大帝国在公元220年后已无可改组修正,只能重起炉灶的再造。”(黄仁宇64)而曹操的“唯才是举”的人才观即是围绕国家一统、“再造”“炉灶”的战略提出的。曹丕为太子,对此应该是有所了解的。重要的是此时具有这一权力身份的只有曹丕。曹操致力于军国大计,自然无暇顾及。曹丕被立为太子,正拥有这一权力身份。“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刘桢、王璨,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风,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钟嵘2)也就是说,其时真正担负起引领文人进行文化建设任务的只能是曹丕。但建安十六年,曹丕刚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与邺下文人游,相交甚欢,何况其时孔融已逝,建安十七年阮瑀也逝去。因此,其时写作比较成熟的“论文”条件并不成熟,但恰恰提供了发现问题的条件。
另一方面,《诗经》、楚辞、诸子以来,中国文学传统不是以文学的独立性、审美性为话语建构的目标,而是认可文学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面参与,并以其内涵的丰富与概念的浑全性,及其阐释的无限性,形成自己的原话语系统的。东汉时期,随着经学失去统治力量,“疾虚妄,”博学务实是社会思想发展新的动向。当传统儒家思想面对新的社会现实显得无能为力时,如何寻找新的思想资源,确立新的话语体系,是社会意识领域面临的迫切问题。桓谭、王充等人在学术、思想领域的非经学思想,已奠定了社会思想嬗变的基础。曹操“尚通脱”、重实用,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主张,打破了以“唯德”察举、征辟选士的制度,但在文化思想领域,如何建立新的话语体系,尤其面对围绕曹氏集团形成的新的士人群体,解决文士们的文化、思想认识,显然是更迫切的问题。因此,这一大的时代思想背景和曹丕的权力身份,决定了曹丕是站在北方基本安定、国家本位的宏观视野来看待“文学”事业(这也有利于超越汉魏禅代的观念之争),从而写作要求创立新的话语系统的《典论·论文》的。
第一,这从《典论》现存篇目总体来考量,国家、君、宗庙等都是其核心观念。如:
《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238)
《汉武帝论》:“孝武承四世之遗业,遇中国之殷富,[……]。”(241)
《周成汉昭论》:“皇天赫怒,显明厥咎,犹启诸金縢,稽诸国史,然后乃悟。”(245)
《内诫》:“古之有国有家者,无不患贵臣擅朝,宠妻专室。”(257)
《酒诲》:“孝灵之末,朝政堕废,群官百司,并湎于酒,贵戚尤甚,斗酒至千钱。”(260)
《佞邪》:“佞邪秽政,爱恶败俗,国有此二事,欲不危亡,不可得也。”(262)
《交友论》:“夫阴阳交,万物成;君臣交,邦国治;士庶交,德行光。”(273)
显然“经国”“朝政”“中国”“有国有家”“国事”等等正是作者关注的重心,《内诫》《酒诲》《佞邪》之论都事关朝政、国家之安危。就是《汉武帝论》《周成汉昭论》这些当时时尚之论,其隐含的主题仍与国家之事相关。
《自序》更把自己的成长与好尚置于汉末天下动荡的时代背景,在肯定个人趣味的同时,揭示了写作的重要性。其对曹操“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曹丕252)的称述,是含有文治武功的政治意图在内的。与徐干《中论》比较,《中论》系统论证名实关系,以批评当时社会的名不符实的现象,完全是一种文人思辨的视角。故曹丕《又与吴质书》称赞其“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110)曹丕《典论·论文》则明显统观全局。更有意思的是,据《魏志》所载,曹丕将自己论撰之《典论》及诗赋抄赠孙权、张昭,并昭示臣下,或许更能显示出曹丕的国家本位意识,而不仅是针对曹植等人。
因此,这与曹操“唯才是举”政策构成了呼应关系。陈寅恪指出:“故孟德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44—45)而曹丕由于领导邺下文人集团,故需要提出新的“文学”命题、标准,以引导广大文士为国家统一大业服务。其实从《典论》的命名看,这层意思更显突出。《说文解字》释“典”:“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几上,尊阁之也。”(200上)“五帝之书”自是神圣的典范了。
第二,概念使用的总体性。“文人”是一个总体概念,而不仅是一般个体写作者。“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常人贵远贱近”等等显然也是普遍性问题。即以建安七子论,曹丕为五官中郎将之前,孔融已逝,不属于邺下文人群体,甚至是曹操的政敌。那为什么还要讨论七子,而不是直接讨论邺下六子?因此,这显然也是一个总体性的概念,是以国家为本位的。通过建安七子的著述活动,建构一个国家本位的文化谱系,从而为新时代的文章写作提供标杆。
第三,从文体说,曹丕此论意在说明不同规定性的文体,需要创作主体具备相应的才能,而创作主体的才能往往有限,从而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文非一体,鲜能备善”,“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一结论(吴瑞霞91)。
这里隐含了一个矛盾。既然不同文体需要具备相应的才能,“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则文人相轻似乎是必然的。因此,曹丕必须站在更高的层面,从国家层面(“经国”)要求文人不以己长,轻人所短;而不是仅从文体层面各体相异来说。否则“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就是为文人相轻辩护了。这就是说,从国家文化层面说,八体都是服务于国家文化大业,都是可以“经国”的。“奏议”“书记”“铭诔”“诗赋”四科之分明显与国家政治关系有轻重不同的关系,即直接到间接的关系。
显然,曹丕的“文章”不是静止提纯的概念,而是具有兼容性的、发展的符号,包含对不同文体、不同地域作者的指涉。如对七子地域风格的概括,对不同文体特点的点评。重要的,这是对作者群体的关注,是总体化的公共性的文学(以文章为基础)观。凡此都说明《典论·论文》是以“国家本位”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的,是对“诗言志”以来政教伦理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以文学独立、审美等来批评之,反而忽视了其在当时的话语建构意义。
(二) “作者自觉”的论述轴心。因为,“经国之大业”是需要写作主体认同的。在此,笔者赞同《典论·论文》揭示了创作主体价值的观点(吴瑞霞90)。“才性”“文气”“生命有限”等等都是与作者主体相关的。虽然,曹丕的“作者”要更宽泛,与王充的“作者”观较接近。但其中的“诗赋”作者是超出了王充的。而这是贯通中国文学史的主要作者主体。
从《典论·论文》的论述看,曹丕的论述包含了创作主体的内在修养、个性的显现、才学的储备、对文体的掌握等等方面。论文直接从“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入题,批评“文人”“善于自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不自见之患”。并提出了解决的思路“审己以度人”。这些都是创作主体的自身问题。而“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典论·论文》238),如何超越个体生命局限,更是创作主体的现实困惑。由此提出“未若文章之无穷”,以“文章”参与“经国之大业”,实现不朽,显然是必由之路。这样,论文最后归结到建安文人中实现了著述不朽的徐干身上。首尾呼应,结构完整。
以此论述轴心论之,创作主体自觉追求“经国之大业”,必然强化“作者”的自觉,通过“奏议”“书记”“铭诔”“诗赋”各体文章的写作,则是实现声名之不朽的最佳形式。
同时,提出“文气”说,肯定作者的才性,也就肯定了个人兴趣,使得文人关注到自我,发现自我。在生命有限的感悟中,强化了自我认识,强化了文人性。曹丕在《典论·自序》中谈到自己对棋、剑等技艺的喜好,其创作中多涉及宴饮、游乐、田猎、交友、相思等个人情感,这些都是个人性的。故钟惺评曹丕“文帝诗便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士气,不及老瞒远矣”(63)。这种“文士气”对邺下文人的影响应该是深刻的。在他和曹植的引领下,文士们畅饮西园,同题共赋,呈才使气,造就了文学的一时繁荣。创作主体到曹丕这里明显被强化了。其中个人才性、个人之“文气”、个人情趣等内涵,都有助于文学作者的自觉。
三、文学批评的原话语建构
置于中国文学传统,曹丕提出的这些概念都有自身丰富的意义。“文人”“文气”“文章”“作者”“文体”等等概念,虽然都渊源有自,但结构在一起整体讨论文章写作,写成文论史上第一篇论“文”之文,仍是曹丕的贡献。关于这些概念的内涵与意义,学界讨论已很充分,此不赘述。问题在于如何避免碎片化认识与纯技术性学理操作?中国古代文学及其批评一直是在具体的文学实践和批评中发展的。《尚书》的“典、谟、训、诰、誓、命”等已包含分类的意识,从中可以看出使用者的身份、实施对象、用途等。“诗”六义之风雅颂赋比兴是更专门的分类,涉及内容、音乐与形式等,但不是文学总体概念层面的。刘歆“七略”之“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这是文化学(图书)意义上的分类,其中《诗经》归于“六义”,“诗赋略”专指赋和歌诗。前者是经学意义上的,后者包含文体意义。这种区分明显受经学的影响。王充对文人、鸿儒等的区分,和结撰篇章的要求,则是子学意义上的。至少,到曹丕提出“文章”概念,是一个最接近文学,又具体区分为四体八科的原批评话语。诚如论者所说:“这说明自东汉中期到汉魏之际,‘文章’概念的外延渐渐收缩,集中在那些可以展示文采和作者个性特征的文体上了。”(李春青93)
就其含义来说,在曹丕之前,先秦“文章”主要有纹饰、礼仪制度、文章博学等内涵。汉代则指文辞、篇什、文章著述。如杨雄以为:“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班固3583)其“文章”包含有“经”“传”“史”“箴”“赋”“辞”等内容。而曹丕的“文章”概念则剔除了“经”“传”“史”“箴”等,尤其加进“诗”这一中国文学最重要的文体,这在普遍宽泛的“文章”概念时代,显然有利于文学文体的凸显。
从其批评内涵说,中国诗论史上影响深远的“诗言志”,就是以“教胄子”的政教伦理为核心的(钱志熙7),而“经国之大业”从政治实践高度,把限于“诗”的“言志”,变为“文章”共同的思想追求,并紧密联系建安文学“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时代风格,使之成为新的“文章”写作标准,这是有其自身意义的。联系汉末天下大乱,社会动荡,人民离散,“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现实看,通过“作者”主体的激活,以“文章”参与到社会秩序重整的“经国大业”中,实现个人价值的不朽。这体现了曹丕文学观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并在公共性话语建构中为个人性留下空间。曹丕本人的创作就可说明这一点。其游仙、宴饮、交友、思妇、生命哀悼等等题材都不是军国大事,曹丕和文士们一起“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范文澜58),个人性的情感、情趣得到充分展现。
同样,“文人”“文气”“作者”“才性”等等都是具有原话语意义的。其中最有价值的内涵都与文学写作相关。“文人”是一个阶层,还是一种身份,学界目前还有争议。但就曹丕、曹植、建安七子等人来说,文人显然只是一种身份。“文气”是从孟子等那引申过来的一个概念,通过“清浊”之别,强调了个性的差异和先天禀赋等因素,赋予了这一概念丰富的文论价值。“才”即“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一般理解为“曹丕所谓的‘才’是对创作主体的学问、见识、智慧、能力的综合评价,它与传统的‘德才’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吴瑞霞90)。这是需要主体努力和自觉追求的。
四科八体的文体分类意识同样具有原话语意义。“奏议”“书记”“铭诔”“诗赋”不仅是具体的文体,已包含了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两种主要文体,即“诗赋”之“诗”,与其他六体之“文”。后来文体分类虽然越来越细,但大体没有超出这两大类。而且,八体虽是以“经国”的实用性强弱、直接性紧密排列的,但“诗赋”排列最后,恰恰体现了“诗赋”政教功能的趋弱,和文体属性的独特性,直至独立性,这已为文学独立预留了空间。
从文学史的实际影响说,虽然《论文》的概念大都渊源有自,但以曹丕的太子身份,赋予其总体化的纲领意义,其影响还是深远的。杨雄、曹植等诗赋小道的表述在当时其实有干扰人们对文学价值认识的嫌疑。《典论·论文》一出,显然有以正视听的作用,至少,以“文章”提升了诗赋的价值。这在古代原文学观的话语传统中,应是毋庸置疑的。还是刘勰说得明白:“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586),指出了政治身份对文学的巨大影响。
以上的分析还是浅层次的,但足以说明《典论·论文》的原话语建构意义。总之,曹丕的文章概念大于文学概念,但包括文学概念。视之为现代的文学自觉,是拔高了曹丕的《论文》;在曹丕处看,可能是“窄化”了。甚至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以此为《典论·论文》的价值,殊不知反倒取消了《典论·论文》的独特价值。因为,曹丕关心的是要建立新的,包括文学在内的话语体系,和新的“文章”标准。这当然是建立在文体区分基础上的。重要的是,不同的文体都应上升到“经国之大业”高度,以其各自的独特性作用于共同性,而形成新的文章体系。即以实用性文章为核心,辅之以审美性文章(诗赋),而成就不朽之盛事。
这显然属于文学公共性话语的范畴。前文提到,曹丕论文是对作者群体的关注,是总体化的文章(文学)观或文学纲领。由文章不朽开辟了文学公共性的主导价值方向,为文学(诗赋)确立了主流价值范围。而文士们追求政治理想遭遇的种种现实落差,则强化了他们的个体性、情感性,从而深刻地影响着文士人格、作者身份的历史形塑,在荣、辱、进、退之中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最终也影响到文学观的发展。这显然不符合文学独立、审美等现代文学观标准。因为现代文学观是建立在个体独立、人性解放的现代启蒙预期之下的,具有丰富的人性要求,甚至是按照进化论的线性逻辑预设的。但这显然不可能是曹丕时代的话题。
吴承学讨论“文章学”概念时认为: 讨论中国文章学成立时代必须把“文章”与“文章学”看成是动态的、有弹性的历史概念,所有相关问题都要从古代文章学原始的具体语境出发,尽量避免以一个固定的或后起的概念为尺度去衡量整个中国文章学(140)。其实不仅“文章”“文章学”概念,“文学”概念也可以作如是观。曹丕的“文学”观体现了它的历史性、实用性、兼容性和多义性。因此,单向度的批评反而可能掩盖其意义。
注释[Notes]
① 质疑“文学自觉”说的有: 刘朝谦认为曹丕的文章不指文学,而是文章理论批评,曹王还没有认识到文学作为一种艺术的、审美的、独立于政治的自由形式的不朽性,还没有把握住文学的审美本质。参见刘朝谦:“《典论·论文》新论”,《四川师范大学学》3(1988): 1—9。孙明君认为《典论·论文》不是“自觉时代”的“号角”,它并没有打破儒家传统观念,相反,它要努力使文章成为经治国家的工具。《典论·论文》劝导邺下文士改变文人相轻的陋俗,用文章为曹魏统一大业服务。参见孙明君:“曹丕《典论·论文》甄微”,《清华大学学报》1(1998): 34—39。汪春泓认为其主旨却是要消弭受儒家经学浸淫至深的士人的抵抗情绪,使士人与世无争,惟以著述为追求。参见汪春泓:“论曹丕《典论·论文》”,《江苏大学学报》3(2002): 38—42。赵敏俐认为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首倡的“魏晋文学自觉说”并不是一个科学的论断,而鲁迅先生接受这一说法本是一种有感而发,虽然具有一定的学术启发性,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文学史规律性的理论判断。“魏晋文学自觉说”不能全面地描述中国中古文学的发展过程,它影响了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和本质特征的认识,因而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中不适宜使用“文学自觉”这一概念。参见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2005): 155—67。
② “疾虚妄”是王充《论衡》的主旨,意在反对当时盛行的“奇怪之语”“虚妄之文”,而体现出求实尚用的思想。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班固: 《汉书》标点本(卷二十二)。长沙: 岳麓书社,1993年。
[Ban, Gu.The
Book
of
Han
(Punctuated Edition). Vol.22.Changsha: Yuelu Press, 1993.]曹操: 《曹操集校注》,夏传才校注。河北: 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
[Cao, Cao.Annotated
Collection
of
Cao
Cao
. Ed. Xia Chuancai. Hebei: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13.]曹丕: 《曹丕集校注》,夏传才、唐绍忠校注。河北: 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
[Cao, Pi.Annotated
Collection
of
Cao
Pi
. Eds. Xia Chuancai and Tang Shaozhong. Hebei: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13.]陈寿: 《三国志》。北京: 中华书局,1982年。
[Chen, Shou.Three
Kingdoms
.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金明馆从稿初编》。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1980年。第47—54页。
[Chen, Yinque. “A Note to ‘When Zhong Hui Completed His Disquisition on the Four Roots of Capacity and Nature’in the ‘Literature’ Section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Collected
Essays
of
Jinming
Library
:The
First
Part
.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0.47-54.]何文焕: 《历代诗话》。北京: 中华书局,2004年。
[He, Wenhuan.Poetic
Remarks
in
Past
Dynasties
.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4.]李春青:“中国古代‘作者’观的生成演变及其文化意味”,《文艺理论研究》5(2013): 87—102。
[Li, Chunqing. “The Gestation, Evolution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of ‘Author’ in Ancient China.”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5(2013): 87-102.]刘劭: 《四部丛刊初编·人物志》。上海: 上海书店,1989年。
[Liu, Shao.A
First
Edition
of
The
Four
Categories
of
Books
.History
of
Characters
.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1989.]刘勰: 《文心雕龙注》,范文澜注。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Liu, Xie.Annotation
of
The
Literary
Mind
and
the
Carving
Dragon
. Ed. Fan Wenl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58.]刘勇强:“一种小说观及小说史观的形成与影响——20世纪‘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现象分析”,《文学遗产》3(2003): 109—24。
[Liu, Yongqiang. “The Formation and Influence of a Fictional Notion and the Historical Outlook over Fiction: An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Judging Chinese Fiction with Western Exampl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Literary
Heritage
3(2003): 109-24.]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04—15页。
[Lu, Xun. “Style and Essays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Herbs and Wine.”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 Vol.3.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504-15.]钱志熙:“先秦‘诗言志’说的绵延及其不同层面的含义”,《文艺理论研究》5(2017): 6—18。
[Qian, Zhixi. “The Evolution of the ‘Poetry as an Expression of Aspirations’ Theory and Its Multi-layered Significance.”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
-ture
and
Art
5(2017): 6-18.]黄仁宇: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
[Huang, Ray.Talks
on
Chinese
History
by
Hudson
River
.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2.]孙明君:“曹丕《典论·论文》甄微”,《清华大学学报》1(1998): 34—39。
[Sun, Mingjun. “An Investigation of Several Aspects of Cao Pi’s ‘A Discourse on Literature.’”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 1(1998): 34-39.]吴瑞霞:“关于《典论·论文》对创作主体价值的探析”,《武汉大学学报》4(1999): 90—93。
[Wu, Ruixia.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Value of Creative Subjects in ‘A Discourse on Literature’.”Journal
of
Wuhan
University
4(1999): 90-93.]吴承学:“中国文章学成立与古文之学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12(2012): 138—56。
[Wu, Chengxue. “The Essay Compo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lassical Prose in China.”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2(2012): 138-56.]许慎: 《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Xu, Shen.Notes
to
Explanations
of
Characters
Simple
and
Complex
. Ed. Duan Yuca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1981.]徐正英:“曹丕《典论·论文》创作动机探析”,《郑州大学学报》4(1995): 28—30。
[Xu, Zhengying.“An Analysis of Cao Pi’s Motivation of Writing ‘A Discourse on Literature’.”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4(1995): 28-30.]钟嵘: 《诗品译注》,周振甫译注。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Zhong, Rong.Interpretation
and
Annotation
of
Critique
of
Poetry
. Trans. and Ed. Zhou Zhenfu.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6.钟惺 谭元春: 《古诗归》,《三曹资料汇编》,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编。北京: 中华书局,2005年。
[Zhong, Xing, and Tan Yuanchun.Homecoming
of
Ancient
Poetry
.Sourcebook
of
Cao
Cao
,Cao
Pi
,and
Cao
Zhi
. Ed. The Chinese Department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