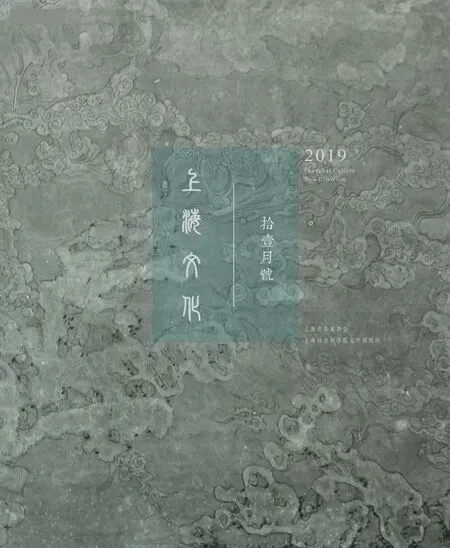他在编织自己的作品李昌鹏的诗
柳宗宣
我遇见它,拆数这六千七百八十二条草丝
这是六千七百八十二条草丝,被拣选的
细柔草丝,有的长一些,有的短一些
有一个个大小的弧度。我无法让它们回复原样
一个杰作,牢固吊在菜籽梗,丝雀口袋一样的窠臼
这六千七百八十二条草丝,各自从哪里衔来
怎样拿口水组织,现在已看不清,它们以前的样式
小丝雀能够把它们养育,织就奇妙的作品
六千七百八十二条草丝,每一根,轻飘
——《六千七百八十二条草丝》
昌鹏的诗集《献给缓慢退隐的时空》把这首诗放到诗集的前面,我以为有道理。我把它列在这文章的前面,以此展开评说——
“我遇见它”,然后拆数一只丝雀巢的草丝。这是一个事件,多年前的一直在作者记忆中出现的事件,后来又将诗人唤醒的,这个出现在诗人记忆里不断出场的一直作用于他的内心世界,他早年乡村生活邂逅的田野菜籽梗间丝雀编织的窠臼,里面的意味是无穷的,作者也看见了,他所见的窠臼唤起了他的感情——是兴奋而激烈的,多年后再去写作这事件或场景,又在里面加入了想象与思悟。诗人不停地看见那雀巢。“看见”是一种稀有的能力。你心中有你才能看见;心中无你则视而不见,所以维特根斯坦说:“我们能看见眼前的事物是多么困难。”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命运。巴尔蒂斯说:“必须看,看了再看。人总是在其所见之下。还得是善看会看之人。”昌鹏把“看”当成了一种艺术,他看到了拆解的程度,“六千七百八十二条草丝”,他看见丝雀的挑选和口水的组织和巢编织技艺。他在多年的观看中,看见了异类的共同,生活与词语的关系,艺术对生活的观照和呈现。他看见了自己的命运。
他在纸面上建筑自己的作品,像那只可爱的小丝巢那样。他看事物看得那样艺术,那样细微、专注。几十年来在纸上落实他所看见的,但他不直说,他描述。整首诗似乎平静得好像无所事事,甚至事不关己。我们知道这是诗人做了冷处理,不让飘浮的感情影响他的编织工作。也可以这样表述,他放弃了已往诗歌的呈现方式,也就是他动用了他欣赏的习得的方式进入诗歌。他描述但不浪漫的抒情,使用的是白描的语象,把物当成物来看——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的论述,即:以物观物。他观看与描述但不抒情,也就是放弃所谓的“以我观我”。或者说,写作者抑制了我的出场,尽量地让所见的事物直接在语言里出场,他遗弃比喻的拟人和象征的手法来表现,通过相对客观的词语来呈示,如同丝巢用草丝筑巢,昌鹏的这首诗没有使用一个形容词。在他看来,精确的描述性语言可能比拟人与比喻意味更丰富,他甚至想让读者看见那只雀巢,和他一样。在诗的开头,“我遇见它”。我们必须遇见,在此时此地。让读者直接和他一样看见那只雀巢,置身于诗人设置的场景,一切在此生长,如词语一样运行。当代诗十分看重此时此地的呈现,他在这一刻写诗,虽然这一刻早已已过去,成为回忆中的场景,但他在诗的表达中,让你有一个现场感,让你有这种词语在场的幻象。
诗人所要做的是不断地看见与编织,让这个事件或图像渐渐显现
如前所述,诗人使用的全是描述性的语言,全诗没有一个多余的形容词和比喻,没有不顾一切的抒情,只是具体地呈现,具体到拆解的六千七百八十二条草丝,使用身体的口水还有他和它们的组织。昌鹏的语言技艺是经过多年修炼才自觉运用这种方式的,他的这种语言方式的运用是选择后的结果,这选择是阅读带来的改变,是他对诗歌审美意识更新而后产生的效果,当诗人们众多使用光滑的形容词,隐喻性的语言,极力于修辞的曲折和复杂变体,他则使用直陈性的语言来写诗,这里面有他的美学考量。他在意新诗对世界的命名与直陈能力,他更在意对诗的观察能力的强调,让语言直指事物的能力得以显现,用他的话来说:“写作诗歌——把发现的世界,在图像和语音中托出来”。他诗中图像的呈现,视觉性的语言,让图和象自身呈现出它本有的奥妙,放弃强加给世界的感情与自以为是的感知,昌鹏在写作时把那些他觉得多余的人的东西放弃了,或者说,先入为主的作者退隐了。一个写作者在意的是让客体不受遮挡地自我出场,让我们看见他所发现的世界的图像。其实这个图像浸染了写作者的情感与思味。一只雀巢在诗人的心里成活了多少年,它消逝又出场,它意味无穷但莫名其妙,它带有着诗人身体里的口水和气息,它的叫声是从写作者的身体里溢出来的,那编织的巢带有他们的体温。诗人所要做的是不断地看见与编织,让这个事件或图像渐渐显现。在昌鹏理解中的诗歌写作是发现世界,而非表现世界或歌唱世界,也非复制世界,那是在写作者的直陈性的语言中在写作者特有的身体的语音中烘托出来的世界。
诗歌文本是意义最丰富的文学文本。文本就是符号单元的有意义的集合。昌鹏的阅读与写作经验让他对此颇有理解。他的写作的自我摸索,对语言更新的自觉意识和他对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阅读相关,他的对符号学的研读影响了他对语言的态度,以及在诗中如何具体运用词句,他在意语词的符号性能指。诗文本就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词就是一个个象似符号。诗的呈现离开了这个系统或结构就没有意味。他在意一首诗的构成,一个象似的词语符号在语言系统中的意味,他注重文本的肌理和叙事文本的诗意内涵和叙事情景的转换,强调语词的能指的可视性和转义,或图像的自我生成,每个语象在词句之间的深意或可玩味处,那因词句相互作用而衍生出的意境——昌鹏有着他的玲珑胸次。
古人钟嵘云:“‘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古人的这个“直寻”,在笔者理解的就是直陈性的描述性的语言,描述直陈了“明月照积雪”这个事实。描述性直寻的语词出现在诗中,生发出写作者无法预料的丰盈意味。昌鹏这些年暗自读了一些诗文本和诗学理论方面的读物,在他的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在农场通宵阅读或写作的岁月一个个令我不安的夜晚……
他读书时期开始热爱的诗歌写作,在他农场的家里一个人在楼上通宵阅读与写作,磨炼出一套新诗写作的手艺,这些年他稳定地保持了他特有的语言风度。他知道如何像美国意象派诗人持守新诗的原则,强调“直接处理”事物,强调“视觉上的具体——阻止诗滑到抽象过程中去”,强调并在意诗的“临即感”。他可能对威廉斯的“客体主义”也不陌生,“要事物不要思想”。还有麦克利的名句,“诗不应隐有所指,诗应当直接就是”。在他所谓的诗的意味是在图形和语音中托出来的,我想也可以这样表述,诗是在语境中烘托出来,那是写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如同神迹的奇妙。用符号学的观念来表述,那是在上下文语词的相互作用的压力中出现的。这新生的诗的意与象与人们常说的隐喻不同,那可不是写作者先入为主的意念,而是语境特殊透现的结果,或者说是诗人私设的一个“象征”而非公共的既有的“象征物”,那是语符的能指在词群的半明半暗中隐现出来的,诗人在诗中不言。如同陶潜所说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我们再回到昌鹏的这首诗。中间出现这样一句:“小丝雀能够把它们养育,织就奇妙的作品。”“养育”这个词的出现是前面描述性词句:“从哪里衔来,怎样拿口水组织”所衍生或逼现出来的。没有这两个句子,“养育”这个词就显出突兀,有了这几个直陈的词句,这个意味深厚的词就自然得体。昌鹏对词语安置或拿捏十分细心,在此表现出他对语言的尊重和修养。他可能是在语境的运作中顺势摘取了这个词:养育。他听到了这个词,受命似地写下了这个带有他体温的词,并且这个词又生出了另外两个:织就、作品。“编织”是十分准确的用词,和前面的“草丝”与“口水”相呼应,同时开启了“作品”的出现。我们此刻恍然理解,诗人他如何在前面细致描述草丝的长短细柔和孤型,我们理解到了诗中的我何以参与在诗境数草丝的细节——而且数出了它的六千七百八十二条。
本雅明有过这样的表述,写作一篇好的散文有三个台阶:一个是音乐的,在这个台阶上它被构思;一个是建筑的,在这个台阶上它被建造起来;最后 一个是编织的,在这个台阶它被织成。这个说法也可同样适用于诗创作,昌鹏的这首诗有着编织的效果,一个类似巢的圆形。
诗人写作这首诗时十分清楚,他再现原样的巢不可能。他懂得那不可复制,他清晰地知道这点,他不会蓦写外部的诗。诗是发现,写诗是再造一个作品,而非复现原样。他清楚我们无法回复消逝场景。诗人与作品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有旋律地编织,作品是“编织”出来的。他善于挑炼,挑炼草丝来编织。用他诗中的句子来说,他“更多的时候是看文字/怎样织成了漂亮的锦缎”。他确实是一个发现文字秘密的一个人。从中他获得发现的快乐。
他谈论的是如何在诗中写诗这件事——他在描叙如何编织一件作品一首诗
我曾有过这样的表述:传统哲学只关注心(心灵和精神)而排斥身体。对身体研究成了这个世纪的新知领域。梅洛·庞蒂把身体作为现象学分析的起点——作为物体的身体,身体的体验,身体的空间性,身体的性别。作为表达和言语的身体,我们的身体与万物交织,我们变成他人,我们变成世界,主体和客体的交织,我的身体和他人身体的交织,身体与自然的交织,写作就是一种交织,回归到“世界之肉”。我想昌鹏对现象学的感性诗学是有体会的。他说他的诗在图像和语音中托出来,这个语音就和写作者的身体有关,这个语音类似于语调和词晕,是写作者在写作某个瞬间给透显出来。当代诗的语感是让人着迷的东西,它是写作者生命气息的外显。而每首诗又有着不同的语感且不可重复,这和诗人生命当下情态相关联。艾伦·金斯堡和他的精神父亲——惠特曼的作品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生命气息,你的阅读能触摸到一个不可见但可感的气场,这大部分来自诗的语感的作用,即内在乐句的呈现。本雅明说过艺术品呈现出来的灵韵,在你的理解中它多半来自语言的内在节奏散溢出来罩在诗作中的一层薄薄的光晕,那创作主体与词语节奏相互生发出来的气息。我们读诗或分辨诗的真伪往往是听诗,即视听它内在的声音和光晕。昌鹏诗中的语音我听到它的真纯:六千七百八十二条草丝。这个句子在诗中出现了四次,在不同的地方出现,这种歌咏式的复沓荡漾出来的语音有着无尽的余韵。
这些年,昌鹏跟从我写诗,和我一起交流诗艺,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我和他建立了只有写作才有可能建立的民主精神,我们无长无少的。我们之间不能用一个词来定义我们之间的关系:师生?同乡?诗友?非血亲的亲人?不是能用一个词来命名的。我们的命运因为写诗的命运统摄在一起。就像他写就的这首诗,这个作品的意味绝非单一的,有多重的不可析解的元素。
昌鹏的这首关于巢的诗,叙述的不是停歇在心中少年邂逅的丝雀巢,他谈论的是作品——可以说,他谈论的是如何在诗中写诗这件事——他在描叙如何编织一件作品一首诗。如果在诗中复制外部消逝的物事是不可能的也是低劣的甚至愚蠢的做法。当我们读完这首诗,隐约明白了他的旨意,并发现诗人的多重叙事在诗中运用,或者说,巢是一个结构符号,这首诗是个符号系统,他的叙事有着多重的叙述形态,它的语言形态有着诗性张力。叙述者的身份有明确的也有隐藏的;有概述也有细描;各种叙事在情境之间转移、过度、混合与交织。它的语言时态也是多重的,如同诗中叙述者的声音。此诗的结构由语言叙述的各种形态所构成,它的符码有着编织的参照系统,用巴尔特观点来旁衬,它就是“断裂和被擦抹的网络”,或者说,这首诗让我们读者不再成为消费者,而是受邀般地参与文本的生产。当我们读到最后,突然发现似乎是在谈论写作的事,如其中这样所说,“我无法让它们回复原样”。这是叙述者在文本中对叙事话语本身的评论,也就是叙事学中所谓的元叙事,即关于叙事的叙事,一种自我意识的叙事。这关于作品如何成就的叙事,其实是在叙述诗人如何写诗,如何织就一件作品,像那只小丝雀一样。
在诗的最后,诗人以“轻飘”一词收束全诗,戛然停止。“轻飘”这一词极具意味,让笔者觉得他是在阐述他倾向的诗学风格。他的这本诗集所有诗作都很短,显出轻的特征,诗确实是轻,轻到可以像草丝飘起来。或者说,他崇尚“轻逸”的美学,是他所持守。轻逸,他很少处理生存沉重的主题,他的诗多是短制,这于他是有考量的,他要显现他写作的整体风格,我也倾向于他的轻逸诗风的建立与维护。
昌鹏何以建立这种轻逸的诗风呢?他可能把写诗当成舒解生存压力的方式,在诗中他有于此透气放空自己的愿望。他的写作很少透出焦虑,偶尔有一两句生存感的体悟性的句子但马上收束,在某首诗中他这样描述锤子:
锤子缓缓的声响,每一声都沉实有力
我停下来。它,移至我腰间
只等一会,我要把它从身上取下来
生活的锤子一旦移置到诗中,也变得如草丝一样轻,在他的描述中变轻,成了一只诗意的锤子。他写诗,是移置了一个空间,在他的作为符号的语词间,他移动它们保持语词的自身的节奏与轻快,它是他发现的另一个世界,与生存的世界无关,他不会将其弄混淆,他保持了诗世界中的神妙与美和他在意的轻逸。这缓解了他在尘世的紧张感、疲累与不安。他干脆除去了语言的重量,让语言有着类似月光的飘荡。文学作为一种生存功能,因为生存之重会做出寻找轻的反映。是的,昌鹏的写作放下词语和身体的重负,飞向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改变着现实面貌,在那里获得安慰和审美的满足。这是他何以几十年来在写诗的原因,维护保持他创造的文本世界诗性,他在诗中快速运行词语,不黏滞,语词在运动,精确地呈现在句子或诗结构中,保持了它们的语速节奏和想象。他理解瓦雷里说过的,诗“应当如鸟儿那样轻,而不是像羽毛”。他的诗,是有生命的,像那只丝雀——那微妙的生命,在诗行飞翔。昌鹏的诗思往往在都市和乡村两个世界自在地飞,后者成了他情不自禁飞回的地方,那个被田野包围的家乡的农场的房子——他的小丝雀的巢建筑在那里,他的童年他的父母生活在那里,但他很快又在诗中回到地铁中来。他在诗中保持稳定从容的坐姿,从地上的传媒大学到达地下的朝阳门,咂着嘴巴里啤酒汁液的微苦经过冬天的北京。昌鹏的诗迷人的地方是他的词句轻逸地在多维空间的运行的飞速和轻盈。对于他诗歌的轻逸美学的指认,还有一个原因来自他作品中呈现的想象,譬如他的诗作《骑马下乡》,诗中那想象的马,让他的诗意的还乡变得轻逸开来——那是一匹时光之马,一匹游子虚构的、永恒的马:
我去一个小村子。我曾在那里待过许多年
我想骑着马去,拜访它——
用马蹄子扣响安静的水泥路面,用马的嘴
叼路边的嫩草,饮用沟渠的清水
此去需要耗掉白天和夜晚,我是慢慢去的
去过以后我会清楚记得去路弯曲,以及
草的长势。此去的遥远,得花费脚力
走到唐朝或者建安年间的乡村。我在马脊上颠簸
马身上的铁甲和我腰间的长刀渐渐清晰
我待过的那个小村子在前方,越来越苍茫
是不是只有这轻逸美学可以遵循并维护呢?昌鹏的生活和写作我是知道一些的,这些年他经营他的诗学,他的天性气质在他的诗作中可以或隐或现的看出来,他的诗状物蓦写皆在细微处显能耐。他身上的女性气息占了上风,引用荣格的观点来旁证,他作为男人心理中的女性一面的阿尼玛成分不可忽视,这影响了他诗作的审美取向——诗作阴柔的元素让我亲近青睐,但作为写作者可以挑战自已的天赋,天赋是我们体内的一根剌,我们似乎可以消解或克服它。昌鹏在写作中是否可以尝试加入新的风格进来,具体地说,是否可在轻逸中加入繁复,在缜密冲淡里融入豪放与疏野?可能我的建议不妥,我们知道每一种诗风都是一个美丽的环套,但我们得变成蛹飞将出去,去建立另外的巢穴——甚至让我们从一只词语的精致的小丝雀,变成一只有凶猛的鹰隼。我写下这句话,就想马上对自己的想法给出否定,还是让昌鹏成为一只善飞的轻盈的丝雀吧——何况他编织的作品具有轻盈的美质。可是在他诗集中,那自我更新的愿望呼之欲出,他的《倒推》一诗就是某种尝试性的努力,是对自己摸索出来的一套写法的反对或推倒。其实,昌鹏的诗集中呈现了不同的语言路径,愿他持续地看,质疑自己看世界的方式,内省自己创新超越的能力,他的勇气与自由;愿他挑炼出全然不同的草丝,筑就他的新的巢(作品)。
天赋是我们体内的一根剌,我们似乎可以消解或克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