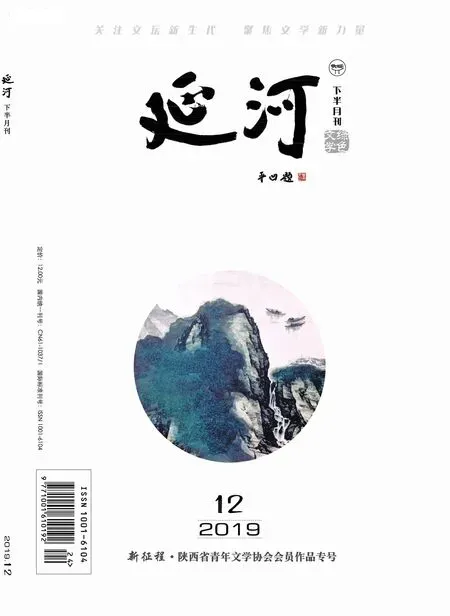流光漫过小村庄
庞 曼
夏日午后,陪妈在村子后头的路上走路锻炼。身体原因,她先头公园艺术团唱歌这一文娱活动取消了。当然了,好嗓子在自己强烈的爱好面前,心有不甘,在家偶也对着点歌机练习。
光阴越来越长,感慨这人哪,骨头越长越缩,只有小孩在长大。看着母亲的身材,摸摸自己的肚子,我怕是也难以抗拒两头尖中间隆的枣核形吧,前景不容乐观呐。我的担忧惹得妈直乐。曾经一米七几魁伟的转娃婶子低低地跟前经过,身子骨折弯得厉害,跟拉弓一样,前倾,像随时要发射出去,看着都操心。人老了,真可怜。想到王小波说的,人终要面对老天爷安排的衰老之刑。
走的是村上的生产路。儿时的记忆里,玉米秆折的拖拉机土路上“嘚嘚嘚”推着嗨,跟着小玩伴一同出来放羊吃草,近旁就是小渠,清澈的水惹人爱呦,随便拉个小衣服便挤娃们中间淘洗。现在早不是疙里疙瘩的泥土路了,也没有干净的水可耍了。东边地里桃子、红杏子肥的,再远一点还种樱桃、草莓。小时候哪有什么好果子吃,就钻玉米地里掰甜秆秆、跳沟里挖毛根根吃。一根冰棍批发二分钱,零卖五分钱,舍不得咬,吱溜吱溜抿着吸食,有个两毛钱的豆糕、三毛钱的奶糕那就惹人垂涎了。
父母上了年龄,家里的地也没有再种了,先是给邻人种了,后来外地商人种草莓用上了,一年给几千块钱,省事清闲。人小觉着天高路更长,村子就是离县城老远的荒郊野岭。那时候的时髦流行语是“上县”,也就是逛县城。凡是去的人必得隆重捯饬一番,起码换件阔气些的新衣服。自行车后座上颠簸得我像个小跳蛙,路两边全是田地,在玉米秆长高时,老叫人有怕怕的想象。雨天刚过,途经那个糟糕的麻布巷,时常稀泥烂河。
物资匮乏。买个西瓜需切个三角小口看看,还要尝上一口,才送去外爷家。那时的瓜瓤粉扑扑的,红得严重不足,怨不得要跟人多说话。有回天黑了,因为没有路灯,爸骑的自行车子栽进坑里卡住了,前杠上的我和车篮里的瓜一股脑滚坑前了,后座上的哥哥跌落坑后边,每个人都负了点小擦伤。我这“红苕女”一听着老汉爷的吆喝叫卖声,花棉袄便依靠在门口树候着,脸蛋儿像两个冻伤了的“瞎瞎苹果”。老汉爷用缝衣服的白色细绳绳儿拉锯一小截卖给我。村子里时常有要饭的来,印象深的是一个拄拐的老婆婆领了个不及拐高的小女娃,那娃跟我一般大小。
过了两年,爸混得好点了,在集体企业当了个厂长。妈常说这闷葫芦不会说话咋当领导人,我感觉像说现时的我。卒有卒的路,马走马的道,不用操心,各有各的路数。去了厂子,爸从床底下拉出一箱方便面,华丰牌的,给我冲一包,把我欢喜的,舍不得用完的调料包就带回家继续冲着喝汤。喝完汤美饱饱的那一刻,我起了那时觉着极其遥远的一个宏愿:长大工作了一定也要拿得出一箱子方便面。另外,我还要加一箱子北京牌锅巴。真大了,要啥有啥,吃啥啥不香的,再也找不到童年的那个味道了。
紧接着,家里有了村里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好多人搬着凳子一起看,好不热闹。我呢,要么在床上翻跟头,要么在叠好的被子上面盘坐,学《射雕英雄传》里的梅超风练功。小小的武侠梦就这么潜移默化入骨,上了大学也不曾泯灭,一介女流毫不犹豫选修了武术。后来爸决计回家贷款自己干事,在村口办起了木材厂,妈打算盘算账,从开始的露天地几根山杨木做起,一点一点滚雪球,盖围墙,作厂房,发展壮大,最壮大时吸纳了村里十几个精壮劳力……再后来,钢材紧俏,铝合金、彩钢瓦红火,木材生意不景气,退出了市场。
小学时,几乎每年暑假,我都要跟我婆到相邻的三渠镇的姑姑家待些时日,爸妈照看生意忙,我俩可以说是被公派去的吧。烧锅的硬木柴连同能用能给的家具一起借拉木头的车接济日子相对落后的姑姑,我和我婆算是押车的,给我塞上好几袋干吃面就打发好了。有时轻便,我跟我婆在路口自己搭马拉车或是蹦蹦车,经过大拐弯的南里庄,然后到三渠口那棵附会了神话雷劈了成精的大柳树下下车,再走土路,走得我糊涂不辨东南西北了再坚持一会会就看到了姑姑家门前那棵熟悉的核桃树了。
上了县城初中,骑自行车,经常迟到。从同学嘴里知道了自己是农村娃,一个确凿证据是没有上过幼儿园。我们这一群,要么朴素勤奋成绩好,要么烂泥扶不上墙,一个一个被老师骂到退学不念了。记得高中时,突然一夜之间,乌泱泱,校门口席地而坐全是麦客,那场面就跟我日后见识的天安门广场候升国旗一样壮观。我婆寡妇抓娃,我爸都记不得他爸。弟兄四个,我一个姑,还有一个小时候送人了的姑妈。家里实实的贫农,不过妈终是感恩爸没有嫌弃她家的大成分。爸是学徒工,开始跟人干木活。后来分家,得了一口锅和眼睛不好的我婆,余外啥都没有。勤劳致富,才彻底改变了贫穷的旧面貌。农村人一辈辈就是娶媳妇盖房。家里的房子在我爸手里盖过四回了。我亲历的是三间平房,上高中时拆了另起的两层楼房,下来就是去年妈生病,出院后哥又装修改造了一回。
县城像只庞大又强大的八爪鱼,触角一路延伸而来,盖严实了,两边田地全被楼房商铺填充得满满当当。花园大酒店因花园段这村名而得名,花园段又让这花园大酒店扬了名,发达了,成了炙手可热的城中村。每家都开始继续盖房,楼高户大,盖得很结实很漂亮,绝对不同于拆迁的胡乱加盖。没有惹人眼红的拆迁,但因为发展,因为划转新城的原因,地皮一下值了钱,房价蹭蹭涨得厉害,一栋连一栋,无处不在起高楼。一时村子涌进大量外来建筑工人,租房生意火爆,随便腾出几个空房间都是额外一笔不小的进账。好坏有点手艺,再勤快点的,沿街面卖个早点、开个面馆过活就够够的了。
算是农忙时节吧,这条路上车也不少,拉麦子的,拉桃子的,卖杏的。路拓宽后,外面大路上的车辆就近取道,村里的小车更是过往频繁。家家户户都有小车,有的一家还几辆,一人一辆。爸上了岁数了,出于技术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他有辆电动汽车。有空,老两口转个狗市,淘买些便宜东西,走个亲戚,就近逛个龙泉山庄和茯茶小镇,自己用着方便。省吃俭用,舍不得给自己花钱的父母奋斗一辈子打下的江山全给了房子和孩子。
坐在家门口,看着对面高层塔吊正忙碌地施工。密集的高层显然已经夺取了村子的部分光照。但这不严重,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直接的经济利益冲击了村里人的观念。门前植几杆竹子,开辟点菜园子,辣子一行茄子一行,庭院再弄个小花坛,抬头瞅高层蜂窝煤一样闷人的孔眼,倒是乐得高楼林立当中富有一独院,近乎别墅,也成了城市人低头羡慕的庄园了。城市人带娃来我们农村,娃娃们兴奋地看外星人一样地去看猪、鸭子和大白鹅,采摘桃子和杏子,和大人一起辨识桃树和杏树,再拓展学习梨花和苹果花……大人小人嘴里不时叽里咕噜洋文对话。我下意识摩挲着同样上幼儿园的我娃,你也该见识“歪果仁”了,咱下来也报个英语班吧。
天主教老的少的,集中一家念经,也有光看热闹的。碰着几个年轻婆娘和小伙子练习吹号,驻足听了听,这些大老外,你甭说,练得还像模像样的。一人掏三百大洋买身服装,组建文艺队,说是还要打腰鼓。家门口的生活是滋润闲适的。谁能想到有这么一天,大地原点上的泾阳人成了西安人了。稍微动弹下都有钱挣,村子富足,从东头到西头,几乎找不到啥可怜人。只有一家因为疾病成了贫困户,在党和政府的关照下,也过得差强人意。
鸢飞鱼跃,一派祥和。用小石子、树叶就地取材“纠方”的,走闲路锻炼的。娃娃们滑着滑板车,在光滑的地面上摩擦摩擦。老婆婶门口小凳子三五一摊,老汉旱烟锅子咂着,歪嘴努着一小壶茯茶,谝闲传,天南海北,无非是闲话如今这庄户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