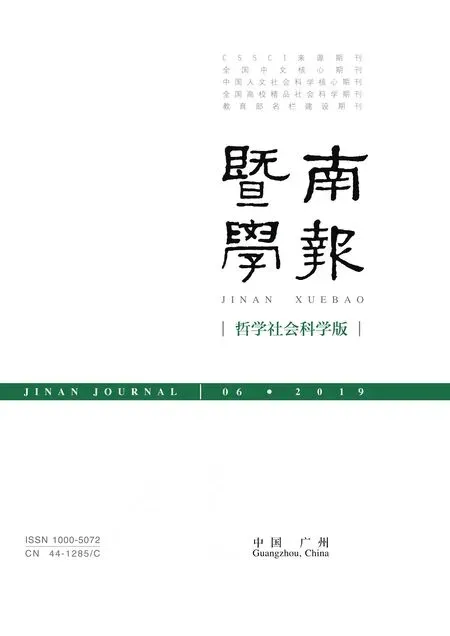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研究:对象、问题与方法
颜 敏
序 言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让距离不再是问题。从事文学活动的人和文学作品都可以在不同空间迅速流转,一位作家上午还在广州购书中心举行新书发布仪式,黄昏时候已经漫步在吉隆坡的大街上接听读者来电;诗人躺在多伦多自家庭院里写成的诗歌,手指轻轻一按,已经传入世界各地的诗歌爱好者眼前。文学传播的速度之快、方式之多,让很多人产生了文学可以跨越一切疆域,进入大同世界的幻觉。然而,只要稍加注意,就会感觉到文学跨语境传播的复杂性。比如为什么安徒生的作品在全世界被广泛翻译和接受,而丹麦其他优秀作家的影响却难出国界?为什么西欧国家的汉学家更青睐中国古典文学而不是现当代文学?为什么在中国曾大量译介的俄苏文学,在改革开放后转入传播低潮?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构成文学传播的不同语境,在文学的跨语境传播中,阻力和动力同在,随之生成的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这些问题促使研究者穿越文学文本的层面,去思考文学与传播媒介、现实语境的复杂关系。
在跨语境传播的视野中,若我们回望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文世界的互动交流,也会感知到这一双重化的进程。一方面,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华文世界的内部通道不断拓展,不同区域的文学传播与交流加速,华文文学的整体化进程与共同体意识不断被强化;另一方面,因历史经验、社会制度、区位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中国大陆和台港澳、东南亚、北美等区域间的华文文学流播具有跨语境性,差异与歧义、纷争与困扰仍在。面对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研究者却显得有些迟钝,在已成体系的文本和诗学研究中,文学传播研究并未占据更多空间。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正是区域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的过程和经验,激活了世界华文文学、汉语新文学、华语语系文学等新的概念及新的研究范式——限于单一区域得来的狭隘思路与理论观点开始遭遇挑战。目前,有关华文文学的比较研究、整体研究和诗学研究方兴未艾,对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过程和经验的清理,将敞开文学汇流过程的诸多问题和规律,有利于在世界性视野中重建华文文学研究范式,实现新的逾越。
本文所要尝试的是,梳理、分析有关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的对象、问题及新的研究视角,将之嵌入当下文学发展语境之中以确立其价值,进而为当下的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提供某些启思。
一、关于总体性命名:为什么是“华文文学”
当我们试图将全球范围内形形色色的汉语写作纳入某种话语体系时,各类总体性的命名方案也随之出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汉语新文学”到“华语语系文学”等,每一种命名,其合理性在被反复言说与论证之时,质疑与反对的声音也从未间断。在此,我试图在对几种总体性命名分析比较的基础上,选择更合适的一种命名,以定位跨语境传播研究的对象和视野。
无论是较早的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还是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学术用语,其命名遵循的都是我国大陆学者对本土以外汉语文学的发现逻辑。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者发现疆域与研究对象不断拓展,命名便通过学术共同体的讨论做出不断改变,从“港台”到“台港澳”,从“台港澳”到“海外华文文学”,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历经十多年的演变历程,在1993年的庐山会议上确立了“世界华文文学”的合理性,并进而成为学科的名称。显然,这里的“华文”和“世界”都隐含着海外视野。“华文”沿用了由海外华人、华裔演化而来的东南亚华人对汉语的命名,“世界”一词则是从海外一词延伸演变而来的。故而世界华文文学最初未将我国大陆的汉语文学包括在内,当时也并未引起太多争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学者顾名思义,发现了概念与所指对象之间的裂缝——世界华文文学本应包括全世界所有的华文创作,怎能将数量众多、影响甚大的我国大陆的汉语文学排斥在外呢?更何况,在我国台湾和东南亚华人圈,“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早已通行,指代的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华文创作。以上争议,反映在研究实践中则是,我国大陆的汉语文学逐渐以“包括在外”的方式处在世界华文文学的体系之中,位置尴尬且独特。然而,就算悬置有关大陆汉语文学的位置问题,将世界华文文学作为语种文学的总称,是否就合适呢?一些学者遵照国际惯例,认为世界两字纯属多余,如陈思和认为它造成了“帽子大脑袋小”的问题,“不如去掉世界两个字,用华文文学来替代,像英语文学、法语文学之类的命名一样更合理更自然”。
如何处理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复杂关系一度成为我国大陆学者的争议热点,由朱寿桐先生提出的“汉语新文学”一词试图超越这些纷争,实现整合的目的,在他看来,这一概念不但可以有效整合“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区别于传统文言作品的汉语各体新文学概念,而且汉语一词凸显了 “言语社团” 因素,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单纯从 “政治社团” 界定可能带来的概念狭隘的欠缺,有利于形成汉语文学共同体意识。但是,在具有连续性的文学传统之内,将汉语文学分为新旧两个世界,造成了没有必要的对立;而用汉语新文学一统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华文写作,则可能重新陷入以我国大陆文学为重心的困境,此外,汉语新文学这一术语内在的症结还在于,从语种出发进行整合,忽视了世界各地的华文文学是不同生命形态和文化特质的表达,是具有多元飞散品格的文化共同体,语种的一统性不过是表象。这一术语虽然在相关学者群体中产生了一定影响,并落实在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多卷本汉语新文学史之中,但要成为跨越国际的学术用语,得到学术界的真正认可并非易事。
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是最近十多年内国际汉学界的热门术语,由美国华裔学者史书美提出,原初意义上的华语语系突出语言社群的构想,以反中国中心为基点,带有强烈的价值论导向,在此基础上,所谓“sinophone literature”指的是中国本土之外,在世界各地以华文写作的华语文学,我国大陆的汉语文学被排斥在外。史书美的表述,在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背景之下,颇能引起某些人的共鸣,但作为语种文学的总体性命名,其合理性和影响力极为有限,它更像是一种偏颇的价值预设而非文学研究实践的升华。该术语在华文世界真正形成辐射力,成为有一定普适性的术语、进入到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分析之中,源于著名学者王德威先生的翻译、解读、调试和转换。王德威将sinophone literature翻译成华语语系文学,认为它指的是中国内地及海外不同华族地区以汉语写作的文学所形成的繁复脉络,中国大陆的汉语文学是包括在内的重要一环。王德威既反对史书美以华语语系对抗中国的二元对立思维,也不赞同我国大陆学界隐含的中心与边缘思维,故而通过对“华语语系文学”的重新演绎,“试图打破原有对立,整合世界范围内的华文文学论述,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学术视野和论述方式,让世界性的华语文学得以众声喧哗”。然而,被改造后的华语语系文学,作为总体性命名的位置也不稳定,在批判声中,黄维梁和朱崇科指出它最根本的问题是,“若排斥其后的意识形态诉求,从翻译的角度来说,它与华语文学、华文文学本质上并无区别,根本没有必要再造一词”。
通过对以上术语的考察,不难发现,带有强烈建构意图的术语,反而容易与真实的文学历史产生疏离;若想回到事物本身,不如选择最贴近事实的、较为自然的命名方式。在我看来,“华文文学”是一个运用时空比较广泛,相对而言较少出现争议,并隐含了上述术语合理成分的总体性命名。为了进一步凸显其作为语种文学总体性命名的合理性,可以对华文文学这一术语从历史(经验)、美学(艺术)和方法(思维)的维度做出初步阐释和梳理。
一是历史(经验)的维度。华文文学这一词语,“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新马华文报刊,就已频繁出现这个词,后来流行于东南亚各国”。它所牵引的其实是数千年,尤其是近三个世纪内文学生活的主体——华人——从漂泊离散到落地生根的历史经验,故而华文文学的“华”,应该理解为华人的华,其中活跃着华人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机制。但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们关注以华文作为表达工具的文学现象、以语种来界定文学的性质更符合文学的内在逻辑,若转化为华人文学之类的命名,所涉及的对象及其背后的理论机制、问题意识便截然不同了。因此,选用华文文学这一命名,以此来保留华人生存经验的多样性,以华文替代汉语、中文以避免汉族中心主义与中国中心主义意识,既认可了华文创作与生活经验的天然联系,又凸显了与主流汉语文学的联系与区别,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与现实经验的一种选择。而由事实的层面出发,我国大陆的汉语文学只能以“包括在外”的方式存于其中。
二是美学(艺术)的维度。从美学的维度来看,选用华文文学而非中文、汉语文学,意味着它所呈现和倡导的并非单一的汉语诗学,而是繁复多样的表述形式和美学形态。为了表达在地经验和个人情志,华文文学发展出了多样化的语言形态。语言多样化的形成机制,可借用后殖民文学理论中的移置与挪用策略加以理解。在后殖民理论看来,移民及后裔为了表达鲜活的在地生存经验,必须将殖民者的原初语言加以转化,拓展出带有颠覆性的有关文学语言的“移置”和“挪用”策略,从而使单数的大写的语言转变成为小写的复数的语言。从汉语到华文,正是文学语言通过“移置”和“挪用”走向多样化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所谓华文,强调了一种随华人生活经验和生存语境变化的文学语言形态,这种复数的文学语言形态与在地生存经验融合,丰富了华文文学这一带有想象性的共同体的美学内涵。因此,选用华文文学这一术语,也意味着认可了建立在语言移置与挪用策略上的美学多样性,有利于发现、维护和建构多样化的文学生态。当然,为了还原华文文学美学多样性的生活之源,必须超越后殖民理论有关中心与边缘的迷思。因为在华文创作中,并不存在所谓的标准语,它总是具体的、在地的,正如王安忆在比较我国台湾和大陆的文学语言后曾发现,大陆作家的文学语言是方言化与俗语化的,而台湾的文学语言则更语文化或书面化。进一步说,就算同是大陆作家,莫言的山东风味和苏童的南方情调也形成了鲜明对比。
三是思维(方法)的维度。华文文学的生成背景,是人、语言和文化的流动旅行过程,它是建立在跨区域经验和世界性视野之上的术语。故而在这一术语指引下,研究的基本思维必然是比较。在实践中,这一思维已被众多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贯彻、发挥,甚至上升到方法论与研究范式的高度。如饶芃子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便倡导将“跨文化和比较方法”作为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进入21世纪后,黄万华在越界与整合视野中对华文文学新的现象与诗学话语的发现与阐释是以整体的比较意识为基础的。美国华裔学者王德威提出的“台湾鲁迅,南洋张爱玲”的视野以及对华文世界内部创作现象与作家进行的整体把握,也贯穿了纵横对比意识。新加坡学者王润华提出了四种比较批评的模式以及将之运用于老舍、鲁迅等人的批评实践中生成了华文文学的跨界研究方法。朱崇科在王德威和王润华等人的理论资源的基础上直接提出了华语比较文学的概念及其操作模式等。这些学者的研究实践说明,若要在研究中真正确立华文世界之内诸多文学现象的意义,必须立足世界性的视野对华文文学进行不同层次和角度的比较。而在本书中,选择华文文学而不是汉语文学、中文文学,也强调了研究思维的转变——从重视多元流动的文学存在到倾向跨区域文学经验的比较分析或者比较性综合。
各类总体性命名的背后尽管有不同的立场或意识形态诉求,但它们的出现,说明了面对世界范围内繁复多变的华文创作,寻求整合研究成为必然的趋势。而在整合研究中,如何突破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话语,变得至关重要,无论是世界华文文学、汉语新文学还是华语语系文学的提出者和演绎者,都不得不面对术语可能导致的问题而在研究中采取更为灵活机动的开放性视野。故而术语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术语在运用中是否实现最大程度上的包容与超越。同样,“华文文学”与其说是一个有固定所指的用语,不如说是一个需要不断演绎和论证的对象,因此,对区域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现象的考察实际上也在敞开术语的生成演绎机制。
二、现象与问题:“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
语境原本是指言语活动的上下文,随着后现代哲学对语境论的重视及演绎,语境的所指越来越宽泛,包括了影响人类认知与实践活动的外在生存空间与内在心理空间,可细化为情境、言语、区域、国家、社会或文化语境。所谓不同语境,则是上述某个层面表现出来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边界。从这个意义来看,跨语境传播就是跨越差异和边界的社会互动过程,这一过程意味着转换、建构和融合,也伴随着隔阂、误解和冲突。在文学领域,翻译等活动是跨语境传播的重要形式,但当我们通过华文文学在国家内部、区域与区域、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流播过程来考察华文世界的内部循环机制及其影响时,华文文学翻译成其他语种被传播的现象不在考察范围内。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华文文学的跨语境流播到底改变了什么?建构了什么?意味着什么?对此,多数学者着眼于文学本身,从文学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转变、文学史观念的重建等方面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描述,鲜有超越文学边界的宏观视野,故而龚鹏程所做的总体判断颇值一提。在《世界华文文学新世界》里,他认为,华文文学是区域互动形成的以文字符号和文学作品组建成的新世界,这个世界既不属于国内法律秩序,也不是国际的自然秩序之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允许多样性的存在,并透过跨国组织与资讯网路表现出新的形态”。这一新形态的形成与新媒介集团的传播活动有关,“就像企业传播网已经塑造了一个全球电子信息流空间那样,新媒介集团正在创建一个全球图像空间,也是一个传输空间。它作为一个有自己主权的新地理存在,无视权力地理、社会生活地理,而自行界定了它自己的国籍空间或是文化空间”。通过数十年的区域华文文学流播过程,“目前华文文学也可说已经建立了一个全球的华文书写空间,形成了一个有自主性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正传播着新的空间感与体验,是不容忽视的”。在此,龚鹏程将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现象放在全球资讯结构裂变的视野中加以审视,认为由此形成的符号性的文学共同体应该具有独立自主性,这是过于乐观的想象,但他将华文世界的整合与外部秩序的变动联系起来分析,在全球化的大语境中思考华文文学跨语境现象的结果及意义,无疑开拓了新的思维路径。
全球化进程已持续多年,在全球一体化加速的同时,新的差异与阻隔也不断出现,各种地方性话语与诉求随之兴盛。这正是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现象持续存在的大语境,有关华文文学的大同想象和差异话语都与之相关。我们进行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的研究也离不开对这一双重化进程的了解与思考。在一体化和地方化的双重进程中,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已经出现复杂多变的流向与结果,故而在提出诸如龚鹏程先生的整体理论构想之前,最重要的是对现象和问题进行梳理分析,以史实化的描述、概括、分析化解纯粹理论演绎的可疑之处。
这一具体化过程,一些研究者早有所警觉、有所探索。2007年刘登翰先生提出华文文学具有“打破疆域”的性质,也是“跨域建构”的结果,提出的“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与龚鹏程的华文文学新世界有着相似的愿景,但刘强调的是这一愿景的过程性,凸显“在共同语言、文化的背景上肯定差异和变化的建构、多元的建构”的过程。另一学者刘俊也注意到了华文文学内部流动——旅行导致的复合互渗现象,提出“跨区域华文文学”的设想,启迪研究者关注华文文学在区域流播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王列耀先生则在“汉语传媒语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视野中,将对这一流播过程的思考落实到具体个案的研究之中,较为全面地探寻了传媒运作与华文文学的诗学话语、流派思潮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当他提出“越界写作”这一海外华文创作的新模式时,已经注意到跨语境生存对作家写作思维的影响。上述研究对华文文学区域互动流播过程的探索,为我们系统梳理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的具体现象与问题提供了借鉴。
要注意的是,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所涉及的现象,如路径、动力、过程、规律和影响等,与一般跨语境传播现象既有共性,又有区别。对于研究者而言,要重视的是在华文文学领域之内的独特现象,它们将构成研究的入口,产生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在路径上,除传统的出版、评奖和教学机制外,学者的游学、作家的游散等以人为重心的文学交流活动非常重要,这些以人的流动为中心的跨语境传播活动怎样运转,对华文文学的跨域融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动力方面,除了商业、意识形态和学术推动,私人交往和情感抒发需求也不容忽视,那么,私人与情感诉求如何融入华文文学的想象疆域之内,具有怎样的推动力?在过程的梳理上,若时空的线索与媒介的线索要兼顾,宏观的鸟瞰与点的聚焦需同在,可否做出更有针对性的选择,从媒介或个案入手来对过程进行人类学似的厚描?在规律的探寻方面,诸如区域不对等性,求同和存异的微妙滑动,社会需求与文学自律间的矛盾等看似普遍的跨语境传播规律,立足于华文文学这一特殊对象时如何融入更具体的问题中去分析?如华文文学经典如何跨疆域生成?区域华文文学在母题、意象、语言方面有无关联,有无演变?如何演变?文学思潮、流派、诗学话语的旅行在华文世界是怎样进行的?在判断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产生的影响时,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如结果是文学繁复还是同一?是边界的消失还是重建秩序?是导致回环衍生的重复美学还是激发作家创新创造的潜能?这些都需研究者在把握现象的基础上对问题做出深入思考。
因此,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研究的基本研究思路是,在对传播现象的梳理中提出有意味的问题,并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
三、尝试新的研究视角:媒介作为入口
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现象的研究,处在文学研究和传播学研究的交叉处,以传播学的思路、方法,开拓文学的视域,解决文学的问题成为一种选择。其中,传播学中有关媒介的思想和研究对文学研究已形成冲击力,媒介作为文学第五要素的观点打破了自艾布拉姆斯以来的围绕文学四要素而进行的文学研究范式,借助媒介视野重新思考有关文学的种种问题已经进行,基本的看法是媒介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生产的思维方式、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同时媒介要素的增加,还将使我们对文学活动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存在态势的认识发生根本性变化。故而选择以媒介为入口来梳理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的现象与问题,是较有成效的方法论层面的突破。
传播学视野中的“媒介”,有不同的定位与所指。在传统的传播学研究中,研究重心是媒介传递的信息与内容,媒介则被视为传递信息的载体、渠道或工具,涉及的媒介类型也相当有限,主要指的是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凸显物质实在性的功能性媒介。后起的媒介环境学派跳出将媒介视为中介的框架,对媒介进行全新定位,极大地拓展了媒介的所指范围,对媒介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究。如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本身就是信息,新媒介的出现改变着人的感知结构;在传统的大众媒介之外,他列出了游戏、货币、数字、文字、住宅、武器等30多种媒介形式。之后,美国学者梅罗维茨提出了媒介情境论,媒介被看成是影响人行动的场景,不同媒介构成了不同的行动语境,它重建人的角色意识,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在我看来,媒介的两种定位思路并不冲突,媒介集传播渠道和关系重构于一身,传递信息过程也是以人为主体开展的社会互动过程。当前,在新媒体的崛起和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媒介的平台性、综合化和人性化的趋势愈加清晰,媒介形态更多变化,我们对于媒介的理解必须综合化、动态化,媒介既是中介,又可能是信息、关系、情境、公共空间和实践区。媒介具体所指既可以是物质场所,也可以是虚拟空间;既可以是外在于人的实体,也可以是人本身。
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是一个持续的流变过程,包涵了众多复杂的现象,媒介所处的位置也摇曳不定,故而对于媒介的定位与形态也采取综合化的理解,强调其多面性。从定位来看,媒介在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中,既是中介,也是信息,情境、平台和过程,具有多种功能;从形态来讲,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的媒介可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一般意义上的传媒,报刊、影视、网络等;第二类是组织与机构,如学会、大学、学术会议、评奖机构、研究机构、作家协会等,第三类是人,处在流动状态的学者、作家、编辑和新闻工作者。这些不同类型的媒介既有交叉互渗,又各具特点,构成了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的媒介网络。在由媒介网络建构的传播场中,媒介作为具有关节点意义的集结点,如一面镜子,凸显现象与问题;也如文学肌体上的细胞,携带了文学的DNA,牵一发而动全身。如能尝试选取具有重要关节点意义的媒介,进行观察、整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再深入研究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现象及相关问题,就能对华文文学的内在机理做出更为细微的理解。此外,研究者及其所从事的研究活动本身也是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的重要媒介,它们以一种不起眼的方式嵌入到了华文文学的生态重建过程,影响之大小取决于研究者在场域中的位置,对此研究者也应有足够的警醒。
以媒介为入口,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研究涉及三个层面。首先是从媒介变化的视角梳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的流变趋势。从媒介视角来看,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起点,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历经了几个阶段。70年代到80年代,书刊是最重要的载体,世界各地的文学杂志和出版社对本土以外华文文学作品的选择性引荐,促成了区域华文文学的交流与融合,让华文文学初具世界性的形构。90年代后,影视网络媒介的力量凸显,不少被改编成电视剧、电影的华文文学作品跨越本土,形成世界性的影响;网络更是以前所未有的便捷方式将区域华文文学连接在一起。华文文学作为跨国际跨区域的文学现象进入到文学史之中。进入21世纪后,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进入全媒体时代,呈现多种媒介共同介入、媒介之间互为平台、相互融通的趋势,即媒介融合的趋势,华文文学文本的多媒体化成为不可忽略的现实。最近几年,随着手机移动网络在全球的普及,微信等社交媒介在华文文学传播中占据日益重要的位置,华文文学的信息特性和交往功能凸显。传播媒介的变化,使得华文文学不断改写其与时代、社会的关系,也使得我们的文本解读方式和研究范式遭受挑战。第二是从媒介运作的角度,通过分析媒介的传播策略、运作方式等梳理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的现象与规律,凸现跨语境传播对华文文学发展的深层影响。如媒介与区域语境的内在关系如何影响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在特定区域下,哪些作家作品最终被凸显,哪些被遗忘与疏忽?同一作家的哪些作品被重视,哪些又被忽略?余光中的《乡愁》在中国内地的跨域解读中,主题被不断固化,重要性被不断凝固,最终《乡愁》获得了超越一切的代表性,成为余光中在内地的标识,这一现象足以说明跨语境传播中的语境选择机制的重要性。又如媒介的话题化和新闻化的价值定位,如何影响华文文学奖的选择机制,形构出怎样的华文文学经典?台湾的时报文学奖和联合文学奖对域外文学作品的选择,就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共同性,反映了时代与区域政策变动对文学评奖的直接影响。通过这些具体传播个案的深入分析,我们可以不断整理出一些可供借鉴的现象与规律。第三是以问题或主题等为线索,分析其在华文文学所处媒介场中的传播过程和流动机制,对华文文学的诗学问题进行整体性的宏观思考。如通过华语语系文学的区域运动路线思考华文文学的诗学话语的建构方式,简略来说,华语语系文学酝酿于北美,发酵于台湾,弥散于大陆,在新马地区余音绕梁的路线图,凸现了华文文学诗学话语的一般运动规律。也可梳理离散话语融入华文文学研究的过程分析学术生产的语境局限,我们可以看到,在欧美已成气候的离散研究,在引入我国大陆华文文学界后,却出现概念模糊、方法单一、成果甚少、渐行渐远的局面。循此路径,可能敞开的是华文文学跨语境传播背后的文学与诗学生产机制,研究结果或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个层面的研究有不同的方向与目标,但不可截然分开,需要研究者在占有足够丰富的材料基础上,分层介入,逐步推进,万不可先入为主,将媒介材料变成已有观点的佐证方式,让自己的研究成为重复性的研究。
结 语
华文文学的跨语境传播作为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其间蕴藏着诸多文学生产的复杂机制,对创作、研究都产生了持续和重要的影响。遗憾的是,相关研究并不见多,现有的研究也多处在史料整理和媒介描述的层面,未能提出较有启迪性的问题,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论述。这一研究现状的出现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此类研究正处在模糊不清的背景之中,找不准自己的研究目标。以上对对象、问题和方法的深入梳理,便是尝试确立好此类研究的基点,以推动未来相关研究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