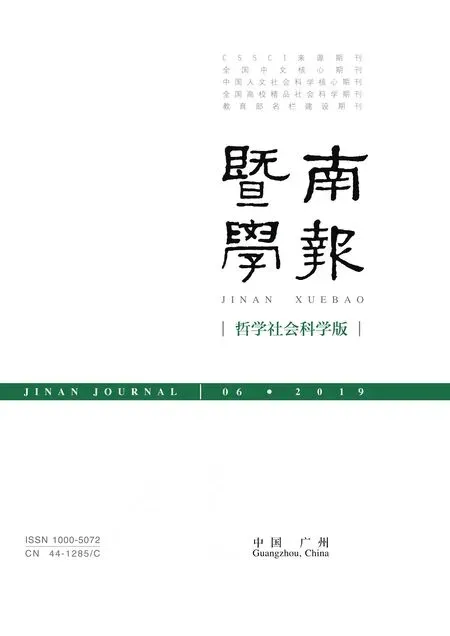论韩非“君道论”的内在矛盾
乔 健, 王宏强
君道即为君之道,它集中体现了思想家对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涵养、行为准则和治世理想的诉求。韩非的君道论近年来受到了中外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揭示了韩非君道论的复杂内涵,凸显了“君道”在韩非思想系统中的重要性。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进一步疏解韩非君道论的政治逻辑与内在矛盾。
战国时代列国国君通过变法逐渐掌控了国家机器,垄断了近乎所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这是当时君王所拥有的最大“自然之势”。然而实际的权力运作中更有可能发生的是,君权愈是集中,君主受到壅蔽或劫杀的可能性也就愈大。于是如何确保君主权位的恒久稳固,如何有效运用绝对化的权力,如何使国家机器高效运转,就成为战国末期政治领域和思想界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在先秦诸子中韩非最为关注这些问题,同时他认为现实中的君王常常是介于尧舜与桀纣之间的中主,因此韩非君道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为中等资质的君主建构出“人设之势”,以使君主简便且有效地控制臣民、控制国家进而一统天下。
“体道守法”“虚静无为”和“因人情”正是君主营造和运用人设之势的德行要求。韩非追求“中主”在践行其君道论的基础上成为“明主”,但是拥有绝对权力的中主必然依道弄法和贪躁妄为,最终沦落为“暗主”,暗主却又是韩非极力反对的。韩非君道论因而呈现出深刻的矛盾——即“体道守法”和“虚静无为”势必朝“依道弄法”和“贪躁妄为”的方向演进,这样“因人情”最终必然逻辑地变为“逆人情”。
一、体道守法与依道弄法
诸子蜂起的春秋战国时代是特别推重“道”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道”成为思想家标示宇宙秩序、伦理秩序、政治秩序及其统一性的最高概括。虽然诸子的“道”具有不同的政治内涵和治道指向,但“道”无疑是诸子思索治道的重要依托。在此背景下,韩非亦对“道”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如下三段最具代表性:
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韩非子·主道》,下引只注篇名。)
夫道者,弘大而无形;德者,核理而普至。至于群生,斟酌用之,万物皆盛,而不与其宁。道者,下周于事,因稽而命,与时生死。参名异事,通一同情。故曰:道不同于万物,德不同于阴阳,衡不同于轻重,绳不同于出入,和不同于燥湿,君不同于群臣。凡此六者,道之出也。道无双,故曰一。是故明君贵独道之容。(《扬权》)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解老》)
前两段中的“道”侧重于“万物之始”的状态和“弘大而无形”的特性,着重体现事物的原初状态;最后一段的“道”经由“理”的中介,可以被认知和把握,着重展现事物的具体性状和规律等。韩非论“道”只是手段,论“君”才是目的。在韩非看来,能够“体道”的君主定然是圣君明主,适如《观行》篇所言“以道正己”者便是“明主”。不少学者指出“道”对君主有“制约”或“规范”作用。然而,在韩非的政治思想系统中“道”原本就是以服务君主统治为指归的,这样的“道”似乎对君主没有实质性的约束作用。韩非在以“道”论“君”的过程中每每笔锋一转,就直接将“君”与“道”对接了起来,比如这里所引《主道》篇指出“道者,万物之始,是非之纪也”后立即转向“明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以及《扬权》篇将“道不同于万物”归结到“君不同于群臣”,即是显例。韩非这种以“道”论“君”的方式深受黄老之学的影响,却与老子思想完全相反。在老子那里“道”与“万物”是一种“长而不宰”(《老子·第五十一章》)的非支配关系,“道”虽然生出并畜养万物却从来不占有和宰制万物,但是现实中的“侯王”只是作为老子批判的对象而存在。在黄老那里“君”对“臣”的绝对支配性,则是通过“道”对“物”的绝对支配性来烘托出的。在韩非那里,“君”独居“道”的位置,这就为君主以一驭多、以简驭繁地控制臣民提供了理论依据。有了“道”的庇护,君权就显得格外强大和神圣。这种以道论君的方式实际上凸显了君主的至尊至贵至圣,为君主名正言顺地独占权力的顶峰寻得形上依据,亦烘托出了君权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具体而言,韩非的“道”是这样为君主统治服务的。韩非首先将“道”解释为宇宙生成的根据、万物的本原及其运行法则,其次以具体的“理”来呈现根本的“道”以标示一物成为一物的纹理、性状和特征,进而用“稽”来联结普遍之“道”和特殊之“理”。由于韩非以“理”释“道”,以根本的“道”总括具体的“理”,以具体的“理”来展现根本的“道”,世间万物因而变得有“规律”可寻,这就为人们进一步认识、理解和把握具体事物提供了理论根据。确切地说,这就为君主从宏观和微观上把握臣民之共性和个性提供了方便,君主因而可以通过利用臣民的行为“规律”,更加高效地使政治事务井井有条,使社会生活整齐划一,最终以尽可能少的政治投资获取尽可能多的政治收益。
韩非进而通过无形而根本的“道”→有形而具体的“理”→柔性而宏观的“名”→刚硬而确定的“法”这一逻辑链条完成了道法之转关。君主的“体道”“循理”与“操名”最终均归结于“君之立法”或曰“圣王之立法”(《饰邪》《守道》)。“道”是天地宇宙万物的总规律,同样源于“道”的“法”则是一切人事规律的具体表征,是臣民必须遵守的唯一律则。这是韩非“因道全法”(《大体》)的内在逻辑。于是,君主“尽随于万物之规矩”和“缘道理以从事”便具体落实为通过具体的法度来控制臣民。适如《功名》篇所言“守自然之道,行毋穷之令,故曰明主”,论“道”只是铺陈,论“法”才是旨归。法家的“法”是与西周春秋的“礼”相对待的,它本质上是一套使所有臣民统统服从君主集权统治的制度体系,具有鲜明的强制性,它尽管包括法律,却不限于法律,而是囊括了近乎所有战国时代君主用于控制臣民的制度规范。法家从来强调君主亦应当“守法”,韩非全然承续了这一法家传统并论证得更为精致。他认为君主在制定法度以后应当“守法责成”,不藏“私心”且“无私威之毒”(《用人》《内储说右下》),同时他大力批判君主的违法之举。
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君之“守法”是君主权力受到“限制”的重要表现。君主守法当然要好过君主的恣心所欲,不过历史上的任何专制君王其实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约束,在专制社会里君主守法完全是“出于君意之自由,非法律本身具有约束之力量”。在笔者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便君主真的能够完全守法,可君之守法恰恰是君主强化自己权威性的绝佳手段——关于这一点,并未引起学界的充分注意。
虽然实施法度最终依靠的是强制力,但是如若连立法之君亦能够守法而治,这无疑是对君主与君法之政治威慑力的大大强化,法之威摄力的强化对君主专制统治及其政治威信的巩固和增强只有益处而不是相反!实际上君之守法就本质而言只是君主遵守自己的意志而已,这对君权稳固及其扩张并不构成根本制约(对某个具体君主而言确实有些约束)。这里需要辨明的是,在韩非那里实有两个“君主意志”:一个是君主恣心所欲的个人意志,一个是君主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必然”地实现的个人意志。韩非从来反对君主胡作非为,尤其反对昏暗之主或聪慧之主仅仅依凭一己之好恶或智能来实现个人意志;反之韩非追求的是君主通过制度的方式来稳健地实现个人意志。这便是韩非在《饰邪》篇所言“道法万全,智能多失”的真正用意。当我们指出“法”在本质上反映君主意志,正是在后一意义上使用的。这一君主意志至少包括:第一,绝对的君权稳固以及绝对君权前提下整齐划一的政治秩序;第二,为了实现绝对的君权稳固必须清除对君权有威胁的一切势力,尤其是铲除对专制君权有约束作用的宗法贵族;第三,牢牢掌控整个官僚系统,尤其是防范和控制其中的重臣;第四,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将君主的政治控制延伸到基层,从而对所有编户民进行直接的人身支配;第五,通过巨大的利益诱惑和严酷刑罚将举国之民抟聚于实现“富国强兵”,进而图谋于称霸天下;第六,全面地控制社会舆论和思想文化领域,禁绝对集权统治的一切质疑和反思。这些君主意志最大程度地反映了战国时代君主集权和争于战功的“时代要求”。于是君主守法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君主在战国变法的基础上,更加有效地运用法度以进一步强化集权统治;二是君主通过自我克制和牺牲一部分短期利益,从而实现更加长远的作为整个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
君主一旦认为法度已不合乎己意,重新“立法”绝非难事——因为立法本身就是君权的固有内容。法家的“变法”虽然首先是指在战国的大争之世彻底改变贵族政治,“定法”则是指在经过法家式的改革后政治制度应当固定下来,但是君主既已拥有了近乎绝对的权力,那么法之“变”和“定”事实上只能够悉听于君主一人——所谓因乎时变之“时”最终只能够由君主给予最终认可和最高裁定。在西周春秋的“礼治”社会里,在上者在行使权力时每每受制于传统礼俗以及各级贵族、国人阶层等的制约,但在由君主“独制四海之内”(《有度》)的专制集权社会里,君主已然失去了任何实质性约束。君主完全可以在依照己意重新“变法”以后再度守法而治,君之守法最终仍然没有逸出君主遵守己意的范围!君主不大可能作法自毙,而法家二重奏般的“定法”与“变法”之论恰恰在理论上为其理想君主将一己之意志因乎时变地融入新法打开了方便之门。可见,君主始终是法家“法治”世界里的最大赢家。这也说明,在专制社会里制度的制定者永远是制度最大且最终的受益者。
韩非主张君主应当“以道为常”和“守法责成”,但是“道法”不大可能对君主权力构成实质约束,反之极大地增加了君主的自我迷信,并助推君主权力臻于登峰造极之势。在《亡征》篇韩非明言“好以智矫法,时以私杂公,法禁变易,号令数下者,可亡也”,然而口含天宪的君王恰恰“自以为智者,以已定之法为枉,好以私智改之”。“体道守法”确实需要君主相当程度的“圣明”,但是“依道弄法”恰恰只需要“中主”之资便足矣。
二、虚静无为与贪躁妄为
君法尽管昭示着体道之君对国家治理的明确规定,但毕竟徒法不足以自行,君主因而需要有一套自己独掌的治理方法,“虚静无为”正是君术的重要内容。韩非的虚静无为虽然不无君主的自我修身和自我克制之意,但其核心内容始终是“御臣”——即君主高效地控驭官僚系统,尤其是防范、伺察、铲除与规范其中的权贵重臣,在这一过程中君主始终隐于无形。
韩非的“虚静”是他修正老子和继承黄老的结果。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老子·第十六章》)是指人在玄妙空灵的精神超越升华中向“道”处复归,从而得以自我挺立和自我实现。黄老的虚静则是指君主在运用形名法术以实现“君臣当位”和“兼有天下”(《黄帝四经》之《经法》《十大经》)的过程中去除成见,排除过多杂念,保持心态平和,做到不急不躁和沉着冷静。初看来,韩非亦强调君主的自我修养,比如韩非在《解老》篇讨论虚静首先便源于他对过甚君欲的深刻忧虑,因而主张君主应当“重积德”以使“神不淫于外”。《扬权》《主道》和《喻老》等篇亦有类似表述。另外在《亡征》《十过》等篇,韩非明言,君主如若一味沉溺于宫室、台榭、陂池、车服及器玩等财货的无尽占有乃至于饕贪无厌,则有亡国之虞。
通观《韩非子》,韩非并不聚焦于君主的“精神修养”,而是强调君主不应被任何有碍于实施集权统治的人和事所干扰,君主应当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活中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在防范臣民侵逼君权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使臣民尊君事上。《扬权》篇云:“虚静无为,道之情也。……去喜去恶,虚心以为道舍。……主上不神,下将有因。……能象天地,是谓圣人。……主上用之,若电若雷。”这是说君主应当模仿“道”,既使自己处于虚无静默的神秘状态,又使自己具有若电若雷一般的政治威摄力,从而营造一种既神秘又恐怖的强大威势。《主道》篇谓:“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道”之不可见的特性被用来推衍君主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亦要保持神秘状态。君主独居“道”的位置,以虚静无事的姿态使自己处于“暗”处,并静静地伺察群臣的不端行为。可见,在韩非那里君主“体道”实乃一种“假象”,君主只不过是利用“道”来烘托自己的高深莫测和幽暗深邃。在《外储说右上》篇韩非通过援引“郑长者言”明确指出,虚静无为是君主自我伪装的重要手段,所谓“虚静无为,而无见(现)也”。在韩非看来,一俟君主将自己的一切信息完全隐匿起来,那么所有臣民尤其是重臣便无从窥测君主神威,所谓“众人莫能见其所极”;同时君之“静”还意味着君主的“不离位”,即君主无论何时何地绝不将权柄借于任何他者(《解老》)。韩非还在《八奸》《奸劫弑臣》《备内》《八经》《内储说》《外储说》及《难一》至《难势》等篇详加论述君主如何做到自我神秘化。可见,韩非的“虚静”与其说是君主的内在修养,毋宁说是君主的一种自我伪装。
韩非之所以将“虚静”最终归结于君主的自我伪装,关键原因在于他对君臣关系的认识与预设。韩非坚信君臣之间不仅是利益关系,而且是一种势不两立的权力斗争关系,君主因而始终处于两难处境——即君主一方面颇为关心如何有效地掌控整个官僚系统,但是另一方面又对官僚系统尤其是其中的重臣几乎没有任何的信任感,并认为他们统统对君权有潜在威胁,尤其是无法确知哪些臣僚才是真正的威胁。《扬权》篇所言“奸邪满侧”绝非虚辞,至少韩非确实是为君主做如此计算的。这一君臣关系说明韩非触及到了一个隐秘的事实——即在君主集权制度下任何人只要占据“君主”之位,那么他就可以行使君权从而成为最富最贵者(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于是君主权位就最具吸引力,因而也最易受到觊觎。既然君主处于权力斗争的中心地带,群臣又每每利用君主所呈现出的喜怒哀乐以取信于君,那么君主除非甘于被臣下所壅劫,否则首先必须尽可能地克制欲望和收敛情绪,使群臣失去壅蔽君主的把柄。韩非一再告诫君主,权力斗争的复杂性远远超乎想象,群臣皆是君主的潜敌,因此君主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在与群臣的权力博弈中首先必须静观其变。另外君主的个人能力有限,与其亲力亲为,不如“舍己能”而因任群臣去具体作为,韩非的“虚静无为”也有这层含义。
韩非并不满足于君主的自我克制和自我神秘化,如何在“虚静无为”中实现“无不为”才是他真正追求的。韩非承续自申不害的形名之术,正是联结虚静无为与无不为的桥梁。不过,韩非认为申不害的术论因其具有“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的弊端,每每丧失禁奸止邪的政治功效,因此韩非的形名之术实际上是“法”前提下的因任授官和循名责实。在此意义上,“虚静无为”“形名参同”和“守法责成”三者有机地统一于一体,即“虚静以待,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虚则知实之情,静则知动者正。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主道》);“人主虽使人,必以度量准之,以刑名参之;以事遇于法则行,不遇于法则止;功当其言则赏,不当则诛。以刑名收臣,以度量准下”(《难二》)。君主根据臣僚的不同才能,依照法度授予他们相应官职,课考其完成职事的情况,从而做出相应赏罚;在这一过程中,君主不受亲情等一切私情的羁绊和情绪波动的干扰,保持极尽冷酷的清晰头脑,使臣僚在法度的细密规定下各司其职,一切人事变得井井有条,从而呈现出秩序井然的状态。
有学者据此提出法家试图追寻一种“去人格化”“非私人化”的“客观政治”。那么,在韩非那里君主的虚静无为能否真的导向一种“客观政治”呢?在我们看来,韩非的此种君术并不能带来客观政治。第一,就君而言,独占“权原”的君主具有无限权变之可能。第二,就臣而言,韩非的理想之臣实际上是君主统治的工具,他们只能够尊君事上和守法听令,不得有任何独立的个人判断和自我意识,必须绝对依附于君主一人,“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有度》),“不得擅行,必合其参”(《八经》)。群臣看似忠诚于自己的职位,但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仆人的忠诚”,其原则是官吏对最高统治者“不容限制的效忠义务”。第三,就君臣关系而言,君臣间除了利益角逐关系外,还像福柯所设想的全景敞视监狱里监督者和被囚禁者之间的关系,君主天生是那位始终隐于暗室之中而不被任何他者所窥测的监督者,群臣则天生是必须受到君主绝对管控的被囚禁者,君对臣的监管达到了全覆盖和无死角的程度。君主将群臣的一切言行悉数纳入一己之视线,牢牢掌控了群臣的所有信息和可能动向,使群臣的一切行为变得可计算和可控制,但在表面上虚静无为。对君而言,臣民的一切无不透明可视;但对臣民而言,君主始终晦暗不明。于是,群臣被统统“显化”和“确定化”,君主却完全“暗化”和“隐蔽化”!
君主在此虚静无为中俨然编制了一个令人无处逃遁的巨大法网,使群臣不能存有任何试图摆脱君法控制的侥幸心理,尤其是不敢有任何政治野心,群臣犹如笼中困兽一般只能悉听于君,他们无从知晓君与君法到底如何变、何时变,因而颇有伴君如伴虎的恐惧感。同时,君主可以随时随地且高深莫测地运用“倒言反事”“挟知而问”以及“疑诏诡使”等宦术来考验臣下的忠诚度。于是君主尽管“无为于上”,但群臣不免于“竦惧乎下”,臣尽管是贤智之士,但最终结果只能是“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主道》),群臣只得抱着始终不渝的待罪意识奴事王廷。在与群臣的权力较量中,君主总是名利双收。不宁唯是,举国境内无所不在的密探随时随地监督和告发背离君主的一切“奸情”(《内储说上七术》)。君主营造出人人自危的政治氛围,最主要的目的便是使任何胆敢壅蔽乃至劫杀君主的企图止于未萌,使臣民连这种想法都“不敢”有,只能选择顺上之为,这便是韩非所言“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说疑》)的真正要义所在。
君主尽管看似虚静无为地隐居于深宫,但是他“明照四海之内,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奸劫弑臣》),于是一位表面虚静无为而内心却贪躁无比的君主形象呈现了出来:一方面,他对身边的一切人事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在极度的孤独中惶恐于最高权位之可能被僭夺——一个视权位为第一生命、不信任任何人,却又希望其他所有人皆处于自己掌控中并能够随时随地为己所用的人,难道不孤独和惶恐吗?表面的不动声色恰恰起到了绝佳的掩饰之功;另一方面,君主绝不甘心于无所事事,无为而无不为的统治手段正好满足了君主对所有人事无所不管的本能需求。此种虚静无为在君欲的不断膨胀中势必异变成为一种政治权谋,成为绝深城府与极尽宦术的合体。有学者指出,韩非的“虚静”透显出杀气腾腾的气象不无道理。
韩非在《解老》篇明言,唯有圣人可以“爱精神而贵处静”,反之一旦“精神乱则无德”。可问题在于,生而在上且拥有绝对权力的中主不大可能是如此这般爱精神的圣人(尽管他们每每自命如是),君主的权力欲只可能无限制地膨胀而不是相反。拥有绝对权力的中主正如韩非自己所言,定然“欲利甚”“智慧衰”“失度量”“妄举动”(《解老》),“不顾社稷而轻为自信”(《亡征》)。然而这类君主正是韩非极力反对的——这大概是韩非所做的一种自我否定。这一“否定”也表明,对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而言,具有个人修养和行政理性含义的治理之术最终不免反噬于政治权谋之术。
三、因人情与逆人情
君法和君术最终均得落实于君主对臣民的赏罚上,而赏罚之所以有效则是因为“人情”有“好恶”。韩非的人情是指人趋利避害的真实情态,所谓“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奸劫弑臣》)。韩非进而指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八经》)。这一“因人情”而治的表述实乃一个极具包容性的叙事。因为最根本的人情——“人之为人”的诉求是,人追求“好”的“可能生活”而讨厌所有的坏生活。人们追求的好生活不仅需要物质保障(这是底限),还需要精神食粮(这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精神追求才构成生活的根本问题。当然,所谓好生活之“好”实为一个永无止境的理想而已,迄今为止仍无一个确定的最好状态。如若为政者真的能够因循人情,社会状态虽不一定臻于最好,却不至于太坏。然而,韩非的因人情只是君主利用臣民的本能反应来实现集权统治的统治方略。
对臣而言,臣下只是单方面绝对顺从君主的工具,甚至于被明确“兽化”:“夫驯乌者断其下翎,则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驯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禄,不得无服上之名”(《外储说右上》);“若如臣者,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内储说上》)。对民而言,农民与战士被视为对君主及其霸业最为“有用”的两类人。韩非深信唯有运用名利杠杆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民众投身于农战的积极性,因此需要使民在农战中得到实惠,同时对无益于农战者统统给予重罚。在此因人情的过程中,所有人被塑造成为千人一面、众口一词的顺民。
不少学者认为韩非的因人情意在强调君主应当“顺应”人情来治理国家。韩非在内的法家确实从来没有试图压抑人的欲利之心,反之极力强调君主应当引导臣民的这一人情。问题是,即便就最低层次的本能欲求而言,“人”并不应当只按照统治者所确定的方向或标准去生活。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种道德理由或其他正当理由说服人们相信,黎民百姓需要/必须为那些贪得无厌的在上者做出各种牺牲。虽然先秦不少思想家对“人之为人”的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则是相通的——他们大多认为人应当超越人与动物所共同拥有的本能欲望去追求某种更高的价值或意义。
在韩非那里君之因人情的治国方略恰恰只是控御所有臣民的本能欲求从而使得“君”变成君以外所有人的“目的”。韩非坦言:“夫上所以陈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显学》)“易民死命”正是君之“因人情”的本质所在。《制分》篇谓:“好恶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上掌好恶以御民力,事实不宜失矣。”这里的“制”“掌”“御”三字颇为传神地将君主掌控并驾驭君以外所有人的政治用意凸显无遗。不过,韩非显然意识到将所有臣民变成君主统治的工具并不合乎臣民的根本意愿,故而主张以严刑重罚使不顺从者就范,对于赏罚不奏效者则“除之”。韩非始终不大关注“人的本质、价值和意义是什么”等人之精神层面的问题,而是出于佐助君主统治的目的刻意强调或夸大“人情”之中趋利避害的那部分。因为只有将人所共有的物欲需求和本能避害的本性紧紧抓住了,君主才有可能通过把握共性从而泯除群生之个性,以达到整体控驭的政治目的。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韩非的“因人情”实质上就是“用人情”,即君主利用臣民对功名利禄的本能需求和对严刑峻法的本能畏惧来实施高效的政治控制,君主通过因人情试图将臣民塑造成为只对君主甚为有用的人,于是“因人情”倒向了“逆人情”,悖逆了臣民有关人之为人的人情。
学界有种说法认为法家的因人情具有“爱民”的政治指向,比如梁启超认为法家“本意实为人类公益”,另有不少学者认为韩非等法家诸子是“爱民”的。在韩非那里君之“因人情”真的以“爱民”为最终目的吗?
臣民在君之因人情中确实获利不少,适如《六反》篇所言臣民只要“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另外韩非反复强调“爱民”是君主应当所为——这或许如学者所言可以反映出韩非具有爱民的“理论动机”,但是韩非自导自演般的爱民说辞无法说明其治道的正当性。实际上法家从不讳言“富民”“爱民”与“利民”等只不过是君主实现御民目的的重要手段,“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计上之所以爱民者,为用之爱之也”(《管子》之《法法》《治国》)。韩非更为极端,他强调所有臣民必须(“不得不”)为君主所用,并且将臣民“有功则利上”的治国之道称作“必然之道”。君主的功名利禄和严刑峻法最终均是为了使臣民在“尽力于权衡”和“死节于官职”(《守道》)的过程中完全听命和顺从君主,毕竟“人不乐生,则人主不尊;不重死,则令不行也”(《八说》)。可见爱民实乃一种自我说辞,这是法家自己的明确说法。
君主之所以需要这般“爱民”,就在于战国时代编户民地位的重要性。他们既是军队的主要来源,亦是其他各类徭役和赋役的主要承担者。作为“民之主人”(即“民主”)的君主必须高度重视“民”。一旦政权缺少了民的支持,或者说民被压榨得不得不揭竿而起,这绝非任何一个稍有理智的统治者所愿意看到的。正因如此,韩非在内的法家强烈建议君主需要“爱民”——尽可能地调适君之无穷欲望与民之有限承受力二者间的矛盾,在“用民”之时切忌竭泽而渔!正是在更加长久的用民层面,韩非坚决反对君主毫无节制地“劳苦百姓,杀戮不辜”(《亡征》),要尊重和保障民众“饥而食,寒而衣”的最低需求(《安危》)。
民之所以不得不接受君主的“爱”,最关键的原因是,战国时代最为主要的生产/生存资料即土地完全垄断于君/国之手,君主直接统筹“为国分田”“制土分民”的所有事宜,并逐渐通过郡县制、户籍制等将基层民众悉数纳入直接控制,于是民不得不唯君是从。在君主全然独占“利害之道”的前提下,“利于民者,必出于君”(《八奸》),一切不合乎君国之“公利”者统统被视作“私利”而归于禁绝之列,所有臣民只得心往君处想而力往君处使,他们若想“活着”或者在物质上过得更加富裕一些,只能够“仰生于上”(《管子·君臣上》)。
韩非的“因人情”不仅逆了臣民的人情,亦逆了君主的人情。初看来,君主所获之大利最多,不仅有物质的无限享受,还有控驭臣民的满足感和实现“伟大理想”(却无视“民”之死活)的成就感,尤其是他拥有任何臣民无法企及的活动空间和选择自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虽然这被韩非明确反对)。但是当君主自视做了其他所有人的“主人”之时,他亦将自己置于“奴隶”的地位。只不过,君主从来不愿意忍受“人”的支配,却心甘情愿于接受“物”的奴役!在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里,个人所占据资源的多少与其拥有权力之大小适成正比,因此“权力”本身就等同于一种可以换取一切资源且最具诱惑力的“物”。在自己无穷无尽的物欲享受,尤其是无限权力欲的裹挟和诱迫之中,君主最终沦为己欲之奴仆——君主亦活得不像“人”。
韩非对此直言不讳,如同将所有臣民兽化一样,他亦将君主兽化,只不过君主是更具神性的“龙”和比“狗”更厉害的“虎”(《说难》《二柄》)。龙虎虽颇富“神”“力”,但终归只是兽。在“以兽治兽”的世界里当然不会有关于精神生活的深远关切。君主缺少精神生活的自我追寻,当然不希望其他所有人有此诉求;君主自己活得不像人,当然不会使他人活得像人。对专制者而言,权力就是第一生命。韩非确实只是为君主的本能欲望即权位的恒久稳固而苦苦思虑,并未认清君主亦应当追寻人之为人的精神生活。韩非治道设计的对象——中主恰恰就是这类只可能无限追求绝对权力而漠视精神生活的君王!韩非的“因人情”只是君主刺激、调动、控驭和满足人情之中最低层次的本能欲求,既使君主以外的所有人不成其为“人”,亦使君主自己不成其为“人”。
四、 韩非君道论的内在逻辑
不少学者已经指出韩非学说内含深刻的矛盾。梁启超将法、术、势分别总结为法治主义、术治主义和势治主义,认为术治主义是“人治主义之一种”,“势治者正专制行为,而法治则专制之反面”。梁启超的观点是否完全准确,姑且不论,但这至少表明他认识到法术势三者是有矛盾的。王邦雄指出君势的抬头导致国法下落,这说明他认识到了法势之间的矛盾。刘家和认为,法、术、势三者虽是互补的,但三者也有矛盾,表现为法术之间、法势之间是有矛盾的。蒋重跃进一步指出,不仅法、术和势三者之间有矛盾,而且三者各自内部亦有矛盾。还有学者从其他角度解读了韩非学说的矛盾处。张祥龙指出:“法家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奇观:初看极为理想,极其现实,极巧妙;初用之,极有成效,极能富国强兵。但它善反噬,稍有疏忽,或简直是不可逃避地会吃掉使用它的人。”在张祥龙的基础上,黄启祥从法家思想对法家人物反噬的角度讨论了法家学说的内在矛盾。尤锐(Yuri Pines)指出韩非君主论的主要悖论是,一方面理想君主被预设成为全知全能的统治者,但另一方面君主一再被提醒在治国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地去除个性化。本文正是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讨论。不过韩非学说尽管内含深刻的矛盾,但是在强化君主集权、维护君主绝对权威上却具有高度的自洽性。
韩非在《大体》篇集中呈现了君主在践行其君道论后所达到的“至安之世”。在这一至安之世里,作为韩非理想中的君主,“圣人”能够体察和因循天地之道,通过“因道全法”将一切政治事务悉数交付于“道法”,并保持“澹然闲静”,既“不急法之外”,亦“不缓法之内”。所有臣民莫不悉知“祸福生乎道法”,因而不得不将言行统统调整于法度以内。如此保全“大体”之君看似“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一如学者所言怀揣着“美的理想”,但实则已通过“道法”的形式将自己意志公布于天下。包括君主在内的所有人看似莫不处于法度以内,但实则只是君主弄法前提下的臣民守法。臣民越是守法便越是依附于君主,绝对的顺民连“怨心”和“烦言”都不敢有。天下所有人统统顺从君主,因此也就没有了战争——这正是战国时代近乎所有君王所期盼的,即通过富国强兵扫荡宇内而唯我独尊。当天下只剩下君之“道法”这唯一的是非准则时,历史书写亦就失去必要性。再结合《难势》《功名》等篇可知,韩非深信无须等待尧舜一般的圣贤之君,只需要中主就可以通过“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实现这一理想治世。
韩非清醒地认识到能够真正体道守法、虚静无为和因人情的君主绝不是平庸君主,只可能是那些拥有超凡聪慧的圣君明主——这也正是《韩非子》中为什么大量出现圣君明主的重要原因。韩非的理想君道并非中主所能胜任,这显示出韩非对理想之君的某种期待以及韩非政治思想的理想性。问题是,如若君主不圣不明,又当如何呢?
韩非认为“法术之士”可以担当起“矫人主阿辟之心”(《孤愤》)的大任。不过,韩非的谏诤之论也存在深刻的矛盾。其一,韩非反复告诫君主万万不可信任任何臣下,君主又因何应当完全信任法术之士呢?其二,韩非深信人情好利,人际之间根本没有超越利害算计的纯粹关系,那么法术之士不惜以死为代价来表明的“尊主安国”之心又从何而来,法术之士与君主之间又如何在根本利益和政治信仰上保持高度的一致呢?其三,韩非坚决反对任何臣僚窥测君心,然而韩非自己却是(先秦诸子中)揣摩君主心理最多者。这不是矛盾,又是什么呢?其四,君主既已成为乱君暗主,又怎么可能洞察法术之士的一片忠心,并相信法家之道可以去乱求治呢?其五,集权制度的“法”偶尔与当下的君主意志会有抵牾,重臣之所以每每深受君主喜爱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会随机应变地在背离法度的同时又迎合当下君主之喜好。在此情形下,法术之士的“强毅劲直”恰恰会招致君主的反感和排斥。为了进谏成功,法术之士需要“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说难》),最大程度地迎合君主好恶,这与重臣的所作所为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进言之,这种获得暗主之宠信的“恶手段”又如何为其所谓的“好目的”做正当性辩护呢?其六,韩非坚决反对重臣结党营私以壅蔽其主,那么法术之士若得到君主信任并受到重用,又如何保证他们不与重臣一样权倾朝野甚至剑指王冠呢?韩非颇有真理在握的高度自信,这也是他偶尔将法术之士等同于圣人的关键原因。然而法术之士冒死直谏只不过是在绝对认同君主集权统治的前提下,去说服君主践行法家的必然之道,从而使所有臣民不得不“爱君”。正因如此,这些直谏之臣的存在对君主的集权统治只有益处而不是相反。
韩非深信“忤于耳而倒于心”的至言最终“非贤圣莫能听”(《难言》),这表明他已隐隐预感到法术之士的劝谏最终难免失败的宿命。然而韩非并不质疑暗主在位的正当性,而是转向了彻底认同。韩非明言即使君主真的错了,只能是“臣任其罪”(《主道》),因为“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忠孝》),甚至于“主而诛臣,焉有过”(《外储说左下》)。这些决绝之辞实际上将君主置于一种可以随意宰制臣民的绝对地位,这体现出韩非“绝对”的尊君指向——即君主再怎么昏庸无道,任何臣下都不应当有任何的反叛之心和革命之举,君主占据绝对权位已然被视作天经地义!虽然先秦诸子大多将君主视作“秩序”和“治世”的最高象征并有程度不一的尊君倾向,但是鲜有如韩非这般绝对和直白者。战国时代君王们最大的“人情”是“好”永保权位之不失(哪怕自己昏庸之至),“恶”失去这种权力(不管什么理由)!韩非显然洞悉君主的这一最大“人情”,并深以为然。在绝对的君权稳固面前,君主的“明”与“暗”已然无关宏旨!韩非的这一绝对尊君观念,当然与韩国长期以来君权不振、国力孱弱因而在列国纷争中每每处于弱势地位不无关系。另外,韩非尽管对他所知的近乎所有君王都颇有微词,但他的这种批判实际上在更高的层次上肯定了理想中圣君明主统治的天经地义,他对现实中的君王们颇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意味。
韩非君道论是他对周秦之间历史变局所做的独特的理论回应。《史记·梁孝王世家》云:“周道尊尊者,立子。……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长子。”《史记·高祖本纪》谓:“周秦之间,可谓文弊矣。”牟宗三指出先秦诸子皆是从不同角度来思考“周文疲弊”问题的,所谓周文亦即“传子不传弟,尊尊多礼文”,它主要是指周代的典章制度、礼乐文化等一整套的制度体系和文化系统,其中“尊尊”乃“文之所以为文之切义也”。周文疲弊的重要表现便是周天子王权式微、礼废乐坏和秩序失范。在牟宗三看来,先秦诸子中唯有法家“将周文疲弊视为一政治社会之客观问题来处理”。处于诸子之殿的韩非将其治世理想完全建立于绝对君权基础上,与他极端化发展周文的“尊尊”观念不无关系。韩非坚决认同三代以来“家天下”的事实,并且从“道”的层面论证了君主永享国祚的不容质疑性。这是韩非之所以极少正面讨论君主权力来源的关键原因,因为三代以来“打天下”始终是“家天下”的最大理由,而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等权位传承方式,只不过是“打天下”和“家天下”之政治逻辑的具体表现而已。韩非向来被视作具有变古倾向,但在绝对认同家天下这一点上他显然处于历史发展脉络的延长线上。韩非又进一步将“尊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西周春秋的“尊尊”是在注重宗法血缘亲疏的礼乐文化氛围中展开的;韩非的“尊尊”则完全建立于君臣市交的冷酷计算基础上,这是他对战国以来列国变法之后,君主集权制度不断得到强化的认同和理论回应。西周春秋的“尊尊”重视在上者与在下者之间的双向关系,即只有当在上者率先尽到应尽之责任后,在下者才有服从之义务;韩非的“尊尊”则强调所有臣民无条件地效忠君主的单向关系。君主在绝对掌控官僚系统的基础上实现臣民统统顺从于君主,便是这一单向政治伦理的集中体现。这一致思逻辑贯穿于韩非君道论的始终。
王元化指出:“许多论者评价韩非,往往撇开他的君主本位的基本思想而加以拔高。”更准确地说,试图拔高韩非政治思想的学者往往并未漠视韩非的君主本位观念,而是“预设”真的存在一位拥有绝对权力,且可以克制一己之欲进而为天下苍生负责的君主。尽管韩非一再强调君主应当节制己欲,但是对于战国中后期已然拥有无上权势的君王而言,其欲望不会比其他任何人少,反之随着见到的、得到的乃至想到的东西愈多,其欲望只可能无限增加,适如《管子·权修》篇所言“人君之欲无穷”。列国国君所主导的“海内争于战功”(《史记·六国年表》)以及因之而来的残酷的列国纷争,是为显证。尤其在韩非那里君主已然被视为“应当”永远掌控绝对化权力,由此不难想见,君主权力欲中永无底线和绝无止境的支配欲必然无限膨胀,更关键的是,君主完全可以利用无人敢违逆的绝对化权力反反复复地徘徊于“制造欲望”和“实现欲望”之间。任何试图低估权力之为恶可能性的高调说辞,终将在权力自负的事实面前黯然失色。韩非君道论以极端的形式呈现出了中国古代“得君行道”思维的理论困境。
韩非的“明主”最终成为一种象征性和符号化的政治权威。该明主在控制臣民的时候亦要做到近乎严苛的自我控制,使自己的欲望和行为严格限制在不致威胁集权统治本身的限度内。现实中的君主若效仿该明主便可以使臣民相信君主权力具有虽远必诛和摄人心魄的强大威势,又使臣民尤其是重臣莫不感到君主遥不可及和永远高高在上。韩非一方面试图最大程度地佐助君主集权,另一方面又提醒君主需要减少个性化的施政方式,韩非君道论因而呈现出深刻的矛盾。不过诚如蒋重跃所言:“迄今为止,人类发明和设计的各种社会方案,还没有发现哪一家是没有矛盾的,有时矛盾的尖锐性与思想的深刻性恰恰是正相关的。韩非思想体系,不但展示了战国时代社会和政治的矛盾,更显示了它作为伟大思想所必须具备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此论甚是。韩非君道论既展示了韩非对东周乱世如何“为治”的独特思考,亦体现出中国古人“得君行道”政治思维的深刻悖论,还体现了君主集权制度的运作逻辑与内在矛盾。我们也绝非自认比古人“高明”,从而无端贬低韩非及其学说,而是要通过进一步的疏解来“接着讲”韩非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本文的意指亦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