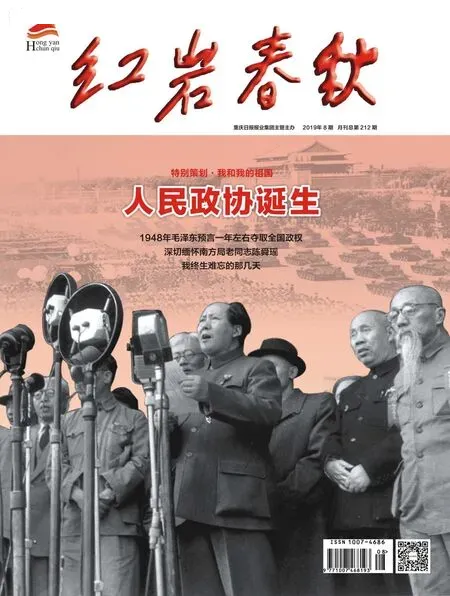风雨老城墙
■许大立
家住七星岗,紧挨通远门,闲来无事,不经意就把通远门老城墙一带,当成了散步喝茶聚友谈事读书写作的好地方。遛久了才知这地方不简单。
据称通远门老城墙的第一块巨石,在三国时期就垒砌上了,距今约1800年。蒙元军在这儿攻过城,张献忠在这里杀过人,近现代通远门周遭还发生了一些惊心动魄惨烈壮怀的故事。通远门厚重的石头足以写成一部车载马驮捧读不倦的史鉴,一本家国情怀可歌可泣的大书,一曲改朝换代吟唱千年的长歌。难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桂冠,落在了通远门及硕果仅存的这段老城墙上。
抗战时期,郭沫若曾在不远处的天官府办公居住,常邀约一帮左翼文化名人如老舍、茅盾、夏衍、阳翰笙、田汉诸公,在天官府11号“马老太婆小牛肉馆”聚会。一次酒后兴之所至,郭沫若给这家小馆子取名“星临轩”并书写牌匾。其语双关,马老太婆之子名曰“星临”,而今文星聚集,实乃名副其实。后来,“星临轩”几易地址、老板,如今移到了通远楼上成了茶楼。郭沫若题写的店名还在,只不过此地空余一招牌了。
近些年,通远门也不乏文人雅士造访登雅。著名诗人梁上泉曾在附近小区居住,偶尔会去城楼上登高望远激发灵感。誉满文坛的女诗人傅天琳,就在俯视通远门的那栋高楼里居住,一住就是十多年。她天天带着小孙女爬城楼,数台阶,骑大炮,等到孙女长大,才依依不舍弃城楼而去。为了记录这段难忘的日子,她写下了长篇散文《家住通远门》。小说家曾宪国更是把通远门当成了自己的茶坊,不论风雨,日日必至,一碗茶,一本书,构思小说。日久天长,写就了长篇小说《门朝天开》。
域中文坛菁英新秀,应我之约请或被我“蛊惑”自行登此楼的也不计其数,如散文家兼诗人、漫画家、摄影师李钢,小说家兼剧作家王雨,出版家兼诗人、散文家吴向阳,诗人兼评论家王明凯,诗人词家兼散文家耕夫,散文家兼文艺评论家赖永勤等。如此盛况,可见通远门文脉畅达承前启后,如江河之水涌流不绝。
其实我对通远门的最初印象来自父母。抗战时期,他们曾在离此百步之遥的莲花池办学,曾一次次说起当年通远门内外的破败与穷困。窝棚遍地,污水横流,难民满街。通远门新生于20世纪90年代。那时,蜗居于城楼上下的成百号人家响应号召纷纷搬离另寻居宅,从此通远门一改杂乱褴褛之容颜。
如今的通远门老城墙,仍威武霸气,横亘于渝中要津之上,虽周遭高楼林立,却难撼动其雄奇于分毫!新楼千栋,时代巨变,掩不去历史,冲不走文化,更显示出通远门的贵煚珍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