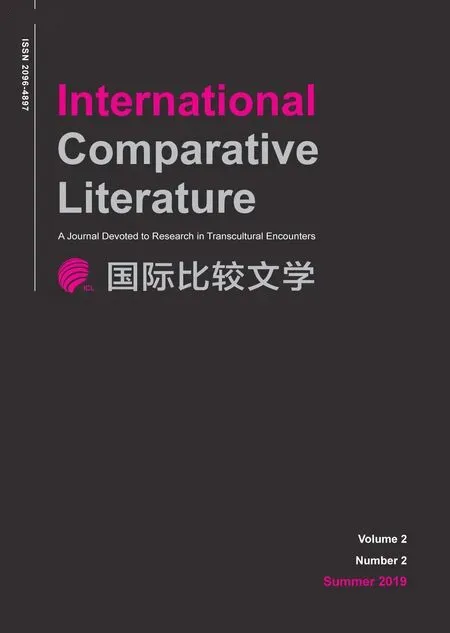谢 志超:《 自由主义传统的书写者:杰克·克鲁亚克》
董伯韬
自硕士论文《〈去吧,摩西〉的艺术性》算起,春华秋实,风雨星霜,从岳麓山到镜月湖,从人生的初春到仲夏,谢志超教授的问学之途由约克纳帕塔法县一路伸延至康科德、洛厄尔镇、纽约长岛……,于是,福克纳、爱默生、梭罗、惠特曼,这些璀璨的名字辉映在她的笔端。而更让人感佩的是,面对这些神魔之人,她始终保有身为研究者的矜持与适度的疏离。爱固然可以是学术思考的起点,但多一份自尊与独立的爱当然更成熟。研究中,她既不率意褒贬,更不趋奉某家之说,而是尽量多地收集、利用最原始、直接的文献,以期进入当日的历史-文化-心理语境。
新著《自由主义传统的书写者——克鲁亚克》凸显了她的这一治学风格。在书的开篇,她即以细密的史料揭示了克鲁亚克形如悖论的人生:外表乐观、开朗,内心却盈满脆弱、感伤;行事独立却惯于依赖;从小厌倦漂泊,漂泊终成宿命;一面一再否定、拒绝外在的秩序,一面不懈追寻、构筑内心的和谐。显然,这已不完全是人们先前熟知的那个出现在文学史或现代名人“点鬼簿”里的克鲁亚克:那个与金斯伯格、巴勒斯齐名身为“垮掉派”代表人物的克鲁亚克;小说家克鲁亚克;禅修者克鲁亚克;因崇敬陶渊明而改名为“陶·杰克·克鲁亚克·明”的克鲁亚克,眼里蕴着叛逆、蓄着依恋、藏着天涯的高傲、俊朗、不驯的克鲁亚克;由作者、研究者、译者、读者共同营造的存在于自己的不存在之中的神话的克鲁亚克。相反,在全书262页正文里,作者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克鲁亚克,一个克鲁亚克一生塑造却没能完整、完全写出的自我——如众所知,纵使是自传式写作,书写者也会有意无意地凸显或遮蔽自身的某些方面,而不会把自己曾经的、当下的、亲历的、梦想的一切和盘托出;自我省察与读者期待会在无形中规限作者书写的方向与边界。
与阿兰·罗布-格里耶同龄,克鲁亚克生于“一战”结束后第四年——1922年,成长岁月里有“大萧条”的风霜,有“二战”的硝烟,有和现代世界一起历经劫毁而夷为历史废墟之寓言的现代文学——《尤利西斯》《荒原》就在克鲁亚克出生的年份先后问世而T.S.艾略特是其一生酷爱的诗人。“我想成为一名作家。我想写很多书。比你还有力量。” 作者在书中援引少年克鲁亚克与其信任的阿门德·斯柏克神父这段对话当有深意存焉。书写之于书写者是一种救赎,是在被世界剥夺之余获得的某种补偿与慰藉。而克鲁亚克最打动她的似乎是其热血燃尽的冷漠与厌世的眼眸里偶尔泛起的深情。“我的哥哥被埋葬在这里。那个雨天,一百多个孩子围绕装着哥哥的棺材唱着歌。我们把他缓缓地放入墓穴。每个人都在哭,除了我。”(《杰拉德的幻想》) “可是彼得,虽知道父亲已经去世,却拒绝相信事实。他走过去,抓起无力的手腕,试图感觉脉搏……他大声呼喊,他的声音孤独、疯狂,响彻整个空旷的屋子。他仍然拒绝相信,带着强烈的迷茫,他伸手轻抚父亲的脸,像个孩子,他现在知道他可以任意轻抚父亲的脸,因为他死了。”(《镇与城》) 哥哥与父亲的死是写实也是象征,象征源自生命根柢处的缺失,象征人存在的困境。而这种缺失和困境是克鲁亚克流浪的起点和原动力,福祉与愉悦——克鲁亚克这样解释“beat”——都在别处,在路上,在寻找中。
流浪是现代人的际遇,更是现代书写者难逃的宿命。像波德莱尔一样,让·路易斯·杰克·克鲁亚克是注定的流浪者、天生的异乡人。他的名字就回响着不同族裔不同文化移徙、邂逅的跫音:“让”是他那有着印第安血统的外曾祖母的姓,路易斯则是身为法裔加拿大人的外祖父的名字。而在自己能够做出抉择前,克鲁亚克就已避无可避地栖居于语言飞地里了。因为父亲里奥·克鲁亚克和母亲加布里埃尔·莱维斯克都是来自加拿大魁北克地区的移民,他从小就习得一种法语方言——即加拿大魁北克人讲的法语——若阿尔语,直到六岁才开始学习英语,十八岁以后方慢慢掌握标准英语,而终其一生,在与朋友把晤闲谈或鸿雁往来里,他都间或使用法语,在法语中,他的生命似乎更为惬意。
书中,作者以细腻灵动的笔触描述了克鲁亚克的身份迷思。“他儿时从父辈们那里听说自己的祖先是从康沃尔郡来的法国布里多尼地区的男爵,从此坚信自己是远古的凯尔特人的后裔,是康沃尔郡的子孙,是真正的贵族。他甚至推断他的家族从亚瑟王国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岛来到康沃尔郡,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而是地地道道的凯尔特人。他由此拆分并解释了自己名字的意义。‘KER是房子的意思,OUAC是在田野里的意思。两年以后,在另一次采访中,他说KER是水的意思,OUAC则是语言的意思,甚至还说Kerouac是古爱尔兰语Kerwick的变体。'”并将这一令人忍俊的轶事与克鲁亚克路上小说创作联系起来,揭示创作主体的个人心理对其作品题材和主题的影响,堪称巧思妙悟。
进而,作者指出,克鲁亚克的流浪之旅不止伸向现实的异地,更通往精神的异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高更、庞德、谢阁兰、克洛岱尔、圣琼·佩斯等西方诗人艺术家就已走出欧洲传统,在东方异质文化中寻找可资借鉴的创作元素。那么,与这些前辈相比,克鲁亚克的异域想象又有哪些异同?作者认为,他们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认为,异域既非棕榈骆驼,亦非民族衣裳,更不是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趣、美丽风景、难忘的记忆、非凡的经历的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而稍有不同的是,克鲁亚克强调:“地理上的漫步毫无意义,真正的救赎不是向外的长途跋涉,而是内在的旅程,最终到达思想的门口。”因而,克鲁亚克在东方文化尤其在禅中寻找的是新的生活方式、是心灵的安顿处,而不仅是创作上的灵感与技艺。在《最后的话·第九篇》中,身为天主教徒的克鲁亚克展现了自己如何在生活中体认禅的真谛:“禅就像凝视一个单词几分钟,直到它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所有意义……禅就像一双手从背后轻轻地捂住你的眼睛让你猜:‘我是谁'……禅就是一种方式,当你在某个遥远的梦境中醒来,你会说:‘啊,太好了!'……禅就是彼得·奥洛夫斯基第一次看见一个穿着裘皮大衣的女子弯腰在一个垃圾桶里翻阅一份报纸,他于是靠过去问:‘您确定在寻找什么吗?'……禅就像把你的信件投入一个弃用的邮筒……”对这一文化现象,作者从比较文学学者的角度做出了颇有启发的诠释,她写道:“在克鲁亚克那里,佛教文化与天主教文化并没有相互抵触,即使在他佩戴十字架参禅冥想的时候,他也从未因此困惑。那时的克鲁亚克,早已跨越东西方宗教文化的重重壁垒,以更广阔的胸襟看待自我与他者,以更平和的心态谛听异质文化间的对话。” 旨哉斯言,置身多元文化的当下,承认 “多”,尊重“异”,一方面保留异质文化平等的观念,另一方面则强调多元中的交融与混血,如是,方能增强自我,丰富自我,而绝非抹杀自我。这,或许正是新人文主义发硎之砥石?
作者在关注克鲁亚克写作主题流变的同时,一样重视这位自我世界的探索者与殉难者在写作形式上的创新。这是颇有见地的,直接呼应时移世易的,并非内容上的机械反映,而是具体形式的创新不是吗?而就克鲁亚克来说,作者指出,他“反对任何缺乏美感与艺术感的写作活动。他的乌托邦式的、反社会反传统的文学创作思想,注定具有破坏性和颠覆性”,在具体形式上,克鲁亚克常常使用第一人称(在上帝已死、意义匮缺的世界,使用第三人称全能视角俯视众生岂非僭越?);在叙事中有意无意隐去怪兽似的宏大历史;对残酷的世界报以露骨的不屑;虽无力也无心倾覆各种主流建制,但却以自己真实的痛苦和迷惘揭示了后者的虚伪与苍白;至于克氏最具个性与原创性的自发式写作,作者认为其长句纵横、破折号绵延的汪洋恣肆的文风包举囊括了不同的创作元素:既上承梭罗、惠特曼,复兼容普鲁斯特,且将美式博普爵士乐、日本俳句等共冶于一炉,亦可谓深造有得之言。
读完全书,稍感遗憾或者不禁感慨的是,学术传统的顽强及其对学者无形间的制约。略举大端,譬如,对文学作历史和哲学的思考这一研究方法仍有些许执念,作者本以材料、辞章见长,有时却不免循例将克鲁亚克及其创作纳入历史-哲学这一并不很有效的坐标系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