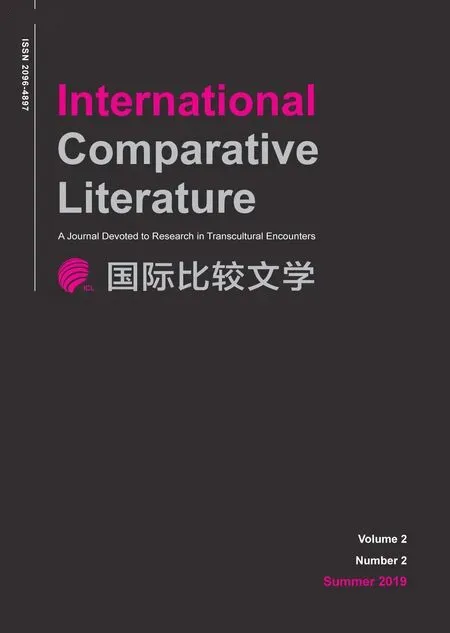( 美)浦安迪:《 〈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
吴可
新近由夏薇翻译,三联出版的浦安迪《〈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以下简称《原型与寓意》)一书,可谓姗姗来迟,因为这本中文世界的新书其实是四十多年前的旧作。有意思的是,根据夏薇译后记的说法,“红学界许多同仁虽然也都听说过这本书,红学史著作及关于海外红学研究的文章中虽然也都早已为其留置一席之地,”可以说,这是一本中文世界的“传说”之书。其先声夺人之势,在出场方式上,倒是与所研究对象《红楼梦》中的一钗,即王熙凤颇有些类似。但何以竟会迟到如此之久呢?此中缘由译者没有分解,或许是因为原因太过明显——更为中文世界读者熟悉的是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初版于1996年,并在2018年再版。《中国叙事学》的基础是浦安迪在1989年3月至5月在北大中文系和比较文学研究所开设“中国古典文学与叙事文学理论”的讲稿整理,之后,根据浦安迪所述,“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同行对我的观点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总体的印象,我在书中添加了相当大篇幅的新内容,这些新的观点和材料,或取之于我的英文专著《〈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1976)和《明代小说四大奇书》(The Four Masterpieces of the Ming Novel: Ssu ta ch'i - shu, 1987),或采之于我在过去二十年间主要用英文发表的许多篇论文里的内容。”
由此可见,某种意义上,《中国叙事学》一书是一本集诸本书之大成者,尤其是浦安迪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叙事学”这一概念,不仅直接回应了被“五四”新文化运动者所接受的西方批评界对中国古典小说“缀段性”,即叙事性匮乏的讥评,做出了四大名著实乃文人小说而绝非通俗文学的判断,而且还将“史诗-罗曼司-小说”(epic-romance-novel)打回到西方的特殊文化背景之下,否认了其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尽管“十回”结构、“平方数回目”演化、“五行框架”等提法,存有不少争议,但《中国叙事学》确实带来了一次较为系统的结构主义式的叙事学理论阐释(或许更多倾向的是一种修辞学)与文本细读的示范。经此一役,回过头来再看《原型与寓意》这本浦安迪而立之年的处女作——脱胎于他的博士论文,在感到亲切之余,又不由得充满一丝隐忧:如何阅读这本迟到的新译旧作?
确实,因为《中国叙事学》或多或少地“剧透”在先,《原型与寓意》字里行间所携带的理论冲击力,大部分都如今只道是平常,但如若就此徘徊在“食之”与“弃之”之间,则显然是忽略了《原型与寓意》的理论密度与比较文学的广阔视野,是有欠公允的评判。这也是《原型与寓意》在文风上(当然也不避免地是浸润了译者风格之后的结果)迥异于《中国叙事学》的所在。正是这种迥异提醒读者注意,在《中国叙事学》中未作过多纠缠,或表述上采取“便宜法门”之处,尤其是两个核心概念“原型”和“寓意”的理论内涵,以及由此展开的理论推演,恰应该回溯到《原型与寓意》之中做较真的反思。只有这样,“剧透”的片段,才能在所谓“旧作”的系统结构之中,获得更新的整体性。由此,我们发现,这种译介上的时间错位,恰恰构成了一种普鲁斯特式的“追寻逝去的时光”,也契合了《红楼梦》“一一细考较去”,所追寻、考较的是浦安迪的研究起点,也是总体性这个概念,或者换用另一个高频出现的术语“全视觉”的所指,即“为什么阅读《红楼梦》这部清代小说会带给人百科全书式的丰富感受”。
“总体性”“全视觉”“百科全书式”,这三种表述传达的是一个意思,也是在讨论浦安迪深受神话-原型批评影响之前就必须明确的一个理论立场,即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有机整体论。浦安迪对有机整体论的竭力捍卫,除了因为他明确交代的“百科全书式”的阅读经验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潜在的巨大焦虑,甚至本身是先于阅读经验的前提性问题——到底要阅读哪一部《红楼梦》?暂且先抛开具体版本不谈,是阅读八十回本,还是被认为有高鹗参与的一百二十回本。这就自然牵涉到“结局”的问题、整体性的问题。尽管浦安迪直到最后一章“结局与结论”,才正面这个问题,并给予高鹗积极评价,“归根结底,他使得这部书得以完成,”“这部由曹雪芹开始、由高鹗结尾的伟大作品中贯穿着一个从‘欢中悲'和‘悲中欢'而来的美学模式,这两种人类经验最终在逻辑上是相互关联的,”但在“导论”开篇的注释里,已经表明了这一巨大焦虑,“当这些书页付梓之际,戴维·霍克斯(David Hawkes)以其精湛技巧最新翻译的前八十回书名为《石头的故事》(《石头记》,对小说前一部分的通称),可能已经在英语读者中间开始取代《红楼梦》,”套用一句可能不合时宜的表述,摆在浦安迪面前,尤其是在成书之际面前的,是两个“红楼”的“路线斗争”——《红楼梦》vs《石头记》。由此,原型和寓意这两个理论概念被更多地压抑到了文本分析的实用性工具层面,而非拔高到“斗争”的战略层面,“我们必须强调,这里所关注的是一个独特而非普遍的分析工具。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将原型概念作为人类思想的原始深层结构的终极标志去追究,或者将其视为进入某个文明‘思维'的钥匙,而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可识别的反复出现的元素来看待,其变化和转换可以在解释一个具有特定传统的具体作品时提供帮助;”“寓意”也非“‘《红楼梦》所寓之意',所指的又是某种特定的修辞写法,”这种特定的修辞写法给人类生活的经验流套上了一个外形,形成了一个最广义上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所辩护的“本义”,“西方文学批评中的allegory一词,在中文中简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应术语。有人译为‘寓言',有人译为‘寓意'。我个人认为,最为接近的用法,大概应该是‘本义'。”跟“本义”相对应的,就是“言外之意”,“在寓言中我们正探讨的是文本文字和它的其他含义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全视觉”明显地将“总体性”和“百科全书式”导向了空间,而非时间。因此,“全视觉”可谓关键中的关键——正是它,显现出了浦安迪对有机统一体的亚里士多德范式的逃离与路径。在以终结为导向,以合乎逻辑为发展推动力,有着明确运动方向的模仿性叙事之中,作为内核的时间性使得统一是经过辩证之后的二元对立统一的有机整体,这样的宇宙观实际上是本体论的二元论,其中有等级的差异,比如自然总是要低于真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原型”之可视化外形的“互补二元性”和“多项周旋性”,这两个结构所呈现出的空间分布特点,如两极性分布、对偶化分布,明显地是在针对时间性的辩证二元统一体:将终有一结束改为无所谓终结,即无限;将有明确方向性的运动改为循环;将辩证法改为包容性的动态互补平衡。正是在此意义上,浦安迪十分反对使用“对称”一词,“两极性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这就是对称的典范。虽然我们可以假设一切可能的互补的对立面与总的存在相平衡,但在小于整体的封闭空间内,它们必然还是不均匀的。”而对称这种“错觉”,正是直接面对第三章所谈“阴阳互补”和“五行体系框架”时容易产生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后者还配了一个静态的、对称的图示。
浦安迪的“全视觉”是本体论的一元论。但“全视觉”本身还有一个理解上的困难,或者说误区,即“全视觉”到底等不等于360度立体全景?答案是否定,不仅因为该全景中存在某种对称,还因为这里的“全视觉”侧重的是一种生成(becoming),而非存在(being)。“全视觉”是一种纯粹的水平广延,纯粹到这种水平可能根本没有线或者面所勾勒出来的明确两个差异性区分,因为一旦有了便会陷入对称的泥潭。对此,浦安迪讲道,“在中国人眼中,因为所有的现实存在于一个水平面上(在西方思想中,“水平面”至少是由二维组成的),人们并不根据存在的两个分类之间的一致性垂直地去探寻寓言所指出的另一个意思,相反地,而是通过增加视野宽度来达到目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便是以“阴阳互补”为标志的原型,浦安迪也特别强调难以区分明确状态的“门槛”之地(不过,他自己更倾向于使用“交叠”(overlapping)或“缝隙”(the interstitial space)的说法),如“动中静”“悲中欢”“无事中的有事”等,表面看似辩证,而实际上是一种含混。浦安迪用它们来证明,互补的交替是永恒的,而所谓的平衡不过是暂时性的,即“全视觉”的基本逻辑——“永无止境的暂时性变化。”
有意思的是这个“门槛”。这不仅对应着《红楼梦》里的“槛内人”“槛外人”之分——这种内外之别始终是原型和寓意的着眼点,而且和阿甘本在《神圣人》(Homo Sacer)中关于“赤裸生命”(bare life)——可以被任意杀死却不能被献祭之人,以及“例外状态”,又仿佛可以构成紧密而富有生产性的对话。居住在大观园中的少男少女,某种意义上都是被放逐在了封建的宗法礼仪制度之外。正因为如此,宝玉才得了“于国于家无望”的“混世魔王”称号,也才能诉求男女、主奴之间的平等关系,并追求自由的爱情。但恰恰是大观园这个“例外状态”,维持,甚至巩固了宗法礼仪。在这个意义上最有讽刺性的是,大观园本是用于元妃省亲的政治性空间,而绝非闺帏的日常生活空间。正如浦安迪本人也提醒我们注意,大观园的“翻建性”“临时性”和“交叠性”,也是他提醒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宝玉最终的出家,即“宝玉最后的行为可以解释为用自我撤回的方式,从虚幻的红尘中的虚幻中退出,”是“一个拉回,”即“入”。当然他把这些也都很迅速地归入了“互补二元性”之中。但如果沿着阿甘本的思路,则所谓大观园这座“青春王国”中人,他们的自然生命其实已被缩减到是时刻处在生死危急关头的“赤裸生命”。那十几条人命正是他们的生存处境之明证与“先行者”,也是荣宁二府持存的基石。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宝玉“混世”的“游戏性”,可以被理解为对这个神圣大观园的污名化、无效化,具有一种未来指向。这或许是有评论认为宝玉乃“新人”的原因之一。
回到浦安迪。为了给这样的“全视觉”一个具体可感的外形,浦安迪不辞笔墨地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论证中西文学世界中“庭园”的不同。正是在这部分初看起来仿佛枝蔓一样的挑战性文本细读中——是《中国叙事学》中一笔带过之处,却也因为牵涉到众多重要西方经典文本,如但丁的《玫瑰传奇》、斯宾塞的《仙后》等,从而成了阅读过程中容易跳过之处,浦安迪生动地展现了精密的比较文学功夫与视野,某种意义上,这一比较文学的视野在提喻法的意义上投影出了他的“全视觉”概念,正如他试图用“庭园”所浓缩呈现出来的一样。
西方的庭园有等级的差异,有生成的和存在的分裂,比如世俗之庭园远远位于天国伊甸园之下。广袤的自然不过是道德的戏剧舞台,上演的是但丁式的从地狱飞升天堂的上升运动,或者是弥尔顿式的堕落。天上地下的诸庭园之间的等级差异,正是通过这种飞升或堕落的方式比喻性、象征性地得以表现。“全视觉”只存在于上帝的伊甸园里。至于中国的诸庭园之间,都是整体之下的诸部分的差异性关系。园中的爱情也无关乎对错、善恶的道德判断,所以宝玉可以“情不情”,“情”与“淫”之间可以二元互补、交替转换。所谓大观之园,也只是作为提喻“全视觉”之整体而存在,它本身并非真正“大观”——墙或槛仍然存在。
大观园中的人也并不拥有“全视觉”。他们拥有的是“全视觉”的幻象或者说错觉。因此,浦安迪认为大观园中之人最终必然要走出园子,大观园也必然会衰败。但这衰败,一方面无关乎园中人对园子的不道德使用,衰败,一如兴盛,本是园子的互补两极;另一方面,衰败、崩溃也并非终局,“被安排了一个无尽总和的‘目标',而不是一个末世论的结局。”因此,命运与无常构成了二元互补,一如“全视觉”及其整体性和它的提喻性“大观园”中大量存在的不完整性,一如连续性和不连续性,一如真实与虚幻,等等,都在一个空间中分布,构成某种秩序的总和。浦安迪最终将这种“全视觉”性的总和收束在了“梦”上——“梦是对人类经验中这种现象的最好模拟。”
与其说浦安迪《原型与寓意》一书有着明显的神话-原型批评色彩,不如说他一直在尝试宽泛意义上的结构主义式的外形塑造。尽管他在塑形的过程中展现出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深入理解与把握,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误读和创造,比如将“五行框架”绘成了一幅圆上四点与圆心的对称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某种自我解构性的因素在滋生。这种自我解构性或许在对于对称性,即“门槛”的极力抵制之上显现得尤为明显。结构性的塑形工作,既显得有效,又似乎显得效率太高,是否存在忽略了文本的褶皱与粗粝处的危险?此是其一。其二,《原型与寓意》虽然题名缀有“《红楼梦》的”限定,但其所诉求的更多是一种与西方以时间性为核心的叙事的“中国的”叙事,这也是《中国叙事学》可以自然征引、增加《原型与寓意》内容的原因,但就阅读期待与经验来看,“《红楼梦》的”所做限定的特殊性,似乎没有得到充分满足,尽管并不会因此而否认浦安迪对于《红楼梦》“百科全书式”的阅读经验。但是,经过理论和文本细读的整个循环之后,读者能够重新回到的起点,仿佛与出发之点存在某种偏差。这种偏差性的东西,或许是作为一本新译旧书的读法之眼光瞄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