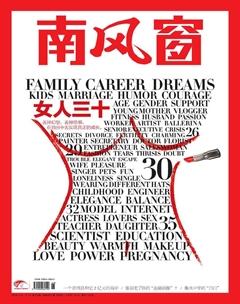后褚时健时代的褚橙
黄靖芳

人们已经很难单独地去看褚橙这个标签。
从它本身的水果属性而言,它不过是哀牢山上青葱果树上的果实,那里的日照毫无遮挡。
果子的各种指标犹如公式般得到计算:甜度、酸度、渣率等,每一项数据都被嵌入到橙子的生长过程中。
这片果园的主人住在195公里外的玉溪“云南第一村”大营街,客厅里挂着褚时健和夫人马静芬的合影。灰黑底的照片上,他们笑得很精神。
“当时折腾了好久,摄影师还会教我们摆什么动作,怎么笑。”87岁的马静芬回忆说。
大风大浪的日子过去了,关于橙子的故事也成为了传奇。只有话题旋涡中的人知道,当初种橙子,不过是为了低调地谋生。“早中晚饭然后睡觉,这样的日子过着没什么意思。为什么去做农业?那时候也不可能去做其他的。”
原本只有2000亩的一片荒山,如今成为了过万亩的果园,每天有车蜿蜒向上。
人们总是喜欢问,褚橙是因为橙子本身还是因为褚时健而声名远扬?不知道。褚时健离世的时候91岁,而他的橙子才17岁。
“褚橙家族”
10月21日,马静芬管理的果园一带纷纷传出禁止再养殖生猪的消息,有农户养的4只生猪都要宰杀,但他们对宰杀的操作毫无概念。
马静芬带上家里的工人一起过去帮忙,然后还包包子,做面食,“大家都吃得很高兴”。
马静芬现在把精力都专注于褚柑的种植上,这是一种在广西更普遍的柑橘品种,就是大家所称的沃柑。因为它水分充足,糖度高,2014年的时候,夫妇俩在云南磨皮村另外找到了新的基地,开辟了新的“战场”。“褚氏”家族的品牌扩大了。五年下来,褚柑固定在3月份上市。
但是,老太太还不满足,她希望能培养出一年多熟一季的褚柑。
她指了指桌面上的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个“试验”中的褚柑,数量很少,即使是来了客人,也只能悭吝地一人分上半个、一个。那是去年晚花结的果子,她让果园里的6个客人尝了尝,并且比划、计算着其中的反馈。“有四个说是甜的,还有两个说是酸的”,结果并不满意。“是时间不对,还是气候原因,还没有搞清楚。”
眼前的老人已届高龄,身形瘦小,却总是想着怎样解决问题,并且保持着一种让年轻人都会惭愧的工作强度:研究如何改良褚柑的生长周期,和团队开会,每周到基地一到两次,有游学团来到庄园,也尽量接待。
她的头发留成了一条长长、细软的辫子。“去理发店麻烦,洗不干净,就让它随便长。”
现在,家族里的每位成员基本都有各自的产业。这样的经营局面,是在2018年前后逐渐形成的。2012年后褚橙的巨大成功,逐渐演化成一个家族产业传承和财富分配问题。在确定接班人的问题上,褚时健的纠结尽人皆知。
较早回来帮忙的是他们的外孙女任书逸和外孙女婿李亚鑫,当时两人刚在加拿大留学毕业。2008年他们回到玉溪,一手建立起了褚橙的营销体系。
儿子褚一斌则晚得多,他常年在国外生活,与股票投资相伴,和父亲的关系从“拧巴”渐趋和解。2013年,父亲一句“我年纪大了,也跑不动了,你看怎么办”的召唤,让他彻底放下国外的事业,归来种橙。
大风大浪的日子过去了,关于橙子的故事也成为了传奇。只有话题旋涡中的人知道,当初种橙子,不过是为了低调地谋生。
两方的抉择曾经让他有过长时间的挣扎,最后,担子在2017年年中卸下了,6月,褚时健决定将褚氏的母公司新平金泰果品公司交给儿子褚一斌。也就是说,褚一斌成了接班人。
在那之后不久,外孙女夫妇所负责的“实建褚橙”开始上市销售。
褚橙和实建褚橙,共享同一个褚橙商标,但后者上市时间更早,因为是更年轻的果树,口味也自然与老树相差不少。
褚橙起步之初,谁也没想到能做到这么大。褚一斌当初还以为父亲只是想种个几十亩的果田,自娱自乐。走到考虑接班人这一步时,家大业大了,马静芬说:“要统一给谁来管,这个事情很难。”
解决办法就是,马静芬、褚一斌和他的女儿褚楚、外孙女夫妇各自拥有公司和基地,独立核算,外界有人评论,变成了“三分”的褚橙。面对好奇、质疑,马静芬在不同场合都表达过态度,這次,她依然硬朗:“反正在我们家没本事的人,还没发现。”
公众对于褚橙的好奇,包含着对褚时健这个传奇人物的刨根问底,以及窥视一个品牌在创始人离开后有可能面临的困顿和踌躇。这些问题,逃无可逃,避无可避,这是早有预料的,在踏上哀牢山之初,褚时健就是看中农业的低调特性,把身心埋在土里,就能免却多数杂音。
连褚一斌也说,近来接受采访少了很多,因为不管怎样说还是害怕被认为是“炒作”。
但毫无疑问,如今所有话题的终点,都落在了他的身上。
哀牢山的哲学
时间一来到10月,山上的话题都围绕在一年一度的摘果。
果园里的橙子就熟在这一季,浇灌这片土地的人赋予了它众多的测量维度,每天都是紧锣密鼓的。
“每天都在检测糖度、外观,(如果达标了)搞技术的人就会跟管事的人说,是不是可以摘了,再开会讨论。”今年的褚橙,在果子第一轮的生长期碰到了春夏间的高温和干旱,“有好也有不好”,最后的果实口径会小一点,褚一斌说,不过口感会更好。
10月底,北京大学的陈春花教授来访,席间他摘下了一点果子给客人尝,他数过,对方吃了接近20个,他据此判断今年“那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那么,接手以来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呢?褚一斌的答案是,没有最大的问题。
“一年有一百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很重要,任何一个都影响到最后的结果。”
褚一斌提到,尽管一家人出身在农村,但也许没人想到以后会以土地为生。他在少年时代已经出国,在不同国家间摸爬滚打,此后他更熟悉的是资本市场,是金融业。在深圳做生意的时候,他为了不被人认出,还用过化名。青年时期的褚一斌是想逃离,他觉得个性严厉、控制欲强的父亲的爱“最无聊,也最伤害人”,因此在国外度过了几十年“自由”的时光。
褚一斌从小就感受到了来自父亲的压力,他小时候患关节炎,缺钙,小学的时候,一天走路下来可能会不小心摔倒两三次。他和褚时健走路,往往是走在前面,跌倒时褚时健永远说:“那么大的人,走路都不会走,起来。”几十年过去了,褚一斌一直到50岁时,都感觉背后有一双很严厉的眼睛在盯着。
但是现在,原先的压力转化成为了另一种陪伴。面对土地,他可以悠然地说,植物是很简单的,你在每一个季节给它需要的营养,它就会对你笑。
变化之间,是两代人命运的流转。刚回国的时候,作为儿子的褚一斌“心理负担很重”。在经营企业如此成功的父辈的盛名之下,“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前辈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怕自己失败了以后给他抹黑,人最可悲的是觉得这明明不是自己做事的方式,但还是要勉强去做”。
褚时健有着个性鲜明的做事方式,熟悉他的人都会提到这样的故事,那就是他能够蹲在一棵树旁边看很长的时间,喃喃自语“这里淋一点”“这个地方要处理一下”—他在对着果树琢磨事情的时候,就像在和另一个人对话。
褚一斌也用了两年的时间去这样琢磨,去耕地,跟农民打交道,跟他们当“不能只是嘴上叫的”兄弟,花了这些时间下来,他感到淡定一些了,不再两眼一抹黑。
马静芬也说,和农户沟通、打交道不是一件小事。十几年前哀牢山还是零散分布着甘蔗种植户的荒山,那时候农户把收获的甘蔗拿去糖厂榨糖,换取一点微薄的收入。改种橙子后,他们也保持小农习惯,最初,市场上价格好,他们就可能自己抢先卖掉。所以现在果园和农户实行类似承包的机制,果园里每户农户每月有固定收入,每年根据橙子的品质和数量,还会有一个激励机制。
褚一斌现在面对土地,可以悠然地说,植物是很简单的,你在每一个季节给它需要的营养,它就会对你笑。
也是在了解这些后,褚一斌清楚地感知到,2015年后“基本上心里有点底了,能看懂父亲的决策,然后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一件事”。“那时候就轻松多了。”
曾经在西南地区担任褚橙经销商的张小军记得这样一个细节:他们在一起做新土地平整,当时的地面刚刚修复完,如果穿鞋的话可能人一下就陷下去;褚一斌毫不犹豫地把鞋子脱掉,直直地走过去。“和土地关系生硬的人,做不来这样的举动。”
10月30日,摘果时间将至,褚一斌在果园里用3个小时把摘果流程都走了一遍,设想生产线、管理环节上有可能遇到的情况,然后在晚上6点半快速地结束一顿晚餐。
马静芬会念起儿子的辛苦。现在大宅子里只有她一个人住,有很长一段时间,褚一斌为了陪她,每天来往于玉溪的家和昆明的公司,每天早上6点起床,晚上7点准时回到家吃晚饭。闲暇时间多的话,他们还会在晚上打上几圈麻将。
未来的路
10月23日,《南风窗》记者来到玉溪桂山路的一个褚橙直销点。摊上在售卖的是实建褚橙,这个品牌太新,一位经过的顾客忍不住问道:“褚橙就是褚橙,怎么还会有其他名字呢?不会是山寨的吧?”
这个疑问,暴露出内部分立之后品牌统一性面临的考验。褚一斌承认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他给出的解释是:“我们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只知道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未来我要去哪里。”
事实上,褚橙在人们心里的形象仍然很难和褚时健分开。自从褚橙的名气打开后,哀牢山不经意地成为了许多不知所措的年轻人“朝圣”的地方。有人不远千里,就是为了看到褚时健,为自己“打打气,找找力量”,也有人看到他如此高龄还在拼搏,认识到“自己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自杀”。
马静芬记得,甚至有陌生人会来到家门口,站上一天,或者干脆跪在地上,求褚时健教会他们怎么赚钱。有时候她会接待这样的客人,但她只给来者说一些最朴素的道理。“目标选准了,坚持下去,就会是幸福的,就会有光明了。”
迷茫的人也许不是为了找到答案而来,只想听到一句布道般的话语。马静芬说,一般别人听完这些话,也都会离开。
褚时健就像一尊神,所以人们难免会想,他不在了,褚橙会怎样?
目前的焦点是上市。在2019年的褚橙产品说明会上,褚一斌宣称计划在6年内上市,有媒体留意到,褚时健在生前曾提到反对资本的干预。两个场面的反差呈现出戏剧性的张力。
褚一斌是主动对《南风窗》记者提到此事的,他解释为“人在不同年龄对于同一件事情的选择不同”。“为什么父亲到了八十几岁不愿意面对资本?他讲得很清楚,在这个年龄段没办法负担股民和社会对我们长期的要求,所以他选择了不去面对这个问题。(但)当时你回头看一下,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的阶段对待资本,是能做到主动出击的。”

销售渠道的多元和规模的扩大,势成必然。现在后继者能给市场的反馈是,他们能否在往后的日子里,继续保持着原有的口碑和质量,而盛名之下,公众的关注可想而知不会减少。
肉眼可见的是,褚橙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不断自我改变,褚一斌如此,马静芬也如此。
87岁的马静芬尽管仍然勤勉工作,但她说是在踏入高龄后才找到了自己。以前她认为自己不过是跟随着丈夫的“褚马氏”,颇有嫁谁随谁的传统宿命感,不过近些年,她说终于有底气地叫自己“马静芬”了。
以前她认为自己不过是跟随着丈夫的“褚马氏”,颇有嫁谁随谁的传统宿命感,不过近些年,她说终于有底气地叫自己“马静芬”了。
2013年,当地政府希望能在褚橙果园基地修建一个庄园,但因为担心游客的增多破坏种植环境,最初褚时健夫妇并不情愿,后来这项工作被马静芬接了过去,她从头学起,负责了庄园的装修、设计和建设,2年后庄园落成。
2007年,她被查出患有晚期癌症,身体的崩坏其实早已有预兆,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老太太的状态却变得更好了。
“找到了平衡。”其实,马静芬除了是褚时健的伴侣,更像是坚定的战友。“我的使命就是传承一个品牌、一种精神,也不单是褚时健的。只要有好的我都讲。”
曾经有人在培训的时候给过她一个演讲的主题:褚橙的哲学。只有小学学历的她连忙摆手:我可不懂什么是哲学。“不可能,我不会讲这个。”
17年種橙子的时光只是光阴的一个片段,人生如浮萍,马静芬直言:“兴趣不兴趣的,都不能这么说。(毕竟)不习惯能怎么办呢?我们一辈子都是在适应环境,不是让环境来适应自己,我们真的是上无一片瓦、下无一寸地的那种人了,背包背到哪里,哪里就是家了。”
她最近的愿望,是在褚橙的预售会上说的:“健康平安吉祥地活到一百岁,不封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