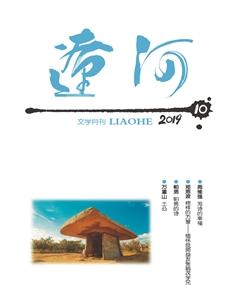米米的春天
沈琪彪
只要没客人了,米米就靠在椅子上嗑瓜子,听师傅师姐她们聊些有趣的人物。她时不时会瞄一眼马路上行走的人。有时是故意的,有时是无意识的,怕把路过的阿名漏过。对着马路的四方玻璃窗很大,占那片木墙三分之二还多。玻璃每天都有人擦,很干净,要不是玻璃上帖着几个红色镂空方块字,还以为是空的。米米洗玻璃很勤。和师姐师傅她们比,米米住得最远。米米她们村到这里,还要过两个小村子。不快不慢,得走四十几分钟。所以每天到店里,米米是最迟的。地师姐肯定扫过了,热水也烧好了,就玻璃没擦。擦玻璃和其他事情相比,不那么重要,可以几天擦一次。米米必须要表现表现,不能让师傅师姐说懒。一个女孩子家家被人说懒,那是很倒霉的,所以米米就擦玻璃。米米把水喷到玻璃上,然后用干净的毛巾擦。从左擦到右,从上擦到下,有斑点的地儿,嘴对着,哈一口气,然后手指顶着毛巾一角,对着哈成雾的那团搓。第二遍又换一块新的干毛巾擦,也是从左擦到右,从上擦到下。这还没完,这才是屋里边这一面玻璃,还有屋外那一面玻璃呢,也像屋内这一面玻璃这么擦。
阿名是今年进的厂子,新工人,是过了元宵节以后进来的。
阿名毕业了,十八岁了,阿爸说,想不想复习一年考大学?阿名读书成绩在班里,不显山露水,毕业不成问题,但要想考中专大学,只有梦里去完成。年年高考,每个班升学率都是个位数,阿名掂量过自己,就是复习成老童生,也枉然。他就说,算了不复习了,太难考,还不如早点工作实在,拿到工资还好补贴家里用。阿爸体谅人。其实家里经济拮据,能多份收入就如久旱逢甘露,很实际的情况,但他不想拂孩子的希望,除非小孩自己放弃了。阿名这样说,他有些感激,蛮懂事的孩子啊!
找这个工作,阿爸挖空心思,费了很大力气,总算把阿名弄进去了。
厂子这块地儿,现在是城郊,过去却是城中心。成也城市败也城市。新城出现以前,这里热闹繁华。新城出现后,大量人口迁移,这里逐渐衰落,连条像样的街道也没了。现在大型国企落户,人口又开始在这里聚集。厂子大门出来五十米,就是国道。以厂门正对面为中心,沿国道两侧,不时增加临时搭的店铺。做小吃的最多,然后就有了小饭店、裁缝店、小百货、理发店,再后来还有邮政储蓄,有农行、信用社。早晨九点前这里还是菜市场,菜摊沿公路摆开,吆喝叫卖,讨价还价,一派热闹。
米米师傅的店,靠厂大门对面那一排,偏右,离中心位子约五十米,算是占了好地段。
米米是过了元宵节以后来的。
元宵节一过,米米在家里就呆不住了。
她觉得十八岁了,成年人了,就不应该在家憨吃憨喝阿爸阿妈的。村里玩得最要好的两个,越来越难得踫在一起。
一个和隔壁村种草莓的小伙好上了,天天往草莓地里跑。米米也跟她去过草莓地,进大棚摘过几次草莓吃。种草莓是个细活儿,跟服侍个婴幼儿差不多,所以那小伙一多半时间都在地头。大棚边搭着个简易棚,吃喝玩睡全搁里头,拉撒就在外头野地里。几次后米米就不去了。她觉得有她在,那一对人虽然好脸好色,有时话却只说一半,看见她,就停了。两人亲热程度,明显缩手缩脚。得,她成碍眼的了,再老去就没意思了。那小伙是个种田地的,皮肤却不见黑,脸面看去还细皮白肉的,奇了怪了,估计是种好。米米想,小姐妹肯定是看上他的相貌。今年正月里见过这个小姐妹一次,说要跟那小伙去外地种草莓,说外地草莓价格好。后来果然就没见过她了。
还有个好姐妹,和村里开货车的小伙好上了。经常和那小伙出车跑长途,一两个月也见不着一次。米米没伴,无聊极了。
无聊了,她就去江边。屋后过几块菜地,就是江堤。下江堤有石块搭的台阶,十几级,到水边,那里搭着几块青石板。附近的几户人家就在这里取水、洗衣洗菜。经过一冬的冷,缩手缩脚的江水,被春风那么一吹,来精神了,水流急了许多,还清爽,颜色淡绿绿的,透透的,能看清水底游动的小鱼。小鱼儿喜吹扎堆,一团团,忽儿东忽兒西,整体游动,方向分毫不差,没有掉队的。丟一粒小石子儿下去,扑通一声,鱼团忽然散开了,过不了两分钟,又聚成一团,再丟,再散,再聚……小鱼儿和米米玩这样的游戏,乐此不疲。堤坡上那些衰败的野草,黄澄澄的,成片,像是给土坡披了一件黄色绒毡,细看,有些绿已急不可耐地钻出来,在黄中刺出尖尖的头来。
天时不时飘来细雨,看不见远方,濛濛的,如雾。没几天再看那江堤,绿汪汪,耀眼。有几只狗也来了精神,去江坡上打几个滚,鼻孔里发些哼哼叽叽的声音,东嗅嗅西嗅嗅。
她独个儿闲逛,一天天离家远去,那天,走着走着,就到了厂门口。
下班铃声一响,大门敞开,涌出成群的工人,红红绿绿的。男的穿红色工作服,女的穿绿色工作服。红多绿少。就有红嘹起嗓子:嗨嗨,美女,是来等我吗!
她知道那是冲着她喊的,她不恼,知道那是闹着玩呢,眼睛灯笼似的在人堆里找那喊话的,咋一看,模样都差不离呢,又不能盯着人一个一个辨,就闪着眼望别去处,脚步碎乱,慌张地走,撇下身后嘻嘻哈哈的哄闹声。
一抬头就看见一块匾牌,上书“彩云理发”,大玻璃窗上白纸黑字“招收学徒”,她就走了进去。
来了这里,米米晚上就不想回去了。店晚上九点关门,米米八点钟就得走。离开这一带热闹处,过一座桥,就是过杨梅弯,这弯拐得大,绕半圈就得十几分钟,路两边没有人家,是茶山,茶山后面是杨梅林。进杨梅弯十几步,右侧又有一条路,路头往山里一拐就不见了,两旁坡陡,杂树丛生,荒凉着呢。不知啥时这右边弯里就成了枪毙死刑犯的地方。隔三岔五就在这里毙人。每回晚上走到这里,米米克制不住就心慌,心跳就会加快,嘣嘣嘣,像敲一扇木门。她总觉得有谁朝她背后丟沙石,她不敢回头看呢,就跑,跑得越快,那谁也追着跑,撒到她后脑后背的沙石更多,直到拐出大弯,能看见前面大树下露出村子一家房屋一角,那谁就不追了,跟着屁股后那沙沙的响声就消失了。
每回过了桥要进杨梅弯时,她都要深吸一口气,就像准备潜泳一样。
我能搭个床睡店里么?米米实在难忍天天晚上过杨梅弯那一遭,她觉得时间久了自个儿精神要崩溃。
那不成。师傅拒绝时宽嘴巴也是咧着的,带着笑意,让人感受不出拒绝的绝情。要能搭床你那俩师姐早就搭了,还轮得着你?俩师姐都是寄住在亲戚家的,想独住那是当然。
哼,就你们几个住倒无所谓,没看见你俩师姐正和男人家粘粘乎乎么?能保证她们不带男人家来?那我这店里成什么了。
米米反感师傳说的,却没法反驳,做生意忌讳这个,不管成不成理,那得守。
最好的办法。师傅说,简单嘛,找个人谈恋爱,不就有人送了!
米米也这样想,内容似乎和师傅说得又不太一样。米米想交个朋友,要男的,朋友晚上送送朋友,那不就很正常了么!
师傅听了,嘎嘎大笑。
店里没客人的时候,师傅就搬条凳子坐在门边,脸朝马路,见谁都要打个招呼。
嗨——xxx,到哪里去哇?
嗨——xx诶,走得嘎慌干嘛去哇?急着去相亲哇!
嗨xx,长久没有看见你了,都忙些啥去了啊?
那被招呼的人,多半认识她,被她那么一招呼,除非真有急事儿要赶,急匆匆搭几句就走。那没急事儿的,碍着情面就会进店里坐坐,聊上几句,话题就很容易扯到来人的头发上,七扯八扯,有些人干脆就留下了。洗个头,烫个发焗个油染个发,做个面膜,生意就做成了,店里就热闹开了。
有样学样,两个师姐也有了见人就招呼的习惯了。师姐年轻,一个大米米两岁,一个大米米几个月,她们那么勤招呼,来的年轻人就多了。
阿名不是俩师姐呼进来的。俩师姐不是啥人都招呼的,看菜下筷,要年轻的要样子好的。
阿名算年轻,相貌却不出众,混进人堆里就找不着的那种类型。
阿名是师傅喊进来的。
师傅不认识阿名,但为了练米米的胆子,师傅看中了阿名。
米米来店里快两个月了,除了会擦玻璃,只会给客人洗洗头泡泡茶。师傅就说了,你俩师姐来这里一个月就上手了,你都快俩月了,啥都不会,你这样还出得了师的呀。
米米也想早点上手,但不敢。来的人大部分都是回头客,店里情况清楚着呐。女人只认师傅,师傅再忙,情愿挨时间等着师傅来料理。男人就随便些了。老男人乐意让俩师姐在头上巅,小男人嘛本来就是冲着师姐来的。不管是老男人还是小男人,再不讲究,也不愿给米米上手做试验,晓得米米是新手。
米米说,没人肯让我试呀!
这是实话,师傅当然晓得,两个大徒弟之所以上手快,是因为她们有试验田——男朋友。
这大廠,外面人叫和尚庙,几千人的厂,未婚女人扳着手指都能数得出来,其余统统是男人,没结婚的居多。这些正当年轻的工人,那精力充沛着呢,就上班那点活,仅仅耗去他们所有精力的一点皮毛,余下的精力呢,只有下了班到处寻事消耗。这理发店就是他们喜欢来的地方,洗个头就能和姑娘逗逗乐,何乐而不为。
俩徒弟就乐在其中,绿叶间的鲜花,格外耀眼。
这干柴烈火的,互相逗遛几个回合,就对上了。惹得师傅也眼热,巴不得能塞回去让阿妈重新生一次,好让自个儿再年轻一次,再热火朝天对象一次。诶,时光又不能倒流,臆想罢了,现实摆在这里,要替这个三徒弟上手一次才是最现实的。想这些的时候她朝路上望,正好看见阿名从厂门口那边方向过来。阿名低着头走路,头发像刺猬,竖着,却又不太坚挺,水草似的随水波一浪一浪。脚步有些迟缓,上班累的。
师傅站在门上喊:嗨,嗨。
阿名还是低着头往前走。他是听见有喊声,像阵风从耳朵边过。他没在意。
嗨嗨,小鬼,喊你呐!师傅不知道他名字,只要比自己小的年轻男子,她统称小鬼。
嗨嗨,小鬼!几次那么喊,阿名注意到了,就停下来寻喊声的来源。正好有辆货车经过,轰轰的声音将喊声稀释成似有似无的驼铃。货车过了,眼前豁然开朗,就见对面木屋门上,站着个中年女人,正对着自己,右手伸展,手掌向上,五指往回勾,耙状。喊的话也听清了,他就回头看了看背后,确定没其他人,才揣着满腹糊涂穿马路,走向门框内的女人。
进了店就有人让座。店里四个女的,他可不敢正眼瞧。就那么块小地儿,眼光扫哪儿都是花花绿绿的衣裳。他抬头看天花板,天花板中央就挂着个电扇。低头,眼前就是地,水泥的,稀稀拉拉伏着一些碎发。他就装着看自己的黄色牛皮鞋,鞋尘粘了油污,乌黑又发亮。他听见满屋子嘻嘻咯咯的笑声,那笑声像是刮着他的脸,一遍又一遍,脸便被刮出道道红。
嗨,小鬼,以前怎么没见过你,你是新来的工人哇!老板娘问他。他终于松了口气,抬头看着老板娘。老板娘长得肥沃,那脸像是吸足了水的肥土。
嗯,过年后进的厂。说完他又低下头看自己的脚,那鞋都被他盯尴尬了,扭来扭去不自在。
难怪了,我猜就是。
米米,给人家后生家泡茶呀。绿衣应一声转身泡上茶,双手端给他。
看你。老板娘根据这后生的黑皮肤,还有傻巴巴的模样作了判断,你是征用土地进来的吧!
啊!这话刺激到阿名了,茶水差点泼了出来。的确厂里有不少征用土地工,他见过,都是上了岁数的。
那你觉得我多大了?
不超过三十。老板娘的话像扯着他的心。
师傅诶,人家还是学校里出来的哎,看他戴眼镜的,看他那手,又细又长,哪像是种田的呀。这是绿衣裳说的。
他感激地看着她,嗯嗯嗯点头。
老板娘连忙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自嘲说自个白活了三十多年,眼珠怎么就生裤裆里去了。这话把阿名都逗笑了。几个徒弟更是嘻嘻嘻笑个不停,装着互相看对方的裤裆,大喊:嘿嘿嘿,我真在你那里看到眼珠了。就都大笑。
米米觉得师傅的眼睛毒,路上走着的阿名,她咋就能看出是个忠厚人呢。也不对,眼毒怎么会把阿名看成三十多岁的土地征用工呢。估计师傅是蒙的,被她蒙对了而已。
师傅说话的嗓音很好听,宽宽厚厚的,语速缓慢,节奏像清宫里的格格走路。男人听了会着迷。
师傅说,啊呀,你头发咋这样乱呢,也太长了哇,太破坏帅哥形象了,修一修,咋样?
阿名从来没想过头发和形象的关系问题,思维还套在这个问题里转不出来,就听见老板娘又说,帅哥的头应该让靓妹来摸才对,米米,你来。
阿名坐着,不敢动了,身体绷得紧紧的,不多会儿他就觉着腰酸脖子硬腿紧,比上班干活还累。米米的身体时不时会踫着阿名,软和,触踫点像是触到电源开关,舒泰,水波荡漾似的扩散。他心里痒痒的,总想把肢体靠过去,靠过去。
理发的过程漫长,米米料理他前脑发际时,那脸几乎贴上阿名的脸。阿名的眼光无处躲闪,风光尽收眼底。米米的鼻尖,密布小汗珠,眼睛,噢,单眼皮,胀鼓鼓的,将眼睛挤成一道缝,额前有细细的发丝,粘着,有几根红杏出墙,伸到她嘴角。许是有些痒痒,她不时吹口气,将讨厌的细发吹开,就露出正中三颗白白的牙齿。她的嘴永远合不严密,中间总会露出一小孔,那正中一颗白牙就永远显摆着,于是,那上唇中央,微微上翘,像婴儿正嚼奶的嘴。
你不像这个家里人。米米听阿名说这句话,已经不止一次了。
阿名送米米回家,他觉得理所当然。
起先阿名送米米,都是到村口就止步了,米米也没有邀请他进村子的意思。天气越来越暖和,夜短了,村里人睡觉就迟了,让村里人看见,少不了多嘴,问起来不好解释,阿名也总是有意无意躲着人。
后来,过了杨梅弯,有个小村子,村头有几颗大樟树,树底下有条小路直通江边。
米米不喜欢回家,多大的人了,还跟弟弟睡一张床。房间是大通间,姐弟的房和阿爸阿妈的房之间,一个衣柜隔着。两头有点动静,谁都能听得清清楚楚。阿爸起夜勤,尿撒进肥桶,嗵嗵嗵响,把隔天的尿水搅起,那尿骚味,阵阵袭来,钻进鼻孔,折腾五脏六腑,憋气塞被角也挡不住那气息。除非倒下就能睡着。
后来,米米说,去江边,不想太早回家。正合阿名意,他也不想早睡。
两人就顺着樟树底下那小路到江边。
江边杂草丛生,月亮底下,一斑一斑阴影,阴影里野虫叫,啥奇怪的声音都有。有一块四方在月亮下,白白的,走过去,才发现是水泵房的房顶,房子很矮,跨大步就上到平顶。俩人并排躺着,满天星,无边无际。月亮圆圆的,像在天空游,云如水,缓缓流淌。米米突然说,前几天我去瞎子那算了命。
哦,怎么说?
说我以后是吃教书饭的。
你吃教书饭?
对呀,我越想越有这个可能,说得还真准。
阿名想,我阿爸阿妈是老师不错,可我都没当上老师,你怎么有可能,还这么笃定。
嗯,是有可能。他说,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米米把身体移动,贴着阿名一侧。应该算是在谈恋爱吧。
阿名也不知道恋爱关系是以什么作为标准的,觉得不应该就是单独在一起聊聊天,牵牵手,送来送去这样。他就伸出一只手,想表示一下,却不知道该把手落在啥地方。米米就拿着他的手臂,垫在她的头下,当枕头了。手臂感觉到微小的份量,有股豪气在胸腔汹涌,他挺了挺胸。微风拂来,夹着青草的气味,夹着芳香。
米米说,半夜有点凉。
那咋办?阿名说。
这样。米米用了把劲,阿名顺从着她的力,翻身,抱紧了。
你真不像这家人。第二天送米米,就到了她家。未进门就听见噼噼啪啪搓麻将的声音。麻将桌就摆在客厅正中央。
见米米阿名进屋,有人就说,啥事这么忙回家越来越迟,变死吧你。
米米不答,拉着阿名进房。阿名问米米你阿爸阿妈呢?答:都在麻将桌上。
没有板凳,两人坐在床沿,默默。进了家,就感觉到米米那股四溢的朝气,泄了,像漏了气的球。花开似的脸,谢了,透出颓废。
厅堂的麻将声,从板墙豁口砸过来。阿名浑身不自在,说,我受不了这个。就走了。
周六,平常闹哄哄的学校终于安静了。吃过午饭,阿爸阿妈有事一起出去了。阿名伸头出窗户,看下面操场里边尽头,无人。那里有一排水龙头。他就捡了一盆自己的脏衣服裤子,下楼去水池上洗。正忙乎呢,见有一男人往他这个方向过来,走走停停,四处张望。
不是学校里的人,他想。继续洗衣服,眼睛一心二用,等那人走近了,发现是米米她阿爸。对方也认出他来了,喊了声阿名,說还自己洗衣服呐,你妈不帮你洗啊!
我妈忙呢!
哦哦哦!他拿眼四处瞄,学校怎么没人呐?
今天周末,都回家了。
哦哦哦!
这人年轻时样子一定不错的,阿名想。寸头,个子蛮高,穿中山装,皮鞋擦得很亮,衣裳扣子扣到顶,像衣领夹住脖子。
好些日子过去了,对于这天下午米米她爸的突然出现,阿名总觉得莫名其妙。他说是路过学校门口,顺便进来瞧瞧。
阿名怎么就觉得那么不可信呢。
问话还多。你爸你妈都是老师?你爸妈呢?没邀他他主动提出来家坐坐。坐下没两分钟,就站起来进了两个房间转了转。直进退出,房间小,转不起圈来。
你爸妈也都住在这?
是啊。
那不太挤了嘛?
废话,还有房子谁愿意全凑这里住。阿名想。
这样怎么行,再买一套哇。
又是废话,买,要钱的嘞,有钱谁不晓得买。阿名想。
他离开后,阿名发现泡上的茶他都没喝一口。
他走后约莫过了个把小时,米米来了。米米是第一次来学校。见了面就说我爸来过了。
前面他还来过我家呢。
啊!他啥意思?
我也不知道啊。
他说了什么没有?
没有说什么啊!
米米发了会呆,眼珠死死的不转动。好一会儿才说,陪我回家。
现在?阿名不明白。
是,现在。见阿名愣那儿,米米补了句:我怕!
阿爸突然来店里,叫米米出来下。脸色漆黑,鼓着。
师傅招呼,啊呀,米米家爸,好难得哦,坐下坐下。
阿爸看都不看她一眼,自顾自转身就走。
米米跟着出去,走出十几步,阿爸回头,说,马上收拾你的东西,回家。
太意外了。阿爸,做啥了?
做啥?別学剃头了,归家去。见米米站着没动,阿爸眼皮一剥,眼珠鼓了起来。敢不归去?我就敲断你的脚筒骨,相信不?
米米连忙回店收拾衣服。她信她阿爸的话。阿妈总是被他打成蜂叮过似的,头肿得像猪头。就因为阿妈一次又一次以为阿爸下不了手,敢跟阿爸对嘴。
米米走出店时,阿爸已经走了。她想到阿名。有阿名陪着,阿爸应该会客气点。
到村头,就见着阿妈了。老远,米米就认出村头站着的阿妈。
这时是晌午,地头干活的人还没到回家的时间,所以村头站一个人,显眼,好认。阿妈一会儿就朝西边望,脖子伸得长长的,脑袋前探,蛇头吐信似的,见来路上没人,就在原地转圈儿,转了几圈又立定,朝西边望。路两边地里,油菜花开得正盛,黄色连绵不绝,引来无数蜜蜂,嗡嗡之声不绝。油菜花的香味,随风飘曳。米米和阿名的身影在花丛中沉沉浮浮,她见着了,不待走近就喊了,快點快点。边喊边迎,看一眼阿名,没表示,随后拉着米米快步走。见离阿名远了,才说,今天回去你小心点,你阿爸今天是中了邪了,到家就骂人,还掀掉麻将桌,面皮都不要了,记牢,别跟他顶嘴。
在大门口就看见米米阿爸坐在八仙桌旁,正面对着门。
见人进来,他长长吸一口烟,那烟滋溜溜短了半截,他猛地站起,烟头一甩,转个屁股就往后院走。
阿名看那还冒烟的烟头,滤嘴扁了,湿漉漉。米米妈连忙跟去后院,稍许,喊了声:进来!阿名正要跟进,被后院出来的米米阿妈挡住了。
不多久,后院就有对吵声。忽然有急促的脚步声,急着一声短促的喊。
要死吧,这个畜生!米米妈往里沖,阿名也跟了去。就见米米抱着头蹲在墙脚,她爸拿着锅铲柄粗的棍子,一下一下往她身上砸。
你个老头子诶,你想打死你亲生囡啊。她妈上去就扯他胳膊。
他使了两趟力,被扯着,挥不出胳膊,罢了,嘴里说,不争气个东西,谈啥恋爱,啥里人不好谈要去谈个光屁股的。正要丟掉棍子,一回头看见阿名,回身就是一棍。听不听我讲的,又一棍,听不听我讲的。
老婆子又去拽他胳膊,被他一挥,人就翻了出去。
哪有这种阿爸,打自己女儿像打条狗。阿名冲上去,横在两人中间。又一棍正劈下,已收不住,挥到了阿名肩上。阿名觉得一阵风从脸面掠过,肩头一麻,耳朵轰一声,然后如蜂鸣久久不息。
走开!她爸两道眉连成一条线,中间打个结,隆起。走开!跟你没关系。
阿名胸脯挺着,针锋相对,不言不语。她爸眉结往上一挑,又举起了棍。
倒在地上的米米妈不停地大喊:打死人啦打死人啦!
闻声赶来的隔壁邻居一哄而上,夺下棍子。有人劝,有人拖。
阿名趁机拉着米米,绕过人群出门而去。
给我站住!米米爸的声音。俩人不回头,小步变大步。
俩人感觉到身后不远有人跟着,阿名的眼角余光体验到了身后的空气,忽然如乌云般压境。他就跑了起来,米米牵着他的衣角,紧跟着跑。
绕着大樟树一圈,顺着小路跑,到尽头,没路了,宽阔的江横在前头。日头不知啥时被一片黑云挡住了,天暗了起来,风趁机肆虐,把江水掀起无数个浪头。回头,远处有人影子朝着这个方向蹿来。
米米握着阿名的手心出汗了,粘乎乎的。眼前成片的水草在水浪中,摇晃着,仿佛醉了。
看,有船!米米指着右前方。果然,右边弧形突出的水岸边,闪出一条小船来,似风中飞扬着的树叶。